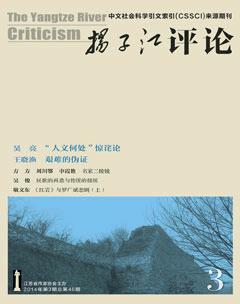“两个小人物”的信存否之辨及其意义
陈扬
“两个小人物”的信存否之辨及其意义
陈扬
2011年到2012年《中华读书报》上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波澜,这些文章是:王学典《“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①(以下简称《揭秘》)、《“拿证据来”——敬答李希凡先生》②(以下简称《拿证据来》),李希凡《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③、《李希凡再驳王学典:拿出1954年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来》④,徐庆全《两个“小人物”的信在哪里?——兼驳李希凡先生》⑤(以下简称《信在哪里?》)、《“历史细节”当然要“问”——兼再请教李希凡先生》⑥,孙伟科《“缘起”何需再“揭秘”——1954年红学运动再评述》以及《炎黄春秋》⑦上马龙闪的《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⑧等。这些往来文章主要讨论的是毛泽东写于1954年10月16日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到的一个细节——两个“小人物”曾致函《文艺报》一事——是否真的存在。笔者阅读了诸先生的文章后,感觉问题并没有说清楚,同时在目力所及范围之内又发现了一些新问题,遂将一己之见求教高明。
在无法得到核心材料(如约稿信,作协、《文艺报》有关档案)证实的情况下,任何讨论说到底都只是推测。而且,这件事情的存在与否实际上无关宏旨,并不会改变我们对于历史的大判断。但通过哪些途径重审历史,发现另外的可能,从推进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来说不无裨益。
调查结论究竟是什么?
1954年,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由于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有不同观点,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于“五四”前夕寄给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编辑部,9月1日发表。8月份前后,他们又合写了一篇批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寄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后于10月10日发表。9月,毛泽东读过二人在《文史哲》上的文章后十分欣赏,通过江青示意《人民日报》转载,被周扬等人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等理由拒绝。达成妥协后第18号《文艺报》加“编者按”转载了此文。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信,后来在发表、选入文集时一般被命名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它公布后人们才知道李、蓝文章的发表有过这样一段曲折,这封信也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起点。
在毛泽东的信中有这样一句:“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引起了王学典先生的质疑。《揭秘》提出了以下疑问:16号《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出后,在一些材料中应该有、却没有李希凡致信《文艺报》被置之不理一事的踪影。一是10月28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没有再提,假如探询信真的存在,为何不就此事“质问《文艺报》编者”呢?二是冯雪峰个人的检讨和以《文艺报》名义作出的检讨均对此事只字未提。最高领袖过问的事必会有一番调查,而冯及《文艺报》竟然没有对此事作出交待,毛也未再追究,实在奇怪。三是李、蓝当年在批《文艺报》高潮时发表的文章对如何写信给《文艺报》被置之不理、走投无路的过程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总之,直至1967年毛信公开发表之前,看不到任何李希凡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的存在痕迹。王文认为以上材料均对此事“缄默不言”的原因,应该是经过调查后,各方都认可了李、蓝并没有给《文艺报》写过被“置之不理”的信这一结论。
首先确定无疑的是,当时针对信的有无问题,肯定对《文艺报》进行过调查,这在王学典、李希凡、徐庆全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笔者需要对徐庆全文中提到的一个论据,即所谓《陆定一传》中所收的毛信的版本进行些修正,并作出这样的推测:针对李信的问题,即便有结论,也只可能是《文艺报》没有收到信,而不是李希凡没写过信。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于1954年10月16日发出后,只在有限范围内传阅。1967年《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的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部分引用了毛信,《人民日报》1月3日转载姚文。《红旗》3月30日第5期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中引用了毛信的大部分内容,《人民日报》4月1日转载戚文。⑨5月2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了毛信全文。1977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信的手迹。手迹上有明显的增删痕迹,前述所有版本以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版本,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等收录的,皆和原信修改后内容一致。⑩所以,若说到版本,此信只有手迹本和根据手迹的改动发表的定本。徐庆全《信在哪里?》提到一个《陆定一传》所收的“很有价值”的版本,该书作者称是在中央档案馆看到了原件,笔者无缘得见原件,但由于《人民日报》刊登的是手迹,可以认为这就是原件的影像。手迹中有一句“然后投《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发表”被圈出,正式发表时作删除处理。唯《陆定一传》的引用保留了这句话,而其他部分用的却是改动后的内容,还有两处明显的文字错误,因此这只能算一个不甚准确的转抄本。⑪
手迹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研究其修改、增删、流传往往能读到比后来公开出版物更为丰富的内容。毛泽东手迹不同于其他,原件上几无被他人篡改的可能,只可能是本人的修改。他之所以圈掉“然后投给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发表”一句,证明确实是对信件一事做过调查,而且这个调查应该很快就进行了(根据张僖、白鸿的回忆是16号当晚)。“文学遗产”的调查比较容易,他们拿出审稿单就自证了清白。那么经过调查后,是什么原因使他保留了《文艺报》的一句没有删去呢?
对《文艺报》的调查结果可能有三种情况:1.李希凡确实没有写过信,也不是这么说的,是当时邓拓转述不清或者听者弄混了,搜查当然没有找到此信,“置之不理”的罪名不成立。2.李希凡说写过信,但搜查没有找到此信,《文艺报》有“置之不理”之嫌,却无法坐实。3.搜出了那封信,可以坐实“置之不理”的罪名。第三种情况可以排除,因为从很多情况综合来看,如当年经手调查的张僖的回忆,都可以确认在编辑部没有搜到那封信。《揭秘》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第一种情况。假设结论真是这样的,不妨按王学典先生的思路,以下的事情就很奇怪: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文艺报》方面的人都不清楚问题真正出在哪里,而从一般情理上推测是李希凡的问题,所以才会1954年11月初《文艺报》征求读者意见会上私下里追问李,1979年第四次作代会上要求他公开回应。那么,像陈企霞这种对任何委屈都反弹得很强烈的人,后来多次表示1954年对《文艺报》的处理是领导上为了推卸责任,栽赃嫁祸,对这么明显的“栽赃嫁祸”怎么在《匿名信》中只字不提?匿名信哪怕不敢直接对毛泽东的说法表示不满,也满可以质问李希凡,可是他没有(这点徐庆全的《信在哪里?》一文中提出过,他的文章虽然旨在支持王学典的观点,但所列证据最多只能支持“各方最后都认可《文艺报》确实没有收到信”这一结论)。1957年作协整风,鼓励鸣放,唐达成、唐因等《文艺报》的编辑都表示1954年的处理很不公平,要翻案,这样大好的机会,为什么不旧事重提?实际上他们当时的言论已经相当大胆,企图要对《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逐条加以批驳”,既然要对《决议》“逐条加以批驳”,何以不驳那句“《文艺报》编辑部对于白盾、李希凡、蓝翎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错误论点的文章,则拒绝刊登或不加理睬”?⑫1967年冯雪峰写《外调材料》倒是提了这件事:去《人民日报》社开会的时候,江青问他知不知道有两个青年曾写信给《文艺报》被置之不理的事,冯雪峰表示不知道,回去后就到编辑部调查一下。“我回来后,到《文艺报》编辑部去查问了一下对李、蓝来信置之不理的事情,却并未在编辑部进行检查和自我批评,这也可以说明我根本没有重视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⑬然后整份材料再未提及此事,连检查的结果都没有交待。如果按照王文的推测,各方都认可了李希凡写信一事不存在,那冯雪峰这颇为随意的一提岂不是太奇怪了么?
综上,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第二种:经过检查,并没有下一个谁是谁非的结论,李希凡说寄过,《文艺报》说没收到,这成了一件葫芦案。各方认可的是《文艺报》没收到信,这点连李希凡也认为是有可能的,毕竟从寄信到收信,这中间的偶然因素太多,任何环节都可能出差错。但谁知道《文艺报》是真没收到信还是随手甚至是故意处理了呢?这也可以算作“置之不理”,所以大体来讲毛信上的话没什么错,这就是他没有删去《文艺报》一句的原因。后来抓住了白纸黑字的“铁证”——“编者按”,未再就信一事批评《文艺报》,但《文艺报》也并不能因此就理直气壮,所以当时的情况下不便在公开场合纠缠此事,冯雪峰及《文艺报》方面的检讨都不主动提,以免自找麻烦。
批判《文艺报》是何时开始的?
回到开头《揭秘》提出的问题,既然毛信里都指出了《文艺报》“置之不理”的罪名,为什么那些材料中看不到踪迹?前文已经解释了部分原因。笔者还注意到,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调门之高,将矛头指向《文艺报》十分突然。之所以说“突然”,因为在此之前,几无《文艺报》要被卷入风暴中心的迹象。毛泽东写于10月16日的信中的确是有这么一句:“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只此一句事实的陈述,而后文严厉措辞的主要指向是以周扬、邓拓、林默涵、何其芳等为代表的“大人物”和《人民日报》,怎么样也轮不到冯雪峰和《文艺报》首当其冲,实在看不出哪里如王文所认为的毛对“置之不理”的事“看得很重”。不光笔者没看出来,当时文艺界的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
“文革”时期流传的《〈红楼梦〉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有这样的记载:
10月18日(笔者按:这里指1954年,下同。)旧作协党组开会,传达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会上,周扬对抗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说他那一伙人的问题仅仅是“忽略”“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作批判”;林默涵、冯雪峰、陈企霞都是与周扬同一腔调,何其芳同志则说:“我们也还没有成为他(指俞平伯)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周扬在会上公开叫嚣“不要因为传达主席的批示,而搞得‘左’了”,并且为俞平伯之流撑腰,说什么“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写作,鼓励辩论”。这次黑会还指定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写所谓“批判”文章,搞假批判。
10月22日旧作协党组开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反动思想的口头指示。周扬一伙顽固对抗。对毛主席严厉批判的《文艺报》编者按,林默涵竟然说成“主要是语法上的问题”。冯雪峰仍然想方设法保护俞平伯。⑭
《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10月24日发表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经过邓拓、林淡秋(二人皆是毛信的受信人)等人的审阅修改,只字未提《文艺报》。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研究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共十九人发言,也无一人提到《文艺报》的问题,不管是对“置之不理”一事还是“编者按”的问题,都没有提。⑮这说明起码在当时的文艺界,斗争重心都还在批判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上,即便是看到毛泽东的信后,也没有人意识到、或者收到过要大批《文艺报》的讯号。冯雪峰本人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文革”时期的外调材料中写道:“主席指示下达后,作协党组是很快开过一次会的(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楚),……但现在追忆起来,对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和主席对于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投降以及拦阻两个青年的战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转载等不可容许的严重事实的批判,到会的人(包括我自己)完全没有引起必须有的重视(这实际上就正是抵制),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此,在会上并没有对主席指示进行好好地学习和理解,更没有按照主席指示和批判进行认真的检查。对于我写的已经发表的《文艺报》编者按语的严重错误,在这次会上(以至《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之前),我也确实没有听到什么人提到过(我是指作协党组和周扬等),我自己更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思想观点所支配,在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之前,竟然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犯了极端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因而《质问〈文艺报〉编者》的发表,我也特别地紧张。”⑯张僖也是到10月28号《质问》发表后,“才知道《文艺报》捅了娄子。”⑰可以说在28号之前,即使毛信中已经提到了《文艺报》置之不理的事,也进行了一番调查,但实际上并没有人把这太当回事。一是搜查《文艺报》的确没发现信,二是对来信不能及时处理是全国报刊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以此来批《文艺报》没有什么说服力。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要先确定斗争大方向,也许是欲扬先抑,想看看文艺界什么反映,毛泽东虽然已经对《文艺报》“编者按”十分不满,但没有在16号的信中表现出来。⑱结果是令他失望并愤怒的,果然《武训传》的情况“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因此才有了调门突然升高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在秘密状态下写作,经毛本人的审阅、修订,28号刊出。直到此时周扬等人似乎才回过神来,知道问题已经不是他们所能控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的了。对《文艺报》真正的批判是从28号以后才开始的。周扬等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对“编者按”那么愤怒,中间江青应该起到了一些作用。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大家都忙着批“编者按”这样白纸黑字的“铁证”了,没有再提“置之不理”的事。《拿证据来》认为“按照李先生的说法,在当年,无论是毛泽东主席还是他本人,或者其他人,都没有把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当回事。这种说法简直令人瞠目!”笔者却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至少对“其他人”而言,之前连“编者按”的问题都没太当回事,何况是一封问询信?而了解领袖意图之后再展开的批判,是按照《质问》的精神,重点抓“编者按”以及“《不能走那一条路》事件”等,对未查到铁证的问询信一案没有再纠缠。
所谓“约稿”一事证据确凿吗?
《揭秘》一文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两个小人物曾向《文艺报》写信的事无法坐实;二、驳俞平伯的文章原来是《文史哲》的约稿。第一个结论是不够有说服力的,因为所有的证据只能表明《文艺报》没有收到信,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没有在《文艺报》查到那封信。不能由《文艺报》没收到信而推导出李希凡没有寄信,什么邓拓转述错听错都是猜测,可能性很小,江青夸大其词有可能,但不会无中生有。《揭秘》给出的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李希凡致《文史哲》编辑葛懋春的两封信件。一般来说,信件的可信度要高于出版的自传、回忆录甚至是日记,因此如果李、葛的信件中能显示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原是《文史哲》约稿的话,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既然是约稿,怎么会再向别家刊物写信询问发表事宜呢?况且4月13日的信中李希凡说还未动笔,5月4日就已经随信把文章寄给葛懋春,其中根本没有向《文艺报》写信问询而被“置之不理”的时间。所以,“在有《文史哲》约稿在先,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他们再给《文艺报》写信的事,在逻辑上可能性很小。”⑲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只有李希凡的两封信,却未见葛懋春的信,这样推测很容易犯“六经注我”的毛病。李希凡的两篇驳文不乏意气之辞,但对其1954年写给葛懋春信的解释合情合理,可以参考。笔者仅就一点讨论一下:就《文史哲》方面来说,如果真是编委会约稿,起初既不是秘密的,知道内情的人又何止一两个,为什么都保持缄默,难道都是为了配合毛泽东信的口径?到底有多少人在当时就看到过毛的信呢?虽然王学典认为信的传播范围不会太小,但就笔者所见材料,李、蓝在1967年之前未见过毛信,只是隐约听说;《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表态性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的作者钟洛(即袁鹰)也没有见过。⑳况且了解信的精神不代表就清楚信中的细节。《文史哲》在远离风暴中心的山东,能有几人知道个中细节?如若他们主动“约稿”在先,有打响头炮之功,却对此事集体噤声,岂不是太奇怪了?而且从王文中来看,连葛懋春也从未向他明确透露过“约稿”讯息。这些人和前述《文艺报》方面的立场不同,他们才是最有可能也最该提此事的,却没有一个人提,这才是真的奇怪。所以,王文立论最根本的证据还称不上“确凿”。当然要找到确凿的证据,如葛懋春的约稿信,实际上也已不大可能。
综上,笔者认为写信被置之不理的事最早肯定是李、蓝在向邓拓汇报情况时透露的,无论是邓拓还是江青,几无可能转述错误,或有胆量无中生有捏造出来,因为日后会调查。毛泽东10月16号的信发出后,作协、文联等有关方面即刻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文艺报》没有收到信,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没有在《文艺报》编辑部找到这封信。但没找到信并不代表李希凡没有写信,所以毛泽东在删去“文学遗产”一句的同时还是保留了《文艺报》那一句,但后来没有再追究此事。既然领袖都没追究,冯雪峰和《文艺报》方面也不再主动提。其他方面如作协领导,也没有穷追不舍,因为已经有了“编者按”这么明显的靶子,所以他们只是在《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中含混地提到一句。而“约稿”一事据王学典先生的推测从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却会产生一些更加无法解释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王文中的两个主要结论——李希凡没有写过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文史哲》的约稿——还不能令人信服。
余论
马龙闪先生的论断是客观的:“王学典、徐庆全先生是从学术争论、学术批判的角度来要求关键细节的真实,他们从微观上,从学术上对‘被置之不理’的信作了有价值的考证;但仍不要忘记,这场批判从‘缘起’之时,就设定是一场政治批判、政治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细节’,哪怕是十分重要的细节,也是不重要,无关大局的。”㉑细节固然不那么重要,但在现今的档案制度之下,要想看到作协、《文艺报》方面的内部档案或其他前所未见的材料都不太可能,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往往只能从细节入手。王学典立足于有限的材料,对已为人所熟知的历史细节提出异议,并引发了当事人李希凡先生的回应,以及孙伟科、徐庆全、马龙闪诸先生的争鸣。随着讨论的步步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呈现出来,这对研究者是很有启发的。笔者此文虽极力自圆其说,但由于学力所限,在写作时也常陷入到“有”、“无”的纠缠之中。总之,若能够对此问题的解决稍有推进,也算达到了目的。
【注释】
①《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
②《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8日。
③《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1日。
④《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9日。
⑤《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25日。
⑥《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10日。
⑦《中华读书报》2012年9月13日。
⑧马龙闪:《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
⑨《揭秘》中说“此信首次公开发表于1967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戚本禹的文章中”,有误。
⑩只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差别,繁简字、异体字等,如将手稿中的“付”改为“附”,再如个别标点符号的运用,基本上与内容无涉。
⑪见陈清泉、宋广渭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388页。
⑫见《检查编辑工作中的错误展开反右派的斗争》,《文艺报》1957年7月14日第15期。
⑬冯烈、方馨未整理《冯雪峰外调材料》,《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此部分“交代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中同我有关及我所知道的几件事的经过”写于1967年11月14日。
⑭见《〈红楼梦〉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红楼梦评论专辑》,红小兵报社编,1974年6月。
⑮见《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6日发表的会议综述及《光明日报》1954年11月14日发表的会议详细记录。
⑯见《冯雪峰外调材料》。
⑰见张僖《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⑱笔者一度认为毛泽东在信中未提及“编者按”是因为在写信时还没有看到,李希凡也有这样的感觉,认为毛是在写信之后才看到《文艺报》和“文学遗产”的“编者按”的。但实际上10月10日“文学遗产”的“编者按”肯定是在写信前就看过了,不然不会有开头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一语。而转载李、蓝文章的《文艺报》第18号应于9月30日出版,即使按李希凡回忆因为转载文章似乎迟至10月上旬才出版,按毛对此事的关注程度,16号还没看过的可能性很小。
⑲见《揭秘》。
⑳见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㉑马龙闪:《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批准号:11&ZD11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