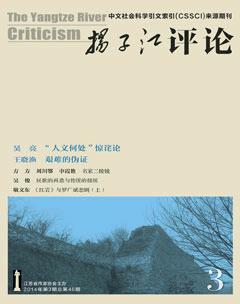超越传统的文学探险──简论黄孝阳的量子文学观及近期两部小说①
刘志权
超越传统的文学探险──简论黄孝阳的量子文学观及近期两部小说①
刘志权
在当前的“70后作家群”中,黄孝阳是一个颇为引人注意、且上升势头强劲的作家。但是,评论黄孝阳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探险。探险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他近期的小说,从《旅人书》天马行空的诗意,到《乱世》打通雅俗兼容并蓄的庞杂,本身就是探险,几乎无法纳入当代小说发展的传统之中(这是一条跃出传统水面的、“带着腥味”的“背鳍青黑的鱼”),已有经验几乎失去了用武之地。二是他的文本,是由庞杂的知识、漶漫的思想、诗性的想象、不羁的个性杂糅而成的语言之流,这对评论者的阅读能力和艺术趣味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三是当我们准备分析或批评他的文本,首先面临着理论方法和标准选择的问题。用黄孝阳的话来说,“传统虽好,已经不够”,不能说他的创作中没有传统因素,但是,如果只用传统的尺子来衡量他,就有刻舟求剑之弊,会漏掉那些特异的、也是黄孝阳引以为豪的东西。
事实上,黄孝阳作品的最大的复杂性正在这里。作为一个推崇智性写作、以思考为乐、自许甚高的作家,黄孝阳从来不只是或只满足于作为一个单纯的写作者,他更乐意做一个传统的破坏者(如同那些总带着匕首、枪或者剑,在最终完成破坏的“旅人”);但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思想体系的构建者和小说文体的探究者。这些年来,他像一只辛苦的工蚁一样,一点一滴地积累和巩固着他以“量子文学观”为支撑的理论巢穴。也正因此,要对黄孝阳作品进行评价,无法回避他的量子文学观②——在我看来,这个带着一定原创性的理论,可视为后现代文学理论之一种。后现代理论作为一种“旅行”理论,在中国向来“只开花不结果”,少见成功的当代小说文本,而黄孝阳却以其量子文学理论和小说文本的互文性的验证,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切实的样本。传统的学院式的小说批评,因此面临着尴尬,而黄孝阳对此也早有预见,如他曾经揶揄过的:“学院好一个‘史’字,遵循的是‘这本或者那本小说是否具有小说史上的意义’。……基本上落后于当代小说的实践。……更令人伤感的是,这种关注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缺乏让人激动的新思维、新方法。”因此,对黄孝阳的批评格外地有意义:“传统”怎样面对一种新质小说文本以及新质文学理论的双重挑战。我们的探险,将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进行:第一,以“传统的”文本阅读,证之以作家自身的文学观,分析作品究竟具体呈现了什么;第二,在理论与实践的参照研究中,对黄孝阳的“量子文学观”及其创作意义尝试作出评价。
一
《旅人书》是一部晦涩深奥之作,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但无论是马原的叙事圈套还是余华、格非等人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的借鉴,先锋的尝试主要是在叙事技巧的层面;而《旅人书》独特的风格,其实主要不是源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技巧,而是不羁的思想的激情。作者自言,“我把《旅人书》分成上下卷,上卷形而上。旅人在天上,是观念之物;下卷是尘世。旅人以‘你我他’之名在地上的行走,是红尘悲喜。这是我自己最初始的设计。”因此,上卷之“城”,也是“观念之城”。进入这个观念世界,首先面对的是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城名之“名”,其实只是皮囊,它其实与卷首的一首诗无关,也无需有特定意义,甚至是作家给评论家设下的陷阱,比如,我们随便另选一首“春眠不觉晓”,而拆分成“春城”“眠城”“不城”,在效果上并没有不同。如果拘泥于名实之分,正证明了我们没有逃脱“语言的囚笼”的自觉。例如,“城”可能以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在森林与沼泽的交界处;可能在海底或岩石之上;可能存在于时间、梦或者心灵处;甚至,还“可能是一条鳗鱼”。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于文本内部。即以第一篇“高城”为例,“风”可能是安放尸体雕塑的土坡,“而这个古怪的音节又可以称呼上帝、男女的交媾、进食等数以百计的事物与行为”。这种最为典型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性的强调,为后现代哲学的进入文本打开了后门。
因此,语言之门首先为《旅人书》设置了拆解的隐喻。小说的第一部分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诗或者寓言,或者干脆就是寓言诗。——因为它遍布着诗意的语言,跳跃式的叙述,碎片的杂陈、断裂的逻辑、奇特不羁的想象,以及出人意表的意象、频繁的隐喻象征等,所有这些元素,都是诗的。这是70篇化观念而成形的诗,我们也许无须刻意分析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因为对于一个块茎状或藤蔓状的结构,或者一副可以随时打乱或展开的塔罗牌(这是作者喜欢的比喻)来说,关联既随意而又似乎无处不在。这副塔罗牌的秘密或者说深奥之处,正在于它到处燃烧着作者思想或冥想的火花,比如艺术的极致和追求、人性之恶、时空观、财富、世界的变动不居、理性与非理性、遗忘与重生、语言的囚笼、爱情的救赎、女性或两性、真理与常识、图书、公德与私德、疯癫与混乱,如此等等。在这些思考里,我们间或可以看到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品钦、福柯、昆德拉等的影子,但作家显然没有臣服于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是,哲学、思想、形象、诗意、美等,以断裂或随意的方式杂糅而成羚羊挂角式的语言之流,这,可能也是黄孝阳理想中的量子文体。
作为“小说”的第二部分,是“尘世”。但“尘世”也并非就意味着“形而下”,无非是,观念的演绎从海阔天空的艺术狂想,落实到了“小说”这一形式载体之上,当复杂的思想在小说的文体律令下被迫隐藏之后,先锋式的技巧追求便水落石出。62篇小说证明了作家不亚于甚至超越前辈先锋作家的叙述技术。在几千字甚至更短的小品式的短篇中,黄孝阳像一个魔术师,总能凭空变出若干花样。他似乎永远不缺少那些峰回路转、充满着张力的故事。如果要翻这些小魔术的底牌,也许包括,第一,他总是醉心于生活中那些“黑天鹅”式的场景——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湍流”,隐藏着太多的偶尔性、可能性、不可知性、随意性,以及两难或悖论,作家搜集这些片断,如同搜集美丽的蝴蝶;第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第二人称叙事(在黄孝阳之前,还没看到第二个如此大规模而集中丰富地使用这一叙述方式的小说家)。“你”的叙事人称,使作家既可以悬于事件之上,像上帝那样冷静地观察、评论、抒情、拆解、敲打;也可以使作家随时溜进故事之中,从而形成复调、双声、突转或者神秘——这种叙事方式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作家独特的哲学,那就是,“你我”是互相指认、甚或合而为一的存在,既可能对立也可能融合(如同量子领域里的叠加态)。
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来看,黄孝阳稍后出版的《乱世》,其实正是《旅人书》的“互文”。从“雅”到“俗”,从碎片到整体,从诗到故事,不走寻常路,几近偏执地敲打或者说寻求小说文体的边界,几乎成了黄孝阳的习惯。《乱世》耗费了作者不少的心力,小说中大到民国三权分立思想,中统军统以及汪伪等组织活动,重要的时评社论,小到民国选拔县长的考卷、《知识青年从军歌》、一些不太知名的民国人物,甚至战争中的统计数据等,都可见作者的收罗之功。所有这些(当然,还可以加上令人叹服的丰富庞杂的法律人文知识),本来有助于作家将《乱世》打造成一部不错的严肃小说,——或者是姚雪垠《李自成》式的传统历史小说,或者轻松地承接新历史小说的传统(只需要在民间生命力,或者小历史小传统叙事方面强调那么一点点)。但是,这一次,作者却似乎宁愿将自己的心血轻易挥霍掉,将小说转向了“通俗”的窄门中去。为了配合民国风,也或许干脆就是作者在语言探索方面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小说摒弃了《旅人书》中诗意跳脱的语言,特意大量运用了颇见功力的旧白话甚至文言。一个写“你是我最好的光阴;你是微凉的晨曦;……在你的头顶,云层是一张恍若隔世的唱片。我翻天覆地地听”的诗人,一个营造了70个观念之城、思想庞杂的小说家,却转而写武侠江湖、人皮面具、香肩柔荑,自然是有意为之的结果。通俗化的形式,本身就是对小说传统的反抗与消解。这里蕴含着黄孝阳的自信和雄心,——但同时也是一种冒险。
冒险体现在小说某些方面的可能削弱。复杂的故事,以及读者的存在感,都是通俗小说的必需品。孝阳再次展现了自己编织大型故事的才能,并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结尾“请读者猜谜”。但,人物之间精致而波谲云诡的关系,“猜谜”的益智游戏,也许能够赢得读者,却固非优秀(严肃)文学作品之必需。
通俗化的追求还带来了另一个负作用:史料的严谨翔实,与人物真实感的缺乏,形成了对照。真实感首先来自于细节的真实,但武侠小说的种种神奇之处,客观上起到了间离的效果;而无所不包的知识(这其实也是通俗化的元素),被分摊到众多人物身上,富有机锋的谈吐固然吸引人,但却多少影响了个性差异的凸显,而且如果细究每个人物的职业及成长,学识之渊博似乎不具有足够的可信性;作者比较看重的法律意识,以及“世人畏果,菩萨畏因”的佛家观念,也没有得到足以让人信服的展开。“科学的精微”,是纳博科夫对好作品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比如卡夫卡《变形记》中,主人公化身为甲壳虫,本为荒诞,但写人变成甲壳虫之后的心理及生理,却无不精细入微。《乱世》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精微,人物可信度的折扣,自然也影响了“温情与人性的至幽微处,以及爱,那一声歇斯底里让天上星辰也为之震动的叫喊”。值得一说的还有小说的套盒结构。在经历了80年代的先锋试验之后,套盒结构也不再新鲜,当代小说已经发展出了叙述者与小说主人公之间复杂的互文叙事。《乱世》的套盒结构有三层(我和朋友/女作者之死/刘无果的故事),其中,朋友参与了文本的修改;“我”的功能,主要在于议论和女人作品的评点;而脸上有伤疤的女作者,则用她原因不明的死,参与了文本的构成(或者,如小说“跋”所揭示,女人的死还蕴藏了作者作为写作者的痛苦)。但这两个叙述层只在全书的前面出现,未能参与与历史故事的“化学反应”,效果多少打了折扣。
二
从《旅人书》到《乱世》,风格、题材等方面如此巨大的跨度,语言或者情节的瑰丽跌宕,甚至是貌似的那些“瑕疵”,显然并非出于草率仓促,而是作家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更为深入的理解无法回避黄孝阳以“量子文学观”为核心的文学理念。
黄孝阳认为,现实主义对应于牛顿的经典力学;而后现代主义对应于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对经典力学的颠覆,启发了作家对传统的颠覆、对常识的否定,对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的局限性的强调。《少城》中他曾以注释的形式强调:“常识是对世俗经验的服从,是对现有利益的维护。而人的根本是:不服从。”而《年城》中的旅人,面对那些在作为所有艺术发源地的“年城”的地下或外围、“用自己的血”来雕刻和建造图书馆的“瞳仁灰白”的人们,通过手刃骑士,转而奔向艺术之城,寻求摆脱自身的命运。黄孝阳也许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永远地”离开了传统的现实主义。
概而言之,在《量子文学观》中,黄孝阳醉心的理论包括波粒二象性(光既是波,也是粒子)、测不准原理(微观粒子的两个量不可能同时被精确测定;观测本身会对结果形成干扰)、薛定谔的猫(叠加态的佯谬,未观察状态下的粒子处于既在A地又在B地的现象)、量子跃迁(粒子状态的变化是跳跃式发生的);此外还有热动力学中的熵(熵量是混乱无序状态的量度),等等。严格地说,从量子力学到量子文学观,中间难免间有误读。但在文学接受的领域,误读往往能产生有趣的结果。作家服膺于微观世界的神奇与神秘,因而衍生了创作上的大量灵感。譬如,波粒二象性和叠加态理论,推而广之,便是“好/坏”(推而广之,包括现实/虚构、真/假、生/死等)非但不对立,甚至也非辨证,而是大可同时存在,既好又坏。这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博尔赫斯“镜”,或者庄周的“蝴蝶”。也因此有了黄孝阳所喜欢的“孪生姐妹”或者“相似的”姐妹意象(如《旅人书·第二部分》之11、28),也有了千姿百态的种种可能。而“戏仿、拼贴、黑色幽默对应量子跃迁玩的魔术。”“在具体文本上,某段突兀其来脱离了叙事流程的话,可能是作者苦心孤诣设置的镜像。”也才有了《旅人书》类似“一头老虎在屋檐下的蒺藜中嗅着蔷薇。活着的人啊,我是慧能、杨过、曾子;我是你们的标本,是雕塑,是上帝行的神迹;在通往生命、道路与真理的途中,我是你胸脯上那两个光芒四射的半球体”等极尽隐喻象征的句子。
在我看来,黄孝阳原创性的“注释”文体,更能全面而集中地体现量子文学观的精髓。这不是阎连科等曾经试验过的注释;它是“超链接”,是文本之中随时打开的时空之门(时空与宇宙理论也是黄孝阳之爱)。它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词、字或者句子上,诸如“老虎”“女人”“跳”“爱”或者“我是我”,等等;而注释内容则可以为议论、哲学、诗歌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它突兀而来的出现形式,如同量子跃迁;它与被注释对象之间,由于意义的互文、悖谬或者深度的拓展,构成了叠加态的关系,也使后者具有了“波粒二象性”;它是“测不准”的,它的存在可能改变了被注释对象的原有意义,拓展了文本的容量,增加了文本的复杂性,甚至构成了新的文体,如此等等。随便举一个例子,《总城》中有这样一句话:“毫无疑问,男人的话是一种可怕的偏见。”“偏见”一词则有以下注释:人的大脑基本上是被偏见所充斥,就像“和尚说的那个倒满水的杯子”。但把杯子倒空是不可能的事,顶多是刹那菩提。偏见失去,“我”即随风而逝。能否存在一种可能:《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什么意思?让大脑成为一张元素周期表,而非简单粗暴地认为世界是银子的,或者说世界是铜的。
在量子文学观的引导之下,黄孝阳进行了万花筒式的文学试验,这种试验目前看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如果要使前进之途走得更为坦荡,个人认为,作家还需要重视后现代理论已经积累的全部经验和困境。
黄孝阳的尝试还让我联想到他的法国先驱博德里拉。这位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认同解构“意义”的后现代革命,认为“凡生于意义者必将死于意义”。认为诸如计算机和媒体技术、新的知识形式正在产生着一种后现代社会形式;他提出了“类象、内爆及超现实”的三位一体;他指出“信息将意义和社会消解为一种云雾弥漫、难以辨认的状态,由此所导致的绝不是过量的创新,而是与此相反的全面的熵的增加”。③
因此,对黄孝阳创作意义评判的可能分歧,其实包涵在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认识之中。认识难以达成共识,与其说是囿于知识,不如说是取决于立场。个人看来,后现代境况客观存在,但未必代表理想的甚至终结的方向。较早的汤因比和贝尔等对此已作批判,即便是如福柯这样的代表人物,也力图回避“后现代主义”标签,后来还坦承与启蒙传统的某些联系。我们反对“绝对的真理”、“不变的本质”、“恒定的意义”(这一批判本身也包含在“现代性”内部),但如果因此认为真理、本质和意义不复存在,便是因噎废食了。事实上,量子领域抑或宇宙理论的相关科学成就,本身就建立在对规律和原理的“相信”上。
基于上述观点,我对黄孝阳“什么小说都用‘人性’这个筐来装,真的很烦啊”的观点,持保留态度。这种观点与语言学革命所导致的从“人”主体向“语言”主体的转型,以及福柯所宣布的“人之死亡”的判断相呼应,但如前所述,在空前复杂的后现代语境里,文学着眼于自由呈现的恣意,还是把灵性拴系于“人”的信念之锚上,与其说是认知之别,不如说是立场之分。
对“人性”的扬弃,促使作家向“复杂性”的探求。黄孝阳明确表示:“我觉得对复杂性的追求是作为人,作为人类社会,作为文学艺术,乃至于宇宙本身最根本的追求。”关于复杂性的误读,还可能是对“熵”的审美转化误读的结果。如作家所说:“传统文学观要求文本结构清晰明确,但熵现在告诉我们,杂乱无章更可能是宇宙的真相。我们对清晰明确的追求,很可能是在背离我们所梦想的‘真实’”。“杂乱无章可能是宇宙的真相”——这一句话并没有错。但是,真实未必是好的,如果“真实”不够理想,那么,我们便不应盲目追随,相反负有改造它的责任。文学的力量也许不在于随波逐流的复杂,而在于在复杂中寻找恒定。我们在后现代的虚空中跌落,手在绝望地胡乱挥舞,而文学,也许是我们在此刻侥幸攫住的东西。
黄孝阳说,“世界在变,而我始终如一”。“我”的存在,意味着还是体现了对“人”主体的确认。事实上,尽管后现代主义容易走向虚无和怀疑,但黄孝阳在提出“量子文学观”的复杂理论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相信”(“相信”是使宇宙走向秩序的负熵)。比如,在《旅人书》中,他选择了相信爱情的力量(《总城》),强调公德并认为自私不等于自由(《念城》),此外还有关于民主、历史、暴力等的真知灼见;再比如,《乱世》中的人物,围绕着法律、民族、生死、爱情的频繁争论,时时闪耀着作家的思想光芒和批判意识,甚或可以说是借民国故事浇今日胸中之块垒。
如果抛开论资排辈的文学史偏见,黄孝阳不只是一个“70后”作家,而是实力被低估的、属于未来的作家。黄孝阳喜欢一句话:我的身体里有龙。《旅人书·泉城》中,展现了一个人的“龙变”。我认为他正处于蜕变时期(“蜕变”也是黄孝阳喜欢的一个词)——风格的变动不居便是证明。我们目前还可以看到他蜕变过程中的“白森森的骨头”,但假以时日,在调节了后现代与传统紧张的关系之后,我们便可以手挥目送他展开双翼的“说不出的幽雅与高傲”。
【注释】
①黄孝阳:《旅人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乱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
②黄孝阳的文论包括《我对天空的感觉:量子文学观》、《文学有什么用》等,散见于《社会科学论坛》、《艺术广角》、《黄河文学》等,近期汇集为《这人眼所望处:量子文学观及人生观》一书,即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58页。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