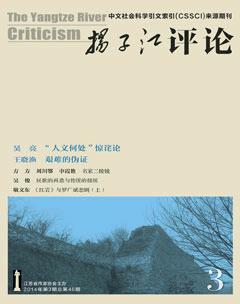“中国式”小说叙事形态面面观
孙仁歌
“中国式”小说叙事形态面面观
孙仁歌
在刚刚完成的《“中国式”小说叙事本土文化渊源释读》一文中,笔者依据中国传统文论经典以及现当代一些研究成果,表述了“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及其话语构成与本土文化的渊源关系,反复强调“中国式”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本土文化元素在“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中的发酵与渗透,也就是说释读“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离不开本土文化制约下所构成的种种形态,具体地说就是在“叙事美学”覆盖下异彩纷呈、花色品种多样的叙事样式,比如话语蕴藉(包括意境、含蓄、话语技巧等)。本土文化元素在“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中的生成与呈示,就是小说受制于中国语境支配的固有形态所在。下面就择其要点具体加以表述。
集意境、含蓄、话语技巧于一体的话语蕴藉在“中国式”小说叙事形态中的呈示可谓比比皆是。乍一看,把话语蕴藉与“中国式”小说叙事形态扯在一起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从理论体系而言,话语蕴藉源于抒情性作品研究的术语范围,而与叙事性作品研究的术语范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在中国古往今来的叙事性作品创作实践中,从来就不排除话语蕴藉的品格。在“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中,如果抽掉了话语蕴藉的原理,那么“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就会显露出更多的弱势乃至劣迹,因为“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对话语蕴藉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赖性,可以说话语蕴藉原理已经渗透其中,而且也是其不可或缺的文本滋养,一旦缺失,就会造成“营养不良“。
所谓话语蕴藉,王一川先生给出这样界说:“是将现代‘话语’概念与我国古典文论术语‘蕴藉’相融合的结果。‘蕴藉’来自中国古典文论,‘蕴’原义是积累,收藏,引申为含义深奥;‘藉’原义是草垫,有依托之义,引申为含蓄。在文学艺术领域,特指汉语言文学作品中那种含蓄有余、蕴积深厚的状况。”①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把话语蕴藉归为抒情性作品研究的术语范围加以表述。但在这里,王一川先生并没有把叙事性作品排斥在话语蕴藉所包容的范畴之外,这也就是从一种中国语境的角度把“中国式”小说叙事文本顺理成章地归于话语蕴藉所接纳的范围之内。说的具体一点就是,中国抒情性作品一向讲究话语蕴藉,而中国叙事性作品也不拒绝话语蕴藉,中国小说文本原本就讲究话术,话术即话语技巧,也是话语蕴藉的体现。“所谓话术,就是运用巧妙的言辞,以达成其高度形式的小说意识。”②如果用西方最新叙事理论的术语来释读“话术”,这其实就是一种修辞。
当然,“中国式”的小说修辞就是用心营构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性很强,能引人入胜,如此,小说文本也就成功了一半。在中国读者看来,小说家首先就是会说故事的人,并且又能把故事说得特别好听,特别有意思,同时又能把说故事的目的与意图悄然地隐于其中,在不动声色中让读者自己去悟,悟出来的东西往往又与小说家的创作初衷相交融。从话语修辞的角度而言,这就是话术之“术”。
1.意境作为一种叙事形态
并非中国抒情性作品才追求意境美,而中国叙事性作品也同样追求意境美。意境作为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它不仅在诗学研究中大有用场,而且在叙事学研究领域也大有发掘与拓展的空间。诗无意境往往不能成为诗,而小说追求意境往往更能成为“中国式”小说。不管人们对意境给出什么样的认知与理解,但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概念应该是:诱发并开拓审美想象的空间。
中国诗固然离不开意境美,而“中国式”小说叙事形态,似乎也不乏意境理念的制约。有不少学者从意境研究中发现意境应用与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不仅古典小说拥有意境的品质,而且现当代一些优秀小说也拥有意境的品质。我们既可以从《红楼梦》的叙事中分享到比比皆是的意境之境,也可以从鲁迅、沈从文、废名等大师的小说中领悟到意境的审美价值所在,即便当代的汪曾祺、张炜、史铁生以及潘军等人的小说文本,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置意境于其中,其主观追求审美想象空间的意愿显而易见。
意境美的实质在于:诱发读者神思,在有限的文字中分享无限的再创造空间,说白了就是让读者想象的翅膀在作者留下的空间翱翔一番。有人把这种审美想象含量高的小说称为“意境小说”。就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陈小手》等小说对乡土人性加以歌唱的叙事基调而言,“意境小说“之说也是可以成立的。笔者同意王学谦先生的看法:“当我们用意境而不是用诗体或散文化来指称这种抒情小说的特征时,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把它置于东方审美系统之内,表明了其传统思想素质和基本美学风貌。”③方锡德先生说得更了然:“意境的追求,推动小说从抒情艺术传统中汲取养料,把抒情性小说引向深入。”④以上两位学者都是“意境小说”研究的专家,他们的看法或论断都有充分的依据,是从学术实践中积沉下来的真知灼见。
倘若要给“意境小说“开出一份清单,没准能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家名篇;倘若要给这些“意境小说”一句共同的美言:那么就是写小说一定要有所保留,只有有所保留才能诱发读者无限想象,这也就意味着对读者的尊重。纵观文学史,好的小说往往都会给读者留下很多作业去完成,按照接受美学的说法,这就是作者的一度创造与读者的二度创造实现和谐匹配。而意境作为一种叙事形态,也正迎合了以上两种创造的完成,因为空间决定想象,有了审美想象才能填补叙事空间所保留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2.含蓄作为一种叙事形态
含蓄作为话语蕴藉的一种典型形态,虽与意境所覆盖的意义有想通之处,却又不等同于意境,有其自身特立独行的内涵,应与意境区别对待。在这里,不妨从小说叙事的角度验证含蓄在小说叙事应用中让有限转换为无限的修辞意义所在。无疑,读者在唐诗宋词中去感悟以少寓多、小中蓄大、品味不尽的妙趣已经习以为常,但读者如何在中国小说文本中去分享含蓄的魅力,似乎还没有那么从容自在。因为在读者的接受习惯乃至阅读习惯也包括一种文化心理层面,太缺少含蓄可以作为小说叙事的一种形态的积淀,尽管有“意境小说”之说法在先。实际上,在“中国式”小说文本中,含蓄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随便取一篇小说作品,都不会是含蓄的空白。从小说的立意、人物的塑造以及种种故事情节的设置与传达,差不多都是在含蓄的制约中进行的,倘若一切都实话实说,毫无保留,那就是散文,而不成为小说。从这个角度说,小说含蓄说的意义可以覆盖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说文本,但就“中国式”小说叙事而言,讲究含蓄却是一种文化心理在小说文本中的折射,并非一种泛泛的含蓄意味。
汪曾祺的《陈小手》就是一篇很含蓄的小说。从小说的标题包装到作者的内在创作意图,从小说外在的表现形式到小说文本的内在深层次结构,都算是在含蓄修辞上做足了准备。陈小手作为一个纯爷们,却以接生为生计,天长日久,身手不凡,不管遇到什么难产都能妙手回春。但不料为联军团长的太太难产赴命,陈小手却成了那个时代恩将仇报的牺牲品。赴命那天陈小手虽然手到病除,化险为夷,保住了联军团长的太太和新生儿两条人命,可就在陈小手转身凯旋之际,却被联军团长无端地从大白马上一枪给打了下来。理由是“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小说就此打住,作者没有给出任何道德判断,末尾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算是留下了无限的道德话题给读者去回味、去交流。在这种饱含民俗力量的有限中,却并不在于刻意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悬念,而在于一种修辞的魅力,即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这也正是汉语言典范形态含蓄的恰当体现。
可以介入含蓄加以分析的小说文本不胜枚举,一些“意境小说”也不乏含蓄的意味,不过也要杜绝为了证明含蓄而滥用含蓄,从而毁坏含蓄特立独行的品格。当代小说家某些小说文本所拥有的含蓄意味,差不多都是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并非刻意追求所得。《陈小手》是如此,其他一些有限之中蕴含着无限的小说文本也是如此。尽管不是刻意追求,但小说文本中实际收到的以小见大的修辞效果,却不容置疑。
3.话术作为一种叙事形态
话术又可谓话语技巧。在“中国式”的小说文本中,既强调故事性,同时也强调话术。强调话术之“术”,就是强调小说家善于运用巧妙的言辞,把一般的故事升华为有意义的小说形式。
中国古代小说重视故事性,而中国现当代小说也不排斥故事性。具有小说意味的故事说得好、说得妙,就会产生一种话里有话的效果。这种效果其实就是话术的体现。当然,这种话术的效果既有“讲”的智慧,也与时代背景、生活现实息息相关。如果只有“讲”的智慧,而所“讲”的内容远离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即便“讲”得妙语连珠、天花乱坠,也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对此,鲁迅先生早就明确提出:“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⑤
能“早感到”又能“早说出来”,既检验小说家的时代敏锐度与否又检验小说家的话术高下与否;“早感到”可能不难,但“早说出来”就没那么简单了。作者先要把“早感到”的东西变成故事,然后又要有能力有智慧把故事说得意味深长、话里有话,让读者三思然后大悟其真谛,从而分享小说文本的妙趣。如新时期小说家何士光的《乡场上》,就是一篇会说话有故事的小说。
小说家“早感到”的是改革开放尤其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能够挺起腰杆做人了,也活得有些尊严了,于是就想通过一个故事把这种感悟说出来。小说主人公冯幺爸是乡场上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过去因为依赖“回销粮”和吃猪肉难等等生活困境常常要夹着尾巴做人,比如要想吃到新鲜极品的猪肉,就要巴结食品站会计和他的女人罗二娘,因此,罗二娘就成了乡场上的贵妇人,连村支部也要让她三分。不过改革春风也在改变着这一切。一天,一件尴尬之事就降临在冯幺爸的面前。罗二娘与一个穷教师的女人发生纠葛,起因是两家的小孩发生了摩擦,其实就是罗二娘的孩子欺负人,拿了人家东西还打人。可罗二娘硬是倒打一耙,说自己的孩子挨了欺负,还要冯幺爸当众作证。众目睽睽之下,几经思想折磨以至反复斗争的冯幺爸,终于挺起腰杆面对公众说了真话,不仅罗二娘不敢相信这是冯幺爸,就连村支书乃至一些平时看不起冯幺爸的人也不敢相信这是冯幺爸。冯幺爸直面社会变革的春风,摇身一变挣断了计划经济沉重的锁链,犹如蛟龙腾飞,转眼之间还原了农民的真面目。
《乡场上》这篇小说之所以后来受到读者好评并获得全国大奖,可能就在于这篇小说先声夺人地释读了社会变革的意义,让读者掩卷之后仍在回味千千万万个哥冯幺爸挺直腰杆立于乡场上的风景。小说故事编得好听,叙述者又“讲”得妙,可谓故事话术并茂。尤其话术之“术”得以恰当而又巧妙的应用,才使得故事出彩诱人,从而构成了有意义的小说形式。
总之,由话语蕴藉统摄下的种种“中国式”小说叙事形态不一而足,诸如含混、模糊形态,抒情、写意形态以及《文心雕龙》“六观法”体系所构成的种种叙事形态等等,都有待加以深入研究并予以表述。事实证明,从本土文化元素研究并释读“中国式”小说叙事形态大有开拓的空间,特别是台湾学者黄维梁应用《文心雕龙》“六观法”评析文学作品尤其“中国式”小说文本的尝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对鲁迅的《药》和《祝福》、钱钟书的《围城》、白先勇的《骨灰》等小说文本的评析,更为引人关注。此外还有夏志清对《老残游记》的新论、乐黛云论鲁迅《伤逝》的思想和艺术以及欧阳子对白先勇《冬夜》的评析等等,都渗透了《文心雕龙》“六观法”的理论体系,充分证明应用本土话语去释读本土小说文本的前途远大,以上所举的成果案例都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所以立足于本土文化元素考察“中国式”小说文本,可以构成的叙事形态不胜枚举,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注释】
①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②谢昭新:《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史》,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③王学谦:《回归自然——中国现代意境小说发展脉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5期。
④方锡德:《现代小说家的意境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⑤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副教授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2013A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