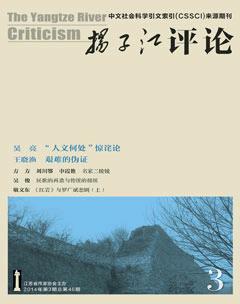残酷的陌生化──中国当代作家的悲悯情怀与文学想象
肖画
残酷的陌生化──中国当代作家的悲悯情怀与文学想象
肖画
“陌生化”本是文学理论中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由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占据重要位置。质言之,陌生化汰旧换新,化腐朽为神奇,使原本习以为常的改头换面、焕然一新,强化、延伸读者的感知过程,从而让读者醒悟曾经习焉不察的事物竟如此特别,由此发现一片前所未有的天地。这既是文学的创新之处,也是文学的伦理所在,而“陌生化”正是使小说能够有所“发现”的方式。语言、题材、角度、修辞等等方面皆可体现陌生化效果。与此同时,陌生化的异于常规的表现手法必须言之成理,否则过犹不及,满盘皆输。
表现“陌生化”的艺术手法可以千奇百怪,而“陌生化”效果背后的人文关怀才是作家和读者更应关注与体会的。有一种“陌生化”却让人感觉残酷,因为这种别样的艺术效果指向的正是众生的苦难,它不仅考验着作家另辟蹊径的文学想象,更蕴涵着作家济世为民的悲悯情怀,这些陌生化在新奇之余,无法不让读者遍生寒意,因为陌生得太残酷,作者“残酷”地撕开生命的表象,我们才得以看清触目惊心的“陌生”。
笔者所谓的“残酷的陌生化”正是指向文学作品中的这一鲜明特征,以此切入作者的悲悯情怀和文学想象。悲悯的力量不是来自苍白的控诉与空洞的口号,而是摘除冰冷的面具,摈弃看客的目光,唤醒麻木的灵魂,让众生对世间的悲苦感同身受。在当代中国,如何以文学观照现实,如何写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当代作家如何巧妙地使用这种特殊的陌生化效果,体现一位有普世价值的作家起码的人文关怀与基本的文学素养?本文尤其关注作家的悲悯,唯有从悲悯出发,想象才不会轻易地变成吸引读者的噱头,陌生化手法才不会成为过犹不及的文字游戏。
在大陆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第一次以“悲悯情怀”为主题,探析传主的人生观与创作观——“在白先勇那里,悲悯已不再只是一种看取的角度和立足的制高点——它已内化为一种精神品格和情怀气质,浇筑在他的作品中,并成为他的作品的内在核心部分”①。王德威概括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提出的小说必须有“大悲悯”,即拒绝煽情的苦难控诉,不是让替天行道形成以暴易暴的诡圈,而是莫言所说的“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的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能真正产生惊心动魄的大悲悯”②。西门闹在畜生道里数次轮回,以动物之眼见尽人世的荒谬与悲苦,因而领悟佛陀的箴言“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知足,身心自在”。
以此种种为前提,本文以“鬼魂的告白”、“盲人的感知”和“动物的视野”三种“残酷的陌生化”为途径,探析中国当代作家的悲悯情怀与文学想象。
一、鬼魂的告白
方方的《风景》与阎连科的《丁庄梦》都以一个男孩的鬼魂为叙述人,前者讲述武汉的贫民窟“河南棚子”里的卑微,后者状写河南艾滋村的绝望。尤其是《丁庄梦》的叙述语言阴冷、诡异,由此呈现的一幕幕凋残景象恰似鬼魂眼里的世界。本文重点讨论的是余华的小说《第七天》,该作讲述一个中年男人死于一场意外之后,七天内在阴间相逢新朋旧友,从他们那里得知生前所不知的种种真相,而能告知真相的鬼魂往往和主人公一样死于非命——死于中国当下不公不义的社会乱象。鬼魂们纷纷讲述暴力拆迁、屈打成招、腐败横行、倒卖人体器官、政府瞒报灾情等社会热点背后少有人知的真相,而此时已难以在人间讨回公道,故此书的宣传是“比《活着》更艰难,比《兄弟》更绝望”。但余华没有把这些冤魂写成厉鬼,而是让他们以平和的心态对人间的恩怨淡然处之。余华显然设置了一个阳间与阴间近乎二元对立的叙述大格局,并在阴间又增设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小格局。残暴荒诞的人间与宁静温情的冥界在叙述大格局中形成强烈的对比,殡仪馆里权势人物富丽堂皇的候烧厅与平民百姓简单粗陋的候烧厅在叙述小格局中又形成鲜明的对比,两重对比明显突显人间的不平等。
那么何处有平等?余华为冤魂安排了一个住处叫“死无葬身之地”:
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③
“死无葬身之地”本是一种诅咒,但这里由一句话变成了一个词,反而实现了众生平等、和谐大同,近乎托尔斯慕尔幻想的乌托邦或陶渊明虚构的桃花源,由此形成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反讽与批判。
《第七天》与余华以往的作品明显不同,尽管延续他一贯的残酷书写,但似乎缺少了《活着》所蕴含的人生厚度,也不见《在细雨中呼喊》所营造的叙述魅力,初读《第七天》容易让人联想到慕容雪村的风格,后者的小说《伊甸樱桃》、《原谅我红尘颠倒》以及《天堂向左,深圳向右》,极尽描述人性的丑恶与社会的阴暗,善良与公义被吞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和慕容雪村一样,余华在《第七天》里没有“现身说法”,读者几乎找不到作家本人对这些负面现象的反思,因此一些评论指出余华的这部作品不过是新闻串烧,将近年来多种社会阴暗面一一罗列曝光,缺乏批判的深度。
这里的问题是小说如何“处理善恶”,米兰·昆德拉以《包法利夫人》曾受到的批评为例加以说明。曾有人指责该作“过于缺乏善”,也有人问福楼拜“为什么他要隐藏起对自己人物的感情?为什么他不在小说中表达个人见解?为什么他要带给读者悲哀?”福楼拜的回答是“我总是努力进入事物的灵魂”。昆德拉因而指出小说有自己的道德,并援引赫尔曼·布洛赫的说法:“小说唯一的道德是认知,一部不去发现一点在此之前存在中未知部分的小说史不道德的。”昆德拉进而说明“为了能够听到隐秘的、几乎听不到的事物的灵魂的声音,小说家跟诗人与音乐家不同,必须知道如何让自己灵魂的呼声保持缄默”。④据此,笔者以为《第七天》并非简单地新闻排列,而是尝试以鬼魂为媒介,想象那些冤死者对人生与世界的反思,让读者看到被强权遮蔽的事实——不是以新闻调查的方式,而是以文学想象的方式,以丰满的语言与深沉的情感进入灵魂的深处。
二、盲人的感知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少有像《推拿》这样如此细腻地刻画盲人内心世界的小说,“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在毕飞宇的笔下出神入化,既延续了他作品中“执着”这一种基本底色与核心气质,也体现了人(特别是盲人)之为人所必需的“尊严”,而对这一普世价值的思考使这篇小说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批判性⑤。
《推拿》的独特价值首先在于作者以“盲人”为题材,其次是由于这一题材的特殊性使作者必须运用相应的写作技巧,最后作者要能感同身受,既巧妙又合理地呈现盲人对世界的感知。同一件事情在视力健全者心里往往习焉不察,但在盲人心里却异乎寻常,将这些非同寻常的感受进行艺术化的处理,诉诸文字,一个全然陌生化的世界便展现在读者眼前。
我们先以“时间”为例,体会毕飞宇如何从盲人的立场来感知时间,想象时间在盲人的意识里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因而呈现赫然不同的时间进程,由陌生化处理后的时间给予读者强烈的冲击力。视力健全者在光影、河流与钟表的滴答声中认识时间,关注时间往往只是为了安排日程,但在盲人小马的心里,时间却有切肤的感受,时间成了他的“玩具”。小马在九岁那年发生意外,在和失明痛苦而漫长的妥协过程中,小马渐渐发现了时间的奥秘,时间在“咔嚓”。
“咔嚓”一下是一秒。一秒可以是一个长度,一秒也可以是一个宽度。既然如此,“咔嚓”完全可以是一个正方形的几何面,像马赛克,四四方方的。小马就开始拼凑,他把这些四四方方的马赛克拼凑在一起,“咔嚓”一块,“咔嚓”又一块。它们连接起来了。“咔嚓”是源源不断的,它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两个星期过去了,小马抬起头来,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博大的事实,大地辽阔无边,铺满了“咔嚓”,沟壑纵横,平平整整。没有一棵草。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座建筑物。没有一根电线杆子。即使是—个盲人骑着盲马,马蹄子也可以像雪花那样纵情驰奔。⑥
时间在小马的心里不再看不见摸不着,而变得实实在在,可摩挲把玩,它变幻莫测,像水一样随意更改自己的存在方式,失明不仅让小马“看到时间魔幻的表情”,更让他体会到“要看到时间的真面目,只能脱离时间”。毕飞宇无意探讨时间的哲学,我们也不必从中解读出“存在与时间”之类的高蹈理论,作者对盲人心灵世界的感同身受较之种种理论探索更能打动人心——感同身受来自于作家的悲悯,而将盲人的这种独特感受表达得栩栩如生靠得则是作家的想象,可见二者相得益彰,对成功的作家而言缺一不可。
世俗中对“美”的定义往往来自于视觉感受,那么应如何表达盲人对“美”的感知?推拿店老板沙复明听说雇员都红公认得长得美,他便琢磨一个人究竟生得什么模样才叫“美”。在世俗人眼里,五官的美不是用触觉来形容的,但盲人对外界的感知靠得往往是触觉和听觉,所以沙复明起初越想弄明白什么是美,就越是让他焦躁不安。视力健全者可曾想象过,闭上眼睛如何去形容一个人的美?如果摈弃视觉的形容词,如何说明对美的认识?“书上说,美是崇高。什么是崇高?书上说,美是阴柔。什么是阴柔?书上说,美是和谐。什么是和谐?”⑦颇有文墨的沙复明联想起一连串诗意盎然的形容词,但这时文字与世界的隔膜表现得如此强烈,词与物无法建立对等的关系,一切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沙复明对都红的单相思,如何感受都红的“美”对沙复明来说就越发棘手,她的“美”让沙复明辗转反侧,连带着回忆起那一次年代久远的初恋,他对“美”几乎束手就擒。无法知道心上人的“美”是痛苦的,但无法知道自己的“美”更是悲凉和无奈的,当沙复明要都红自己说说自己的美是什么样的,都红却说“我和你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另一位盲人推拿师徐泰来天生失明,也没有沙复明那样复杂的心思和华丽的辞藻,当金嫣告诉他自己是美女,并问他什么是好看,徐泰来用了最能让他感觉美妙的事物来形容什么是“美”:“比红烧肉还好看。”对“美”的感受从视觉变成了味觉,这种陌生化的表达不是文人为了标新立异而采用的通感,而是盲人用最朴实真挚的情感来表达自己无法体验的美好,红烧肉诱人的香味与口感成为他对“美”最动情的想象。
《推拿》让视力健全者进入盲人的心灵,看到一个极其陌生化的世界,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终归来自于人生的残缺。如果不是因为失明,小马何至于不得不数着时间度日,沙复明、徐泰来也能摆脱语言的局限,真正看到心上人的容貌。以残缺为代价的陌生化何其残酷,而毕飞宇对这些陌生化的合情合理的把握不只体现他的文学想象,更渗透着他的悲悯情怀——站在盲人的立场,倾听盲人的心声,撕下慈善的面纱,还盲人与视力健全者同等的尊严,真正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作者对都红表现出明显的偏爱,细致地刻画出她如何拒绝旁人无论出于真情抑或伪善的“关爱”,坚持自食其力,坚守一个人应有的自尊。⑧
三、动物的视角
以“动物的视角”观照人间在《生死疲劳》里蔚为大观,地主西门闹死后在五十年里数次轮回,带着前世的记忆,化身为各种家畜重返故土,见尽故乡的沧桑巨变、兴衰荣辱,一种佛家的大彻大悟油然而生,因而在小说的后记里,莫言提出小说里的“大悲悯”——“唯有对生命的复杂性有了敬畏之心,小说的复杂性于焉展开……悲悯也是写作形式问题,因为一旦跨越简单的人格、道德界线,典型论、现实论的公式就此瓦解。”⑨一旦既定的模式被打碎,则须另辟蹊径,推陈出新,让笔触深入生命的驳杂层面,改变读者对世界的惯有看法,作品中的陌生化效果由此而来。
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在它们眼中,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和陈应松的《太平狗》两篇小说皆以一条狗的视角观照芸芸众生。
《越过云层的晴朗》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一条黄狗,讲述自己和几任主人之间的故事。狗的眼睛只能分辨黑白,看不出色彩,这只黄狗看到的世界因此黑白分明,没有中间地带,这就意味着人类的世界不管多么复杂暧昧,在狗的眼里却是非此即彼。作者给这条黄狗设定了一种判断人物好坏的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即“相由心生”——善良的心灵必定拥有美丽的外表,而卑劣的灵魂一定配备丑陋的外表。这种识人辨世的标准当然行不通,如此单纯的眼光只是作者对世界怀抱的淳朴善良的愿望,人性的错综复杂有时让黄狗无所适从,黄狗就像未经世事的幼儿一样,对自己喜欢的人的亲近毫无功利,而它所喜欢的人又往往是被社会抛弃的自我封闭的人——黄狗最怀念的主人小哑巴并不哑,而是因为父母双亡从此变得不爱说话,黄狗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但多年后,黄狗终于知道小哑巴的父母的死因,是一个想要建庙的人向它吐露了压抑多年的秘密:当年“破四旧”,此人响应“伟人”的号召,砸庙的时候碰见塑像的石匠“冥顽不灵”,为了“教育”落后分子,他们放火烧了石匠的家,结果只有一个孩子逃出来了。
忠诚善良的黄狗最后离开了人世,灵魂“越过云层,去拥抱它背后的太阳了。那里始终如一的晴朗……被无边无际的光明笼罩着,再也看不到身下这个在我眼里只有黑白两色的人间了”⑩。黄狗经历人间冷暖,尽管眼中的世界非黑即白,却了解到人所不了解的世态人情,临终时的世界仍然陌生,它却得以解脱,天堂的归宿正是慈悲的升华。小说结尾这种宗教式的启悟其实来自作者真实的伤痛,迟子建在小说后记“一条狗的涅槃”里写道:“这部长篇似乎冥冥之中就是为爱人写的‘悼词’,虽然内容与他没有直接的关联。我其实是写了一条大黄狗涅槃的故事。我爱人姓黄属狗,高高的个子,平素我就唤他‘大黄狗’。他去世后的第三天,我梦见有一条大黄狗驮着我在天际旅行,我看见了碧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那种在人间从来没有见过的圣景令我如醉如痴。”⑪迟子建的爱人意外死亡,作者自述这部小说的写作近乎是自我疗伤与灵魂抚慰,作者的全副身心全然寄托在黄狗身上,读者能明显感觉整篇叙述情真意切,哀婉动人。
陈应松作品的底色是阴暗,下笔毫不留情,将笔下的人物逼至绝境,不仅直视中国底层草根的艰难与挣扎,也揭露赤贫之中民众的愚昧与暴戾。和迟子建的作品不同,《太平狗》是一个缺乏温情但催人泪下的故事:一条叫“太平”的狗跟随它的主人程大种从神农架山区来武汉打工,主人在城里受尽白眼和欺凌,狗对主人不离不弃,主人却对它痛下毒手,它反倒凭着对主人的忠诚死里逃生;主人最后误入武汉的黑工厂,在非人的环境里被迫劳动,狗找到了主人却无能为力,主人死在黑工厂,狗千里迢迢伤痕累累回到神农架的家,主人的家人渴望知道他的下落,却只看到从狗的眼里滚出了一滴一滴的泪珠。《太平狗》体现了陈应松在小说中一直以来的思考——“弱势人群”的出路何在?什么造成了“弱势”?“弱势”与“国民性”的关系是什么?“弱势”的暴戾如何化解?本文对此不再赘述。底层之间的倾轧,草根之间的算计,在《太平狗》里依然醒目,狗的勇敢与忠贞越发显出人的卑劣与丑恶,小说篇名近乎是对世道人心的反讽,“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太平狗》不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对狗的冷静客观的描述反而越发引人想象。《生死疲劳》以及《越过云层的晴朗》尽管借由动物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如果在叙述的语气上太过人性化,则会过犹不及,变成童话故事,失去陌生化的效果,因为人类毕竟不能真正知道动物的内心世界,《太平狗》没有让狗“说话”,也甚少深入狗的内心,只是对狗的特征、行为如实白描,以狗的视野为参照,反衬出人的世界竟是如此荒凉、残暴、陌生。当“太平”被主人卖给屠狗贩之后,又被人买走,拴在楼顶,在寒冷的城市深夜思念故乡和主人,神农架的原始野性在体内流淌,和主人失散的“太平”与人一样伤感,城市陌生的何其诡异,陈应松如此想象“太平”对世道人心的观感:
到了晚上,思念主人和故乡的赶山狗太平终于发出了凄厉的长鸣。这是寒潮加深的某一个晚上,太平的脖子上勒着短短的铁链,它无法习惯这么一根链子,在山野,在它的丫鹊坳,它是自由的、奔放的、散漫的,脖子上除了毛就是吹拂着的村风,还有温和的阳光……可从楼顶望着满城迷离恍惚的灯光,它悄悄地淌下了眼泪。这是孤独的时刻……孤独。离别。无法交流。灯火像星空一样,带着诡异和狞笑,无声地跳动在大地的深处。⑫
主人死后,“太平”跟着主人的气息魂归故里,一种只有动物才能察觉神秘感引领它跟随主人的魂魄回家。陈应松以沉敛的感情写出了莫言提出的小说应有的“大悲悯”。
节段预制拼装造桥技术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效益,近年来得到大力推广,其核心是通过体外预应力将预制节段“化零为整”。由于体外预应力需通过锚固块及转向块才能将预应力作用传递到梁体上,因此,这类桥梁关键构造在于预应力钢束锚固块及转向块,在设计时应重点考虑。
“故乡!……”它在心底里大声说。它喊。它,太平,一条狗。一定是回到故乡去了,它的主人。那缕白烟正向遥远的天际飘去,在很远的地方,在川、陕、鄂交界的那一片山岗上,总有这样的烟云,像透明的梦境,从它的眼际飘过!……那气味突然从很深的地方泛了出来,还没有死去,它蛰伏在太平的心灵深处。那气味使它回忆起了过去的一切;那气味拖曳着它,牢牢地拴住了它,让它不可遏止地带着坚定的步伐,向那儿走去!它跟着飘渺的主人,跟着云端里的呼唤,在星星的指引下,嗅辨这那若断若续的来路,向回走去。⑬
结语:陌生化与文学伦理
在形式主义的理论操演中,陌生化是“文学性”赖以生长的上好土壤,让现实中习焉不察的环境判然有别,唤起读者对同一对象的重新认知,建立自成一体的纸上王国。钱钟书引梅圣俞的诗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状难写之境,含不尽之意”与西方理论互为阐发,见证古今中外的文学创新均不离陌生化的手法,而对陌生化的合理运用正是文学的伦理所在。上文引用昆德拉对小说的理解:“小说唯一的道德是认知,一部不去发现一点在此之前存在中未知部分的小说是不道德的”,那么小说应如何认知,怎样发现?在众多的创作技巧中,陌生化首当其冲,为小说在演变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让文学的传承保持活力。
【注释】
①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一九四九年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③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
④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75-78页。
⑥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⑦毕飞宇:《推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⑧除了上文引用的刘俊的文章,还有王彬彬的文章《论〈推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也论述了该作如何表现盲人的“尊严”。
⑨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一九四九年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9页。
⑩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⑪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267页。
⑫陈应松:《陈应松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⑬陈应松:《陈应松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