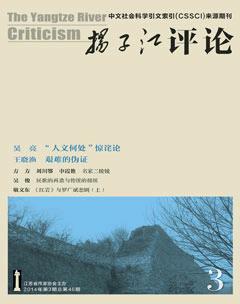“人文何处”惊诧论
吴亮
“人文何处”惊诧论
吴亮
历史总是会发生两次——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又来造访我们了,这一次造访不是以二十年前的集体寻找遗失物的缺席方式,而是以它的新世纪代言人刘再复先生声称那个如同流浪行吟诗人一般的“人文”找不到自己应有处所的惊诧方式;不过,这一愤世嫉俗的惊诧呼告非但没有表明所谓的“人文”无处可居无迹可寻,反将刘再复始终未在他文章中定义的“人文”两字高高安置在神圣进而神秘的处所,即刘再复在文章最后反复强调的人的内心,他慷慨地承诺每个人只要有向善之心,“人文”即可安居我心——如果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真的可以如此简单地像禅宗顿悟般易行,那么刘再复在文章开头充满忧患地提出这一问题就十足多余:既然心诚则灵,人人皆可佛在我心,慨叹乃至惊诧佛居何处便是一个凡夫俗子的假问题。
人文即世俗,人文不比世俗更高更神圣。将人文高悬在世俗之上,不过是极少数高级知识持有者和高级知识自诩者的头脑幻觉——刘再复先生引用他的老朋友李泽厚旧文“四星高照,何处灵山”八字破题,将李泽厚错谬百出的所谓时代描述作为出发点甚而彪炳为“时代性的大提问”(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这是一个怎样幼稚、皮相和充满偏见的时代描述啊),不过是出于一种膜拜哲学精英的陈见陋习,视艺人为倡优,惟迷信文字建构的抽象哲学体系,进而企图以哲学(更不要说是半吊子哲学了)来覆盖世界、注解时代和投射现实。
刘再复首先介绍了所谓“四星”,乃歌星、影星、球星、节目主持人——但我们依然不清楚这个“时代大提问”究竟是面向世界范围,还是面向中国大陆的。从文章不同段落看,刘再复的议题时而专指中国大陆,时而泛指世界,这得看他的需要而定——四个时代主角传唤上场,刘再复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说“四星高照”,既无褒贬,也无偏见。只是说,当下这个时代乃是以“四星”为符号,为中心的时代。刘再复继续指出:与“抬头望见北斗星”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不同,这个时代乃是一个欲望燃烧的物质化的浮华时代。哦,知道了,与“抬头望见北斗星”相比,这个“时代大提问”就是赠送给健忘的中国大陆人民的。然后刘再复转引李泽厚“进一步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是“物质生活全面展开”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类生活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哦,有变化了,“这个时代人类生活”云云,既然说到了“人类”,那么这一划时代的“时代大提问”就是李泽厚赠送给全世界人民的思想礼物了,是这样的吗,刘再复先生?
为了澄清上述疑惑,现在,就让我们从世界开始谈——谈世界,也就兼顾了谈中国——请洞达世界大势的刘再复先生或李泽厚先生告诉我,自古以来,哪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没有全面展开,物质生活在哪个时代未曾作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与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刘再复先生除了喜欢引用鲁迅还喜欢引用马克思,好的,我们这里就引用一段马克思经典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如果刘再复先生对这段话也能倒背如流,那么就请你代替李泽厚先生解释一下,你们所谓的我们这个“时代物质生活的全面展开”是从哪一年开始算起的,又以什么技术发明或重大事件为其标志?而你们自诩的哥白尼式历史大发现与马克思坦承“一经得到”就用于他本人研究工作的历史唯物主义“总的结果”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目不暇接,犹如漫长的梦幻戏剧,时间加速,疆域膨胀,制度与危机,衰败与繁荣,帝国与奇迹,救世与革命,马克思本人尚且不敢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虽崇尚浪漫激进,却仍言行谨慎恪守谦虚。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纪常常会因为某一个领域的偶然发现或某一项令人惊叹的发明而出现“时代命名”,它要么是一条定理的发现,要么是一项技术发明,却罕有人敢于弄出一个笼罩全球的“时代大提问”。孔德顶多说:缺乏精神力量,将发生巨大灾难。黑格尔顶多说:群众正在崛起。马克思顶多说:丧钟将要敲响。尼采顶多说:虚无主义的洪流在奔腾泛滥。他们讲得朴素且有力,他们当然不需要自我吹嘘。十九世纪没有电影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哲学家的声音只有他的同行才听见,哲学家的大问题只属于一小撮人……二十世纪以后,尤其到了二十一世纪,安居在舒适学院里的哲学教授们(还有哲学家吗?我不敢肯定)与“四星”一起在电视中出镜,他们都俨然成为了现代媒体的嘉宾。歌星影星主持人施施然歌舞升平,那么留给哲学教授的戏份,就只剩惶惶然危言耸听。哲学教授或历史教授在现场演播室或录音室里掉书袋、讲笑话、故作深沉乃至悲天悯人,其实与“四星”所扮演的舞台角色无异。一个世界级足球明星身价亿万不过是拜现代传播技术所赐,正如由竭力标榜“人文”的电视文化大讲堂度身定做的教授明星,如今他们妇孺皆知朝闻天下收视率一路蹿升;不过很遗憾,他们是被李泽厚先生与刘再复先生忽略、藐视或者刻意忘记的“第五星”,纵然我们这里有诗为证:两岸人文啼不住,明星直上九云霄。
发现“四星高照”的始作俑者是李泽厚,尽管这是一个非常蹩脚的发现——相信去国多年的李泽厚对友邦美国学院教授很熟悉,精英圈子小则惺惺相惜,应该晓得乔姆斯基、詹明信之流者再怎么尖锐地批评白宫和五角大楼也不会酸溜溜惊呼诺大一个美国的人文精神居然被汤姆·汉克斯、乔丹、玛当娜和温弗莉的光芒四射所遮蔽——同样是媒体时代的大众娱乐大众文化,经济自由与表达自由的云泥之别决定了两者的深刻差异;同样是新闻主持人,新闻要保密,国情不接轨,国情不同自然行规也不同,白岩松学不像华莱士,柴静也做不了法拉奇。
遍览刘先生全文,处处“人文”,却不知此“人文”究竟为何意、为何物?刘再复说:现代“物质生活”全面展开了,故“古典生活”之“衣食住行”即增加了“性健寿娱”,且不说刘先生疏忘了“声色犬马”、“骄奢淫逸”和“福禄寿喜”源远流长之古典性,即便回到刘再复心仪的十五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彼时所谓“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人文”难道不就正是包含着这些世俗快乐和享受生活的诸项内容?体育明星、电影明星、歌星与主持人的职业分工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蒙昧时期:英雄与巫司、凯旋与表演、祭祀与狂欢、仪式与放纵。围绕和推动这一切的力量其实不是什么秘密,无论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一样公开承认(这个结论不完全属于他们):人类文明的起源,不外就是人出于生物求生本能驱使的一系列竞争与合作过程,他们的一切活动均以获得足以使自己生存下去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指归,物质生活不仅是上述那些带有精神性质的活动的起因和基础,也是那些活动所要达致的目标——生殖、觅食、丰收、避灾、祛病、掠夺、复仇……首先是为了生存的、欲望的、身体的,然后才慢慢演进为禁忌的和文明的。
吾国学人近年讲“人文”,言必提“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刘先生这次再提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两位旷古奇才,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外之外。“意料之中”无须解释,西谚说“站在巨人肩上”,古人云“登泰山而小天下”是同一个意思。所谓“意料之外”则可援用鲁迅语,一句叫做“引以为愧,翻然思变”,另一句叫“老调子已经唱完”——巨人的肩膀是那么容易爬上去的吗,登上了泰山阁下您就不准备下山天天呆在泰山顶上看日出了吗,翻然思变,立地成佛,狠抓私心一转念,思想说变就变了吗?
如何评价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绘画,刘先生依然沿袭“神/人”两元论的旧唯物主义机械方法论,声称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大教堂天顶画中“注入了振聋发聩的人文精神”,断言米开朗琪罗“不是赞美上帝,而是描绘人性”,紧接着又“人文理想就暗藏在上帝创世之处”——请问刘先生,你既然已经判定“神主体”是“无精打采”的,你又怎么会在“神主体”那儿发现“有血有肉”的“人主体”的呢?这里我不与你争辩究竟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我责问的是你在表述重大观点的时候是否应该遵循起码的逻辑。尽管刘再复一直没有明确他所谓的“人文”到底包括什么具体内涵,但是被刘再复所不屑的“黑暗的中世纪宗教”,也就是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毕生为之忠诚服务(特别是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罗马教廷,却已经对“人文”有了决定性的定义,即“神学”、“哲学”、“诗学”和“法学”。毋庸置疑,“神学”位居“四位一体”的“人文”之首,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基督教,没有教皇朱理二世及他的继承者利奥十世,这三位广受后世无比敬仰的旷世巨匠会有几多“描绘人性”的作品留给我们。其中,最富绘画天才的拉斐尔在二十岁就画出了《大公爵圣女像》,那圣洁而带有胆怯的表情不仅具有母性美,更多的是一种安静虔诚的宗教感情,绝非可以用“有血有肉”来敷衍故事。至于刘先生信手拈来的但丁及其长诗《神曲》,亦有轻率解读之虞:说“但丁的《神曲》借助宗教的外壳,注入了巨大的人文内容”,不仅完全漠视基督教深邃宽广的人文精髓与践行其信仰的久远行迹,还严重扭曲了但丁作为一个虔诚基督徒的真实面目,但丁痛恨的是为非作歹的神职人员,他从未怀疑过上帝,“今生的幸福在于蒙受神恩”是他的信条,但丁恪守神学之德——信德、望德、爱德,基督教自有人文精神,并不需要从外部注入。但丁生活在十三世纪,文艺复兴要过两百年,启蒙运动则要在五百年之后才在欧洲出现。
由于因陋就简的唯物主义历史教科书影响过大,习惯背书的人们总是人云亦云地认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技术是一个接一个的历史阶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似乎已经被科学理性所取代,成为一种过去式——这一描述不仅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文艺复兴”作为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不是谁替代了谁,更不是谁战胜了谁。“文艺复兴”孕育催生了早期现代性,进而产生了“信仰”与“理性”的分离,“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一句话,最后造就了“神学”与“世俗”的大分离。
但是这并不是唯物主义的过错,更不是宗教的过错。刘再复先生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所在,却找错了原因。刘先生的思想混乱乃是这个世界日益光怪陆离之混乱投影——约束人性乃至压抑人性是宗教之误用,解放人性乃至放纵人性则是唯物主义之误用。鲁迅在他的早期作品《文化偏至论》提到“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他当时选择了尼采的个人主义。一百多年过去旧事重提,仿佛仍然生存在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范围里。刘再复先生的立意是良善的但也是天真的,他从对大千世界的忧患回到了个人的小小内心,虽然不再谈主义。不过,我们不必老是再拿鲁迅说事,鲁迅非先知更非圣贤。鲁迅自承他的早期作品(自然包括这篇颇具檄文风格的《文化偏至论》)只是“译述”而已,其中提及的“重物质”而不重“灵明”绝非是“鲁迅的发现”,“立国先立人”也并不像刘再复那样夸张地赞誉为“天才命题”(古人早有“修齐治平”一说)。鲁迅的某些深刻常令我惊惧,但并不等于凡鲁迅说的话就一定深刻。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鲁迅讲的大实话——鲁迅的遗嘱中有一句是写给他儿子的,要他“长大后找个事做,不要做空头文学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鲁迅以他的大白话,令我惊惧。
(注:刘再复《四星高照人文何处》一文刊于《东方早报》2013年9月30日。)
※当代著名学者,《上海文化》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