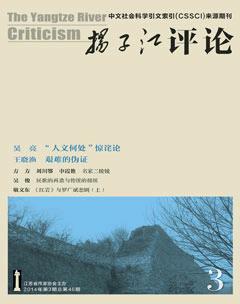《红岩》与罗广斌的悲剧(上)
敬文东
《红岩》与罗广斌的悲剧(上)
敬文东
革命前奏
1966年是稍微有点记忆力的中国人永远无法释怀的年份。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它都“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①。那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给无数人提供了太多的机遇——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和这一年5月16日以后的火爆绝然相反,这一年的2月十分寒冷,即将成为文化旗手的江青受林彪委托,邀请军界要人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和寒冷的气候完全不同,座谈会进行得十分热烈。上海无疑给江青留下过太多难以磨灭的记忆,她的青春年代曾在这里较为耀眼地焚烧,附带着满城风雨的绯闻,以至于几十年后她特别喜欢把许多重大的事情放在上海进行。江青临去上海的前一天,林彪,一个瘦弱得只能撑起自身思维的人,一个怕风、怕光、只能生活在恒温状态的神秘人物,在林办机要秘书的帮助下,向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志坚发出了指示性的电文:“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②不愧是名将,言简意赅,但劲道十足,耐人寻味。
1966年,中共最高层正在酝酿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毛泽东痛感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反攻倒算,正在寻找机会向他钦定的接班人、“走资派”的现役总司令刘少奇摊牌。作为教育家从井冈山开始到而今的政治盟友,林彪向刘志坚暗示了太多的东西,后者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时间跳入1966年后,革命话语的即兴色彩又开始它的新一轮顽皮,它的新灵感将绽放出更为火爆的花蕾。本着林彪老谋深算的指示,2月20日,在潮湿、阴霾和寒冷的上海召开过多次座谈会后,江青在军界的帮助下,终于拿出了一份具有无穷威力的纪要。这份纪要即将成为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仰仗它的帮助,只需要少许力气,就能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1966年4月10日,经过毛泽东亲笔润色修订后,中共中央以文件为方式,向全党转发了这个精心编织的纪要。江青肯定十分得意,因为纪要的核心内容很符合她眼下的需要:文艺界在建国15年来,一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③一听就知道,这是毛泽东两、三年前那两个批示的翻版,是它们在即兴色彩的新一站向革命话语发出的高亢和声。
作为纪要伙同其他众多行为集体催生出来的产物,中共中央在这一年的5月16日正式发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通知(简称5·16通知)。通知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强烈要求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完全跟不上革命话语即兴色彩的顽皮步伐,已经成功地堕落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时间转过一圈之后又回到起点,曾经被认为已经消灭掉的资产阶级看起来又得到了还魂丹,觅回了自己的性命。现在,他们已经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前程,富国强民的革命目标有被毁掉的危险。我们的故事即将认领和享用这场殊死搏斗显露出来的若干特征。
话说《红岩》出版后不到半年,罗广斌便和他的两个搭档一同调入重庆市文联,成为专职作家。尽管有很多不满意,但对于新工作罗广斌还是持乐观态度:“这件事又好,又不好。好处是:时间属于自己;行动完全自由;和文艺界接近,便于提高。不好之处是‘脱离’了斗争”,有可能陷写作于不利的危险④。作为一个在党委领导下的创作小组,自调入文联后,三个人的主要任务是为《红岩》的续篇四处搜集资料;出于对“‘脱离’了斗争”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坚决抵制,到1966年,他们共计积累了超过千万字的笔记和对多位革命志士的采访记录。
对于三位前红色说书艺人,有着爆炒腰花般油腻、乌红面孔的1966年显然来势不善:早在前一年秋天,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歌剧《江姐》已经全面停摆⑤;1966年5月,电影《烈火中永生》受到江青的点名批判后随即禁止上演。根据革命话语的新顽皮,江青给电影找出了一大堆病灶,它们在江青的意识流说话方式中,个个都显得十分要命,一年半以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找出的病灶又有了新变化:“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小说里的许云峰是工委书记,而在影片里成了市委书记,这是根本不同的。歪曲白区工作……地下办《挺进报》是盲动主义。把华蓥山游击队写成是重庆市委领导的,而重庆市委又受上海局领导,是城市领导农村斗争。既违背主席思想,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不是上海局,而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许云峰、江姐两个形象不好,许像旧知识分子,江有些娇气,华子良为疯子……”⑥虽然江青将矛头对准的是众多的第二度理解-解释,但所有被封杀的,都来自前红色说书艺人制造出的初步性理解-解释和最初凝结的价值以及它的意义倾向性。不祥的兆头使罗广斌等人在山雨欲来之前的满楼狂风中,感到了阵阵凉意。
在1966年荡涤人心的最初几个月里,小说《红岩》似乎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在此时,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决定再版这部影响日益深广的长篇小说。这年6月下旬,亦即宣告“文革”正式爆发的5·16通知发出一个月后,张羽受出版社委托,致信罗广斌等人,询问他们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党史小说重版时是否会做适当修改,以求跟上继续革命越来越豪迈的步伐。写信的时候,张羽还不知道,在此之前两个月,罗广斌已经揭开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革命的序幕⑦。1966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罗广斌、杨益言在百忙中终于腾出手来,致信张羽。他们声称,和地理语法的严厉要求相吻合,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状态,尽管小说肯定需要继续打磨,但因为革命工作千头万绪,只有“等这里的斗争任务基本结束以后,(才能)花些时间修改”⑧。写那封信时,罗广斌肯定还记得,早在1965年1月人民大会堂那个寒冷的深夜,江青就向他们发出过指示,小说必须按照将来完成的革命样板戏定下的调子进行大规模地修改,以求凝结新的价值,走入正确的第二度理解-解释所要求的那个更为高迈的境界。对于江青的指示,红色说书艺人自然不敢有半点违抗。
回信的当天,已经深陷于二次革命的罗广斌肯定不曾想到,他今生不会有任何机会亲手修订他心爱的《红岩》了。5·16通知飞马传出之后不久,疾风暴雨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在四川收获了它的首批重要成果:马识途(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文联党组书记)和著名作家沙汀被打成四川的“三家村”(一种反动小组织的别称),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被册封为“周扬黑线的追随者”⑨。我们的故事早已讲过,马识途是罗广斌走上革命道路的引领人;和任白戈一样,他还是《红岩》的坚定支持者⑩。马识途、李亚群和沙汀在继续革命的步伐前率先倒地不起,让罗广斌感到十分惊恐。“他的烟抽得更厉害了。”⑪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内,伴随着革命话语即兴色彩更新一站大张旗鼓地莅临,罗广斌开始了他忍耐已久的行动。1966年4月,他“认真学习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4月18日的《解放军报》社论,认为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纲领性宝贵文献,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他根据文件的精神,联系本机关的实际,就勇敢地起来造反了”⑫。1966年4月下旬的某一天,在重庆市文联机关的一次会议上,秉承纪要和社论的基本精神,罗广斌慷慨激昂地对与会人员高呼:“重庆文联烂了,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个头勉强攀升至160厘米的汉子无疑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会场顿时炸开了锅。文联秘书长、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王觉有点听不下去,站起来大声呵斥罗广斌:“干脆,你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好了!”罗广斌毫不示弱,大声回以颜色:“是黑线专政,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⑬说这句话时,罗广斌大约不会想到,过不了多少时日,同样的言词将原封不动地安置在他的头上。
1966年5月16日以后,革命话语即兴色彩的顽皮特性在继续革命的深化阶段导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作为一种不断变更自身外延的话语定式,它能同时为敌对双方所借用,作为互相打击的理论依据⑭。话语市场上一件更为令人瞩目的事情紧随其后,趁机冒出头来:遵照同一个即兴色彩的内部口令,敌对双方对同一件事完全可以给出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第二度理解-解释;依靠敌对双方的努力,同一个即兴色彩能让剩余价值网络和理解-解释网络不断扩大⑮。就在罗广斌将矛头指向市委的同时,作为反击的一方,后者的手段显然更为高明、迅捷和有力。他们很快就找到突破口:翻《红岩》的案,认定小说是修正主义作品,是按照周扬黑线的文艺思想来写的——纪要发表后,这样的口实太容易找到,它几乎就在寻找者的手边或眼前。没过多少日子,重庆市委就派出工作组,要求罗广斌如实交代党史小说在创造过程中与“黑线人物”的关系⑯。谈话是在重庆市文联一间办公室里进行的,距离罗广斌设在文联大院的家仅仅咫尺之遥。他的夫人胡蜀兴感到阵阵凉意;面对咄咄逼人的追问,罗广斌怒火四射,十几年忍气吞声滋生出的反抗念头更为强烈。
在二次革命的前夜,罗广斌看似突兀的火气其实来得一点都不突然。自1949年大屠杀之夜到如今,他已经反反复复接受过上级组织的四次审查。审查的核心每一回都集中在为何他能从大屠杀之夜皮毛未伤地安全出狱?这是不是和他的反动哥哥罗广文有关?他是不是以出卖组织得来的钞票才购得了自己的性命?在对他作审查结论时,评语一次比一次差。最近一次的结论是在1964年作出的。在那次匆匆忙忙作出的考语中,对他当年在看守所的表现视而不见,对他在大屠杀之夜率众越狱深表怀疑,仅仅勉强给了他一个“未叛党”的粗糙结论⑰。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得下放在远离重庆市区的长寿湖渔场做场长。“1963年,罗的名气已如日中天,共青团中央提议推选罗广斌为全国青联访日代表,被‘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一句话便轻易否决。1964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亦遭同样原因否决。日共邀请罗渡海东访,再次被有关方面婉辞,罗终未能越雷池半步。广阔社会的显赫名声和小局部的重重怀疑、不信任和压抑,结合得如此完美:20世纪60年代偏居西南一隅的大作家就生活在这种困境中。应该写出伟大作品的笔,只能畏畏缩缩地写检讨书。应该被尊敬、鲜花和崇拜簇拥的一代才子,却只能被‘下放’到远离城市的渔场,做相当于‘弼马温’的‘场长’。长寿湖渔场的雾蔼是沉重而寂寥的,罗广斌就在那儿消磨着才华横溢的日子。”⑱屈指算来,1966年发生在重庆文联办公室的那次审查,已经是上级组织对他进行的第五番折腾。
真不知在文联那间俭朴的办公室里罗广斌究竟搞清楚了没有,市委对他的反击同样依据他不久前依据的5·16通知。1967年7月,在罗广斌抵抗专门为他而设的工作组有过一段时日后,中共西南局决定迅速找到突破口,扫清西南地区尤其是重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毕竟《红岩》带给罗广斌的名头实在太大,他在一般的革命群众那里有着无可比拟的感召力。7月中上旬的某一天,西南局以批判周扬黑线为借口,联系本地的实际情况,迂回曲折了一番之后,径直指名道姓地声称,小说《红岩》是修正主义作品⑲,具体证据如下:歪曲历史(即以江青的言论为准的,指责《红岩》歌颂执行王明路线的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引者注),与马识途、肖泽宽等牛鬼蛇神合谋,是反党黑帮集团集体炮制的产品;以刘思扬为名美化富豪出身的罗广斌⑳;歌颂头号走资派刘少奇㉑。“《红岩》这部书的出笼难道是为了歌颂红岩村吗?是为了反映以红岩村为代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吗?不是,不是,完全不是,绝对不是!这部书是为了讴歌1948年到解放前夕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正确领导’而创作的。是为了这个地下党市委正、副书记(叛徒)翻案而创作的。是为了给《挺进报》和川东起义、川北起义的错误作辩护,为了给推行叛徒哲学的所谓‘狱中斗争’,作粉饰而创作的。是为了给刘少奇树碑立传而创作的。根据这部黑书炮制者的描述:1948年时的地下党重庆市委一贯正确得很。至于组织的破坏又怎么样呢?据小说的概括,那是由于党组织中有人读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后所造成的恶果。小说在这里挥曲笔,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之后,接着就极力描绘了一个有着斑白的发丝的‘党的负责人’,说是靠他收拾局面,一切才又化险为夷。至于这个‘有着斑白发丝’的能人是谁呢?如果你没有从小说中读懂的话,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就直接地告诉你了,原来这里写的他们‘心目中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同志。’……仿佛重庆根本就没有过红岩村的存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就是红岩的代表……小蟊贼罗广斌伸出的扒手,大强盗刘少奇斑白的狼尾,都被英雄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一个揪住了……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胜利,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定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红岩》这部反党小说批倒批臭!”㉒毫无疑问,初步性理解-解释在革命话语即兴色彩的新阶段遭到了彻底否定,小说《红岩》在党委的指导下曾经凝结出的正确的价值,也被认为犯有极为严重的路线错误,拥有完全错误的意义倾向性:完成性动作被认为在生产《红岩》时自摆乌龙。很显然,伴随着革命话语即兴色彩的灵感突发,围绕着歌乐山上下的本事组建起来的剩余价值网络和理解-解释网络进一步扩大,话语市场趁机拓展自己的疆界,展开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和罗广斌对此的反感与愤怒绝然相反,我们的故事必须对此持绝对感激的态度。
面对重庆市委的种种刁难,罗广斌十分震怒;有革命话语即兴色彩撑腰、做主,他决定这一回拒绝沉默,必须起而行动。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市委的反击更为有力,既遵循又大幅度地违背了牛顿第三定律:就在罗广斌致信张羽的第22天,亦即1966年7月22日,派驻文联领导革命运动的市委工作组动员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交出他们近四年来为《红岩》续篇搜集的资料,由市委工作组代管,以免失密㉓;看罗广斌依然没有投降的明显迹象,半个月后的8月3日,市委在一天内连发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量体裁衣,十分明确地给罗广斌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为了和纪要中承载的最新型号的即兴色彩相吻合,还把罗广斌绑在马识途所代表的文艺黑线的战车上,指责《红岩》是文艺黑线的正出产品,通过马识途进而和已经被打倒的前文艺总管、罗广斌并不十分熟悉的周扬联系在一起——后者不久前被迫摇身一变,从前红色文艺总管跃迁为文艺黑线的现役总舵主㉔。
必须要承认,刚刚爆发的“文革”为罗广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反击机会,革命话语即兴色彩的新灵感也给他批量供应了必要的底气㉕: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才算真正符合通知的精神,坚信自己是站在毛泽东的思想的旗帜下实施反修防修斗争。“文革”正式开始后不久,多年不被信任的怨气使他向全市发表公开信并成立战斗小组,率先夺取了市文联的领导权。《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发表20余天之后的1966年8月底,对修正主义分子已经忍无可忍的罗广斌决定把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市文联的炊事员郭青等人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时,罗广斌当即表示坚决支持。他对拉起旗杆招兵买马的郭青等人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㉖和多年前不幸一语成谶的彭咏梧、王璞、刘国鋕极为相似,罗广斌也鬼使神差地摸到了自己命运的开关。随着这句话消失在空气中,罗广斌距离他的悲剧的最后完成仅仅需要4个月;他无法知道,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会再有11·27大屠杀之夜的幸运,这一回他遇到的不是歌乐山、白公馆和它的看守长杨进兴,而是力量更为巨大的革命话语,是革命话语无比顽皮的即兴色彩——在它们的胸腔内,不会有杨钦典、李育生的存身之地。
就在罗广斌准备二次革命的当口,一个多月前给他写信的张羽也揭开了他十余年不幸生涯的序幕:随着电影《烈火中永生》遭到点名批判,张羽被勒令在家闭门思过,没有资格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昔日完成性动作的监控者,现在成了革命话语即兴色彩又一轮顽皮中的被监控者。
二次革命终于开始
和已经过去的数千年相比,1966年无疑拥有一个质地特殊的秋天,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极少数杰出的秋天以它们非凡的肃杀或丰收才可以和它相提并论。这一年的苍天依然像往常那样俯视人间,对各色人等漠然相向:它对人间的沧海横流、英雄本色已经熟视无睹,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引起它的惊奇——何况这些年“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莽撞行径已经让它彻底腻味。作为进入秋天这个盛大宴席的过门,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名曰“炮打司令部”,不点名地将矛头指向他曾经内定的接班人,资产阶级设在共产党内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㉗——作为对那张大字报的酬谢,后者从此运交华盖,在河南某监狱内令人惋惜地匆匆丢掉了性命;没过多少时日,应和着第一张大字报带来的革命效应,毛泽东身着军装,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一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第一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此,红卫兵运动像从前的革命火种一样星火燎原、全面开花;10月8日至25日,伴随着阵阵秋风,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清算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资产阶级被消灭数年后,竟然在共产党内死灰复燃,这无疑是令革命话语及其掌控者目瞪口呆的事情。
适合密谋、地下帮会与反叛活动的雾都重庆,拥有特殊地理语法的山城渝州,像它在卫国战争期间充任临时首都一样,这一回又走在继续革命的最前沿,深为灵感大发的即兴色彩所肯定和表彰,只因为它正处于即兴色彩所需要的那种迷狂状态。“山城重庆,祖国大西南的重要工业城市,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后方的重要基地,李(井泉)家王朝的川东重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烽火连天的战场,因其斗争特别激烈残酷,特别曲折复杂而全国瞩目。”㉘——地理语法和革命话语的即兴色彩一拍即合。自进入那个质地优异的秋天以来,我们的故事的主角罗广斌在他所做的一系列事情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是参加并发动了11·27大屠杀17周年的纪念活动㉙。
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开始前,伴随着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罗广斌为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早有准备和预演。10月23日,他和杨益言写出大字报《致重庆市文联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信》,公开亮出造反立场;两天后,重庆市文联由他和杨益言联袂主持,进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郭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等人被选为“文革”筹备小组成员,组长是炊事员郭清,但筹备小组实际上由罗广斌、杨益言控制。10月26日,重庆市文联“文革”小组正式行使领导文联机关进行“文革”运动的权力。时间越来越接近纪念大会到来的那个日子,罗广斌等人的动作也更为疾速、有力:11月8日晚,罗广斌、杨益言将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组长牛文拉到市中心解放碑进行辩论,进一步扩大对市委的反抗态势㉚。“解放碑下人山人海,看《红岩》作者亮相造反。”㉛党史小说的作者在重庆敞开自己的立场,对重庆的各个造反派组织无疑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
时令已经进入重庆的初冬,潮湿的寒风缓缓伸出舌头,舔舐着市民的全身,但重点是脸颊和裸露的脖子;和时令相反,作为即兴色彩的物质体现,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如火如荼的新阶段高歌猛进,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纷纷来到重庆或在雾都建立联络站。1966年11月27日,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举行的纪念大会显得十分热烈,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参加了这次盛会。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一声令下,随着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应声倒地,红卫兵坚信自己才是革命烈士的嫡出子孙,一贯执行刘邓路线的重庆黑市委无权染指这个伟大的纪念活动。出于对红卫兵的高度支持和认同,我们的主角马上就要出场,让中共西南局担忧的事情终于来临:“罗广斌是乘坐敞棚吉普车进入体育场的,并且绕场一周接受崇拜者们疯狂的敬意。那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接受红卫兵朝觐的场面。在全中国只允许一个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存在的年代,罗广斌在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娃娃中煽起的偶像崇拜,实在有点离谱。”㉜尽管那些娃娃们并不知道,罗广斌的冒失举动完全出于无奈:他在拉肚子,为赶时间,临时搭乘了一辆敞棚吉普车,机缘巧合地剽窃了惟一一个教育家才该有的做派㉝。但毫无疑问,是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给他带来的巨大荣誉,才造就了离谱的事情的发生。
罗广斌是在他家的世交马识途的带领下,在西南联大附中参加学生运动并从此走向革命道路的。1966年11月27日,他显然是“把他在西南联大搞学生运动的方法搬到文革中来了”㉞。但罗广斌揭竿而起的目的是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就像当年在秀山、在白公馆是为了听从毛泽东的教育理念、向教育理念奉献新式孝道一样㉟。他认定他的对立面重庆市委以及重庆市委的上级领导(比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已经完全陷入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潭,作为党史小说的主要作者,他自认为比其他人更有义务参与到打倒当权派的造反运动中去。这是对即兴色彩的灵感大发发出的坚定和声,也是对小说《红岩》中凝结的价值的意义倾向性的无限放大。
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遵照同一个革命话语的教诲,基本上是站在市委一边的四个群众组织(即所谓的保皇四军㊱)试图向造反派反扑。在山城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保皇四军的战士们像今天的假药贩子和伪文凭兜售者一样四处散发传单,扬言要在1966年12月4日,在罗广斌乘坐敞棚吉普车绕场一周的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㊲。“消息既出,重庆造反派和外地赴渝的红卫兵便认定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坚决对其造反。”㊳所有的造反派都依据革命话语的即兴色彩,所有的造反派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这无疑是人类阐释学历史上较少遇见的极端时刻,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屡见不鲜。
那个注定会将罗广斌拖入更深的悲剧的日子终于来临。12月4日上午,大田湾体育场人山人海。被雾气遮蔽的太阳投下了潮湿、阴霾的光线,两派之间的冲突趁太阳眨眼的间歇已经全面展开。罗广斌的盟友、以重庆大学学生为主的造反派815派率先攻上保皇四军的主席台;815派的头目强行要求发言,却遭到保皇四军主持人的坚决拒绝。几经推搡,815派的头目被保皇四军的纠察人员推到台下㊴。准备前来捣乱,早已先期进入会场的815成员趁机摇动旗幡,说保皇四军动用武力,反对革命派造反。“主席台上的冲突一开始,被阻隔在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便如狂潮急浪一般向水泄不通的体育场发起拼死冲击:混战就此开始。台上台下数万群众,开始是喊叫、谩骂、吐口水,马上升级为推搡、为扭扯、为撕打。拳头不够,旗杆、标语牌、脱出的鞋子、地上的砖头,统统成了武器,于是满场喧嚣,满场哭喊,满场血腥。……接着双方始而辩论,接着就‘暴徒’、‘土匪’、‘滚出去’地骂开了。”㊵作为反动堡垒的主席台很快被815派全面占领;司令部被端,保皇四军顿时溃不成军,丢下一地狼藉的断旗杆、碎红旗、标语牌、鞋子、帽子,仓皇逃窜。造反派迅速占领会场,继而很快把整个城市都占领了——比当年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还要干净、简单和利索。在这次冲突中,作为胜利的必要代价,以815为代表的造反派一方受伤人数达200余人㊶。到这天晚上,另一个重大消息接踵而至:造反派中有数人被保皇四军送上奈何桥,此刻他们正在惨淡的桥上倾听狂风发出的凄厉呼声㊷。
尽管这一天罗广斌并没有亲临现场,但有证据表明,他一直在幕后指挥㊸。这一天过去后,他即将再次走到前台,只因为12·4惨案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借口,活学活用革命话语即兴色彩的罗广斌以及他的造反派同仁必须死死揪住这个昂贵的由头,把战火引向更高迈的境界。(未完待续)
【注释】
①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9页。
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内部发行,1966年,第1-2页。
③《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内部发行,1966年,第5-6页。
④罗广斌致张羽信,1962年5月14日,手稿复印件。
⑤参阅空军政治部歌剧团整理供给《江青企图扼杀歌剧〈江姐〉的言行》(1977年4月1日),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江姐〉专集》,1980年,内部发行,第126页;参阅耿耿《江青插手歌剧〈江姐〉内幕》,《人物传记》1999年第2期。
⑥《(江青)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编辑部编《江青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汇编》,1967年10月,第43页。
⑦参阅杨益言《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红岩战报》第1期(1967年4月15日)。
⑧参阅张羽《我与〈红岩〉》未删稿,手稿复印件。
⑨参阅穆欣《“国防文学”是王明机会主义的口号》,《光明日报》1966年7月7日。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任白戈是‘大黑帮’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的字样。
⑩1962年4月16日,罗广斌在致马识途的信(手稿复印件)中,赞扬马识途:在《红岩》的写作过程中,“不仅有你的心血,设计和构思,还有着你多年的关切、担心、喜悦、焦虑……没有你的指点,我们不可能沾在蛟高的角度处理这个庞大的题材。”
⑪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文史精华》2000年第8期。
⑫参阅“军工井冈山”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二评山城罗广斌事件》,《军工井冈山》1968年第1期。
⑬杨益言:《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上海交通大学红岩战斗队编《〈红岩〉与罗广斌》第一集,1967年8月,第20-21页。
⑭对照一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在敌对两派中的形象就很说明问题。保罗广斌的一派认为李井泉和任白戈在迫害罗广斌,反罗广斌的一派则认为他们在保罗广斌,都异口同声地说李井泉和任白戈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才会迫害或保护罗广斌。(参阅“文革”时期重庆出版的革命小报《横扫》、《815战报》、《红岩村》等)
⑮其实,连当时中共最高层的许多人都不能准确理解革命话语即兴色彩的新涵义。1966年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在讲话中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头号人物刘少奇“在讲话中更是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新路线: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参阅《坚决将资产阶级司令部打进地狱》,《红岩村》第3期,1968年4月)
⑯参阅“军工井冈山”等《评山城罗广斌事件》,《军工井冈山》1968年第1期。
⑰石化:《说不尽的罗广斌》,《红岩春秋》2000年第1期。
⑱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顺便说一句,周孜仁是重庆著名的815战斗团机关报《815战报》的主要编辑。
⑲参阅“军工井冈山”等《评山城罗广斌事件》,《军工井冈山》1968年第1期。
⑳参阅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罗广斌是周扬反党黑线的走狗》,《山城红卫兵》,第16期,1967年3月1日。
㉑说小说歌颂刘少奇倒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1966年7月15日,距离刘少奇被打倒的时间只能按天来计算了。就在这一天,罗广斌、杨益言写出了揭发萧泽宽的材料,其中有言:“《红岩》的写作,是在我们1956年向市委书记处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后才开始的。”为澄清有关《红岩》中的李敬原是写萧泽宽的问题,他们特别说明:“小说中没牺牲的人物篇幅写得少,多是完全虚构,如对李敬原的描写,他有‘斑白的发丝’,等等,历史上便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中,倒是想按着少奇同志这样白区工作的正确代表写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更多情况)。”(1967年6月24日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战报》刊载原件照片,此处引自何蜀《在创作〈红岩〉的前前后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大事年表》,未刊稿)
㉒引自只有半张复印件的重庆红卫兵小报,报纸和作者以及本文的题目均不可考。
㉓对此何蜀有较为详细的交待:“(1966年)7月22日深夜,牛文找罗广斌谈话,简单地说了两点:一是罗等三人揭发沙汀、马识途、萧泽宽等人的材料和罗等与他们的接触不相称。二是罗等1964年到南京档案馆等抄录敌特材料的记录本,为防在文革期间失密,暂交工作组代为保管。谈话之后,罗、刘分别上交了笔记本,杨益言上交笔记本时问:我还有记录江青同志讲话的本子交不交?工作组答:你觉得该交就交。杨遂将笔记本上交。”(何蜀《在创作〈红岩〉的前前后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大事年表》,未刊稿)
㉔参阅《军工井冈山》编辑部等《评山城罗广斌事件》,红岩村编辑部《批〈红岩〉揪叛徒资料之五》,1968年7月,第5-10页。
㉕重庆市曲艺团说书艺人徐勍在何蜀整理的口述纪实中提供的说法能够印证我们的结论:“(1966年)11月初,一天晚上,听说罗广斌、杨益言把市委工作组牛文他们弄到解放碑台子上去辩论,实为批斗……我没有挤过去看。但我对罗广斌、杨益言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你们这样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公众人物,也来凑什么热闹,造什么反?后来,有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说罗广斌从白公馆出狱的事,一直有人怀疑。市里审查了几次,他自己讲的,和一些特务交待的,大有出入,而他不同时间在各单位作报告时讲的,内容也有出入。因为市委审查他,他就有怨气,认为受了迫害。趁文革之机,就起来造反了。”(何蜀整理《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未刊稿)当年的亲历者,重庆815战斗团的骨干周孜仁先生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十分诚恳地写道:“他(即罗广斌——引者注)一生向往革命,为此不惜背弃优裕的权贵家庭。国民党把他投进黑牢,共产党却对他并不宽容。他曾用横溢的文学才华抗争,成功了,是令人羡慕的巨大成功,但没有丝毫改变尴尬的处境。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儿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第108页)
㉖向东等引自罗广斌当年的战友杨向东的口述,参阅向东《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重庆晚报》2005年5月29日;参阅杨向东1993年6月29日致张羽的信件,手稿复印件。
㉗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5日。
㉘《军工井冈山》编辑部等《评山城罗广斌事件》,红岩村编辑部《批〈红岩〉揪叛徒资料之五》,1968年7月,第2页。
㉙1966年9月以来,罗广斌一直在联合红卫兵造“黑市委”的反,“罗等三人背着工作组拉拢勤杂人员于九月二日成立了红卫兵,张贴了决心书,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人野心勃勃……力图对市委发动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上述引文是当时尚未被打倒的重庆市委对罗广斌的秘密跟踪报告,转引自“军工井冈山”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二评山城罗广斌事件》,《军工井冈山》1968年第1期)差不多与此同时,“黑市委”派出调查组到北京某监狱提审了徐远举,要后者证明罗广斌当年在白公馆的叛变表现。由于徐远举坚持己见,调查组未能如愿。(参阅“军工井冈山”等《关于罗广斌同志的历史——三评山城罗广斌事件》,《军工井冈山》1968年第1期)
㉚参阅何蜀《在创作〈红岩〉的前前后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大事年表》,未刊稿。
㉛何蜀整理《口舌人生中的一段插曲》,未刊稿
㉜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第53页。
㉝参阅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第55页。
㉞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文史精华》2000年第8期。
㉟从等级制度的角度看,上级肯定要驱使下级,下级肯定对上级有意见;从心理学上看,下级在遇到可以合法造上级的反的时刻,私仇以合法的面貌出现去收拾上级的合理性是存在的。(参阅田奇庄《人妖颠倒的1966——我经历的文革回忆片断》,《思想者》2006年第3期)此处不是说罗广斌一定是这种情况,但肯定存在着这种情况,何蜀就持这样的观点。(参阅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文史精华》2000年第8期)
㊱这四个组织包括三个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小兵”、“赤卫军”;一个工人组织:“工人纠察队”。这四个组织被罗广斌们称为“保皇四军”,只因为他们大体上站在市委一边。(参阅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第45页)
㊲参阅首都大专院校赴渝战斗兵团代表发言《妖雾弥漫压山城:向首都革命群众汇报重庆地区资本主义复辟情况》,《红岩战报》第一期,第3页。
㊳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第68页。
㊴815战斗团主要由重庆大学的学生组成,攻上保皇四军主席台的815头目叫周家喻。(参阅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第83页)
㊵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第67页。
㊶参阅何蜀《重庆一二·四事件》,《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12期(总第72辑)。
㊷参阅杨益言《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上海交通大学红岩战斗队编《〈红岩〉与罗广斌》第一集,1967年8月,第22页。
㊸何蜀整理的材料对此有过记载:“12·4早七点,杨益言在办公楼晒台观察。罗、刘在罗家楼上观察。……冲上主席台时,杨、刘由罗派去。11点左右有人来找罗谈大会打死人消息后,罗对杨、刘谈后,杨、刘才去了。杨说:‘到了会场主席台后,才想起抓凶手的。’12·4第一张传单,由罗口授,杨甦(重庆市文联《奔腾》文学双周刊文学评论编辑)记录,但查到了杨山(时为重庆市文联业务组成员)记录稿。上有罗修改笔迹。这传单写的时间,杨甦口头交待是午饭前写的(但二杨对口后改口说午饭后写的)。下午两点开始写大字报的。这原稿上没多大改动,看来罗早已胸有成竹。这传单由好几个单位转抄出去。”(何蜀整理《罗广斌专案组笔记摘选·罗广斌、杨益言在“一二·四”事件前后》,未刊稿)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节选自《事情总会起变化——以中国共产党党史小说〈红岩〉为中心》(秀威出版社,2009年)一书,经敬文东先生授权,内容首次公开在大陆发表。感谢敬文东先生对本刊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