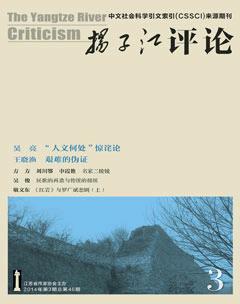艰难的伪证
王晓渔
艰难的伪证
王晓渔
韩少功先生把《革命后记》称作“艰难的证词”,认真读过,深感对之作出评论是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文章中的问题实在太多,几乎每段都有存疑之处,无论在事实还是在逻辑层面,都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地方,如果一一讨论,可能篇幅会比原作多出许多。比如文章用300字讲到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情形,王彬彬先生用了2000多字做了补充①,篇幅是前者的七倍。二是双方辩论空间是高度不对称的,韩少功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远远大于反驳其观点的空间。这里所说的空间不是篇幅,而是指“尺度”。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很多证据无法出示。所以,本文只能“避重就轻”,重点分析这份证词无法自洽之处。
没有“前传”,何来“后记”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关键词,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到共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革命贯穿始终。即使改革开放,也被视为“新的伟大革命”。但是,“革命”又包含着不同的含义,比如辛亥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截然不同。如果放到世界范围内,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也有着根本区别,阿伦特专门撰文分析两者差异②。抽象地讨论“革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讨论者理解的“革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你说革命有暴力,他说有“天鹅绒革命”;你说革命之后有乌托邦,他说革命之后有革革命;你说革命是革天命,他说革命是革人命。
《革命后记》主要聚焦于“文革”,“文革”和革命是什么关系?韩少功以修辞游戏的方式回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表示“文革后记”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革命后/记”,“文革”不属于革命;一种是“革命/后记”,“文革”属于革命。但是,这不等于韩少功没有自己的立场,他没有把题目定为《文革记》,而是命名为暧昧的《革命后记》,正文时常把“文革”视为革命一部分,倾向于“革命/后记”的论述。
革命只有“后记”,没有“前传”。“文革”是如何发生的?《革命后记》很少涉及。30年代的肃反、40年代的整风、50年代的反右,这些革命的“前传”都被略过了。但是,没有“前传”,何来“后记”?“文革”不是在1966年5月16日凭空产生的,有着漫长的演进过程。韩少功在《革命后记》开篇表示,自己的全部记忆仅仅涉及“文革”,“充其量宽延至前后的三十年,即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后半场”。如果《革命后记》是一本回忆录,自然没有问题,可是个人回忆在整篇文章里的篇幅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个人感想,用感想代替记忆,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整篇文章有200多处注释,包括很多历史类著作,内容远远超出了个人回忆的范畴。
最后讨论“革命能否带来公平”时,韩少功以“抒情的必然性”的方式简短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讲到一位老大姐自陈,游击队在黑灯瞎火中常会来睡上一把,但老大姐不觉得这是羞耻。这时,韩少功表示:“在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那年月,拥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怜惜,更像战友之间悲伤的提前诀别。”是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像这位老大姐一样“思想进步”?女性是否有权利反对这种独特的诀别?如果有女性反对,会不会变成“反革命”?在韩少功那里,这些问题似乎不存在。
韩少功接着讲到革命中的很多“污垢”,然后总结:“革命就是狂飙,就是天翻地覆,就是破坏与剥夺,就是不得已的恐怖暴力,也是走投无路之后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必有误伤,必有冤屈,必有污秽,必有凶狠,必有失控和混乱……”这种逻辑把必然性等同于正当性,因为必然发生,所以必须接受。因为随时都可能掉脑袋,所以必须随时睡上一把?必然性是不是虚构的?必然性属实,就等于正当性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就成了“凡是发生过的,都是合理的”。韩少功似乎觉得这样不太妥当,表示“与其说这一切值得夸耀,毋宁说更值得悲悯”。谁来悲悯?需要悲悯的是谁?韩少功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接着写出一段抒情的文字:“正是一种令人泪流满面全身发抖喘不过气来的痛感,才能扩展人们对艰难和悲壮的理解,使致敬一刻像大海那样深广而宁静。”
没有超越的“超越左右”
在《革命后记》中,韩少功似乎采取了超越左右的立场。他对“文革”有称赞也有批评,他批评左右合营“代价公司”,他认为“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个趔趄的连体人,栽进了同一个坑”。“超越左右”是当下思想界难得的共识,但这并未促成不同观点之间的沟通,因为言说者都认为自己是“超越左右”,对方陷入派别之见。“超越左右”成为政治正确,用于自我合法化。
“左”与“右”,是一对错综复杂的概念。在中国的语境里,“左翼”不等于“左派”,“右翼”不等于“右派”。简而言之,“左翼”带有褒义,多指权力的批判者;“左派”属于中性兼有贬义,多指权力的附庸者甚至是主导者;“右翼”带有贬义,多指国家主义者,“右派”属于中性兼有褒义,多指持不同意见者。
韩少功使用褒义的“左翼”和贬义的“右翼”,讲到“左”多为“左翼”如何,讲到“右”则是“右翼”如何,这一词语的选择已经说明了他的立场。“左翼”的命名将“左”正当化,“右翼”的命名将“右”污名化,“超越左右”只是占据道德高地。这样说像是绕口令,不妨以《革命后记》为例。韩少功指出,称赞“文革”的一方怀念当年的“平等”,批评“文革”的一方斥责当年的“平均主义”,“双方大体上确认了当年的一种‘平’”,所以是“双头的连体人”。这个逻辑非常奇怪,仿佛只要有了“平”字,不管双方理解的“平”是不是有差异,不管双方对“平”持何种态度,双方都是一样的。于是,反对“平均主义”,被等同为反对“平等”。这是“超越左右”吗?
“平等”和“平均主义”不能完全等同,即使同样冠以“平等”之名,也存在根本差异。孟德斯鸠说过:“在共和政体下,人人平等;在专制政体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就是一切;在专制政体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为人一钱不值。”③在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④批评“文革”的“平均主义”,正是批评那种人人接受奴役的平等,批评“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的平等。批评者认为“文革”是“平均主义”,与称赞者认为“文革”是平等的乌托邦,两种观点截然不同,韩少功却将两者混同起来。
在韩少功那里,毛泽东“鼓励学生闹事和工人夺权,容许造反派自由结社、散传单、烧档案、封报馆、扛机枪、占领官府大楼、全国免费大串联”,被称为“零障碍和无限度的‘民主’和‘自由’”。他表示:“一个西方记者如果此时在中国人面前说教‘民权’,肯定觉得自己班门弄斧。”韩少功使用的“鼓励”和“容许”两词,已经说明那些行为只是“奉旨造反”,与“民主”、“自由”、“民权”没有关系。但韩少功把“奉旨造反”等同为“民主”、“自由”、“民权”,成功地把后者污名化。
韩少功表示,“把‘平等’污名化”,某些知识精英“比黑道走得更远”。他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若不是缺少一种属于自己的人渣辞典,那就是他们经常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对自己找不到北。”不知这个说法是否适用于“把‘民主’、‘自由’、‘民权’污名化”的某些知识精英?我所关心的是,“把‘平等’污名化”的主要是谁?是某些知识精英,还是那种以“平等”之名建造等级金字塔的乌托邦实践?
选择性记忆
与其他赞美“文革”者不同的是,韩少功对“文革”有称赞亦有批评,经常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叙述模式。把一个已经被否定的对象改写成“理性中立客观”的五五开,这是最为高明的辩护方式。
韩少功这样讲述“‘文革学’不大提及的一面”:“一方面是暴虐,一方面却不乏热情、爽朗、忠厚甚至纯洁——至少就大多数人而言,与通常的土匪、黑帮、军阀、占领军、绿林乱党不同,他们的暴力与物质利益毫不相干。即便在暴尸街头之际,也鲜有人哄抢商店、打劫银行、收取保护费、轮奸妇女、绑票勒索、吃饭不给钱、瓜分古董与金条等抄家所得……这些案情哪怕在当今对‘文革’最大规模的揭露之下也极为罕见,几乎闻所未闻。”
“即便在暴尸街头之际,也鲜有如何如何”,这种句式让人读得心惊胆战,“暴尸街头”这种恐怖的景象在“即便”之下,变得无足轻重。这里暂且不去引用历史文献,一一列举韩少功笔下“乌托邦”的虚幻,韩少功自己提供了反证。他讲到自己认识的一位姑娘,揣着五块钱出门,两个月后回来,夸耀衣袋里还有七块。“吃饭不给钱”在串联中非常常见,韩少功为何“几乎闻所未闻”?或许,在他看来,不是“吃饭不给钱”,而是“吃饭不要钱”。“吃饭不给钱”是道德败坏,“吃饭不要钱”说明社会风气良好。至于经济学常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韩少功是不用考虑的。那位姑娘的两块钱来自何处?韩少功说,“不是借自沿途的红卫兵接待站,就是来自好心人的捐助”。那位姑娘后来有没有归还红卫兵接待站的借款?韩少功没说。
对于自己描述的“乌托邦”,韩少功也觉得过于绝对,补充说,“当然,抢军帽或撬单车或有所闻,极少数人渣趁火打劫一类也不能排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通过“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场灾难被描述成五五开,又通过“大多数人……,极少数人渣……”,五五开又变成了三七开,三分“人渣”,七分美好。在韩少功的描述下,“大多数中国工人在‘文革’中就受害较少,他们享受‘领导阶级’的地位优越”、工人和农民“一般没有挨批斗的经历,没有下放和挨打的皮肉之苦,一直活在政治安全区”。此前的三年大饥荒呢?此后农民为何又要冒着坐牢危险私自签署包干协议?
韩少功表示自己“无意粉饰什么,只是指证圣徒化与警察化的一样阴阳脸”。如果像阿伦特那样探讨“平庸的恶”,可以弥补反思“文革”中的不足。但是,《革命后记》呈现出的景象,更像是利季娅笔下的苏联:在1960年代,“报上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斯大林的地方越来越多。比如,当然,斯大林处决了很多无辜的老布尔什维克,但他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就像,’一次阿赫玛托娃说,‘承认他是吃人的恶魔,但口琴吹得好。’)”⑤
韩少功反对对“文革”的“宫廷化”、“道德化”和“诉苦化”。我同意这些观点,赞同更多从制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但在《革命后记》中,不乏称赞好人好事的“宫廷化”,也不乏动辄痛斥“人渣”(不仅趁火打劫者被视为“人渣”,与韩少功观点不同者也被视为“人渣”)的“道德化”,更不乏对美国的“诉苦化”。韩少功认为从“离婚、薪水、疾病、稿费、房产、后人吃啥喝啥”讨论领袖没有意义,是“长舌妇和民间神探”,但在讨论大饥荒时,他却引用了一段“据说”:“据说,正是在这一年的某日,毛泽东在卫兵面前失声痛哭,决定不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直到自己患上水肿病,一年后瘦了十多斤。”记载与之不同的《毛泽东遗物事典》⑥,却被略过了。这让人怀疑,韩少功反对的只是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
类似的选择性记忆比比皆是,以致韩少功并不讳言“选择性记忆”。他讲到现场观看中央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的情形,“鼓掌者们在久违的温暖前梦醒,在一种卑贱者解放的绚丽天地里晕眩和飘飞”。他对样板戏的造神宣传和革命图标化一笔带过,然后说:“这些观众面对悲怆的乐浪,激越的旗帜,纯洁无辜的手足,普天下人人平等的阳光造型,就没有一次热泪盈眶的权利?”最后,他说,“哪怕它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可是针对知识分子们对“文革”的回忆,韩少功又说:“他们要做的是理解、沟通、说服以及协调共进,不是强加于人和视而不见,满足于悲情的自产自销,成为另一个祥林嫂。”既然是“悲情的自产自销”,又怎么是“强加于人”?
在韩少功的选择性记忆里,“文革”前夕,美国水深火热,“夜不闭户和路不拾遗在中国很多地方却成为寻常”。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听起来很美好,有时却是家徒四壁、路有饿殍的代名词。
反西方的西方中心
美国(以及“西方”),是韩少功的心结。在讲述“文革”为主的《革命后记》里,美国出现的次数几乎不亚于中国。对“文革”作全面辩护是困难的,韩少功放弃了这个打算,而是表示“文革”有错,但美国也有错。
讲到“文革”禁区,韩少功称“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敲槌禁声”,理由是美国以法案方式搁置“抽屉问题”,欧洲在种族、排犹主义上“封杀异议,绝无自由”。韩少功认为“文革”与冷战对手形成同构,“差不多就是美国麦卡锡运动的镜像,一种逆向的高倍数放大”。他称欧罗巴人曾经参加烧死女巫的起哄,为何不能理解中国“文革”中的双重人格?韩少功还批评美国电子监听大网“闹得四面八方都隔墙有耳”,质疑“美国的‘大脚侦缉队’是不是也要挨门查户口”。在他看来,美国和英国在三四十年代严打金融自由和厉行计划分配,几乎是上门打劫神圣私产;媒体市场化和“水军帖”一样,“一手遮天并无太大区别”;在美国惹恼非裔或犹太裔,“警察立马拎着手铐上门”。中国那些要死要活献身革命者,“一般来说并无枪口威逼,不是迫于美国那样世界上最大的警察队伍、最多的监禁场所、最昂贵的司法开支”。韩少功还列出这么一组数字:美国因为枪支管控不力导致的死亡率“接近两个‘文革’”,陷入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希腊自杀率“远超‘文革’”,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竟是‘文革’的数十倍”……
这些描述有太多歧义。禁止讨论“文革”与反对种族歧视是一回事?这就像莫言先生把言论审查和机场安检等同视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上出现过错误,就意味着他们要理解这个错误?美国有户籍制度和居委会?大脚侦缉队挨门查户口从何说起?政府介入市场,就是“上门打劫私有产权”?美国警察拎着手铐上门之前,需要哪些程序?中国没有发生过“反右”?“文革”中“受害者”的死亡率可以等同于其他死亡率?
韩少功的这些观点似乎是在“反西方”,却又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因为西方也有问题,所以“文革”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反西方的西方中心”经常表现为两种形式:当有人主张学习西方之长处,他会说西方也有短处;当有人说中国有问题,他会说西方也有问题。比起“以西方之是为是”,这种“以西方之非为是”是更为隐蔽也更为彻底的“西方中心”。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反西方”思潮常常来自西方,是西方自我反思的产物。可是,韩少功把“他者的内部反思”当做“批评他者的武器”。这就像那个著名的笑话,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批评美国总统,苏联人说,这有什么,我们也可以批评美国总统。
韩少功讲述了自己访问西方国家的创伤记忆,入境处移民局官员查验了他的护照、签证、访问邀请书、旅馆预订信息之后,然后问:“有钱吗?给我看看。”韩少功感到自己受到歧视,深感屈辱,从此明白:“一条入境闸口黄线分割的,不仅有不同制度,还有富与穷、贵与贱、高等物种与低等物种、掏得出绿票子与掏不出绿票子的。富国不是雷锋,也没义务当集体雷锋,对数以亿计的穷棒子展开臂膀微笑热拥。”
韩少功与移民局官员的分歧,究竟由何而生,我无法确定。读到这段,我想起自己入境某西方国家时,入境处官员查验过一系列证照之后,也问过携带多少现金。我当时没有联想到自己被歧视,也没有想到这与“富与穷、贵与贱、高等物种与低等物种、掏得出绿票子与掏不出绿票子”有什么关系,只是告诉对方携带的现金在不申报的金额范围之内,就过关了。
虽然过关没有遇到问题,但我从来就没有认为富国都是雷锋,也不会把西方国家视为“民主乌托邦”。民主从来没有宣称自己是乌托邦。民主的优点不在于它是完美的,而是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因而建立“纠错”机制。民主不是“人人都是雷锋”,也不是“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种理想国的景象只能出现在严厉的思想改造之后。韩少功的“创伤记忆”,说明他此前对于“西方”和“民主”有着乌托邦的想象,以至于一旦在现实中面对任何“不完美”之处,价值体系立即走向过去的反面。
与“反西方的西方中心”相似,这是一种“反民主的民主乌托邦”:先把民主认定为乌托邦,一旦民主出现任何问题,就得出“反民主”的结论。乌托邦思维却是自始自终没有放弃的,韩少功认为五七指示“描绘出一幅比《礼运篇》更为具体和清晰的图景”,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美好前景”,“不幸的是,多年后人们觉得这些说法日益飘渺”。为何有着那么美好的蓝图,现实中却有着那么多的灾难?蓝图与灾难是什么关系?谈到灾难就是悲情,就是只讲到一方面没讲到另一方面,就是缺乏深入反思?
韩少功引用萨缪尔森的“合成谬误”,指出某种在微观上看来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反之亦然。这种提醒非常必要。如果说《革命后记》有什么价值,那就是它从各个可能的角度试图为“文革”做出一份“艰难的伪证”,这份“伪证”因为逼真具有了精神病理学样本的价值。
我并不赞同“告别革命”论,但革命如何被激活?需要激活的是哪种革命?革命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革命后记》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注释】
①王彬彬:《替韩少功补个注释》,《南方都市报》2014年5月25日。
②[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3页。
④[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董乐山、傅惟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页。
⑤[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蓝英年、徐振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⑥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