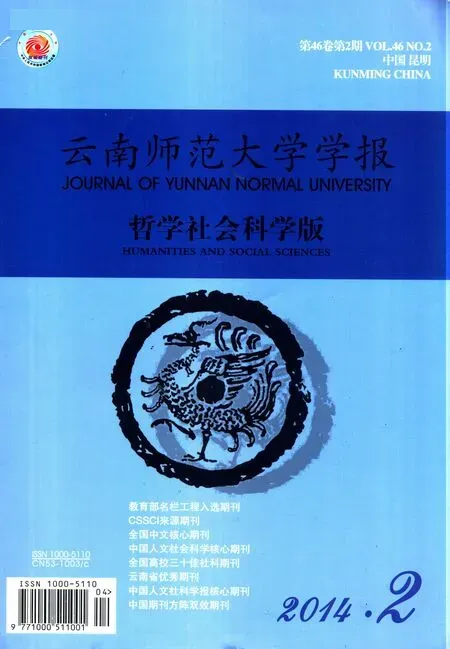福建汉语方言地理分布和内部关系*1
张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福建汉语方言地理分布和内部关系*1
张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福建省境内的汉语方言主要是闽语和客家话。这是两种不同的方言,但也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闽语是境内使用人口最多,通行范围最广的方言,内部有很多一致性,但内部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其中南北闽语的差别大于东西闽语的差别。这种语言特征一致性和差别性交错分布,使福建省的汉语方言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
福建;方言;闽语;客家话;纷繁复杂
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简称闽。全省总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根据福建省统计局2003年公布的数字,全省总人口3,409万人,其中汉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99%以上,还有畲、回、满、蒙、高山族等31个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不到1%。少数民族人口中,以畲族占多数,约23万人。
福建全省通用汉语方言。主要的少数民族畲族日常所说的畲话也是一种汉语方言。除了西北部的泰宁、建宁两县约28万人说赣语,北部浦城部分乡镇约27万人说吴语,以及一些属于官话的方言岛、移民点方言(如南平城关土官话、长乐琴江村京都话、武平中山军家话等)以外,全省通行的汉语主要方言是闽语和客家话,其中尤其以闽语为最主要。从方言的种类来说,福建省境内的方言并不算复杂。平时很多人认为福建话难听难懂,戏称为“南蛮鴃舌”,主要是由于闽语本身的一些特点,以及闽语内部的分歧所造成的一种印象。
一、福建省的闽语和客家话
(一)闽语是汉语最主要的方言之一,除分布在福建省外,还集中分布在台湾、海南、广东、浙江、广西等省区。所以,闽语虽以福建省的简称“闽”命名,但闽语不等于福建话,福建话也不等于就是闽语。不过,闽语主要分布于福建省,是省内通行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个大方言,使用人数将近2,800多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90%以上。根据闽语内部的差异,我们把福建境内的闽语分为6个方言片。[1]
(1)闽南片 主要分布于福建省南部厦门、漳州、泉州,以及周围的34个市县,使用人口约1,325万人。

(2)莆仙片 主要分布于福建省东部沿海莆田、仙游两个市县,以及周边市县的一些乡镇,使用人口约250万人
(3)闽东片 主要分布于福建省东北部福州、福清、福安,以及周围的19个市县,使用人口约1,000万人。
(4)闽北片 主要分布于福建省北部南平、建瓯、建阳等8个市县,使用人口约250万人。
(5)闽中片 主要分布于福建省中部三明、永安、沙县等3个市县,使用人口约70万人。
(6)邵将片 主要分布于福建省西北部邵武、将乐、顺昌等5个市县,使用人数约85万人。
(二)客家话也是汉语最主要的方言之一,除分布于福建省外,还集中分布于江西、广东、台湾、广西、湖南等省区,四川和海南境内也分布着很多客家方言点。客家话是福建省境内通行的第二个大方言,主要分布在福建省西部地区的长汀、永定、武平、上杭、连城、宁化等12个市县,称为客家话区的汀州片,使用人口约480万人。
以上方言的地理分布,请详见《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B3-5之“福建省的汉语方言”图。[2]
(三)福建省境内闽语和客家话的关系。从“福建省的汉语方言”图可以看出,戴云山脉位于福建中部,纵贯南北。其东部沿海平原地带是具有显著闽语特点的地区,西部山地丘陵地带是具有显著客家话特点的地区,中部山区地带是具有某些客家话成分的闽语地区。从东往西看,闽语的成分逐渐减少,客家话的成分逐渐增多;从西往东看,客家话的成分逐渐减少,闽语的成分逐渐增多。
福建省境内的闽语和客家话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在语音和词汇上,确实有不少共同的地方。罗杰瑞直截了当地说:“客家话和闽语很接近,如果不是同一个来源,就不好解释。”并且指出,闽、客方言至少有三方面的共同特点:
(1)中古舌上音,闽语仍读舌头音,客家话也有这种遗迹。
(2)边音鼻音很多字,都读阴调类。
(3) 闽、客方言有一些共同用词。[3]
我们下面可以进一步论证。例如:
(1)声母方面,古非组字,闽语与客家话都有读重唇声母[p- ph-]的。如“放”客家话的长汀读[pi54],闽语的厦门读[pa21]。
(2)韵母方面,闽语(特别是其中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基本保留着中古[-m -n -]三套鼻音韵尾和[-p -t -k]三套入声韵尾的格局。
(3)声调方面,闽语和客家话都保留入声声调,并且根据古清浊声母分入声为阴阳两个调类。
(4)词语方面,有不少基本词语,闽语与客家话也是相同的。例如:

瓯(小杯子)岫(巢穴)喙(嘴巴)衫(衣服)鸡僆(小母鸡)新妇(媳)徛(站)长汀话33s21tue54sa33te33lu54se33phe33thi33厦门话au44siu22tshui21sa44kue44nua22sim44pu22khia22
没有,多数闽语和客家话都是阳平调,字形上从俗写作“无”或“冇”,其共同来历,当是古开口一等豪韵明母字。有学者认为,其本字是“毛”,《汉书》有“饥者毛食,寒者毛衣”句,可作参考。
吃(饭),除了建瓯以外,闽语和客家话都说“食”,有的地方直接写作训读字“吃”。
滴(水),闽语和客家话都说“滴”,见于《广韵》入声锡韵都历切:“水滴也。”闽语和客家话表示数量少,一点儿也说“滴”或“一滴仔”。
鼻子,这个“鼻”字汉语方言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广韵》去声至韵的“毗至切”,另一个是见于入声的“以鼻为弼”。闽语和客家话都是来源于去声的“毗至切”。闽语多数地点读阳去,少数地点读阴去;客家话有的也读阴平调,符合古全浊声母去声字可以读阴平的古今语音演变规律。
还有,把包袱解开说“敨”,把两件东西对接起来说“鬥”等很多基本词语,闽语和客家话也都是相同的。这一类例子多了。
语法方面,闽语和客家话都有“有”字句。口语里“我有食饭”,“他有去北京”这一类句子是常说的。
但是闽语和客家话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方言,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以下例举几条。
(1)古全浊声母字,如“盘饭同郑穷皮贼糖伴”等,闽语不论平声仄声,今声母多数读不送气的清塞音或塞擦音(“盘饭同郑穷”),少数读送气的清塞音或塞擦音(“皮贼糖伴”);客家话不论平声仄声,今声母多数读送气的清塞音或塞擦音,只有个别字例外,如“渠(他)”都说不送气的[-]。
(2)古非敷奉及晓匣母的合口字,如“飞分翻符扶,灰化胡祸”等,闽语文读今声母都读[-]或[-];客家话文读今声母绝大多数都读[-]。一般说来,闽语是没有[-]类声母的。
(3)古知徹澄三母字,如“猪竹张,超抽畅,池陈虫”等,闽语白读今声母是[--],跟古端透定三母字的今声母相同。客家话这些字今声母一般读[--]或[--],跟古端透定三母字今声母[--]不相同。
(4)一部分古匣母字,如“行猴含糊”等,闽语白读今声母是[-]。另有一部分匣母字,如 “话学鞋闲”等,闽语白读今声母是[-]。以上两部分字,客家开口字(“猴含”等)通常读[-],合口字(“糊话”等)通常读[-]。
(6)一些基本用词也不相同。例如闽语稻籽的植株都说“粙”,稻子的籽实都说“粟”,籽实脱壳后都说“米”,是“粙粟米”三分;客家话稻子的植株都说“禾”,稻子的籽实都说“谷”,籽实脱壳后才说“米”,是“禾谷米”三分。
二、闽语内部的统一性和分歧性
就福建境内的闽语而言,有很大的一致性,也有显著的差异性。这种一致性和差异性是相伴相随的,表现了闽语的重要特征。
(一)先说闽语的一致性,就是它的共性
闽语有很多共性。例如黄典诚先生曾提出8条语音和35个常用词语标准,可以鉴别闽语。[4]其他学者也提出过一些标准可以参看。这些标准说的都是闽语的共性。其实,仔细想起来,只要两条,就可以概括闽语的共性,也可以作为鉴别闽语的标准。
(1)罗杰瑞根据闽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读为不送气清音,少数读为送气清音的事实,提出假如某个方言“啼~哭头糖叠”四字读送气清音[],“蹄铜弟断豆脰项脰:脖子袋毒”八字读不送气清音[],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只要略微加以某种说明,这12个特征字确实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语音标准。
(2)我们仔细比较研究了闽语的口语常用词语,可以再提出“囝,厝,鼎”三条,作为闽语方言词汇的共同特征。以下比较闽东片福州、闽南片厦门、闽北片建瓯、闽中片永安等四处方言这三个常用词的读法[5]:

福州厦门建瓯永安囝厝鼎
这是三个通行闽语各地方言的极常用口语词。从现有调查资料来看,“囝”不见于其他汉语方言,是闽语方言严式特征词。“厝”虽然见于湖南新化,以及湘粤桂交界地区的平话土话,“鼎”虽然也见于江西于都、南昌等地方言,但语义上和闽语方言的用法有明显距离,是闽语方言的宽式特征词。这些特征词可以成为判别闽语和非闽语的最重要根据之一。当然,闽语的特征词不止这三个,还可以找出另外的特征词。例如闽语各地方言管脚叫“骹”,《广韵》又作“跤”,肴韵口交切:“胫骨近足细处”,汉语其他方言都叫“脚”。从语音上来说,“咬”字可能也是闽语的特征词。“咬”字又作“齩”,汉语方言中包括官话、吴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都来自《广韵》上声巧韵“五巧切”,是一个古疑母字。但闽语跟其他方言不同,都来自《集韵》上声巧韵“下巧切”,是一个古匣母字。
有的时候,反证也可以用来说明某一种方言的共同性。例如,《广韵》屋韵丁木切:“豚,尾下竅也。 ,俗。”《集韵》都木切:“豚,博雅‘臀也’,或作 ,俗作 。”这个字的用法几乎见于除了闽语外的所有方言区,表示底部、臀部、剩余的部分(如烟头等),但好像不见于闽语。这是一个反证的例子。
(二)再说闽语的分歧性,就是它的差异
其中有东西的差别,还有南北的差别。总起来说,南北的差别大于东西的差别,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曾经是作为两个独立的方言区的。以下分别加以简要的说明。
(1)首先说说东西差异。福建境内东西闽语大致以南北走向的戴云山脉为界线。戴云山脉东侧直至沿海平原闽南、莆仙、闽东三区为东部闽语,有的学者称为海岸闽语;戴云山西侧以及北端闽中、闽北、邵将三区为西部闽语。东部闽语与西部闽语有明显差别。
①从语音上看,东部三区闽语的声母都符合典型闽语“十五音”系统。这是从早期的《戚林八音》,以及《彚音妙悟》和《雅俗通十五音》的声母系统传承下来的。恰恰在这一点上,西部闽语受到客家话等其他方言的影响,突破了典型闽语的“十五音”系统。例如沙县、永安一带,古精庄章三组字分化为舌尖前音[]和舌叶音[]两套声母,古精组字都读[],古庄章组字主要读[]。古精庄章组字今声母的分化,对汉语方言来说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不可小看其价值。

露卵螺鳞笠永安沙县建瓯松溪
这种边音声母擦音化的变化,东部闽语现在还没有记录。其他汉语方言也还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报告。这种语音演变的特殊现象,曾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
③从词汇上看,一些口语常用词也有很明显的差别。例如“他(单数第三人称)、人、猪、泥土、雾、说话”等6个口语词,东部闽语福州、莆田、厦门等地分别说“伊、农、猪、塗、雾、讲话”,而西部闽语永安、沙县、建瓯等地分别说“渠、人、豨、泥、露、话事”。请注意:以上比较条目中,东部闽语管人叫“农”,是典型闽语的说法,来历久远。[6]西部闽语管猪叫“豨”见《方言》卷八,又《广韵》上声尾韵虚岂切:“楚人呼猪”,用法历史也很悠久。由此可见,东西闽语的这种分歧,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2)其次再来说说南北差异。假设从莆仙地区经永春、大田、永安一带从东到西划一条闽语的南北界线,界线以北包括闽江流域一带为闽北,界线以南晋江、九龙江流域一带为闽南。那么从南往北看,方言的韵母数目逐渐减少,例如厦门话韵母多达82个,(再往南的广东潮阳话韵母竟达90多个),往北走古田话的韵母是47个,福州话的韵母如果不计“松紧音”的差别也才48个,而建瓯话的韵母竟少到只有34个。从北往南看,方言的韵母种类越来越繁复。以辅音韵母为例,北部除了宁德、周宁等少数方言点有[---]和[---]等辅音尾韵母外,多数方言点只有[-]和[-]尾韵母,而建瓯、松溪、建阳等方言点只有[-]韵尾。往南走一进入闽南方言区的地界,永春,泉州一线,[---]和[---]等辅音韵尾俱全。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比较方法,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南北闽语的显著分歧。
下面以闽东片的福州话,闽南片的厦门话为例,选取几条最主要的语言特征,进一步讨论闽语的南北分歧。
②福州话韵母有“松音”与“紧音”之别。阴平、阳平、上声、阳入跟紧音韵母相配,阴去、阳去、阴入跟松音韵母相配。这是韵母和声调之间的一种成系统的、整齐的搭配关系。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其他的汉语方言里,具有这种特殊搭配关系的方言是很少的。我们知道,厦门话韵母也是没有这种搭配的。
③福州话多音节连读,后字声母常发生有规律的音变,它的变化往往为前一音节韵母(特别是韵尾)所决定。这是福州话里一种很复杂的声母类化现象。厦门话没有类似明显的变化,但厦门话频繁而有规则的变调现象,以及非常复杂的文白异读系统,却是福州话所望尘莫及的。
④福州话和厦门话一些口语常用词不一样。据陈章太、李如龙举例如下:[7]

道路衣裳眼镜书本(味)香福州墿衣裳 眼镜 书香厦门路衫裤目镜册芳
以上福州话的特征在北部闽语有一定代表性,厦门话的特征则几乎可以代表南部的所有闽语。由于这些特征分歧造成的差异,使得福州人和厦门人如果都说自己的方言,他们几乎是不能互相通话的。假如以是否能够互相通话为标准,闽北话与闽南语确实可以看成两个不同的方言。
三、闽南话的分布内部关系特点
就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来说,闽南话是福建境内最重要的闽语方言。上文所说闽语还集中分布在台湾、海南、广东、浙江、广西等省区,其实主要指的也是闽南话。例如,台湾省内除了西北部苗栗、桃园等少数地方比较集中分布有客家方言之外,其他市县几乎都通行闽南话,使用客家话和台湾少数民族语言的居民,大多也通晓闽南话。据统计,能够使用闽南话的人口多达2000来万人,大约占台湾全省人口总数的90%以上。广东省东部汕头、潮州、潮阳等12个市县将近1000来万人口,几乎也都通行闽南话。海南省境内主要通行海南闽语,也称琼文片闽语,就其主要特征来说,也很接近闽南话。港澳地区说闽南话的人也很多。不仅如此,闽南话甚至远涉重洋传播到东南亚及南洋诸岛各国,以及世界许多地方。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省界、走出国门的汉语方言了。初步估计,现在中国境内外说闽南方言的人口至少在6000万人以上。[8]就海外使用人口与影响力来说,能够与闽南话相比较的汉语方言,大概只有粤语。
闽南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但也略有分歧,例如广东东部潮汕一带和福建南部厦门一带的闽南话能感觉到明显的口音差别。最明显的是阳平调调值很不一样:“皮平台糖门民”等字潮汕一带一般都读高平调值,而厦门一带一般都读低平调值。就是福建南部一带的闽南话里,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的口音也稍有不同。不过,无论怎么说,闽南方言内部的一致性是最主要的。分布于中国境内外的所有闽南话,互相通话几乎没有困难。其中尤以福建、台湾两省闽南话的一致性为最大。对于非闽南话的说话者来说,他们很难觉察福建和台湾两地闽南话的差别。所以W.W.Compell(甘为霖)1913年编纂《厦门音新字典》的时候,语料取材于台南,词典冠名却是厦门,说明100年前厦门话跟台南话就是分不出多少差别的。100年后的今天,这种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多少变化。[8]方言高度一致性的事实,有力地证实了闽台两地“语同声,文同种”的至亲关系。
[1] 周长楫.福建省的汉语方言[A].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文字说明)[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 熊正辉,张振兴,黄行等.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 罗杰瑞.张惠英译.汉语概说[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4] 黄典诚.闽语的特征[J].方言,1984,(3).
[5] 张振兴.闽语及其周边方言[J].方言,2000,(1).
[6] 黄典诚.闽语人字的本字[J].方言,1980,(4).
[7]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8] 周长楫.闽南方言大词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黄龙光]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ZHANG Zhen-xing
(InstituteofLinguistic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The main Chinese dialects in Fujian Province of China are Min dialect and Kejia dialect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Min dialect is the most popular one but it falls into different sub-dialects, of which Northern Min dialect and Southern Min dialect show greater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other than Eastern Min dialect and Western dialect. The linguistic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renders Chinese dialects in Fujian Province complicated features.
Fujian Province; dialect; Min dialect; Kejia dialect; complicated
2013-12-10
张振兴(1941—),男,广东汕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
H17
A
1000-5110(2014)02-0049-06
——以常用量词用法比较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