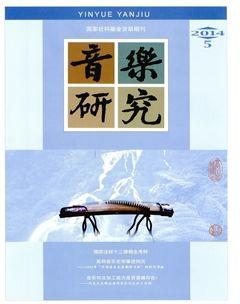儒家注经十二律相生考辩
陈克秀
在《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未出土前,先秦有关记述十二律相生之法的传世文献,仅《吕氏春秋·音律》一则。而明列十二律相生之假数的传世文献,都出于两汉。这其中,首为《淮南子·天文训》;再,即为《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它们均出自杂家著述,或史家记载。
儒家涉足十二律相生之数理,当从郑玄开始,与《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律书》比较,已经是相当之晚。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后作注,出十二律相生之法及律数。自此,十二律相生之法便开始出现在儒家经籍、儒者说乐律等等的著述之中,中国乐律学史上的一些矛盾、混乱亦随之而产生。仅以“郑玄《周礼·大师》注”言,就出现了一注而各有其说的四个“郑玄《周礼·大师》注”,即《汉魏古注十三经》之“郑玄《周礼·大师》注”;郑玄注、孑L颖达疏《礼记·月令》孔颖达所出之“郑玄《周礼·大师》注”;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二十年》孔颖达所出之“郑玄《周礼·大师》注”;《唐宋注疏十三经》之“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大师》注”。这些“郑玄《周礼·大师》注”,生律起始,都是黄钟下生林钟,但蕤宾生大吕,则有“蕤宾下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大吕重下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上生大吕”(蕤宾重上生)、“蕤宾下生大吕”之分别。此况既令后世目眩,又为各取所需凭添口实。特别是近世学者,有取其一而无视其二者,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不一而足。
笔者撰写本文,就期冀以儒家注经为考索,比照杂家著述、史家记载、出土文献,考辩矛盾之根源、诠释混乱之渊薮,理清乐律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基本情况。
一、郑玄《周礼·大师》本注
“郑玄《周礼·大师》本注”,笔者之所以作如此称谓,一是由于其出自《汉魏古注十三经》之郑玄注《周礼》,版本最早,仅有郑玄作注,而无其他人作疏;再,即为区别于另外的三个“郑玄《周礼·大师》注”。
“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云:
黄钟初九也,下生林钟之初六,林钟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应钟之六三,应钟又上生蕤宾之九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下生夷则之九五,夷则又上生夹钟之六五,夹钟又下生无射之上九,无射又上生中吕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异位者象子母,所谓律娶妻而吕生子也。黄钟长九寸,其实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终矣。
将《易》乾六爻,坤六爻,与六律六吕相比附,此属汉儒经师首创。“黄钟九寸,其实一籥”,《汉书·律历志》云:“度者……本起于黄钟之长。”“量者……本起于黄钟之籥。”“权者……本起于黄钟之重。”这里仅言“九寸”、“一筲”,尚缺“权(衡)”。此两点,在下面的“孔出郑玄《周礼大师》注”、“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亦完全相同,因无关十二律相生之宏旨,本文故不再述。
依上面引文的十二律上生下生之次序,“黄钟初九也,下生林钟之初六”到“应钟又上生蕤宾之九四”,与《淮南子·天文训》生律次序无异,而从“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下生夷则之九五”,则与《淮南子·天文训》生律方向不同。如此生律,即为“大吕重下生”(见表1)。
从表1看,蕤宾下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的“大吕重下生”,将大吕、夹钟、仲吕、夷则、无射五律,都生出了十二正律的范围。十二律中,竞有五律为半律。这样的十二律,如果以律管排列,则不是以一律之差之分寸而渐次减短,而是从黄钟到蕤宾一高一低(一长一短);从林钟到应钟一高一低(一长一短),如果吹律,则不是以一律之差(半音)渐次升高,而是从黄钟到应钟动辄一正声一半声(高八度)。丘琼荪撰《历代乐志校释》曾云:
倘能“求声索实”,试以四寸有奇之大吕,夹在九寸黄钟与八寸太簇之间,将成何律耶?盖所得者皆半律,以此半律与全律相间而组成音阶,古今中外,无是法也。(见表2)
如上述,郑玄乃儒学大师,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郑玄注经,当有所本。而这样的“大吕重下生”所本者何?将上面引文中的生律次序,与“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终矣”合而观之,答案立即可见,日:《吕氏春秋·音律》。
《吕氏春秋·音律》云: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高诱注:律吕相生,生者上生,下者下生。
以上面所引“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与《吕氏春秋·音律》相比照。二者的“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之后,《吕氏春秋·音律》列黄钟至蕤宾七律“为上”;林钟至应钟五律“为下”;而“郑玄《周礼·大师》本注”则省去了律吕之名,直言“五下六上”。其“五下”也就是《吕氏春秋·音律》所说的林钟至应钟“为下”五律;“六上”则是《吕氏春秋·音律》所说的从黄钟至蕤宾而除去仲吕一律的“为上”六律。在“郑玄《周礼·大师》本注”看来,“无射又上生中吕之上六”,已经达到了“一终”,也就是一个圜的十二个律,仲吕“极不生”,故改《吕氏春秋·音律》“七上”为“六上”(见图1)。
但是,“郑玄《周礼·大师》本注”生律的上生、下生次序,却是“上者下生,下者上生”,即“六上”全部“下生”,“五下”全部“上生”,与高诱注“上者上生,下者下生”正好相反。
于是,在“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中,蕤宾是“六上”之一律,下生大吕;大吕是“六上”之一律,下生夷则;夹钟是“六上”之一律,下生无射;无射是“五下”之一律,上生仲吕(见图1)。如此,生出的十二律中,便出现了五个半律。
但是,孔颖达与郑玄一样,都企图以《吕氏春秋·音律》之七上、五下之划分为依据,生出以黄钟为首的十二律。“郑玄《周礼·大师》本注”,是不接受高诱注“上者上生,下者下生”,而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直接把黄钟至蕤宾“为上”七律,除去仲吕“极不生”一律,作“下生”;把林钟至应钟“为下”的五律,作“上生”,结果生出了五个半律。孔颖达是看出了其中之不当,于是便明以高诱之注作解释,暗取《淮南子·天文训》的生律方法和次序,顺延《吕氏春秋·音律》“为上”“为下”之分,郑玄“五下六上”之注,推出了子午以东以西之说。以“东管西”、“西管东”为前提,将本是“生出短(低)管”的“下生”,“生出长(高)管”的“上生”作拆分,中间插入了一个连接状语于动词的“而”字,在动词“生”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代词“之”字,遂将《吕氏春秋·音律》所云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除去黄钟,余六律全是由“西”、“上而生之,故云上生”,套入高诱注就是“上者上生”;将《吕氏春秋·音律》所云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五律全是由“东”“下而生之,故云下生”,套入高诱注就是“下者下生”。如此,《吕氏春秋·音律》“为上”、“为下”也不再是上下、阴阳之分,而是由“管”它们的子午以东或以西的律,是“上而生”它们,还是“下而生”它们所决定的;若是“上而生”它们,它们就叫“上生”,亦即“为上生”、“上者上生”;若是“下而生”它们,它们就叫“下生”,亦即“为下生”、“下者下生”。这样,不但为“蕤宾上生”找到了说辞,而且把高诱注之“上者上生,下者下生”也完全套进去了(见图2)。
孔颖达的这个阐释,要说明“上者上生”,就必须要从“西”(下)说起,比如,蕤宾在《吕氏春秋·音律》中为“上”,那么就要从生蕤宾的应钟说起,由于应钟“上而生”蕤宾,蕤宾便为“东”(上)“上生”,就是“上者上生”(见图2);要说明“下者下生”,就必须要从“东”(上)说起,比如,林钟在《吕氏春秋·音律》中为“下”,那么就须从生林钟的黄钟说起,由于黄钟“下而生”林钟,林钟便为“西”(下)“下生”,就是“下者下生”;等等。毋庸讳言,孔颖达的阐释令人发噱。简而言之,即全部是采用“倒着说”,不是从头到尾,而是从尾到头,说太簇必须先说林钟,说林钟必须先说黄钟。
最有意思的是,孔颖达虽然说“子午以东”、“子午以西”,但却始终回避说子午以东为阳,子午以西为阴,因为他怕落入“阳下生阴,阴上生阳”之窠臼。如果落入这样的窠臼,他的阐释就更不成立。孔颖达如此婉转曲折,就是要避开阴阳,拆解上生、下生,最终变主为从,倒因为果。
不过,尽管如此,要将高诱注“上者上生,下者下生”,说成是生出以黄钟为首的十二律之法,其中仍有矛盾难以化解。首先,既云“子午以东为上生”,是由于子午以西“上而生之,故云上生”,那么,黄钟是在“子午以东”,是由谁“上而生之”?为回避这一矛盾,孔颖达借黄钟的特殊地位,将本在“子午”之列的黄钟“不入其数”。但黄钟既“不入其数”,“子午”之“子”又从何来?第二个矛盾就是,既言“五下”“皆是子午以东之管”,“六上”“皆是子午以西之管”,而大吕却是由蕤宾上生;言蕤宾是由应钟“所管”“以西管东”可以,但大吕是由蕤宾上生,这就不是“以西之管”,而是“以东管东”了(见图3)。
应该说,孔颖达的这个解释,与《吕氏春秋·音律》之黄钟至蕤宾七律“为上”,林钟至应钟五律“为下”、高诱注之“上者上生,下者下生”实际已无关涉。与前面所述之“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也互不相及。《吕氏春秋·音律》、“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中的“上”、“下”、“上生”、“下生”之概念,被孔颖达所谓的“上而生之”、“下而生之”,全部替换了。
后世学者引“孔出郑玄《周礼·大师》注”,多取孔疏《礼记·月令》所出之注,而少谈《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二十年》之说。原因即在于孔疏《礼记·月令》所出之注,是可以生出以黄钟为首的十二个正律;而少谈《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二十年》之说,则因为孔氏的阐释为纳《吕氏春秋·音律》之“七上”“五下”人“黄钟下生林钟”、“蕤宾上生大吕”之秩序,将“上生”、“下生”强作拆分,有悖于“上生”“下生”的公认含义,即清人陈澧所云:“凡物之形,长者高,短者下。故十二律长生短,则日下生;短生长,则日上生。”@并且还回避了儒家“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的律吕相生之家法。
历史上对于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二十年》之说的响应者有清人许宗彦。许宗彦注《吕氏春秋》,取孔颖达之说以变通,云:
高诱《吕》注所谓“上者上生”,言黄钟等七律由上生而得,如蕤宾上生乃为大吕,故云上也。“下者下生”,言林钟等五律由下生而得,如黄钟下生乃为林钟,故云下也。
尽管历史上的一些儒家学者,都一口咬定《吕氏春秋·音律》与《淮南子·天文训》、“郑玄《周礼·大师》注”生律方向一样,但以孔颖达的阐释为依据者,反而不如今天的学者多。
三、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
“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即为《唐宋注疏十三经》之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中所出“郑玄《周礼·大师》注”。云:
黄钟初九也,下生林钟之初六,林钟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应钟之六三.应钟又上生蕤宾之九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上生夷则之九五,夷则又下生夹钟之六五,夹钟又上生无射之上九,无射又[上](下)生中吕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异位者象子母,所谓律取妻而吕生子也。黄钟长九寸,其实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终矣。
贾公彦(生卒年不详),唐人,疏《周礼注疏》。似乎是贾公彦既看到了“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也看到了“孔出郑玄《周礼·大师》注”。前者欲本《吕氏春秋·音律》,但生出五个半律,且“律娶妻”、“吕生子”互不完全相合。后者,无论孔颖达以生花之笔作怎样的解释,也掩盖不了照抄《淮南子·天文训》之事实。于是,“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便舍弃与《吕氏春秋-音律》的联系,删去对《淮南子·天文训》的照抄,直取《史记·律书·生钟分》、《汉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生律之法,就此而又出了一个“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到,“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史记·律书·生钟分》、《汉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生十二律,黄钟下生林钟,蕤宾下生大吕,也使得大吕、夹钟、仲吕三律,生出了十二正律的范围之外而成半律(见表5)。
以前面所述“郑玄《周礼·大师》本注”所包涵的内容比对“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取《易》之乾六爻、坤六爻,二者完全相同。生十二律上生下生次序二者不同:“郑玄《周礼·大师》本注”本《吕氏春秋·音律》之七上、五下,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则取《史记·律书·生钟分》、《汉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六阳律皆为“上”下生六阴吕,五阴吕皆为“下”上生六阳律;凡阴吕除“极不生”之仲吕全部“为下上生”、凡阳律全部“为上下生”。以“同位者象夫妻,异位者象子母”,“律娶妻而吕生子”来看,“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与此最为切合。按照这样的上生、下生次序与规定,蕤宾是阳律,就必须要下生、娶妻大吕;大吕是阴吕,必须要上生,生子夷则。而所谓的“五下六上”,则是六阳律为上,五阴吕(除去仲吕)为下,既与“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不同,也与“孔出郑玄《周礼·大师》注”不同(见图3)。
应该说,十二律的阴阳观念早已有之,但“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将阳律、阴吕作“夫妻”、“子母”,“娶妻”、“生子”等如此具体、贴切地诠释,则可以认为是前面的三个“郑玄《周礼·大师》注”所不及。故对于后世的一些儒家学者来说,他们对“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保持沉默,但对“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这样的蕤宾下生,由于其严格地遵循了“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的“阴阳之序”,许多人都不以为误,并视其为十二律相生之另法。清人钱大昕即云:
蕤宾下生者,正律之寸分也。重上生者,倍律之寸分也。史公言十二律分寸取倍数,言生钟分取正数,各有所当,不可偏废也。
钱大昕把蕤宾下生所得之半律,说成是“正律”,把蕤宾上生正律说成是“倍律”,并且认为蕤宾的下生、上生,“各有所当,不可偏废”。清人陈澧亦云:
惟《汉书·律历志》蕤宾生大吕,夷则生夹钟,无射生仲吕,皆曰下生;大吕生夷则,夹钟生无射,皆日上生。然所得大吕、夹钟、仲吕皆半律,必倍之乃得全数,不如《吕氏》、《淮南》之法为直接矣。
蕤宾下生,生半律“倍之”而再回正律全数,此亦有可能就是“郑玄《周礼·大师》注”中,律数全为正律,所经过的一道计算程序。因为,在上述的四个“郑玄《周礼·大师》注”中,无论是“大吕重下生”、还是“蕤宾下生”,其后所列之律数分寸,全部都是正律律数:
大吕长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长八寸,夹钟长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长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吕长六寸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万二千九百七十四,蕤宾长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钟长六寸,夷则长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吕长五寸三分寸之一,无射长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应钟长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四、大阴阳、小阴阳
将《吕氏春秋·音律》七上、五下之划分,作所谓的“上者下生,下者上生”,是不可能生出以黄钟为首的十二个正律的,上述“郑玄《周礼·大师》本注”即是明证。而取《淮南子·天文训》之法,生出以黄钟为首的十二个正律,当然是圆通无碍,但经师孔颖达却仍托《吕氏春秋·音律》,变七上、五下为六上、五下,拆解上生、下生为“上而生之”“下而生之”。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虽亦云为“郑玄《周礼·大师》注”,但却直取《史记·律书·生钟分》、《汉书·律历志》之生律法。
宋人朱熹,对此心知肚明。即,若不改变蕤宾“为上”、“为阳”的位置,若固守《吕氏春秋·音律》七上、五下的子午划分,明取《吕览》,暗用《淮南》,终难顺理成章。于是,朱熹首先离开《吕氏春秋·音律》之七上、五下,将蕤宾从“为上”、“为阳”的范围中划出,归人“为下”、“为阴”之列,并提出了律吕相生“大阴阳”、“小阴阳”的两个范畴。朱熹云:
乐律自黄钟至中吕皆属阳,自蕤宾至应钟皆属阴,此是一个“大阴阳”。黄钟为阳,大吕为阴,太簇为阳,夹钟为阴,每一阳间一阴,又是一个“小阴阳”。自黄钟至中吕皆下生,自蕤宾至应钟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朱熹是睿智的,他的“大阴阳”不取《吕氏春秋》之子、午划分,而取子、巳划分,子、黄钟,巳、仲吕,平分十二辰、十二律为前六后六、六上六下。蕤宾在六下,以“大阴阳“之“阳下生阴,阴上生阳”,上生就理所当然。子午分阴阳是古法,将十二辰以子、巳分阴阳,也是古法。蕤宾上生的问题,就此而名正言顺。
这个划分,已经离开了《吕氏春秋·音律》的七上、五下,变成了六上、六下。尽管与生黄钟为首十二律的古法仍有差异,但要比孔颖达之说高明了许多。起码,它没有拆解为上、为下,为阴、为阳、上生、下生的历史传统认知。没有扭曲古人以十二律为时空构件的基本意义(见图4)。
朱熹的“小阴阳”说,也就是阳六律、阴六律(见图3)。以朱熹的“大阴阳”“小阴阳”来比照,《淮南子·天文训》为“大阴阳”的“上者下生,下者上生”,而《史记·律书·生钟分》、《汉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则是“小阴阳”的“阳下生阴,阴上生阳”。《吕氏春秋·音律》则是以子、午分阴阳的“大阴阳”,“上者上生,下者下生”。如此,朱熹的“大阴阳”、“小阴阳”,也总算是把儒家经师注经之十二律相生的混乱,做出了一个清理和纠正。即,以“大阴阳”来说,十二律的阴阳之分是十二律的上、下两组之分;以“小阴阳”来说,十二律的阴阳之分就是阳六律、阴六律之分。以儒家确保黄钟为十二律之首的家法来说,要么是“大阴阳”之“阳下生阴,阴上生阳”,要么就是阳六律下生阴六吕,阴五吕上生阳六律。
清人毕沅疏《吕氏春秋》,见“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高诱注:“律吕相生,上者为上,下者为下”,云:
《吕氏春秋·音律》以子、黄钟,午、蕤宾分阴阳;《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以亥、应钟,巳、仲吕分阳阴,二者无论是对于中国古代之律历,还是对中国古代之乐律,意蕴深厚而意义重大。限于本文之主旨,这里仅作简述:《吕氏春秋·音律》之七上、五下,以子午分阴阳,不仅是夏历十一月冬至配子、黄钟,亦可谓是周历“建子之月为岁首”的一个春、秋二季之划分。《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之五上、七下,以亥、巳分阳阴,则是秦以及汉初“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的一个冬春、夏秋的四季之划分。从生律的方向来看,《吕氏春秋·音律》为右旋,六六相生;《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为左旋,八八相生。二者是在同一二元构架中的一正一反(见图7)。
结语
综合上述,儒家注经涉足十二律相生,是从郑玄注《周礼》开始。但是,“郑玄《周礼·大师》注”,一注而四出处、三不同。
《汉魏古注十三经》之“郑玄《周礼·大师》本注”,为“大吕重下生”,根源即在于郑玄谈十二律相生本于《吕氏春秋·音律》的七上、五下之划分,但却以“上者下生,下者上生”生十二律,结果是在十二律中生出了五个半律。这个“郑玄《周礼·大师》本注”,反证了《吕氏春秋·音律》高诱注之“上者上生,下者下生”之确凿。
《唐宋注疏十三经》有孔颖达疏《礼记·月令》之“孔出郑玄《周礼·大师》注”和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二十年》之“孔出郑玄《周礼·大师》注”,二者均照抄《淮南子·天文训》的十二律相生之法,为“黄钟下生林钟”、“蕤宾上生大吕”(蕤宾重上生)。但在《春秋左传注疏·昭公二十年》之“孔出郑玄《周礼·大师》注”后,孔颖达为将《吕氏春秋·音律》的“为上”、“为下”,纳入《淮南子·天文训》的十二律相生之秩序,将“上生”、“下生”强作拆分,有悖于“上生”“下生”的公认含义。以《淮南子·天文训》的十二律相生,作“蕤宾重上生”,生出以黄钟为首之十二正律无误,但孔颖达欲将《吕氏春秋·音律》之生律方向,等同于《淮南子·天文训》之生律方向的种种说辞,甚谬。
《唐宋注疏十三经》还有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之“贾疏郑玄《周礼·大师》注”,与《史记·律书·生钟分》、《汉书·律历志》、《晋书·律历志》生十二律同,为“黄钟下生林钟”,“蕤宾下生大吕”,其生律次序是凡阳六律皆下生,凡阴六吕除去仲吕一律皆上生,十二律中生出了三个半律。
朱熹的“大阴阳”、“小阴阳”之说,事实上是对儒家经师谈十二律相生的一个清理、纠正;也可以说是对孔颖达所谓的“以东之管”、“以西之管”,“上而生之”、“下而生之”的一个否定。即,不将蕤宾一律从“大阴阳”之“为上”“为阳”中划出,使其置于“为下”、“为阴”之列,无论做出何种说辞,欲以“阳下生阴,阴上生阳”之儒家家法,生出以黄钟为首的十二个正律,是不可能的。清人毕沅,亦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其死认生黄钟为首的十二律之一法,竟将《吕氏春秋·音律》的蕤宾“为上”,指责为“不当”,并认为高诱注“上者上生,下者下生”为“传写之误”。
朱载埔云:“‘六经有听律之文,无算律之说。”而自汉以降,儒家经师谈十二律相生之法,亦可谓矛盾、混乱甚多。直至朱熹,方做出了较为明晰的条理。
然而,由于儒家家法,死认黄钟为首,“黄钟之宫,音之君也”等等,并加之其有着强大的话语权,遂造成了所谓《吕氏春秋·音律》与《淮南子·天文训》类同,十二律相生只有生黄钟为首十二律之一法的历史迷雾,且使后人深信不疑,鲜于过问。如此,十二律相生只有生黄钟为首十二律之一法,音阶只有“增四度、大七度”之一阶等等,至今仍具有十分强烈的影响。
《吕氏春秋·音律》、《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是在同一二元构架中的两种生律方向,二者为今天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均、宫、调,乃至于律、调、谱、器,意义十分重大。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