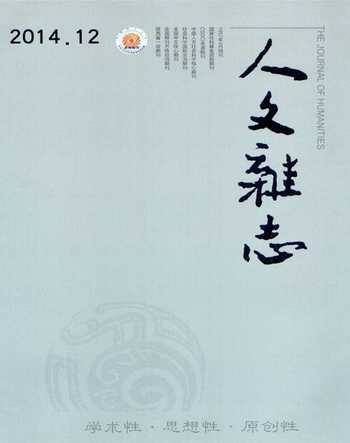艺术发生学的审美人类学阐释
张利群 张逸
内容提要 艺术起源一直是古今中外众说纷纭的话题,在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发生同步及原始工具作为艺术前的艺术观念基础上,审美人类学研究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人及其身体作为艺术与审美的原发点基本观念,从基于身体的人与世界关系建构、艺术发生的人与工具关系阐释、身体作为艺术和审美生成的原发点三个研究视角,深化拓展了艺术起源的审美人类学阐释空间,揭示出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的发生学意义与人类学意义。
关键词 艺术起源 发生学 原始工具 以人为本 身体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2-0051-05
关于艺术起源问题,古今中外文论美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流派纷呈,学派林立,形成“摹仿说”、“巫术说”、“游戏说”、“表现说”、“升华说”、“劳动说”以及从“一元决定论”到“多元构成论”等各种学说及其理论模式,从不同研究视角奠定艺术起源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理论资源。人类学兴起之后,又提供了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视野与视角,不仅确立以人类起源作为立足点探索艺术起源的研究思路,而且依托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以及田野作业与社会考察等实证性研究方式提供大量历史资源与现实资料,推动艺术起源探索的人类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立足于劳动探讨人类起源及其艺术起源问题,在确立劳动创造人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创造美、劳动创造艺术的基本观念,为艺术起源问题探讨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指导思想。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潮流,艺术起源问题探讨更为深入和拓展。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史前艺术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艺术起源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认为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都是一个发生、生成、进化的过程,提出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而又颇具争议的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的观点。主要基于工具制作导致人类发生由此认定工具作为人类起源的原发点,进而推断原始工具具有物质与精神融合的工具实用性与身心愉悦性相统一的功能性质,认定工具产品具有原始艺术(前艺术)形态及其特征,由此得出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的观点,从而开辟了艺术起源的发生学研究新领域和新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将艺术起源放置在人类起源的视域中探讨,将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路径,无疑使艺术起源研究具有人类学意义,对于推动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兴起与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和影响。
审美人类学作为美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形成的新兴学科,具有交叉、综合、互补等优势与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具有美学注重于宏观思辨性研究与人类学注重于微观实证性研究结合而构成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及其研究视野与视角,更为关注审美发展与人类发展的起源与现状两端,以“原始以表末”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的研究方式揭示审美与人类关系及其指向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的艺术原发点和发展趋向,从而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美学研究的人类学意义与人类学研究的美学意义。就艺术起源问题探讨而言,审美人类学研究能否具有可能性与必要性,能否开拓新的研究空间,能否更好阐发艺术、审美起源的人类学意义,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基本问题所在。
一、基于身体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建构
从审美人类学研究视角探讨艺术起源问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于,不仅能够更为深化地拓展以工具制作作为原发点的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观念,而且在于开拓以人的身体作为原发点的以人为本的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的研究视域与视角。如果基于艺术发生与人类发生同步观念认定人类制作的工具为史前艺术发生的原发点的话,那么就能够进一步推论当劳动创造人的同时也就创造了艺术的双向共生与双向同构观点,证明人与艺术既是同步发生的,又是双向共生与双向同构的。正如劳动创造人的同时人也创造劳动一样,人类制作了工具的同时工具也成就了人类,人类创造了艺术的同时艺术也推动了人类的进化。由此可以认定,人类自身就是劳动创造、人类创造的第一件艺术品。因此,艺术发生与人类发生同步的聚焦点不仅仅是工具,而且也是人类自身,人也是艺术发生的源头与原发点。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艺术发生学观点主要是基于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自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从审美人类学研究视角探索以人为本的艺术起源原发点,必须立足于和聚焦于人的身体,因为对于人类起源而论,无论体质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需要以身体作为聚焦点与契合点;对于艺术起源而论,无论主体还是客体、美还是审美、快感还是美感,也都需以身体作为聚焦点与契合点。
艺术发生基于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与审美的关系。但正如基于史前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物质与精神交织、交融、渗透的整体性状况而指称原始艺术为前艺术一样,审美也是融入人与世界关系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亦可称为前审美形态或原始审美形态。将人类发生放置在劳动创造人、艺术发生放置在劳动创造艺术与劳动创造美中理解,放置在史前物质与精神一体化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来认识,放置在人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的关系中来探讨,就可以依据劳动创造人而人也创造劳动的双向同构性推衍出劳动创造人的同时也创造美而美也创造人。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改造人自身,改造人类存在、生存、生活、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以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人改造人自身不仅推动人类发生、生成、进化和发展,而且使人更为“人化”、“人类化”,并不断导向诗化、艺术化、审美化的人的生成与建构及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将人类发生作为艺术发生与审美发生的源头,将人类发生过程视为人类艺术化与审美化生成过程,从而可以认定人自身及其身体就是艺术发生的原发点,人自身就是劳动创造的第一件艺术品,也是人类自我观照及其审美观照的第一个对象。如果认定劳动创造人的同时也创造美及其艺术的话,就意味着艺术与美就可以涵盖于劳动创造人之中,意味着劳动不仅创造人以及缔结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也创造艺术以及缔结了人与艺术及其审美的关系,那么毫无疑问人在劳动中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人自身,当人与世界都可以作为劳动对象及人类改造对象的同时,当然也就可以作为艺术与审美对象。劳动创造人及其艺术与美,也就是创造了艺术化、审美化的人与人作为艺术与美。由此,在劳动创造人的过程中艺术与美同步发生和生成,人及其制作的工具就成为“艺术前的艺术”、审美前的审美,人与工具都生成为第一件艺术品与审美品,都应该成为艺术与审美起源的源头与发生点。
二、艺术发生的人与工具关系的审美人类学阐释
将工具制作视为人类起源与艺术起源同步的发生点,进而还必须讨论人的制作与利用工具的需要在何等程度上推动工具的发生与工具在何等程度上推动人类发生,并由此缔结人与工具关系。人与工具关系实质上是基于劳动创造的相辅相成、互相作用、合为一体的关系,亦即人创造了工具与工具推进了人的生成的双向共生、双向同构的关系。因此,当认定工具为前艺术和前审美形态的同时,亦可认定人自身也是艺术对象与审美对象,也是艺术品和审美品,也是艺术与审美发生生成的原发点。这一观点的论证主要基于三方面理由。
其一,工具制作与利用基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一方面来自环境条件的外因,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及其环境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与道理;另一方面来自千万年人类发生、生成、进化过程的生理心理积淀与遗传基因的内因,是顺应环境与改造环境的双重建构的内在需要,最终以工具制作和利用促使由猿到人的转化。工具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和表征,人也成为能够制作和利用工具,并以之区别于动物、人猿揖别、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人类起源的发生点。因此,人类对工具的崇拜和依赖心理是基于人的存在与生存的需要,也是基于人类发生与生成的需要,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可以还原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和表征,以史前工具作为前艺术看待必然离不开制作和利用工具的人。
其二,工具的“对象化”性质与“属人”性特征。即便从人类发生与史前石器工具制作具有紧密联系,从而认定工具是人类创造的物质生产工具而其劳动产品又是含有精神创造因素的前艺术作品的思路来看,工具的前艺术特征其实质也是指向人及人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特征的。一方面在于工具是人创造的并以之实现人的存在、生存、发展目标,可谓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的自我确证、人反观自身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工具所具有的“属人”性、拟人化、人格化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人的手足及其身体的延长,使之成为人的身体及其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也因此具有人类学本体性意义;再一方面是工具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人自身,工具制作和利用使人的体质与心智发生重大变化,推动人的发生、生成、进化,使人之所以为人。因此,如果将史前工具作为前艺术来看待的话,将人自身作为艺术发生和审美发生的原发点也在情理之中。
其三,身体作为工具媒介的功能作用。无论是在工具制作前还是后,也无论在工具利用前还是后,身体既作为工具使用,又是制作和利用工具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身体作为工具的功能性与本体性意义而论,人以自身身体作为工具,使身体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交往交流的手段、媒介、载体,并且随着人类发生、生成与进化,人利用身体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身,也改造作为工具的身体,既使之更为工具化从而更加强化身体的工具性功能作用与效果,又使之更为“对象化”、“属人”化、人文化,更能体现人的本质及其本质力量,增强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竞争力。从身体作为制作和利用工具的主体、载体、对象角度而论,身体作为工具的功能作用与效果显然与制作和利用工具的人紧密相关,工具价值应该是人使用工具产生的价值,是人与工具关系构成的系统值、关系值。如果身体没有作为工具被使用,如果工具使用没有制作、利用与掌握工具的人,如果没有能够熟练、灵巧、灵活运用工具的手及其身体,工具就会失去其作用与意义,也就无法认定为工具。因此,工具一定是人的工具,是人的身体功能的延伸;人一定是能够利用工具的人,利用工具直接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人的身体成为工具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工具也成为人的身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身体作为艺术和审美生成的原发点
人类从自然界走出来以及与动物界分离出来,主要基于以劳动为中心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既来自对世界的认识又来自对自身的认识,亦即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认识。一方面是以世界作为认识对象从而反观自身,在认知世界的基础上认知自身,通过“他者”认识自我;另一方面是以自身认识为基础而推人及物,推己及物地认识世界,既是人自身的“人化”、“人类化”、“自我确证”的认知建构过程,又是将对象世界“人化”、“对象化”、“人格化”的审美建构过程。因此,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对象所展开的人与艺术的关系,遵循双向共生与双向同构的规律和原则,身体无疑成为两者的聚焦点与聚合点。身体既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工具、中介、媒介,也是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主体与对象、本体与载体,当然也是艺术与审美的主体与对象及其生成的原发点。
其一,身体是人的本质及其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从工具对人类起源发生所起的重要作用中,不难看出工具与人的身体密不可分,同时也可看到身体本身其实也是人作用于世界的工具,也体现出人的本质及其本质力量。人改造和利用自身身体作为工具无论是在狩猎还是采集、交流还是交往、竞争还是选择、活动还是行为中,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身体作为工具的认识和改造世界与人自身改造的功能作用。身体作为媒介直接沟通人与世界关系,身体作为载体承载人的体质和心智及其本质力量,身体作为人的本体聚集和积淀着个体与集体的感觉、体验、经验、思维、方式。从语言发生来说,以体态语言、肢体语言、声音语言作为工具、媒介、载体的语言发生过程,其实质就是口耳相传的身体交流,其中无疑负载着这些语言形式中的艺术与审美要素,以至于导致原始艺术与口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原始绘画、音乐与舞蹈发生。
其二,缔结于身体的人与“文”及其“体”的关系。从“文”起源的发生过程来看,文通纹,最早发生的所谓“人文”,其实就是在身体上图饰的纹身,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多元的摹仿与表现、巫术与宗教、信仰与崇拜、神灵与鬼魂、敬畏与禁忌、自我确证与自我保护等功能作用中不乏美化与装饰意义,也是借助身体作为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纽带及其交流媒介,以至于导致绘画、音乐、舞蹈、文字及其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发生。从“体”起源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缘起于人的身体而产生对于身体构造与构成的认知,无疑既从原始崇拜的信仰系统中延伸出图腾、神鬼、灵魂、自然等原始思维及其意识观念,又从本体论意义上延伸出天体、宇宙、道、气、生命等认知观念。最为重要的是从人体的身体之“体”所蕴含的艺术与审美要素中延伸为文学、艺术与审美的移情化、拟人化和人格化的创造方式,形成诸如文体、体裁、体式、体性、体势、体貌、体态、体味、体验、体察、体会等附着于“体”的文艺审美范畴,并推衍于身体部位,形成诸如文心、文脉、文气、文眼、诗眼、形神、风骨、主脑、骨架、肌肤、肌理等“人化”文艺审美范畴概念。当然,这些概念产生是文明、文化发生发展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与原始思维发生过程的断裂,也不意味着对身体的原发性及其依附于身体而产生对图腾、神鬼、灵魂、自然等体认的无知。其追根溯源与一脉相承的贯通性不仅揭示出身体在艺术与审美发生学中的作用和意义,而且也昭示出身体对于艺术与审美的发展至今仍然具有深远意义。
其三,美感发生依存于身体的生理心理基础。从美感发生所依存的身体生理心理功能来看,人所具有的能够感受和反应及其产生快感与美感的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功能作用,其实都会随着人类进化中的“人化”、“人类化”进程而不断提升和发展为“属人”的眼睛与耳朵。马克思认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此,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97页。由此可见,人的五官与身心及其感觉都应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审美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并逐步依托生理基础向心理发展,依托快感基础向美感提升,从而构成身心一体的身体感觉与反应,在人与世界关系中身体不仅成为快感与美感的发生点,而且也成为审美及其艺术的发生点。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②人不仅遵循“美的规律”创造客体,而且也遵循“美的规律”创造主体,即人自身,使人也成为美的创造物及其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人作为美与艺术的原发点与原生点从发生学角度阐释了艺术发生与人类发生同步的缘由和根据,揭示了人的身体作为艺术审美主体与客体双向同构的建构与生成意义。恩格斯指出:“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9页。因此,人类对于自身及其身体的认识,无论是出于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需要还是适应和改造外界环境的需要,无论是出于实用功利性需要还是精神愉悦性需要,无论是出于生理需要还是心理需要,都曾采取过各种各样的使其“人化”、“对象化”与“修饰化”的方式,如纹身、涂脸、面具、披发、束发、头饰、手饰以及形形色色的装饰物和佩戴物,以强化和凸显身体功能,在其功利性中无疑蕴含艺术与审美要素及其产生愉悦性功能,身体因此也被艺术化和审美化,人因之既生成为审美主体又成为审美对象。
伊格尔顿指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在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登所作的最初的系统阐述中,这个术语首先指的是不是艺术,而是如古希腊的感性所指的那样,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因此,审美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首次冲动——这种冲动是肉体对理论专制的长期而无言的反叛的结果。”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这充分说明了美学何以又称为感性学的缘故,也说明审美发生与身体、感性、感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对于探讨艺术与审美起源问题也是颇有启发的,在阐发史前工具制作与利用在人类发生进化过程中的人之所以为人标志性作用以及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的观念时,无论是从其制作与利用的主体与对象而言,工具都离不开人的身体,而且从功能性与本体性意义而言,工具无疑就是人的身体及其身体功能的延伸。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在工具制作与利用之前还是之后,人的身体既是人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工具,又是人自身之所以为人的本体;既是在劳动中以及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和改造的产物,又是身体“人化”、“人类化”、“对象化”的产物。据此可以认定,身体与工具都在人类起源与艺术起源的同步发生中产生重大作用,如果将工具视之为艺术前的艺术的话,或者说是艺术和审美的原发点的话,那么在人类起源的发生学过程中,人及其人的身体亦可视为艺术前的艺术,或者说是艺术和审美的原发点。由此,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的发生学原理才具有人类学意义,提供给审美人类学研究更为广阔和深入的空间。
作者单位: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张逸,广西师范大学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