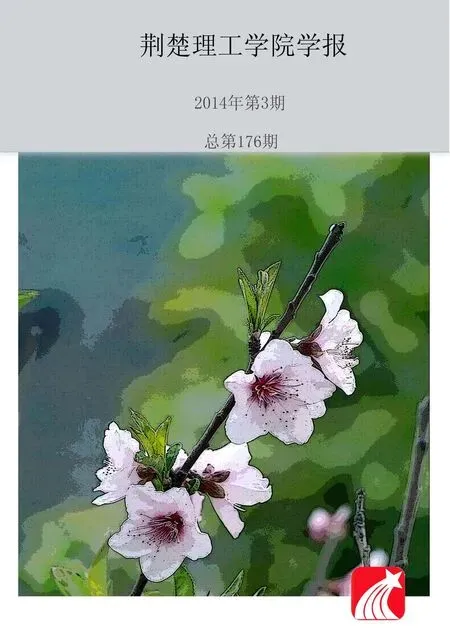场所的国际化
——试析《尤利西斯》中20世纪初作家的“自我移植”现象
李巧慧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场所的国际化
——试析《尤利西斯》中20世纪初作家的“自我移植”现象
李巧慧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作为人诗意的栖居地,场所常常指代故乡或祖国,蕴含依恋和忠诚等美好的人类情感。但在现代主义经典《尤利西斯》中,艺术家所栖居的场所却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国际化的新场所不但提供了新型体验和再度场所化的可能性,而且实现了反思旧场所的审美距离。以斯蒂芬的莎士比亚理论和斯蒂芬与作者乔伊斯的自传关联为基础,《尤利西斯》创建了斯蒂芬、莎士比亚和作家本人组成的移民作家群。他们的场所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诗意栖居场地的不懈追求,更表现在对旧场所心理、理性、文学等多层面的批判和审视。因此,斯蒂芬、莎士比亚和乔伊斯组成的多维三棱镜不仅连接历史与现实、文本与世界、人物和作者,更提供了透视20世纪初移民作家场所意识的多重视角。
场所;国际化;自我移植;反思
我国历史文化中一直流传着一种“橘枳传奇”。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1]。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2]。南橘北枳是说南方的橘子移植到北方后其味道、色泽等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能称之为橘,只能称之为枳。人们经常用这个习语来说明同一人或物因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异。“淮南”和“淮北”指代不同的生存环境,“橘”和“枳”指代本源相同,却差别巨大的两个人或物。在地域或空间(本土或国际)的移动和转移中,移植分为脱离原生态环境和植入新生态环境两个环节。作为生物生长过程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改变了生物的生态位,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的基本特性。移植的动因可分为外因和内因:前者作用于被移植的对象,引起其生存环境和性质的变化;而后者通常来源于移植的人或物本身,这种类别可称为自我移植。和其他生物不同,人的移植常常带有心理、个体和社会等因素,具有强烈的场所意识,反映了人追求理想的不懈精神。在《生态文艺学》中,鲁枢元认为,“在我们考察文学艺术家的成长发育时,不妨把‘生态位’的理论作为参照”[3]205。本文就以自我移植和生态批评理论为基础,分析《尤利西斯》中移民作家的场所意识。通过斯蒂芬的莎士比亚理论和斯蒂芬与作者的自传关系,乔伊斯创建了斯蒂芬、莎士比亚和作家本人组成的移民作家群。这个多维的三棱镜不仅连接历史与现实、文本与世界、人物和作者,更提供了透视20世纪初移民作家的多重视角,折射出他们独特的场所意识。
一
人所栖居的场所是“物质元素和心理元素的统一,是被赋予丰富内涵的空间”[4]。场所常指人所栖居、依恋的家园、故乡或祖国。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人际交往的增加和国际交流的加强,人的场所意识呈现出流动性、移居性、多变性甚至国际性的特点。人们不再把生活、工作、爱情和生死只托付给一个地方,而是不断改变自己栖居的场所,以“自我移植”为原型的移居或移民(本土或国际)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许多人都试图演绎这种“橘枳传奇”,成就自己的梦想,艺术家也不例外。艺术家移居他地,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寻觅诗性的现实存在。
和普通人不同,作家的场所意识不但包括这些对居住地域的感情,而且还具有深厚的文学特性。在《文艺生态学》中,鲁枢元分析了作家的艺术生态位和场所意识的主要因素。除了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政治背景对艺术家的影响,他认为“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时代的价值偏向、精神氛围对于一个文学艺术家的成长发育来说更起决定作用,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文学艺术家生态位中的‘精神因子’”[3]208。这种精神因素不但提供创作的素材也决定作品的影响力,因为只有社会的认可和读者的接受才赋予作品社会地位和艺术价值。由作品和读者组成的艺术之维构成了作家文学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普通作家不同,移民作家的场所意识更为复杂和多变。这并不能说明移民作家缺乏场所意识,因为场所的存在不是取决于居住时间的永久性,而是人对场所的关怀和敏感。长期定居在固定不变的地方有时会削弱人对环境的关注,甚至使人“狭隘、固执、因循守旧”[5]261。移居和流浪反而会增强人对环境的注意力。另外,对于漂泊不定的移民作家来说,文学作品本身也有某种场所性质。昆德拉说,“正是在那里(作者注:艺术作品)他决定安置自身,扎下根子,居住下去;正是在那里,他最终地找到了他仅有的同胞,他仅有的亲人”[6]。一般而言,作家的地域场所和艺术场所可以合而为一,即他的作品描写所居住的地方,又能被这个场所认可。和他们不同,移民作家场所的置换常常打破这种和谐统一的过程。作家的故土、创作地、作品内容和接受的地区呈现断裂的现象。在《尤利西斯》中,斯蒂芬离开都柏林、前往巴黎的举动构成了作家场所国际化的过程。
作为斯蒂芬的故土,都柏林是斯蒂芬原发性的栖居场所。这里见证他纯真无邪的童年,目睹他踌躇满志的青年。斯蒂芬了解都柏林的方方面面,熟悉它的一草一木。但这一切却代表具有压抑性和束缚性的家庭和社会力量。斯蒂芬由此产生了以憎恶和逃离为特征的否定性场所意识,这种场所意识常常附着于原生态位,它代表将被脱离的生态环境。萦绕在心、挥之不去的过世母亲的形象象征了家庭生活对斯蒂芬的羁绊,而一事无成、寻欢作乐的父亲更是他尽力反抗的男性形象。爱尔兰屈辱的殖民历史、毫无希望的独立大业、滞后的经济形势构成了斯蒂芬要逃避的特殊社会环境。对斯蒂芬来说,都柏林有时象令人窒息的、纠缠不断的海草,有时是令人恐怖的、不能摆脱的梦魇。都柏林已失去场所应有的魅力、温馨和亲情,家不像家,国不像国。
非场所活动的增多是斯蒂芬否定性场所意识的重要特征。和象征依恋、忠诚等情感的场所不同,“非场所指代公共的、暂时的、事务性的现代空间”[7],如飞机场、运动场、公司、工厂。虽然它们不能给人提供惬意、温暖的家的感觉,却常常以其舒适感和实用性而受到现代人的喜爱。不愿回家的斯蒂芬终日流浪在外,他有时在图书馆高谈阔论,有时在酒吧酩酊大醉,有时徜徉在无人的海滩,有时在妓院灯红酒绿。这些非场所可以提供逃避和逍遥的空间,但却缺乏依恋、温馨的感觉。
作为具有否定性特征的场所,都柏林往往压抑,甚至拒绝接受斯蒂芬的文艺思想。斯蒂芬不但尝试文艺批评而且创作了许多诗歌。但都柏林文艺界的精英对斯蒂芬不屑一顾,不能理解甚至拒绝接受他的作品和思想。文艺界的泰斗拉塞尔与斯蒂芬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在国家图书馆,斯蒂芬向众人解释自己的莎士比亚理论,“拉塞尔却不耐烦地批评到:但是像这样来窥探一个伟大人物的家庭生活,那可……当我们读《李尔王》的诗篇时,该诗作者究竟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干我们什么事?”[8]2后来,拉塞尔干脆一走了之,不愿听斯蒂芬胡说八道。当时拉塞尔正在把年轻诗人的作品收成集子,都柏林都在翘首期盼,但却没有斯蒂芬的作品。斯蒂芬试图投稿给《爱尔兰家园报》,作为编辑的拉塞尔却说,“读者来稿踊跃极了”[8]2。这样的推诿也显示了艺术家斯蒂芬的窘迫。正是基于文艺界对斯蒂芬的如此不屑,斯蒂芬的朋友勃克·穆利根(根据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穆利根的原型系爱尔兰作家、爱尔兰复兴运动的参加者奥利弗·约翰·戈加蒂(1878-1957))声称自己是惟一赏识斯蒂芬的人。
斯蒂芬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理念与当时世俗化的文艺界也格格不入。斯蒂芬的美学标准不是经济收入或社会效益,而是艺术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力。根据这个标准,他将艺术形式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他认为能使读者产生“怜悯”或“恐惧”的艺术具有静态美的特征,而使读者产生“欲望”或“厌恶”的艺术则是动态的。“因此引起这种感情的艺术,无论是色情的或是说教的,都是不恰当的艺术……艺术家所表现的美不可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动态的情感或应当引发一种静态美”[9]。在文艺界,世俗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大众化报刊的出现和崛起是这种文艺观的重要体现形式。它们开始悬赏小说,《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提到的文学作品《马查姆的妙举》就是《珍闻》(当时的时尚杂志)的获奖作品,作者菲利普·博福伊先生是伦敦戏迷俱乐部的成员。报刊甚至充斥犯罪、丑闻、流言、离婚、性,报道离婚诉讼、溺死者和诈骗案,以喧嚣、刺激来吸引读者。布鲁姆认为,“如今啥都可以印出来,是个胡来的季节”[10]153。它们需要具有煽动性、轰动性、耸人听闻的新闻和报道。《电讯晚报》的主编和编辑们认为报纸所提供的精神食粮应该包括“青春的词汇…带刺的东西”[10]261,具有“震惊欧洲”[10]261的效果,记者们应该“趁热给他们(读者)端上来,血淋淋地和盘托出”[10]263。
缺乏正常的接受空间使艺术家斯蒂芬产生了孤独,甚至隐形的感觉。“白天我呆在铅色的海洋之滨,没有人看得见我;到了紫罗兰色的夜晚,就徜徉在粗犷星宿的统驭下。我投射出这有限的身影,逃脱不了的人形影子,又把他召唤回来,倘若它漫无止境地延伸,那还会是我的身影,我的形态吗?谁在这守望着我呢?”[10]119-120斯蒂芬并不缺少创作的灵感和才华。徜徉在夜色笼罩的海滩上,他思潮澎湃,才思喷涌,创作的欲望勃然而发,当即在海滩上写下了动人的诗句,但随即感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读到我写下的这些话?白地上的记号”[10]120。虽然创作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主干和基础,但这并不是全部。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实现,因而文学作品必须有读者的参与才能最后完成。接受之维的缺乏中断了斯蒂芬的创作活动。
斯蒂芬对自己的故土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而有可能实现他逃离的就是要寻求一个新生态位,实现新的场所化过程。场所为社会关系的构成提供背景和处所,而场所的变化就可以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和背景。艺术创作有其社会特性,不同的场所对它有不同的影响力。“文学这种精神植物,其生命力既是很顽强的,又是很脆弱的。就其顽强性看,可以说它在任何社会土壤中都能生长……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文学艺术有时又经不起打击”[11]195。文学创作这种既顽强、又柔软、又自由、又不自由的特点要求艺术家要寻觅适宜的社会场所。富有流动性的现代社会给场所的置换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斯蒂芬场所的国际化旨在催化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
法国巴黎成为斯蒂芬的首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加,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不再局限于某个国家,而是覆盖整个世界,遍布英、法、美、德、意等多个国家,但这种全球化的先锋艺术运动也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状态。都柏林狭隘闭塞,法国不但经济发达,而且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文学艺术界的先锋运动。塞尚和高更掀起了绘画领域的印象派运动,夏尔·波德莱尔开启了诗歌的象征主义狂潮,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已成为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法国是那个世纪之交艺术先锋运动的大本营,时尚之都巴黎代表他的艺术梦想和完美境界。《尤里西斯》提到了两种巴黎的时尚杂志:《芭蕾短裙》和《白长裤和红短裤》。斯蒂芬对巴黎产生了以依恋和向往为标志的肯定性场所意识,巴黎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更是他的希望和理想所在。栖居场所的国际化可以使斯蒂芬了解世界范围内先锋派的文学理念,领略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
斯蒂芬栖居场所的国际化具有现实性和“想象性”的双重特性。斯蒂芬场所的国际化首先有其现实基础。他确实离开祖国,到了巴黎,但母亲临死前的召唤使斯蒂芬不得已回到都柏林,中止了自己的移植过程,成了落魄的失败者。当斯蒂芬离开都柏林时,飞向新生态位时,他是翱翔的雄鹰;而当他从巴黎返回都柏林,回归原生态位,他是坠海的凤头麦鸡。“长得像鹰的人。你飞走了。飞向哪里?从纽黑文(英格兰的港口)到迪耶普(法国港口,与纽黑文隔着英吉利海峡相望,暗指斯蒂芬的巴黎之行),统航舱。往返巴黎(暗指不得已回到都柏林)。凤头麦鸡。伊卡洛斯。父亲啊,帮助我吧。被海水溅湿,一头栽下去,翻滚着。你是一头凤头麦鸡,变成一头凤头麦鸡”[10]34。斯蒂芬转回故土,但却“身在曹营心在汉”,虽逗留在都柏林的大街小巷,却整日魂系巴黎。这赋予斯蒂芬对巴黎的场所意识浓厚的虚幻性和理想性。斯蒂芬的脱离过程占主导地位,而植入过程只是未能实现的可能性。前者呈现出重复性、理想性、无为性的趋势,后者是具有偶然性、短暂性、甚至虚幻性的特征。
这种双重特性的国际化使斯蒂芬的场所意识主要体现在视角的外位化和反思性。斯蒂芬对巴黎的向往为他提供了暂时脱离旧场所的外位栖居点。这个视点不仅使斯蒂芬享受了一时的自由,而且拉开了他与旧场所的距离,使他得以获得新视角去审视和反思自己的旧场所和旧体验。约翰·丹尼尔认为,“不管我们居住在哪个地方,生活在哪个社会,参加哪些活动,我们都会变成坚定的参与者;因此,我们需要陌生人和外来者,他们可以激活我们的感受,让我们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5]262。移民作家离开了旧场所,获得了参与者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才得以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故国旧人。
二
小说不但描绘了斯蒂芬的自我移植过程,而且通过他的“莎士比亚理论”,再现了莎士比亚的同样经历,形成了对艺术家自我移植的深层透视。虽然斯蒂芬和莎士比亚是批评家和研究对象的关系,但同样的经历又使他们有平行关系。斯蒂芬逃离都柏林,远赴巴黎的举动与莎士比亚离开故乡斯特拉特福,居住在伦敦的经历颇为相似。“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伦敦与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的故乡位于埃文河畔)相距之远,一如今天堕落的巴黎之于纯洁的都柏林”[10]6。“莎士比亚理论”暗示了斯蒂芬对移植的向往,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代表了斯蒂芬的理想和追求。
史料记载,莎士比亚确实出生于英格兰中部沃克郡的斯特拉特福。1582年11月28日,18岁的莎士比亚和26岁的安妮结婚。这个集镇在16世纪中叶大约只有一千五百个居民,它与考文垂相隔不远,距伦敦不过100英里。“爱德华六世时期斯特拉特福成为自治镇,开始管理自己的事情”[12]。关于莎士比亚离开故乡,前往伦敦的时间,人们认为大致在1587左右。而关于其中的原因,争议颇大。但毋庸置疑的是莎士比亚到达伦敦后,成为有名的演员和剧作家。1594年5月,宫内大臣剧团成立之时,成为股东之一。他在伦敦20多年,大约1611年左右告别剧坛,返回故乡,1616年4月23日谢世,葬于故乡。
斯蒂芬的莎士比亚理论着重研究了莎翁的早年家庭生活,凸显了旧场所意识的顽固性和影响力,强调作品与场所之间的密切联系。根据斯蒂芬的研究,莎士比亚早年在故乡斯特拉特福的家庭生活非常不幸。在他结婚后不久,妻子安妮开始与自己的弟弟通奸,给莎士比亚的一生蒙上了阴影。安妮于1585年二月二日生下一对双胞胎,其中儿子名叫哈姆雷特(女儿名叫朱迪斯)。1596年八月,十一岁的哈姆雷特夭折,死在斯特拉特福。
这位剧作家在旧场所的人生经历一直折磨他的灵魂,决定了他戏剧作品的精神特质。斯蒂芬认为《李尔王》《奥赛罗》《哈姆雷特》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都被莎士比亚早年的不幸生活罩上了阴影。作家莎士比亚离不开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莎士比亚。“对莎士比亚来说,撒谎的弟兄,篡位的弟兄,通奸的弟兄,或者三者兼而有之的弟兄,是总也离不开的题材…从心里被放逐,从家园被放逐,自《维洛那二绅士》起,这个放逐的旋律一直不间断地响下去”[8]36。作品内容与作家经历的紧密联系使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很强的自传性,读者在剧作中到处都可以发现他的痕迹,“他把自己的名字——威廉这个美好的名字,隐藏在戏里。这出戏里是配角,那出戏里是丑角。就像从前的意大利画家在画布的昏暗角落里画上了自己的肖像似的,他在满是‘威尔’字样的《十四行诗》里,表明了这一点”[8]33。
斯蒂芬重点研究了《哈姆雷特》,认为莎士比亚以《哈姆雷特》来影射自己的人生。首先,去世的国王和莎士比亚有同样的耻辱经历,莎士比亚本人甚至扮演过幽灵的角色。淫荡的王后以安妮为原型,邪恶的新国王和莎士比亚的弟弟相去不远。当剧中的哈姆雷特王子和幽灵相见,斯蒂芬就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对自己的儿子,夭折的哈姆雷特·莎士比亚说话。王子哈姆雷特不仅以同名的莎士比亚之子为现实基础,更凝聚了莎士比亚复仇的怒火,手持他复仇的利剑。因此,莎士比亚不仅是国王哈姆雷特,更是复仇王子哈姆雷特。如果哈姆雷特以刀剑实现了自己的复仇计划,那么莎士比亚则以笔为剑实现了心灵的升华和精神复仇计划。他以自己的戏剧来描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发泄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此后,莎士比亚回到故乡,“在那里,他走完了人生的旅途。…掘墓者埋葬了大哈姆雷特和小哈姆雷特。国王和王子在音乐的变奏下终于死去了”[8]37。莎士比亚拒绝与安妮同墓,卓越的作家身份超越了失败的丈夫和父亲的身份。但这种超越式的回归证明了旧场所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莎士比亚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
斯蒂芬具有心理学特征的莎士比亚理论是自身场所意识的投射。斯蒂芬以弗洛伊德式的手法分析了旧场所的创伤对莎士比亚的影响以及艺术创作对这种创伤心理的升华作用。虽然莎士比亚新场所的艺术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超越旧场所带来的伤痛,但却没有逃脱旧场所的强势牵引。和莎士比亚不同,被迫回国的斯蒂芬尚未取得这样的艺术建树,所谓的艺术升华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旧场所对莎士比亚的牵引与其说是他的心理感受,不如说是被放大了的斯蒂芬的痛苦。莎士比亚理论不过是斯蒂芬被囚禁的灵魂的呻吟,心理学式的探究不过是其焦灼精神状态的膨胀。
三
斯蒂芬和作者乔伊斯的自传关系早已被大家所认可和接受。如果斯蒂芬的故事主要限于想象式的向往,那么乔伊斯的流亡生涯应该是斯蒂芬场所国际化的现实延伸。作为20世纪初艺术家自我移植的生动一例,乔伊斯的传奇人生不仅回答了彻底“出走”后的艺术家的命运问题,更展示了成功移民作家独特的场所意识和艺术价值。和莎士比亚相同,乔伊斯一生都在讲述和都柏林有关的故事,但他具有否定性特征的旧场所意识更具理性、计划性、反思性和现实性。
早在乔伊斯的青年时代,他拒绝加入、甚至批判天主教。在给诺拉的信中,他说,“我通过写作以及我的言行公开与它宣战,即使我成了流浪乞丐,也绝不向这种社会秩序低头”[13]34。他也提到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我们家有17口人,我的兄弟姐妹对我无足轻重,只有一个弟弟能理解我”。后来,母亲的去世更割断了乔伊斯与家人的联系,虽然“他认为自己的放荡不羁带给母亲莫大的痛苦,但却把她的死归咎于父亲的冷漠和虐待”[13]34。1904年6月乔伊斯甚至写了一篇极尽讽刺攻击之能事的文章,猛烈鞭笞都柏林以及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所有居民。
1904年10月20日,乔伊斯和妻子诺拉到达奥地利帝国的国际性城市利雅斯特。1909-1912年间,乔伊斯曾往返于爱尔兰和欧洲之间,试图在祖国出版《都柏林人》,结果是遇到重重阻碍,小说的部分散页在印刷厂被烧,却不了了之。后来,乔伊斯一直在欧洲各国间颠簸流离,到过罗马、苏黎世、阿姆斯特丹、伦敦等,但居住时间最长的是巴黎,共有20年。当时,巴黎是那些来自美国等国家的年轻浪子们进行不落俗套、令人振奋文学尝试的聚集地。“作家们背井离乡来的欧洲,寻求较为自由的创作空气。他们在巴黎找到了。……这些空气对乔伊斯也很适宜”[14]130。乔伊斯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更是和这种移居式、流动性的生活方式不谋而合。他在都柏林完成了《都柏林人》和《斯蒂芬英雄》的部分内容,但代表作如《画像》《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都是在流亡期间完成的。虽然乔伊斯生在爱尔兰,流浪在欧洲大陆,但其代表作都在其它国家出版,《肖像》《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苏醒》大都是在美国或英国最先出版或连载。甚至英国法院的禁令和美国道德协会的斥责都使作家乔伊斯具有了强烈的国际性。成名后,他拒绝了许多人希望他重返都柏林的邀请(包括叶芝和萧伯纳在内),后来客死他乡。
有人认为,移民作家生活在海外,但他的根却扎在早年生活的故国,特别是那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传统。这种早年生活确有非凡的影响力,但不管是植物的根系还是人的精神之根都具有非凡的再生能力。场所的置换给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文化土壤和新的文学素材。流亡生活使艺术家得以耳闻目睹新场所的人间百态,扩展自己的体验范围。“文学体验是一种起伏不定、无穷无尽、流动变化的过程”[11]154。现代社会场所的流动性丰富了体验的流动性。艺术家走出家门,面对一个全球化、无限广阔的世界。在乔伊斯的笔下,都柏林市井男女的灵魂有时也穿着来自异域的外衣。《尤利西斯》中都柏林的大部分地名都是真实的。这常使人错误地认为这部小说完全是都柏林生活的翻版。其实,作家的创作常常糅合了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理念。《尤利西斯》当然也是乔伊斯早年生活和海外流亡的双重结晶。在《乔伊斯》中,作者彼得认为《尤利西斯》中布鲁姆与玛莎·克利富德的故事来源于乔伊斯本人在苏黎世的一段亲身经历。1918年秋,乔伊斯住在高校大街19号,他的住所背临库尔曼大街6号。在这里,乔伊斯结识了住在对面公寓的玛莎·弗莱曼施,并经常以化名与她写信。这和《尤利西斯》中布鲁姆的做法不无雷同之处。乔伊斯的许多作品如《都柏林人》和《芬尼根的苏醒》也都是他新旧体验的融合和交汇。
两种文化、两种生活的对比和交错为艺术家的审美和判断提供了参照物。艺术家对于旧场所的体验不断深化,才能成为移民作家艺术创作的素材。对故国旧人的描写和回忆事实上是艺术家立足新场所,“审视旧场所”[15]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乔伊斯的作品始终都在反思和审视故国的文化、宗教、政治和人生。这种反思得益于他国际化的人生经历和审美视角。他脱离旧场所,开辟新场所,才能获得移民作家特有的批判性。
1939年5月,《芬尼根的苏醒》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都柏林《爱尔兰时报》报道了这件事,但竟然误认为它的作者是肖恩·奥凯西(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乔伊斯认为这决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个被人策划的阴谋”[14]150。如果乔伊斯对这件事的过度关注揭示了乔伊斯阴魂不散的旧场所意识,那么他和爱尔兰之间相互陌生化的事实和被置换的名字是否也证明流亡在外的乔伊斯的外位性和对都柏林的批判性。
居于不同时空维度却息息相关的斯蒂芬、莎士比亚和乔伊斯共同演绎了自我移植的传奇经历。这种艺术家的橘枳传奇在20世纪愈演愈烈。和乔伊斯同时代的移民作家还有康拉德、贝克特、詹姆斯等,20世纪下半叶也见证了昆德拉、拉什迪、奈保尔、高行健等的崛起和成功。这些当代作家几乎撑起了世界文学的半个天空,高行健和奈保尔更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闻名天下。文学舞台就这样上演着一波又一波移民作家的传奇经历。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充斥着张力的体验并没有变化。移民作家流亡海外,寻求诗意的栖居地,但却只能品尝飘零的痛苦,经历多重的场所化过程。这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场所意识,并促使他们不停地思考自己与不同地域的场所关系。这种充满张力的、变化的、流动的存在既是他们不得已的归宿,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多变的艺术创造空间。因为国际化的场所迁移的本质特性就是超越新旧场所的简单对立,经历场所的不断置换,审视和反思自己的场所意识,正是这样的作家赢得了移民作家名讳。既然场所是价值的凝聚点,那么不断变化的、多重的、继发性的现代场所化过程也就给作家提供了多元的艺术价值场地。这是移民作家批判性、反思性和创造性的源泉所在。
[1] 万建中.周礼[M].大连:大连人民出版社,1998:260.
[2] 石磊.晏子春秋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233.
[3]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4] Buell,Lawrence.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M].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1995:63.
[5] Anderson Lorraine,Slovic Scott,O’Grady John P.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M].New York:Longman,1999:261.
[6]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03.
[7] Buell,Lawrenc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M].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69.
[8] 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中[M].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9] 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下[M].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470.
[10] 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上[M].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11] 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2] 桂扬清.埃文河畔的巨人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3] Ellmann Richard.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M].London: Faber, 1975.
[14] 彼得·科斯特洛.乔伊斯[M].何乃锋,柳荫,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5] Buell,Lawrence.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M].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2001.
[责任编辑:王乐]
2014-04-05
李巧慧(1974-),女,河南漯河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I106
A
1008-4657(2014)03-003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