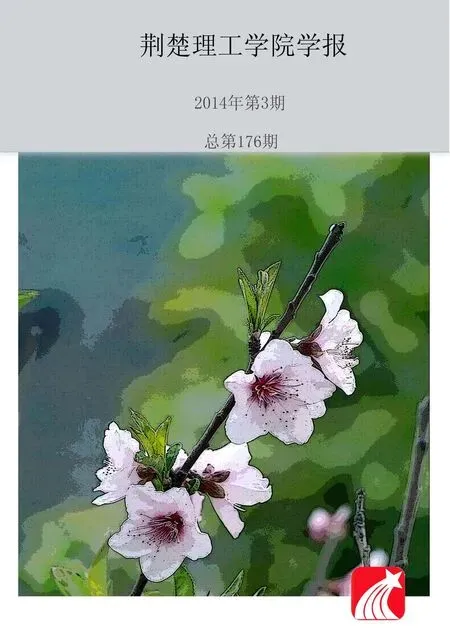“虹影式”的努力:关于女性的精神成长
——评《饥饿的女儿》
管兴平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虹影式”的努力:关于女性的精神成长
——评《饥饿的女儿》
管兴平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公认为是虹影的代表作。通过对女主人公六六的精神成长过程的叙写,作家显露出了女性主义的创作倾向,而这和作家的个人体验,所受政治的影响,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有关。小说中偏见和洞见共存,显示出了一种“虹影式”的努力。
虹影;精神成长; 女性主义
《饥饿的女儿》(1)是虹影的代表作。这部自传体的小说写的是一个私生女的人生经历。“我”是在重庆贫民区长大的。“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虽然在十八岁生日那天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生父,却对他没有一点感情。“我”的母亲早年从家乡逃婚出来到重庆做工,那还是在民国时期。她遇到了一个袍哥老大,结婚生下一女,丈夫对她打骂,她又逃出来,遇上了在四川打工的浙江人,嫁给他,生下两女两男。时代进入了共和国时期,在大饥荒年月,一政府工作人员对“我”的母亲有好感,接济她家,她主要是为了全家人的吃喝,和他产生了“爱情”。他和她有了“我”,但是两人最终是不可能在一起的,造成了“我”的身世的模糊。
小说一方面写出了“我”弄清楚这个事情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我”作为女性的个人成长史。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历史老师有了一次偷情,其中大多是由于自己的情欲冲动造成的。在这一异样的情感历程中,历史老师给了“我”某些方面的启蒙,同时他的怪异也吸引了大胆的“我”。后来历史老师死于非命,但是他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抹不掉的印痕。“我”因怀孕而打胎,后决定离开当地,并开始写作,四处流浪。在小说中作者特意表明,在大胆这一点上,“我”似乎是天生的,这种独立生长的“女性意识”,使得小说不免带上了女性主义色彩。
作者讲述了很多故事细节,明确表露出了对当时政权的不满。作者在海外或者是为了迎合读者需要而作,或者就是作家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态度。其实这两者都是存在的。前者是因为要生存(生活),为了生存,尽力争取西方读者的同情和理解。后者是因为作者本人参加过1980年代末学生活动,因而她是持有一定的政治立场的。这样一个特异的政治运动,影响了作家本人和她的精神成长,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作家本人,是她精神变异的明确开始。在她的精神生活层面上,这一点极其明显,并经常被人指认。虹影本人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政治挤压后的精神变异和冲出束缚、走向自由的宣泄结合起来,构成了虹影抵抗的、解放的热情来源。这使得她趋向于女性主义立场。
要理解虹影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创作倾向,还可以从她的其他作品得到印证。虹影在她的一部小说集《康乃馨俱乐部》(2)中有一篇小说叫《吸鸦片的女人》,可以看出写的是民国作家萧红,虽然小说并没有明确指认小说中的女子就是萧红。在作家笔下,她虽然是为性欲所控制的“坏女人”,但是值得同情。作家也写出了侠客(萧军?)的性无能,书生(端木蕻良?)的无耻。将男性写得很坏,女性充满自主性和主动。这篇作品的女性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与之相比,《饥饿的女儿》中的“我”则更带有多面的复杂意味。因为“我”的见多识广和复杂身世,“我”的精神探求和变异,“我”的情感取向与价值理念,都与前者有着极大的差异。从比较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虹影的创作理念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她的写作,带有了更为自觉的女性主义理念,摆脱了初期有意为之的写作态度,而趋向个人实际的生活经验,这更深一层的进步很能使人信服。
在一部随笔集《我们的痛苦,我们加糖》中,虹影有她自己关于女性主义的独语。关于女人看男人的一些说法。“第二,说这是因为男权社会几千年,把女人的社会角色固定在了闺帷、卧房、产房、厨房里,而女人也把自己的角色固定化了,认为外面的世界本来就是男人的世界。一句话:被男人奴役惯了,就甘于自我奴役。这么说,女人的苦恼至少男人要付一大半责任。这是修正式女权主义立场。我声明,本人属于这一派。”[1]虹影的明确的立场使得她目的明确,其小说也具有了一个独特的背景。同样,在《饥饿的女儿》中,也有这样的创作理念,但是更为突出的是,小说将这样的理念融进了关于女性的精神成长过程之中。
小说主人公六六是一个内向、沉默、孤独又有一点叛逆的女子,她的精神成长是比较特异的,也是属于不正常之列的。她孤傲,坚决果断,注重自我。这些也可以解释她的性格的形成以及在写作上所获得的成功。历史老师对她有一些启蒙,他们又有过一次情欲。可是她偏要说是自己情欲高涨主动去找他,主动担负下了这一在当时有着严重后果的责任。不管事实真相会是如何,但是可以确定六六的述说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态度。女主人公对生父的拒绝,具有长大和精神变异的双重象征。从中也可以看出虹影的写作策略:不要有根的(有血缘)的家庭、祖国,而要当前喂养了自己的西方和西方化的生活,这才是她的衣食父母。这既是一个依靠,也是一个保证。在这一路途上,她还没有走到她的目标,她还要继续向前,不知何时回头。
不能确证六六是否完全理解了西方化的生活,但是她却逐渐形成了西化的思维方式。她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生长,西方是作为六六的“他者”出现的,但是这个“他者”却是她转变的主因,她的融入和拥抱“他者”并没有考虑这一“他者”是否完全接纳她,更多的只是一种个人主观愿望。在小说中,虽然虹影极力要找六六身上的女性主义的中国源头,但是从小说内容来看是失败了的。六六的女性主义倾向主要是作家借一种“他者”的观念来观照人物,而来剥离女性成长的精神,反省精神成长过程中的因由得失。这一反思自我的取向显然是违背了中国人中的悟性、智慧观念,取得了西方化思维理念。但是小说更多的是从外在的影响来叙写六六的成长,而不是从“心学”的角度,这同样也是违反了中国化思维方式的。
作为对六六的外部观察的结果,虹影是通过外在自然环境对六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来达到。小说主人公所成长的城市带有斑驳的锈痕,在作家笔下又带有了一种遭受风雨侵蚀的人生的痕迹。“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麟,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是那么凄凉莫测。”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小说已经预示了“我”被环境的挤迫,一种不自觉的时光变幻景象潜入意识深处,有些闪着光斑,更多的是黑暗,内心的黑暗。
同样也是外部观察,时代风潮处在变化之中,作为少女的“我”也赶上了,“我”身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改变的契机。1980年代早期的服装变化和政治气氛的改变是有着内在一致的。旧时代气息的流行也无法改变“我”——“我”的少女时期是破败的,至少从外表上来看是这样。“我”的不快乐使“我”一改娃儿气,大胆接触心目中的偶像——历史老师。在作者的叙述中,女性主义者的幻想得到释放:这个历史老师——“我”心中的偶像和爱人将自己当作朋友看待,给“我”讲了许多报纸上的事情(现实的和政治的)以及对之进行的分析,这些扩展了“我”的少女空间,也说明了“我”是早熟的。当然,作家也将少女的性启蒙对象指向他——这个偶像和恋人。历史老师和他的启蒙都具有父权的象征意味。送了“我”一本书:《人体解剖学》。“我再低下头来,看生殖器官图,我第一次感到我的阴唇好像在微微启开,阴道里像有一条舞蹈的火蛇,扭动得使我难忍难受。”这种女性表白的提前到来使得“我”的成长更带有了富于女性主义色彩的意味:“我”在接受父亲的教导之后又彻底地颠覆了父权。
作为女性精神成长时期的支撑和陪衬,历史老师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说明了女性主义的心理和精神痕迹的昭然若揭。虹影设置的这一偶像和恋人形象既有着父权意味,又有着情色意味,更有着政治意味。历史老师的启蒙从中国文化的立场来看是带来了道德沦丧的。但是偶像对于自己关注的对象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这种欲望就是父权意欲。而同时虹影将主人公“我”的迎合看成是少女长大成人的必经一途,尽管大胆出格,但是切合西方女权主义思路,其中的情色意味可以回溯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少女还书时的精神优势进一步说明女性试图居于上风的企图。更为重要的是,作为1980年代的开放的中国,其形象是迎合西方的。而历史老师给“我”讲遇罗克,给“我”看《今天》油印刊物等也是深具政治风险的。少女的精神成长过程因而带有了融入和反抗的双重意味,虽然可能这种融入和反抗的对象并不同一,但是明显的也是女性主义的反叛主题。历史老师的自杀结束了少女的理想生活,她处在失败之中,但是她的精神开始真正长大。
多年以后“我”在流浪中偶尔回家一次,见到了母亲。生父患癌症去世,父亲和母亲也已分居。“我”夜晚陪着母亲,“鸡叫第一遍,江上轮船的鸣叫零零落落,传到半山腰来,像有人在吊嗓子那么不成调地唱着,一遍又一遍,都不满意,又重新起头。”这场景已经有一些陌生的感觉了。“我”已经脱离了“母体”,开始了“我”自己的生活道路。小说最后写到“我”作为五岁半的小女孩在城市雨中的奔跑,“我”的跌倒,爬起和继续奔跑的寓意是明显的。而口琴声传到耳边,“就像在母亲子宫里时一样清晰”,既是女性独白,又是女性宣示,“我”已精神长大。
与另一位女性作家朱晓琳比较起来,虹影的姿态完全相反。朱晓琳在国内教书,偶尔到国外生活,她忘不了歌颂中国文化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偏向;虹影与严歌苓有相似的地方,严歌苓有一个时期的写作也是极力取悦于西方,要表明自己一贯、彻底热爱西方的态度,让人感觉她的写作根本就和国内、政府没有任何关联,好像自己不是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她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少不了受到政治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会让作家心灵上留下痕迹,精神上发生改变。相比较而言,虹影要走得更远。最突出的是她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态度,尤其作为一个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女作家,虹影对政治和历史的解读应该是具有很强的社会冲击力的。但是其对历史(大饥荒,文革)的书写又认同了一些海外研究者的看法,让人看不出她有什么自己的独特见解,在这些方面她又表现出了愤愤不平,这一点格外突出,说明了虹影的女权主义理想中的富于情绪化的一面。
作家写中国当代历史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特体验和关注角度,好深入到历史深处并保持一定的中性客观立场,而且要是“自己的”。就此而论,虹影的这部小说深度是不够的,尚缺乏历史的穿透力和撼人心魄的力量。
联系以上所论,读虹影这部小说感觉到有浓重的政治气味,作家的政治偏向太明显,因而写作理念有概念化、机械化倾向。小说中一些情绪化的和变态心理行为的出现,也说明了作家有着足够的小家子气,而对现实缺乏全面理解和观照。偏见会影响小说家的写作水平,洞见会消除盲视,带来启蒙的理性之光。《饥饿的女儿》中一部分偏见和一些洞见共存,显示出了一种“虹影式”的个人努力。不过,面对这一位抒写女性本位的作家,我想要说的是,这样的小说(带有一些个人扭曲记忆的)和国内一般写庸俗现实的作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一个取悦此,一个取悦彼。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一致。或许,这样的小说并不是好的小说,或者可以称为不好的小说?
注释:
(1)虹影.饥饿的女儿[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虹影.康乃馨俱乐部[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1] 虹影.我们的痛苦,我们加糖[M].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143.
[责任编辑:王乐]
2014-04-01
管兴平(1969-),男,湖北潜江人,长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I206.7
A
1008-4657(2014)03-00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