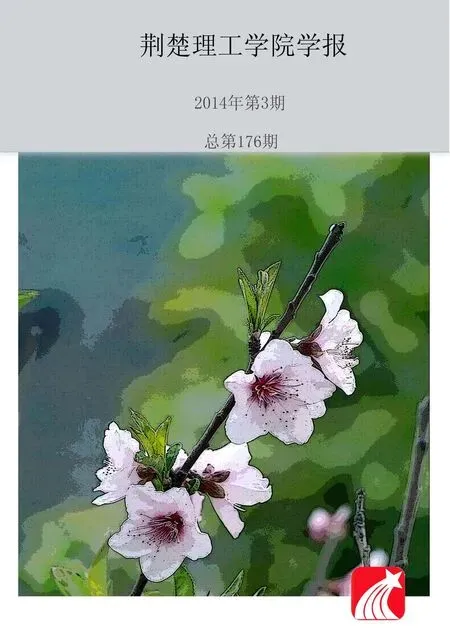司马迁《史记》对于传记的史性再造
王斌俊
(中国青年出版社 书刊审读室,北京 100708)
司马迁《史记》对于传记的史性再造
王斌俊
(中国青年出版社 书刊审读室,北京 100708)
作为《史记》重要体例、重头内容的纪、传,是从属于记史任务的。司马迁赋予纪传以鲜明的史性品格,完成了传统“传”类文章的一次升级、再造,促进了史性传记的诞生,为我们今天写作和光大史性传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鉴戒。
《史记》纪传;史性传记;传记写作
如今,世面上对于传记的概念理解比较混乱,记写历史上、生活中真人真事时,所持的写作原则亦有分歧。鉴于《史记》的巨大影响,再度审慎地研究司马迁史笔之下的纪传,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很有裨益。
传记概念和写作上的乱象,涉及怎么去看《史记》纪传体例。是否能将其理解为“文学(性)传记”,不能。那它可是那种纪念性、“歌德”式的记述人物的文字?肯定也不是。《史记》的纪传有着特别意蕴,是司马迁以伟大史家的思想光芒予以观照、予以改造了的传记,是在记文属性上有了提升、完善的传记。司马迁赋予了原生“传”类文章以宝贵的史性品质。
一、《史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欲辨《史记》的纪、传,先从《史记》的著作性质说起。
司马迁想要写的是什么样的书呢?是史书。其目的,一言以蔽之:记史论世。其中又以记史为最基本的任务。他完全以此为宗旨、目标来结构和安排该书的框架、结构,多方面、多体例地展现历史内容和自己的评说。从《史记》宗旨、结构和所取内容这些大的方面着眼,而不是囿于局部视野、细枝末节的眼光,就可以明了《史记》确实是部伟大史著。
司马迁记史,就是记载华夏这块大地人类社会至汉代以前的所有历史。人类历史即社会运动发展过程;故历史首先就是集为群体的人的活动。这种活动既以群为之,也以类为之,且群与群、类与类之间还必然发生交流互动关系。在司马迁记述的历史阶段,人类活动总是突出表现为居于万众之上的帝王的活动,故司马迁创设“纪”的体例记之。“纪”既有记录的意思,也有纲纪的意思,反映着把王权当做社会纲纪、总揽的观念。因此“纪”为先,也为上、为总。
除了最高的统治王权,社会运转和国家维持,自然少不了上到文臣武将、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的活动。各色人等,群分类聚,皆为历史活剧的重要角色;各种行作,分门别类,都是社会舞台关键舞者。故司马迁以“传”的体例记之。“传”既有记载之义,也有留传(chuan,阳平声调)之义,表明司马迁认为所传之人物、之行当,都有功于社会,有利于民族,值得入史记之,传诸后世;或于社会、于历史有密切关系、重要影响,也须随史传告,警戒后人。较之“纪”体,“传”不仅载人,还用以记行业、少数民族、经济部类等,这是个值得重视的变化和特点。说明“传”体的设置,虽借助于沿袭,内涵却已有嬗变;皆是缘于记史的需要。
由于司马迁作《史记》就是为了记史,且以记述大通史来结构、组织《史记》的文本书写,所以作为全书重要体例、重要内容的纪、传两大板块,完全为记史服务,是从属于记史的。于是,便赋予了纪、传以鲜亮的史性品格,铸就了《史记》纪、传的创新价值和独特的体裁地位。
二、《史记》中纪、传的史性特征
《史记》纪、传的历史属性特征,可从司马迁相关写作的一“有”一“无”来得到证明。有即增,也就是取纳;无即减,也就是摈弃。
一“有”,是《史记》记人物述行状有了否定性内容、负面评价。此前,尽管名称不同,但凡是传记类文字,正如杨正润先生所言,是出于纪念、缅怀而生发的,“起源于人类本能的自我纪念”[1]。一概不会提及纪念对象也就是所传人物的缺点、短处等负面内容,正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就此类文章的体裁、目的和用途而言,这样做,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也许就是这样一种传记在今天也还不绝如缕的缘由吧。但是,《史记》纪、传却一改这种做法,既把人物的正面写足,也不隐讳其负面,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客观公允予以记载和评价。司马迁之所以能脱开旧的窠臼这样做,皆因他是从记史出发,遵循了历史属性,是历史记述的客观真实性根本要求统一制导了记人叙事的真实、客观。
一“无”,是指《史记》纪、传几乎没有通常“传”类文章所要记的个人性、私密性很强的内容,个人及家庭生活细枝末节的“故事”。司马迁记人时有意识地裁减了这类素材,剪裁刀服从于记史的大脑,取用材料的砝码显然向关乎社会大事情、大活动比如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教方面的内容倾斜。也就是十分关注具有社会性,体现出种种社会关系,超出个人生活、私密空间的对于国家、社会和群体具有意义的内容。这个一“无”并非取决于文章学上的材料“剪裁之法”,而是由《史记》记史的根本宗旨决定的。《史记》整体撰写旨趣并不是围绕各个人物展开结构,全面立体而细腻地去记述个人的历史过程,而是将对于各色人等的记述和评价,完全、彻底地纳入到历史宏大叙事的框架之中,亦即完全以记史为动机、为目标、为主轴来记述人事(人之事,事中人)。
上述一“有”一“无”恰恰完成了《史记》的一个“大有”:《史记》纪、传具有完全的历史属性。这也就是统称其为“史传”的内在依据。正是这个“大有”,开了史性传记之先河。
司马迁这样做,就当时区别于通常的“传”类文字,赋予纪传以史性,将传统“传”类文章转型,为其记史而用这方面的意义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否则,没有这一“有”一“无”的超越,也就实现不了转型升级。但转轨之后、得具深沉史性的纪传被后世人从史著中分离出来(各种“正史”的纪传沿用《史记》体制,仍属记史,是直接为记史服务的),定型为独立的史性传记(大多为史家所撰),再注意择记传主的生活细节、个性细故等,以使传主形象既真又切,则是另一回事了。这是在史性传记内部的一种生长、发展。
司马迁本来并无心思改换传统传记的属性和写作原则,更不是特意要创立传记新写法,但他留下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无意间开创出传记写作的一片新天地,创设了传记的一种新写法。而且不仅仅是写法上的改变,更是作传理念、原则亦即传记观上的一次遽变,传记体裁的一次升级,传记属性的一种完善和进步。实际上是创制了史性传记。它完善、提升了起初的“道德性传记”、“礼义性传记”或“纪念性传记”——那种只歌功颂德,评功摆好,情愿善意、“忠孝节悌”地为尊者贤者亲者友者讳的传记类文字。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中论道:“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2]75此论注意到了“述者多方”这方面的别异,而未能发现和揭橥不同传记性质上的区别,也没有关注到《史记》在传记属性上所发生的质变,认为所有传记在体裁属性上差不多都一样,这是不够深刻、不够明达的。
三、《史记》纪传体的价值和意义
司马迁开创的史性传记,对于真实反映历史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理性的重要内容,具有非凡的社会意义。
分析一下《史记》纪传对于记史的作用,对于表达历史理性的作用,可使我们领略其价值和意义,也给予我们今天写作史性传记以原则性指导。
司马迁记史有三大目标,按他的话说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首先,看司马迁纪传与第一个目标的关联。在“天人之际”的探究记述方面,是以“人事”(与“天命”概念相对)为重、为要、为主的,重心落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上。在“天”和人(主要是华夏大地的人类群体)关系上,司马迁虽未完全超脱出“天道”“天命”概念的束缚,但也只是比较虚渺地绎了“天”的抽象概念、人类早期臆想和猜度的“天”和人类的关系。他把重点还是放在了接地气的人世凡间亦即人类社会,具体地说就是那个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华夏民族,重笔浓墨地突出人间社会中的各类人物,包括最高统治者、最高层的政治权利集团和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之类,这就抓住了社会运动的主体和基本动力源。近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这是最为概括和抽象的近现代理性表述。在较为容易被感知的层面上,这一基本矛盾每每都表现在人类的不同阶层、不同类别、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上。人和“天”的关系,即使是在人类早期,也是表现在世俗社会中人类阶层、社会分工结构性群体之间的关系,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变化上的。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在华夏人类刚摆脱蒙昧野蛮的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门槛不久,就在历史观层面发现和抓住“人”这一历史的主体,社会矛盾运动的动力源,是站在了时代精神前列的,非常难能可贵,很了不得。新兴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积极的士人人格心理特质和精神风貌,还是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催生了司马迁在精神思想相当程度地独立、自觉、自主的情况下这样的学术开创和思想建树。司马迁的史记史学紧紧扣住“人”大做文章,路径方向正确;范围和构成也广泛、全面,视野开阔;更关键的是,他并不是站在极少部分人的立场,而是站在比较客观、超然的真正史家的立场,也就是对于人类各阶层关系的全视角、全覆盖的立场。这是进步的立场和科学的角度,从而生成正确的治史方法与态度。惟其如此,《史记》纪、传才达到了“以史带人、以人见史”的突出效果。这种以人为本、史中记人、人中见史的做法,就是史性传记通常须要遵循的原则。
其次,分析一下司马迁纪传与第二目标的关联。“通古今之变”即客观、真实地记述全部历史即通贯历史,揭示历史演变过程带有恒常性、规律性的道理。为此,《史记》以纪(即帝王传)、传(包括“世家”“列传”,“世家”实为诸侯传)为主体,为重头内容。“书”体中亦有大量记人论世的内容。所谓纪,初有“能起纲纪作用的人”之义。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本纪》中说得好:“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2]57“传”字本有传扬、流传之义,转音又指“文字记载”。司马迁采用这二词作为他记史两大手段的名称,作为煌煌历史巨著《史记》两大重头体裁的铭牌,赋予纪、传二词新的内涵,大大拓展了“纪传”概念的意义,创设了纪、传两种记史的体例。实际上也就是更新、再造了传统的传记体裁。其实,在《史记》中,从记人载事,记述人群社会活动,借以反映客观全面、鲜活生动的历史的角度看,纪、传可谓一体。《史记》的“纪”与“传”除了在记述对象上作了区分之外,在记人论世的原则、标准上并无不同。纪传体在史书中对于记史的直接作用自不待言了;即使它从古代史书体制中脱胎出来,自立独行,被称作“传记”,也仍然保持其史性,仍属历史范畴,仍为历史著述的组成部分,起码也能作为重要补充。
最后,再看看纪传体与司马迁第三个目标的关系。“成一家之言”这方面,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成就了《史记》文本本身,包括这一巨著所呈现的结构体系,内容铺陈及其意义揭示,思想倾向和观点表达,也就是司马迁的富有独创性、标新立异性,体现自主认识和独立判断的历史“一家言”。二是在史观、史见这一更高级层面上,更带有指南、统驭和引领意义上的“一家言”。这个“一家言”未必直接形诸文字,却完全是文章著述的魂,体现于《史记》的字里行间。司马迁的这个“一家言”,反映了他进步的史学思想、治学态度和根本方法,是代表学术进步方向、站在了当时思想文化的高地上的。《史记》纪传体例的创设与精彩书写,无疑得力于司马迁高屋建瓴的史观史见。没有后者,也就不可能有纪传体创新和传记体裁再造。今天的我们,写作和光大史性传记,也必须重视在史观识见上的修为,争取以处于时代精神前沿的史观识见来驾驭传记文本的构建,驾驭自己的史笔文才。像司马迁的纪传那样,既保持传记宝贵的史性品格,又焕发出熠熠闪烁的文采。
司马迁以大家治史的如椽巨笔,赋予“传”类文字以深沉的史性,向记人物述行状投以历史理性之光,在成就中华首部大通史、全景史的同时,孕育了史性传记之婴,为后世提供了新型传记范本,一种在内里就有别于、独立于传统“传”类文章的新品类,为人物传记走向“科学传记”打开大门,开辟了广阔空间。史性传记对于真实反映历史有重大意义,对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具有更大价值,曾发生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还在人格化的历史描述方面更能展现历史的褶皱,过往社会生活的腠理。现实表明,这种发轫于司马迁史笔之下的传记新品类,越来越在更讲理性、更讲科学、更加崇真求实的时代大行其道。史性传记,虽道远任重,却前途光明。
[1]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1.
[2] 刘知几.史通[M].姚松,朱恒夫,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3] 司马迁.报任安书[M]//[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5.
[责任编辑:王乐]
2014-04-20
王斌俊(1957-),男,河北大名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
I207.5
A
1008-4657(2014)03-0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