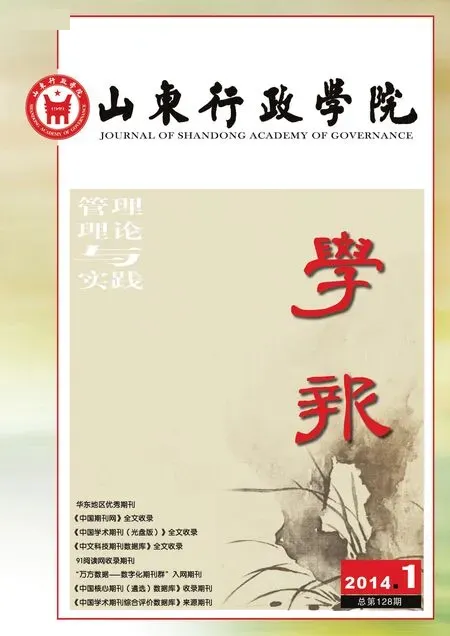新刑诉法视野下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防控
陈玉忠
(山东行政学院,济南250014)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资源的主要获取机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效行使防御权的保证和诉讼理性的体现[1]。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和完善,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后以辩护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在立法上强化了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到律师业务,新《刑诉法》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不是降低而是有可能加大了潜在的职业风险,对此必须认真对待、加以重视。
一、新《刑诉法》律师调查取证制度的改进
新《刑诉法》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侦查阶段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但有很大限制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业务限于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申告以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全面确定。律师以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出现是“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原第33条),相应地,辩护律师自该阶段开始享有阅卷权、调查取证权。2012年新《刑诉法》第一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是以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出现(第33条),也就是说将律师的辩护人身份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按照辩护人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第35条),辩护律师取得了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利。
当然,与刑事诉讼其他阶段相比,律师在侦查阶段时的调查取证权是有限制的,或者说其内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该法第36条对侦查期间辩护律师的业务范围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一方面,与原第96条相比,辩护律师不仅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而且增加了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的权利(第159条更加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阶段有提出辩护意见和要求的辩护权利);另一方面,按照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案件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至少在内容方面,好像又没有涉及到,立法上模糊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体制上的障碍。该法第40条规定了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佐证了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是有限制的、部分的,涉及到其他方面的调查取证权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同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1条同样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侦查过程中辩护人拥有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的权利。
新《刑诉法》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后以辩护人的诉讼法律地位,对于我国法制建设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及时、有效地搜集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将其告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弥补侦查遗漏,使不应入罪的案件在尽早诉讼阶段终止,在某种程度上说,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对于减少冤假错案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也必须认识到,与其他诉讼阶段相比,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还是部分的、有限制的。那种盲目地认为律师调查取证权在不同诉讼阶段是无区别的观点是片面的,会随时让律师的职业风险不期而至,甚至从天而降,为律师本人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二)新《刑诉法》实施后,律师调查取证的职业风险是否有所改观还须进一步观察
新《刑诉法》并没有排除律师调查取证的职业风险,但力图从小处着手,降低辩护律师的职业风险,为刑事辩护创造良好的环境。
首先,新《刑诉法》第42条与1996年刑诉法38条相比,主体由“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形式上看,力图弱化“律师伪证罪”的特定主体的窘况——“任何人”而不是特指规范律师的行为。当然,司法实践中该条与刑法第306条就像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真能借此改善辩护律师的职业环境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幸事。
其次,在界定“律师伪证罪”的客观要件“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中删掉了“改变证言”,直接规定“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也就是说,从字面上解释,“改变证人证言”行为并不是构成律师伪证罪的客观要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引诱证人作伪证”、“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涵盖、包括“改变证言”行为,这项修改更多在字面上进行规范而已,实践中律师的职业风险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
再次,在新《刑诉法》第42条第二款,增加了“律师伪证罪”承办机关的规定,“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以及“及时通知律所或者所属协会”。2012年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细化规定,“以外的侦查机关”是指“上一级侦查机关或者由其指定其他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同时不得指定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的下级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立法意图运用“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公正的原则,通过在制度上回避原侦查机关达到对“律师伪证罪”立法规定不进行大修改的基础上运用程序公正改善律师执业大环境的目的。当然,实践中通过上级监督下级的途径实现“律师伪证罪”责任追究机制的公平正义,有待于今后实践观察。
二、刑事律师调查取证职业风险的防范措施
如何避免因调查取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这是一个理性的职业律师必须思考和研究的现实问题。近几年,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过程中,因涉嫌伪证罪被拘留、逮捕甚至判刑的新闻屡上报端,例如李庄案、北海四律师被拘案等。在如此大环境下,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尤其要充分意识到调查取证存在着极大风险,一定要慎之又慎,安全执业总是第一位的。
(一)律师调查取证要时刻绷紧风险防范意识之弦
第一,不要直接向被害人或者其家属或者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以免被反诬,如确属必要,则尽可能多的向法院、检察院申请收集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收集证据。对于律师能够识别的伪证,不要交给法庭,防止陷于当事人的圈套。有些被告人或者其家属为了“捞人”不惜一切手段,例如事先“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然后请律师调查取证,或者让律师把证人证言交给法庭,结果可能是律师栽进去。
第二,律师取证要有程序意识,严格遵守程序法规定的取证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取证,但是前提是必须经得相关人的同意才可以进行。律师制作询问笔录,就必须记载证人是否同意,就必须亮明律师身份,不然就会构成自己执业的危险[2]。所有调查材料均应有律师对被调查人要求如实提供证言、作伪证应负法律责任和被调查人同意接受调查的记载,在调查笔录制作完毕之后,应交证人仔细核对,并在修改处加盖证人的印章或证人按指纹确认,最后由证人签名或盖章,同时签署或由他人代书说明“笔录已看过或已向其宣读过,与其所述无误”的意见。
第三,律师取证时不宜一个人,至少由两名以上的人员进行,可以由一名执业律师和一名律师助理进行,以免证人将伪证责任推给律师而无旁证。一方面,律师两人调查可以相互配合、相互监督,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避免违法调查取证;另一方面,可以相互进行照应,一旦发生风险时,可以相互证明调查取证工作的合法性。
第四,律师调查取证时能够录音录像就录音录像,请公证处一起固定证据也是个不错的办法。在中立的公证人员在场见证下,提供法定的公证书证明,很大程度上可以肯定律师调查取证的合法性。但是,不能将公证见证和录音录像作为非法取证的手段,认为有公证和录音录像就律师就可避免风险了,纵使做的再天衣无缝,也终有被查究的可能[3]。
(二)遵守职业纪律,律师调查取证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新《刑诉法》赋予律师自侦查阶段开始就以辩护人诉讼地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在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中,可以“不被监听”地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及其案件相关情况;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这些内容在未公开之前,根据有关国家法规的规定,绝大部分属于国家秘密(例如,公安部《公安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等)。有资深律师得出一条结果:刑事案件中,侦查情况和案卷材料均属于国家秘密,不得泄露[3]。由此可见,每个刑事案件,律师调查取证的案件有关内容均可能成为泄露国家秘密罪的规范内容。如律师从检察院复印案卷后,在接待当事人过程中,当事人趁律师不注意时,用手机轻易拍走几份证据材料,那么律师有可能陷于为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嫌疑。因此,律师在调查取证工作中了解到的犯罪嫌疑人的详细情况、会见笔录、在逃同案犯、关键证人、关键证据的重要内容不能告知家属,让家属查阅、复制和摘抄,一旦发生家属利用得到的案件信息串供、毁灭证据、证人改变证言、案犯逃匿等严重结果,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的风险随之而至。在遵守职业纪律与家属沟通方面,一定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要向家属解释律师的职业道德,国家秘密的法律规定,律师违法的后果,又要研究提高与家属的沟通的技巧和水平,创造和谐、安全、愉快的执业环境。
(三)对于风险大的主观证据一定要慎之又慎
新《刑诉法》第48条规定的法定证据中,物证、书证、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客观性较强,可变性较小,律师取证的风险较小,律师可以依法谨慎取证。例如证明被告人不在现场的机场登机记录、贪污案件需要取证的会计账簿、银行汇款凭证、工商局登计档案,律师应当积极、尽力地依法调查取证。
对主观性证据而言,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客观性差、可变性强,律师一定要认识到只要接触一定就有风险。对于侦查机关已经调查过的证人,律师要认真审查其是否改变证词,其改变证词的目的是否系有意包庇犯罪嫌疑人而作伪证。如果确实存在作伪证的可能,则应当立即拒绝调查。如果证人对犯罪嫌疑人作不在场的证明,而卷宗内有数人已证明该犯罪嫌疑人在场,则要审查证人是否存在作伪证的可能性[3]。
对致力于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而言,调查主观性证据可能是个“囚徒困境”,不取证没把握,取证又有风险。对一个有责任心的刑事律师而言,始终存在一个职业道德与职业风险相纠结的两难境地。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既规避风险,又能取证?律师对人证最好的解决之道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四)控方证人尽可能少碰,律师可以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为宜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为实现上述职责,律师不可避免地在刑事诉讼中千方百计地收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研究、琢磨、提出对其有利的各种理由。而控诉机关与此相反,公诉人为了追究控诉的成功,也总是寻找列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和理由。按照目前的体制,公检法办案人员的业绩考核与案件有着重要的关系,“错案责任追究”使得公安拘留、逮捕的案件,只要不起诉就是错案,起诉了不做有罪判决对检察机关也是错案。错案影响办案人员的福利、待遇甚至政治生命,这就是刑事律师职业风险存在的一个大的制度环境。其实,“律师轻易就调查控方证人,在香港也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不会定罪,但会惩罚律师”[4]。大部分国家强调一旦发生争议,证人笔录就没有法律效力,证人要出庭,律师遇到这种情况不会去调查,而是申请法院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因此,刑事诉讼中证言的笔录中心主义与不合适的司法办案人员奖励和惩罚机制纠缠在一起,使得律师一碰控方证人,面临的风险可想而知。笔录中心主义产生的大问题,必须用证人出庭来解决。律师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通过法庭询问、质证达到辩护的目的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如果多次申请证人出庭,法院依然未予采纳,对其采取相应的对策,立即以真伪难辨为由请求法庭排除证言笔录。
[1]贺红强.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局与突围[J].海峡法学,2011(4).
[2]段建国.大律师法庭攻守之道[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徐宗新.刑事辩护实务操作技能与执业风险防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8,93,114.
[4]陈瑞华.刑事辩护的前沿问题[EB/OL].华律网,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