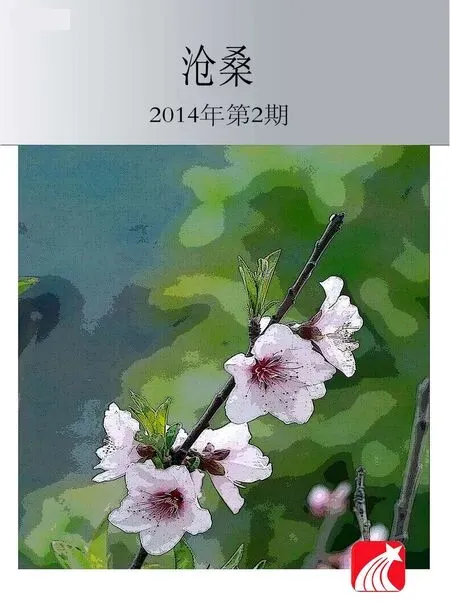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司法审理程序
刘军
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司法审理程序
刘军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核心,也是皇权赖以维系的坚强柱石,在政权建立及巩固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故而成为凌驾社会之上的特权群体。但是,北魏试图将宗室行为纳入国家法制轨道,严格限定宗室罪案的审理程序和运作原则。绝大多数宗室案件的处置与异姓官贵并无差别,体现家国一体,昭示统治者执法之公允。最大限度压缩宗室的法律特权,是北魏政权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北魏 宗室阶层 司法程序
法律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阶段的主要标志,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拓跋鲜卑从神元帝拓跋力微至道武帝拓跋珪,正是由血亲部族向阶级国家跃进的关键时期,以“言语约束”为主要特征的部落法逐渐被代表王权尊严的成文法所取代。史载,穆帝拓跋猗卢“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1](卷1,P9)。昭成帝拓跋什翼犍“法令明白,百姓晏然”[1](卷111,P2873)。道武帝拓跋珪则奋先世之余烈,在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将建立封建法统的历史任务继续向前推进。北魏建国之后,历代皇帝都试图将统治集团成员的行为纳入到既定的法律框架之内,以实现其身份地位的历史转变。贵为皇亲国戚的宗室阶层作为代北贵族集团的核心力量,自然是法律约束的主要对象。笔者的构想是将宗室这个特殊社会群体所引发的法律纠纷设置在北魏国家法制变迁的整体背景下,围绕其法律地位及司法运作程序进行宏观整体式考察。
本文论述的时间起点设在道武帝建国前后,终点则是北魏统治后期的孝昌年间,这是因为“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1](卷111,P2888)。国家法制已经严重偏离了正常轨道,我们自然无法找寻有关宗室法律问题的特点。由于史料的局限,供解剖分析的案例大多属于宗室上层,而对于普通宗室成员的日常法律事务,迄今为止知之甚少,这使相关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北魏建国之初,国家体制胡汉杂糅,简略粗糙,而且多因事立官,缺乏起码的稳定性。司法制度则尚未完全摆脱部落行国阶段的原始特征,使得成文法典的精神与部落的裁判传统掺杂混淆。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很难确知北魏前期审理宗室案件的完整过程,只得通过对当时司法制度的简略了解来进行推测。北魏建国之初,除三公郎中王德修订成文法典外,统治者还效法汉晋创建了一套比较简陋的司法规程。《魏书》卷113《官氏志》载,道武帝当初设有名为“白鹭”,主伺察的候官。且于天兴四年(401)九月以外兰台御史“总属内省”。此外可能还设有负责监察的专门机构御史台[2](P244)。属于禁卫系统的内侍内行诸职也兼负纠举之责,如安颉“太宗初,为内侍长,令察举百僚。纠刺奸慝,无所回避。尝告其父阴事,太宗以为忠,特亲宠之”[1](卷30,P715)。有学者推断:魏初内行系统掌握了监察大权[3](P70)。至于审判权则主要归于“坐朝堂,决刑狱”的秉政大臣和与之职权类似的“三都坐大官”[3](P125)。当时的司法审理程序大致是“论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1](卷111,P2874)。总之,秉持“尚壹刑”主张的北魏早期,宗室的法律事务不大可能超越当时司法运作的基本规程,相关案件的审理主要局限在国部,于内侍内行系统展开。
直到孝文帝太和年间的汉化改革,国家司法才算转入正轨,形成较为完善、固定的制度。《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上·广陵王羽传》载:“后罢三都,(元)羽为大理,加卫将军,典决京师狱讼,微有声誉。”大理,即九卿之一的廷尉全面接管国家司法,取消胡汉分立状态,标志着北魏司法全面走向汉化,这是拓跋族进化的有力证据。案件的审理程序随之正规化,《魏书》卷77《高崇传附高道穆传》载高道穆奏疏:
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按,一如旧式。庶使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
办理宗室案件也必须严格遵守此程序,首先是御史中尉等监察官员的主动纠举,而后由廷尉等司法官员量刑治罪,最终奏报皇帝批准执行。同书卷21《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载,御史中尉崔亮举奏北海王元详贪贿淫乱诸丑行,“请以见事,免所居官爵,付鸿胪削夺,辄下禁止,付廷尉治罪。”这套程序与惩办庶姓官员并无不同,《魏书》卷三三《王宪传附王云传》载具体案例:“(兖州刺史王云)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财货,又取官绢,因染割易,御史纠劾,付廷尉。”高贵的宗王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的宗室成员。当然,宗室案件的审理情况复杂各异,因此我们只能就相关环节展开具体的分析。
一、按验弹劾
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很多宗室案件的处理是以御史中尉弹劾起始的。御史中尉,太和十七年前《职员令》定为正三品上,太和廿三年后《职员令》改为从三品。御史中尉是北魏中央最高监察官员,负责纠举各级官僚的不法行为。纵使皇亲国戚,也不能摆脱御史中尉的鹰鹯之逐,故而时人有“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皆得纠察”的观念[1](卷14,P354)。而皇帝对于御史纠察宗室的权力是予以充分认同和尊重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见《魏书》卷77《高崇传附高道穆传》:
(孝庄)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执赤棒卒呵之不止,(御史中尉高)道穆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深以为恨,泣以诉帝。帝谓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私恨责之也。”道穆后见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道穆免冠谢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独于公主亏朝廷典章,以此负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谢朕。”
此事虽关系皇姊的颜面,孝庄帝却并未姑息迁就,高道穆则因秉公执法得到了皇帝的理解和赞许。御史中尉纠举宗室非违,属于“公事”,宗室凭借身份的优越感,在潜意识中难免会将事态向皇族“家事”的方向导引。但在北魏最高统治者看来,“家事”逊于“国事”的原则绝不能存在任何的含糊。高道穆的事例并非“主圣臣直”式的政治说教,它反映的乃是冰冷的法律准则。再将时间向前推移,宣武帝欲处置辅政大臣叔父北海王元详,“召中尉崔亮入禁,敕纠详贪淫,及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专恣之状”,元详遭拘押后,又“示以中尉弹状”[1](卷21,P562)。可见,宣武帝不是利用生杀予夺的君权直接置元详于死地,而是将他引入正常的司法渠道进行惩治,这无疑是北魏后期制度固化的必然结果。御史中尉对宗室成员的弹纠不会受其地位高下的左右,即使孝文皇弟、都督中外诸军事、赵郡王元干“贪淫不遵典法”,还是为御史中尉李彪纠劾[1](卷21,P543)。至于一般的宗室成员更是不在话下,所谓“皇太子以下违犯宪制,皆得纠察”的原则的确被切实地执行了。北魏督察宗室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御史中尉对宗室的监察范围相当宽泛,而职务性犯罪是主要对象。比如河南尹元融“性尤贪残,恣情聚敛,为中尉纠弹,削除官爵”[1](卷19,P514)。齐州刺史元诞任上贪暴,为民所患,后为御史中尉元纂所纠[1](卷19,P448)。秦州刺史元琛,贪暴不法,“为中尉纠弹,会赦,除名为民”[1](卷20,P529)。冀州刺史元遥对胡商设籍征税,以充军用,“胡人不愿,乃共构遥,云取纳金马。御史按验,事与胡同,遥坐除名”[1](卷19,P445)。出帝时,“(元)世俊居选曹,不能厉心,多所受纳,为中尉弹纠,坐免官”[1](卷19,P488)。宗室官员用人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御史还要追究其连带责任。孝明帝时,司州牧、汝南王元悦任用亲信丘念操纵选举,御史中尉郦道元缉捕丘念,同时参劾本主元悦[1](卷 89,P1926)。
北魏宗室源于生藩鲜卑,本无纲常名教的约束,入主中原后阖门无礼。这与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贯彻华夏纲常名教的初衷背道而驰,对其巩固统治显得尤为不利。因此北魏格外重视宗室对封建礼教的践行情况,御史中尉是这方面的主要监督者之一。《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上·赵郡王干传附谧传》:“(元)谧在母丧,听音声饮戏,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同书卷32《封回传》载,尚书右仆射元钦与从兄元丽妻崔氏通奸,被时任领御史中尉的封回上书弹劾。同书卷19《景穆十二王下·安定王休传附愿平传》:“(元愿平)坐裸其妻王氏于其男女之前,又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御史中丞侯刚案以不道。”
宗室犯罪也可由案件当事人通过正常的诉讼渠道上达有司,以便对责任人进行惩处。《魏书》卷18《太武五王·广阳王建传附渊传》:“(广阳王元渊)坐淫城阳王徽妃于氏,为徽表讼。”同书卷20《文成五王·安乐王长乐传》:“(定州刺史、安乐王拓跋长乐)鞭挞豪右,顿辱衣冠,多不奉法,为人所患。百姓诣阙讼其过。高祖罚杖三十。”北魏充分维护投诉者的权益,不会因为宗室的缘故徇情枉法。
二、议罪量刑
宗室罪行事发,在遭到弹劾纠举之后,就会面临依法惩处的问题。北魏对宗室进行处罚的权力主体主要有三:廷尉、皇帝和宗室族议。
自秦汉以来,作为九卿之一的廷尉,始终是国家最高的司法官员。中古时期,尽管国家权力开始从九卿向三省转移,但是廷尉的职权还是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北魏情况依然如此,据太和十七年前《职员令》,廷尉卿官居正二品上,太和廿三年后《职员令》改为正三品。我们发现,孝文帝之后廷尉审理宗室案件的事例很多。《魏书》卷65《李平传》载,宣武帝时,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谋反,李平出征前言道:“臣愉天迷其心,构此枭悖。……如其稽颡军门,则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则鸣鼓衅钟,非陛下之事。”同书卷19《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澄传》载,孝明帝时,司州牧、高阳王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举奏:“请以见事付廷尉推究,验其为劫之状,察其栲杀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获雪。”京兆王元愉是孝文皇子、宣武皇弟,高阳王元雍乃献文皇子、孝明叔祖,且“入居西栢堂,决庶政”[1](卷9,P221),二人身份可谓贵重至极。即便如此,有罪也须经过廷尉的环节,可知廷尉审理有罪宗室在当时是通行的惯例。北魏的廷尉卿中不乏铁面无私、刚直不阿者,他们对宗室罪案一视同仁,在按验定罪过程中绝无丝毫宽贷之处。同书卷57《崔挺传附崔孝芬传》:“(崔)孝芬为廷尉之日,章武王(元)融以赃货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同书卷66《崔亮传》:“徐州刺史元昞抚御失和,诏(廷尉卿崔)亮驰驿安抚。亮至,劾昞,处以大辟。”又同书卷77《高崇传附高谦之传》:“正光中,尚书左丞元孚慰劳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还,置孚归国。事下廷尉,卿及监以下谓孚无坐,惟谦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书同卿执,诏可谦之奏。”可见,在廷尉审理过程中,宗室成员并无从轻发落的资本。
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和皇室的家族长,对司法裁决具有最终的决定权。《魏书》卷111《刑罚志》:“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实则就是皇帝在顺应鲜卑旧俗的形式下,收回了习惯法中贵族对部民的生杀大权[4](P54)。《魏书》卷15《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寿兴传》:
初,(元)寿兴为中庶子时,王显在东宫,贱,因公事寿兴杖之三十。及显有宠,为御史中尉,奏寿兴在家每有怨言,诽谤朝廷。因帝极饮无所觉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寿兴赐死。
元寿兴有罪,但必须皇帝“注可”,方能行刑,可见北魏对司法执行权控制的严格。就拓跋早期发展状况而言,一直存在犯罪者“临时决遣”的解决办法,而皇帝更是可以凭借最高权威越过正常的审理程序,直接对有罪宗室进行裁决。此类处分的对象一般是宗室中犯有严重罪行的近属宗王,与惩治办法连带的通常是一则措辞严厉的问罪诏书。如使持节、征南大将军、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内山阳东郡诸军事、城阳王元鸾攻击赭阳不克,大败而回。孝文帝引见元鸾等将领,责之曰:“卿等总率戎徒,义应奋节,而进不能夷拔贼城,退不能殄兹小寇,亏损王威,罪应大辟。朕革变之始,事从宽贷,今舍卿等死罪,城阳降为定襄县王,削户五百。古者,军行必载庙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归,今征卿等败军之罪于社主之前,以彰厥咎。”[1](卷19,P509)又《魏书》卷19《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载,长安镇都大将、南安王拓跋桢任上贪纵聚敛,孝文帝与冯太后于皇信堂引见王公,商议惩办事宜,孝文帝诏曰:“南安王桢以懿戚之贵,作镇关右,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壅绝诉讼,货遗诸使,邀求虚称,二三之状,皆犯刑书。昔魏武翦发以齐众,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己忍亲,以率天下。夫岂不怀,有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畴日,循古推刑,实在难恕。皇太后天慈宽笃,恩矜国属,每一寻惟高宗孔怀之近,发言哽塞,悲恸于怀;且以南安王孝养之名,闻于内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同书卷20《文成五王·河间王若传附琛传》载,定州刺史元琛贪污受纳,胡太后诏曰:“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此举旨在昭告天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示皇帝公允执宪,绝无偏袒之意。
由皇族中德高望重者组成的宗议,也可以在皇帝的直接授权和指导下议处非违宗室。如辅政大臣北海王元详贪淫遭禁,宣武帝“引高阳王(元)雍等五王入议详罪”[1](卷21,P562)。广阳王元渊“坐淫城阳王徽妃于氏,为徽表讼,诏付丞相、高阳王雍等宗室议决其罪,以王还第”[1](卷18,P429)。再如《魏书》卷59《刘昶传附刘辉传》载,驸马都尉刘辉与妻兰陵长公主不睦,公主妒忌成性,滥杀无辜,手段残忍,“太后敕清河王怿穷其事。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和之状,无可为夫妇之理,请离婚,削除封位。”宗议环节不同于常规的司法程序,它是宗室“私”的家族场域的管理者,遵循的不是铁的国法,而是约定俗成的家规,从中亦可看到宗室法律特权性的存在[5]。
总之,宗室在监察及司法审理的程序方面并无过分特权可言,上至辅政宗王,下到普通的宗室官员,只要违法乱纪,就有可能遭到御史的弹劾、廷尉乃至皇帝直接的审理和判决。北魏将犯有严重罪行的宗室强制引入国家司法程序中来,或多或少地避免了阿附权贵、徇私枉法的发生,对于维护国家秩序和政治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张金龙.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
[3]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4]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刘军.拓跋宗师考述[J].唐都学刊,2012,(1):84—89.
刘 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责编 张佳琪)
※ 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鲜卑部落联盟研究”(项目编号:12C011);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北魏宗室阶层士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12QY046);吉林大学“985工程”建设基金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