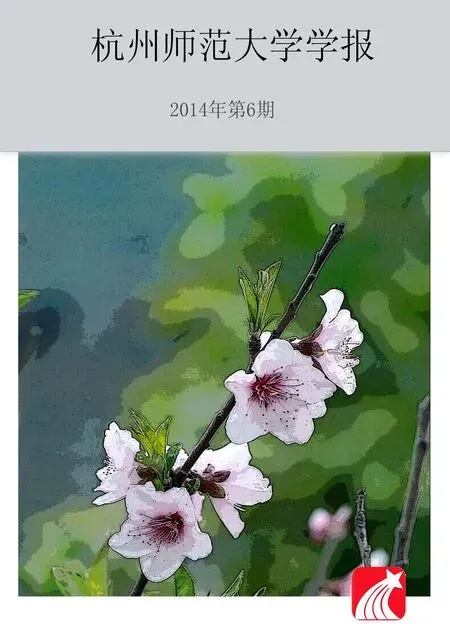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
——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中心
段怀清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作为晚清首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对于中国的认知、传译著述等,无疑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其中对于文学的认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翻译和书写实践上,以及在对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具体认知与解读上——其经验都是划时代的、奠基性的,亦由此开启了晚清以来直至当下中西之间跨文学—文化交流的序幕,甚至影响到19世纪末及整个20世纪中国对于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与使用。
马礼逊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西文化交流语境中使用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他使用这一概念的具体语境又是怎样?为什么他在文、诗这些文体概念之外还要使用literature这一抽象性的概念?他使用这一概念的具体指涉或内涵又是什么?同时,在马礼逊的理论与实践中,他所谓的西方文学(或者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又是指的哪些对象?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怎样的意义与基础上,影响到了同期或后来传教士们对于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使用?同时,马礼逊表示出了要将西方的literature这一概念引进介绍到中国来的意图吗?为什么他会产生这种需要?这是一种现实的跨文化对话交流的需要,还是超越现实需要的一种“文化殖民”,即通过这种概念术语的引入来推进非本土的外来思想的进入?
一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马礼逊与同时代绝大多数新教来华传教士一样,在来华之前并没有接受过专业且系统的文学教育和训练,他们的文学理念,也基本上不属于19世纪西方正在形成的文学主流意识,而他们大概也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读者或文学作者。历史地看,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们更多是泛宗教意义上及古典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与作者,而不是世俗意义以及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与作者。
这一事实可以从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得到佐证。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包括三部分,即按照偏旁部首安排分类的第一部分,按照字母安排分类的第二部分,以及英—中对译解释的第三部分。*马礼逊《华英字典》的英文名称为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First, 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Keys; Part the Second,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And Part the Third, Contain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该书1822年由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印刷,由伦敦的Black, Parbury, and Allen出版。这三部分所收纳解释的字词句相互补充,尤其是第三部分英—中对译部分,对于更好地理解前面两部分所收纳的字词句亦多有裨益。
《华英字典》的编写体例,我们可以从中、英两个语言背景或话语体系,来观察作为语言——文化中介(cultural agent or cultural middleman)的马礼逊,是如何来嫁接两个不同文学传统的,尤其是在19世纪初期,当中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才刚刚开始在贸易之外的文化接触与对话之时。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首先从华—英角度(即从汉语到英语),涉及中文语境中与“文学”相关的字词,其词根主要有“文”与“学”。但有一点特别需要留意,那就是马礼逊无论是在以“文”为中心的组词及解释中,还是以“学”为中心的组词及解释中,尽管涉及了几乎中国传统文学中所有基本词汇,但没有出现过“文学”这个词,或“文”与“学”搭配在一起使用的例子。换言之,马礼逊当时没有从中国现有词汇中找到可以与literature直接对应的词。
具体而言,《华英字典》第二卷中有对中文“文”一字的英文解释,其中相关联者有:fine composition; letters; literature; literary; literary men。[1](第2卷,P.279)在《华英字典》第一卷第785页翻译解释“梁昭明太子始撰文选”时,“文选”的英译为A Selection of Elegant Literature。换言之,英文literature在这里对应的中文是“文”,而不是后来更广为人知的“文学”。另在第一卷第755页中,翻译“精选古文一本”时,古文一词翻译为ancient literature——古文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中所指非常清楚,而英文里的literature作为一个概念也颇为常见。在中国传统文学理念及体系中,“文”显然不包括诗,更不包括小说、戏剧等不入高雅正统文学范畴的“俚俗”书写文本形式,而在西方语境中,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显然包括了诗、小说、戏剧等文体形式,甚至以此为主——比较而言,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及体系中高度崇“文”的传统不同的是,西方文学理念和体系中,并没有这样一种过度崇文的传统,甚至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高文学价值和地位的所谓“文”,在西方文学理念和体系中则未必依然能够享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尊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还是与文学理念以及文学经验、文学史传统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关。在马礼逊的理解中,中文里的“文”一词,有时是指具体的“文”,他翻译为elegant composition,譬如“诗文策论”中的“文”,即作如此解;但像“昭明文选”、“精选古文”中的“文”,他又翻译成为超越一般文体界域的西方意义上的概念“literature”,这反映出马礼逊当时对于中西在文学概念体系之间究竟如何转换对应,恐怕未必已经全然梳理清楚明白。不过,对于“文”的具体语义,在翻译和阐释实践中马礼逊还是较为谨慎的,譬如在“佳文”一词中的“文”,他就翻译为elegant composition,但有时又翻译为good essay。[1](第1卷,PP.776-777)
对于“文”同一字在不同词语搭配以及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引申或差别,马礼逊所给予的关注是适度的,也是颇为难得的——19世纪10-20年代的中西之间的文化对话,毕竟还处于草创阶段,而且马礼逊当时在广州、澳门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亦极为有限,根本不可能与本土受过良好教育及文学学术训练的文人学者展开直接的接触交流。*一直到1809年底,在从广州发回英国的一封信札中,马礼逊还谈到自己对于《大学》《中庸》已有一定了解,而对《论语》的了解还甚为不够,称“自己的知识还不完备”。参阅艾丽莎·马礼逊编《马礼逊回忆录》(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影印本)第1卷,第268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不过,尽管如此,马礼逊还是注意到“文”这个词根在汉语词语世界或文化语境中的巨大存在与特别的词语及文化生成力。在《华英字典》中,他还列举了不少与“文”相关的词条并分别予以了解释:
Literati,第一卷,第166页;
Literati,第一卷,第309页;
Literati,第一卷,第320页;
Literati,第一卷,第759页;
Literary man, a man of letters and ink, 第一卷,第515页;
Literary, national examinations in china, detailed account of,第一卷,第759/779页;
Literary examinations, those who are disallowed to attend them enumerated,第一卷,第129页。
与“文”这一词条的英文关联解释有所不同的是,《华英字典》“学”词条中不仅专门提供了有关中国“文章学”(Of Chinese Composition)*当然马礼逊这里所谓的“文章学”,主要是就科举考试的“八股”而言,故他注重介绍了“文章”、“诗”和“策”这三种文体概念。其中在解释“文章”这一概念时,既用了fine writing, 亦用了essay。而在“策”的翻译时,马礼逊用了political essay。的关联词汇或表述,而且相关展开性的文化阐释亦极为丰富,几乎可以作为19世纪20年代中西之间围绕着文学理念、文学史传统、文学体系等所展开的一次具有一定水准的无声对话,但其中亦未见提及“文学”这一中文表述。这也再次说明,当时在中文语境中,“文学”这样的搭配是较为少见的,而且所指也未必就对应西方的literature。而且在这一词条介绍中,涉及众多与本土“文学”理念及话语体系有关的词汇概念,譬如“古文耸动人精神者莫若国策”一句中“古文”的翻译,[1](第1卷,P.783)马礼逊译为ancient writing显然就有问题,英文中的“古代著作”,与中文里的“古文”,有很远的距离。事实上即便在中文语境中,亦非所有古代著述均可列入“古文”之中。古文不仅有其固有的义理章法,而且还有其独特的书写史和文本史,绝非一个笼统的古代著述这样的表述可以取代。“文章著作备于六经”一句,其中“文章”,翻译为elegant composition。[1](第1卷,P.785)“诗文策论”,翻译为verses and elegant composition。在该词条中,马礼逊先后列举了文字、文章、文、文选、诗文、文体、策论、论文、文人等中文词汇,但他没有提到中文中的“文学”这一概念,这只能说明,当时“文学”这一表述在19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或者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中国古代文学更多是从文体形式来形成文学概念,譬如文、诗、词、曲以及小说等,在超越于上述种种文体概念之上的一个涵盖性的整体概念,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中未见列出。换言之,就是在由中文翻译为英文的语境中,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并没有提供直接来自于中文原文的“文学”一词之例证。
而在对“学”一词的解释中,马礼逊增补了一段文字,是用来解释英文里的literature与中文里的对应内容的: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consists much in voluminous collections of such short essays as are described above, in verses; letters of statesmen and scholars, to the several monarch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c. of such pieces of esteemed composition, there are thousands of volumes.*此句大意为:中国文学包括上述卷帙浩繁的类似长度的短文以及诗歌。参见马礼逊《马礼逊文集·华英字典》(影印版)第1卷,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85页。
这里马礼逊其实已经注意到中西文学观念以及传统之间的“差别”:在中国语境中,像政治家、学者们的一些文论著述,亦纳入到中国语境的“文学”范畴之中。这在马礼逊所理解的西方文学理念中,显然是较为少见的。当然这还是仅就著作者的社会身份或职业身份而言,尚未真正涉及文本、文体、语言修辞以及审美形式等。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这种相对较为独特的文学理念及文学传统,使得马礼逊在翻译或解释一些中国词汇及句子时,不得不在原有基础之上添枝加叶,以弥补词汇及句子外表形式上被隐去的内在寓意。具体而言,马礼逊注意到,在中国语境中,有些句子或俗语中,并没有直接出现“诗文”或“文学”概念,但翻译成英文时,却需要添加,否则西方读者就可能产生疑惑甚至误解。譬如对于中文原句“你少年贯通古今”,马礼逊翻译为:When you were young, you were well acquainted with modern and ancient literature。[1](第1卷,P.307)这里原文中的“古今”,被翻译成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古代或现代。当然这里也是在西方意义上首次出现了与中国文学相关的“现代文学”这样一种表述,尽管其中并没有关涉现代文学的具体内涵。类似例子还有“好攻古文”,被翻译成为:fond of attacking(studying) ancient literature。[1](第6卷,P.259)
类似的例子还有。譬如在《华英字典》第一卷第353页中,有“圣天子好古”一句,马礼逊对于好古的翻译是这样的:Good Emperors love the sage maxims of antiquity, and give the precedence to literature。这里马礼逊将好古的“古”,翻译成了the sage maxims of antiquity,之后可能觉得不足以尽述原文之意,遂又补充了一句:and give the precedence to literature。再譬如“志士游今洞古”,马礼逊的翻译是:A Literary man of resolution rambles amongst the literature of modern times and penetrates the ancient。[1](第6卷,P.258)这里原文中的“古今”,也被马礼逊理解成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
上述解读,主要是围绕着由中到英的词语翻译和阐释,而在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中,马礼逊则多次直接使用literature这个词。
比较而言,最能够代表马礼逊时代无论是他自己抑或是从《康熙字典》等中文文献那里*据马礼逊1807年11月4日从广州发给友人的信,以及他的《华英字典》序等,《华英字典》的字词来源,基本上是参照《康熙字典》。而《康熙字典》亦被认为是当时收录字词最多的一部辞书(计47035个字)。唯一令人费解的是,当时的《康熙字典》是四十二卷,而马礼逊在信中说是“三十二卷”。,均没有在中文里发现一个足以与英文literature“完全”对应词汇的证据,就是《华英字典》第六卷第258页中对于英文literature一词的中文翻译。马礼逊的翻译是“学文”而不是“文学”。[1](第6卷,P.258)“学文”与“文学”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马礼逊没有使用今天所熟悉的“文学”而选择了“学文”来理解英文里的literature一词呢? 最直接的解释,就是马礼逊当时无法从《康熙字典》等中文文献里,直接找到将literature翻译成“文学”的足够证据。本土文学话语系统中,不能为他提供现有的熟语或惯用词汇。这也是一个证明“文学”这个术语在晚清因为中西跨文学—文化交流而进入中国或被“激发”“唤醒”而重新“找回”并“回到”近代中国文学语境之中,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以与西方进行交流对话的关键词平台,直至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思维”而不是中国传统的“诗思”与“文思”的历史证据。而中国传统文学语境中的“诗思”与“文思”在近代中国的淡出,取而代之以更具有近现代色彩的“文学思维”,无疑是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冲击—回应”模式下的思想个案,事实上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并没有成功地将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无论是宗教意义上的抑或世俗意义上的,也无论是古典意义上的抑或近代意义上的——引进到中国并使之落地生根。但他们的探索,却拉开了中国文学从传统语境及相对封闭的自我语境,进入到近代语境和世界语境的序幕。
二
《华英字典》中有关“文学”或literature的相关解读或文献分析,只是在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而在思想与学理层面,马礼逊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传统,以及如何与西方文学进行比对认识的呢?
如果我们稍微检阅一下马礼逊初抵广州之时所能够接触到的“中国人”,就大致可以了解他能够学习到的汉语及中文的基本情况了。在1807年11月初写于广州的一封信札中,马礼逊谈到了他当时在广州学习语言所能够找到的语言教师。而在此之前,不妨先来看看他又是如何描述中国社会的语言分裂或隔阂的:
带着对于当地语言的尊重,我正在花时间来学习方言,现在我已经可以用日常用语跟我的帮差交谈了,他就是我的语言老师,不过他是从乡下来的,其发音极为粗鄙。广州城里有教养的人说,他们听不懂乡下人的话,还有那些干苦力的话。……这对我来说确实困难重重。无论是官话(Mandarin Tongue)还是文言(Fine Writing)大部分百姓都不懂。穷人的数量是惊人的;而我们必须向他们(穷人们——作者)传递福音,并为他们而写作。[2](P.163)
上述中国本土的语言环境,显然也给马礼逊的语言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困难。他提到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曾给他推荐过一位从北京来广州、与传教士们一道经商的山西人,此人据说也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人”,其实也并不识字(但据说会讲拉丁语),所以能够给马礼逊提供语言学习帮助,不过只是帮助他学习官话发音。此外,马礼逊还跟着另一位广州本地的年轻人学习广州方言以及学认汉字,据说此人也是一位基督徒,其父在葡萄牙的耶稣会学院已有12年,原本计划成为一位神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最终成了一个遭到其同胞冷落的人,生活亦陷入到穷困潦倒之中。[2](PP.163-164)
马礼逊的种种相关描述,呈现的是当时最早来华传教士所遭遇到的极为边缘、尴尬甚至艰难的处境——不仅是生活处境,还包括语言文化处境。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那些中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与文化,可以想见会是怎样一幅景观。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学—文化的叙述,不少时候与他们来华之后的个人经历关系甚为密切。当他们不能从中国文人与学者那里——包括中国的书面文献——获得有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合理解释时,他们对于中国及中国人的叙述,就基本上只能依靠自己的观察与揣测推断。而这种状况,亦基本上构成了初期新教来华传教士中国叙事的基本面貌和文化特性。
而马礼逊的上述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信息亦相当丰富,其中特别提到“官话”和“文言”大部分百姓都不懂的“现实”——当然也是事实。这一信息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稍晚一些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在语文策略上所采取的双向适应策略:一方面采用文言文来适应本土知识精英的文学及文化品位需要,并表达传教士们对于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学传统的基本“尊重”;另一方面采用各地方言的白话文来尽可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底层百姓的需求,以达到能够与这些急需要福音启蒙与心灵慰藉的普通民众进行正常交流的条件。正如马礼逊上文中所述,这些数量众多的平民百姓,尤其是那些未曾接受过教育的文盲以及苦力,正是基督福音需要传递到的对象。而马礼逊的这段文字传递出来的另一个关涉晚清以降中国语言文学的重要信息,就是语言文学的功能应该而且事实上也即将发生重要变化,传递与时代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个人处境、宗教信仰与体验、西学及新学相关题材内容的书写文本逐渐增多,甚至大有超越传统经典文本的趋势。这就势必在文本的著述、出版以及传播、使用和接受上带来不少新的知识—文化景观:传递时代新知识、新思想与新感受和新处境的文本,正在呈现出超越传统经典文本不断被复制、重读与传承的原有压倒性趋势,而时代知识—文化结构,也逐渐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纷繁复杂的样相格局。
也就是在上述语境、格局以及由新教传教士们所作出的趋势判断之中,马礼逊对于中西文学之间更富于学术探索意味的考察亦一点点展开推进。不过,就马礼逊那些寄回英伦的书札中所涉及的中国文学而言,不少地方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譬如1807年12月11日自广州写给友人的信札提到“中国文学”——“我现在正在采取更为自由的方式来掌握中国文学”[2](P.182)——可以想象初抵广州的马礼逊,在几乎无法与当地人正常交往且还屡屡被骗的情况之下,又是如何来掌握中国文学的。*有关马礼逊被广州当地人敲诈、甚至被他的语言老师欺骗的记载,参阅《马礼逊回忆录》第1卷,第177-183页。这里所谓的“文学”,极有可能是指一种传教士意义的“文献”——一些与历史、语言、文化、风俗或者比较浅显的创作类读本等相关的启蒙性本土语文文本而已,而不可能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原因很简单,就在马礼逊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他的信中还在一边说“我正在尽力少花点钱来学习认字和广州话发音”。[2](P.184)
这种所谓“一点点地展开推进”,还可以通过1808年9月14日的信札窥见一斑。尽管到广州不过一年,但马礼逊对于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已经有了初步了解,甚至对于作为考试内容之一的“四书”“五经”也能说出一二,而且使用了在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描述中国的知识阶级时使用频度相当高的一个词:literati,但仅限于此,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或文学更深入透彻的认识了解。
从马礼逊此间往来书札看,一直到1809年年底,马礼逊的书札中谈得最多的,还是语言学习,以及《圣经》翻译,间或亦谈到他的《华英字典》,很少谈及中国典籍,当然即便谈及也甚少展开评价。其中一则有关“四书”的评议,出现在马礼逊1809年10月11日从澳门寄出的书札中,对于自己当时尚未读完的“四书”——还只是读完了《大学》《中庸》,并正在读《论语》,而《孟子》尚未读——马礼逊还是有点急不可耐地发表了自己的阅读意见,“其中不少极为精彩,但也有不少错误观点,从总体上看,这些典籍在思想上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而在“四书”之外,中国文学的浩瀚典籍,对于马礼逊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启大门;而事实上至此马礼逊也未见谈及“文学”或“中国文学”的任何真正话题。*可以进一步佐证的是,1810年10月初,伦敦传道会发给马礼逊的正式书札中,所涉及他当时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三项:语言学习、语法书及词典编纂以及圣经翻译,并没有涉及任何与中国文学有关的话题或事项。参阅艾丽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第1卷,第306页。
情况在1813年左右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尽管还很难说就意味着马礼逊对于中国文学或与中国及西方世界相关的“文学”话题产生了关注或兴趣。在这一年3月26日自伦敦发给马礼逊的一封书札中,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提到了与中国文学相关的话题,但这里所谓“文学”或“中国文学”,显然仍未超出历史文献范畴,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
您瞧,从这封信札来看,无论您选择有关中国“文学”(文献)的哪一分支,我们彼此之间都不会相互干扰。至于欧洲大陆,他们亦正试图在中国“文学”(文献)方面有所作为。[2](P.319)
有足够的理由证明,斯当东这里所谓的literature,并非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当然亦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中任何意义上的单独“一门”。它其实就是泛指一切形式的中文书面文献或文本,既没有文体分类,亦没有语言修辞以及审美形式意义上的限定。这与新教传教士们当时视其繁多的译经释经、宣教布道的文本为literature颇为类似。
而这似乎亦显示出,在19世纪初期的中英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对于“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其实都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有着历史意义、文体分类意义或审美意义上的“偏差”。而看上去传教士的宗教文化身份,似乎对这种“偏差”亦有所强化而不是相反。
这一点在伦敦传道会1812年的年度报告中对马礼逊的工作总结评议中亦有回应:
他(指马礼逊——作者)也翻译了一些中国文学(文献)并寄回了英国。这些文学(文献)来自儒家经典,以及被中国文人们奉若典范的《史记》。[2](P.327)
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还是文体分类中,“四书”“五经”都不可以简单地划归所谓“文学”,这无疑降低了这些儒家经典的“圣典”意义而流入到“子”或“集”的范畴之中。而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或标准之中,这些儒家经典同样难以简单地划归到“文学”之中。这进一步说明,一直到19世纪10年代初期,马礼逊对于中国文本的阅读,不仅在数量上仍极为有限,而且亦不能够为其建构起一个有关中国文本史或文学史的基本面貌,更无法让他对中国文学做任何实质意义上的评议。不过,因为《圣经》的中译,马礼逊实际上已经开始对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及书写史有了初步的了解接触。随着《圣经》中译的全面展开及推进,《圣经》中的一些赞美诗,甚至同时代人创作的一些赞美诗,马礼逊也开始尝试着翻译成诗体中文文本,但据记载,这种尝试依然“严重”依赖其中文助手。1814年6月17日日记,“将三首颂诗及赞美诗付印。这些都是由我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由柯先生和他的公子润色成为诗体文本”。[2](P.407)显而易见,这种有限的双语文学实践无论在文学层面还是在文学翻译层面,都处于初浅的水平。
而更能证明当时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所使用的literature一词甚至在西方语境中亦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学的一个例证,就是在1815年由米怜起草提供给差会的有关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的计划书中,对于这所拟办中的教育机构的目标有明确描述:这所拟在马六甲创办的书院,是为了传授科学和人文(literature)*《马礼逊回忆录》第1卷,第426页。有关该计划中涉及中国文学、历史的叙述部分,据信该报告基本上为米怜起草,所以将在“以米怜为中心”的个案分析中予以讨论,此不赘述。——此处的literature一词,无论是从具体语境还是英华书院开办之后的实际教育内容看,几乎涵盖了西方科学教育之外的一切,而非具体的文学。
这是就literature一词与science一词对应使用的情况。有时候,马礼逊又将literature与religion对应使用。1817年9月4日一封从广州发出的有关自己宣教工作近况的书札中,曾提到马礼逊每天所必须面对的无数的宗教的与“书面文字”的劳动[2](P.479)——这里的literary labor,显然不是指具体的文学,而是指一种书案工作:宣教布道是外出的口头劳作,而伏案书写(包括翻译、编纂)等,则一概被称之为literary labor。*马礼逊去世之后,其后亦曾担任过英华书院院长、后为伦敦大学中文教授的修德(S.Kidd)在Dr. Morrison’s Literary Labors一文中所述,亦非今天意义上的专属“文学”领域的工作,而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文字”、“文化”之著述工作。参阅《马礼逊回忆录》附录二。
而上述分析亦表明,在马礼逊的语境中,literature不少时候是与science(或哲学、历史等)以及religion这类概念对应并列的,并非是指具体的文类概念。而这种状况或语境需求,无论是在同时期的中国语境中还是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似乎都不大容易找到完全对应——中国有一套几乎完全独立的有关其自身的知识与文本分类的体系及历史。而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oseph Abel Remusat)以及德国语言学家维特尔(John Severin Vater)1817年致马礼逊的书札内容看,他们所关心的,亦是马礼逊作为一个“汉学家”在字典编纂、圣经翻译、儒家典籍及中国方言研究方面的工作和成就,基本上没有提及具体意义上的“文学”。
三
马礼逊的中国文学经验,其实有时亦反过来倒逼着他去关注西方语境中的文学以及西方文学,并促使他曾一度尝试着从文学角度或层面来进行中西之间的文化接触与交流。但这种接触交流注定了是极为有限且浅尝辄止的——且不说马礼逊等传教士的文学修养与文学知识结构,就是他们各自所属的差会,也并不鼓励传教士们在这种世俗的“文学”语境中耽延沉浸太久,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于基督教福音的传播与信仰,甚至在基督教语境中,差会亦同样不鼓励传教士们从文学角度来突出《圣经》的文学性而非“圣经性”。换言之,传教士的宗教身份与文化身份,注定了他们对于世俗意义上的文学的关注与牵涉,均只能是个人性的、有限度的甚至是工具手段性的。
而从马礼逊回忆录所提供的信息看,其工作实践游移在传教士世界和汉学研究界之间——甚至在经济上还直接受益于东印度公司。这并不奇怪,尽管这种双重生活及身份并不为传教士团体所乐见。而作为“汉学家”的马礼逊,其背后已经不仅仅只是英国皇家学会中正在启动成长的汉学研究,甚至还因为其往来书札而与整个欧洲汉学界皆有联络。而从当时那些汉学家写给马礼逊的书札看,他们当时所关注的,多为语言、典籍、历史等,基本上尚未细分深入到文学之中。即便是偶有涉及文学话题,足够的文本细读与分析亦极为罕见。这也注定了马礼逊时代无论是英国汉学抑或欧洲汉学,都尚未确立起以文学为中心的汉学研究分支,也不会在“文学”这样一个范畴中展开中西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交流。
因此,尽管马礼逊当时主要的宣教活动地域在马六甲——广州、澳门的宣教活动基本上是不被当地官方所允许的——鲜与当地真正意义上的文士接触,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文本状况以及所造就的文人特性亦缺乏足够广度和深度的认识了解,并因此而未能将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概念真正带入中国,进入到中国的文学语境之中,从而与之产生具有近代意义甚至现代朝向的对话交流,但马礼逊的经验,却因为其30余年的具体实践以及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而昭示着后来的新教来华传教士,成为他们逐渐渗透到近代中西跨文学—文化交流语境中的“文学”领域的引路人。
[1]马礼逊.马礼逊文集·华英字典(影印版)[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2]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影印本):第1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