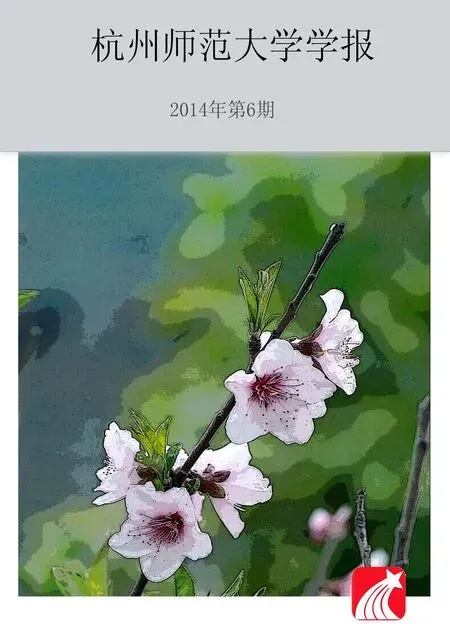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高传峰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宁夏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00)
1909年3月,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收波兰、俄国、英国3个国家的作家作品共计7篇。同年7月第二册出版,收芬兰、美国、法国、波思尼亚、波兰、俄国6个国家的作家作品共计9篇。《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这是周氏兄弟抱着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希望,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的“结果”。[1](卷10,P.176)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序里,鲁迅对《域外小说集》的出版给予很高的期许:“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1](卷10,P.168)。虽然《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在晚清受到了冷遇——在东京销售了20册,上海也不过如此,“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1](卷10,P.176)但它对周氏兄弟后来一生的文学活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学界对《域外小说集》已有颇多关注,可《域外小说集》并非是在1909年才横空出世的。《域外小说集》能够“收录至审慎”,[1](卷10,P.168)离不开周氏兄弟在此前的文学翻译活动中积累下的丰富经验。本文将关注点集中在1909年之前周氏兄弟的翻译活动上,希望能对此有一个清晰地梳理和把握。
一、周氏兄弟早期的译介作品
1903年6月,留学日本的鲁迅在由许寿裳接编的《浙江潮》第5期上发表译作小说《斯巴达之魂》的前部分和雨果随笔《哀尘》的译文,并有《〈哀尘〉译者附言》。这可以看作是鲁迅最早的文学活动。由于《斯巴达之魂》的半译半作性质,我们可以说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起步的。随后的1904年5月,在鲁迅的帮助下,时在南京水师学堂的周作人开始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在这一年第8期的《女子世界》杂志上,周作人发表了翻译自《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的作品《侠女奴》,并在其后几期连载。这是周作人最早的翻译文字。1906年夏秋之间,周作人随鲁迅一起赴日本,开始了亲密的翻译合作。这一合作,一直持续至1923年7月兄弟失和。
为了对周氏兄弟的早期译介活动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笔者对周氏兄弟的早期译介作品按年份列表如下。

周氏兄弟的早期译介作品(1903—1908)
注:1.以作品初次见刊时间为准统计;未见刊的,以出版时间为准;未发表的,以完成时间为准。
2.鲁迅部分参考《鲁迅全集》第18卷《鲁迅生平著译简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鲁迅年谱》第1卷(增订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鲁迅翻译文学研究》(吴钧著,齐鲁书社,2009年)附录“鲁迅译文目录”;《鲁迅翻译研究》(顾钧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中的“鲁迅翻译年表”;谢仁敏的论文《〈女子世界〉出版时间考辨——兼及周氏兄弟早期部分作品的出版时间》(《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等资料。周作人部分参考《周作人年谱(1885—1967)》(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周作人研究资料》(张菊香、张铁荣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孙郁、黄乔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翻译家周作人论》(刘全福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附录三“周作人译事年表”;华东师范大学徐从辉博士论文附录六“周作人著译系年”。
我们发现,除《斯巴达之魂》《侠女奴》外,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涉及法、美、英、俄、匈牙利5个国家,后来《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中共收录7个国家的16篇作品,而法、美、英、俄4个国家的作家作品就占去10篇。周氏兄弟早期翻译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域外小说集》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周作人的翻译以小说为主,也有民间故事(1篇)、散文(1篇),集中在文学领域。而鲁迅除译小说、随笔外,还翻译了历史著作(如《世界史》)、自然科学文章(如《物理新铨》中《世界进化论》《原素周期则》二章),相对要庞杂一些。但周作人自1904年开始翻译作品以来,每年均有译作发表或出版,鲁迅1905年则未有译作,之后数量也较此前减少。
再次,周作人发表于1906年的译介小说《一文钱》和发表于1908年的译介小说《庄中》《寂寞》后来均收入《域外小说集》(收入集子后分别改名为《戚施》与《默》)。这说明1909年出版《域外小说集》时周氏兄弟的一些翻译理念,最迟在1906年已经产生。而正是在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听中川爱咲先生讲授的细菌学课程时,因“幻灯片事件”而大受刺激,遂决定弃医从文。这中间的关联,值得研究者思考。
第四,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前已经有过3次合作翻译的经验,即1907年合译《红星佚史》《劲草》,1908年合译《裴彖飞诗论》。《红星佚史》和《裴彖飞诗论》的合作都是采用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方式,而《劲草》的合作则是由周作人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虽然后来出版《域外小说集》时周氏兄弟的合作翻译更多地是在理念上,但其中一篇小说《灯台守》里的诗歌亦是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
二、1903—1906年:在晚清域外小说译介的潮流中
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深受晚清文坛域外小说译介环境的影响,第二个阶段则开始为《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做准备。这两个阶段的分界时间是在1906年,其中第一个阶段,是裹挟在晚清域外小说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
(一)翻译的起点:《斯巴达之魂》*鲁迅在《浙江潮》第5期分别以“自树”和“庚辰”的笔名同时发表了译述作品《斯巴达之魂》的前部分和翻译作品《哀尘》。由于无法分辨这两篇作品完成时间的先后,这里按照作品发表时排列的先后顺序,将《斯巴达之魂》视为鲁迅翻译的起点,而将《哀尘》放在后文论述。与《侠女奴》
鲁迅的译述之作《斯巴达之魂》分别于1903年6月15日、11月8日发表在《浙江潮》第5期、第9期。鲁迅之所以发表《斯巴达之魂》,与当时留日学生中的拒俄运动热潮有关。由于1903年沙俄妄图吞并我东三省入俄国版图,留日学生自行组成了义勇队以抗击沙俄,并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拒俄。《浙江潮》第4期刊登了留日学生给政府的上书,云:
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据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国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而小说《斯巴达之魂》,是对学生上书中所提到的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波斯侵略故事的展开讲述。文中的斯巴达军敌众我寡,又有叛徒出卖,但他们在斯巴达王黎河尼佗的带领下,与波斯军队展开激战,最后遵从“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国法全军覆灭。唯有一人克力泰士因为眼疾未上战场而得以苟且偷生,但他的妻子涘烈娜在得知他未死后拔剑自刎。在涘烈娜精神的感召下,克力泰士重返战场,以死殉国。鲁迅在这篇小说正文之前的小序中写道:“迄今读史,犹懔懔有生气也。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1](卷7,P.97)这里的“巾帼”指的即是小说中的涘烈娜。鲁迅译述这篇小说正是想借此“以激励祖国人民为拯救危亡的祖国而战,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保卫祖国而战”。[2](P.108)
译自阿拉伯民间故事的《侠女奴》是周作人的第一篇翻译作品。主人公埃梨无意中窥得四十大盗藏宝的秘密,得其钱财而归。其兄慨星在效法的过程中,因贪财忘记口号被困于室内而被四十大盗所杀。埃梨运其兄之碎肢体与金货归家,遂与四十大盗结仇。因为女奴曼绮那的机警灵敏,埃梨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杀身之祸,而四十大盗却在报仇过程中全部死亡。这篇作品译于1904年,当时周作人还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得到了一册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英文插画本《天方夜谭》,便翻译了这篇故事来做试验,并得以在《女子世界》杂志上分期登出。
本来,周作人的《侠女奴》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在内容上并没有多少关联。《侠女奴》也绝不似《斯巴达之魂》那样教人反抗,它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罢了。但周作人却在这篇《侠女奴》的序中执意点出曼绮那的“英勇之气”,“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以反抗:“有曼绮那(Morgiana)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悉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3](P.3)周作人之所以出这样的“风头”,[4](P.161)是时代的风尚使然,是迎合《女子世界》杂志,但鲁迅对他不无影响。
(二)科学小说与侦探小说
晚清最后十多年,由于“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5](P.27)域外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得到了“晚清思想文化界的真正重视”。[6](P.29)而晚清译介外国小说的主要类型有4种:“侦探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6](P.29)根据陈平原的研究,迟至1900年,这4种类型的小说已经全部被介绍到中国来。[6](P.29)周氏兄弟在晚清译界登场,分别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
1.鲁迅与科学小说的翻译
鲁迅选择翻译科学小说,首先是“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1](卷13,P.99)个人因素而外,鲁迅亦受到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启发。在其翻译的第一部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的“辨言”中,鲁迅指出,“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卷10,P.164)这无疑是对梁启超“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观点的进一步思考。[5](PP.53-54)而鲁迅要通过翻译科学小说,使读者“于不知不觉,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1](卷10,P.164)的目标也是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宗旨相符”。[7](P.92)
《月界旅行》写的是美国一枪炮会社的社长巴比堪突发奇想,率众铸造哥伦比亚炮,最后和法国人亚电、反对者臬科尔乘弹丸一起飞往月球的故事。原为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出版于1865年的作品。日本井上勤1886年将其译为《九十七时二十分间月世界旅行》出版。鲁迅据井上勤的日译本重译为中文。由于日译本的错误,原作者被署为美国的查理士·培仑。《地底旅行》写德国的博物学士列曼与侄子亚蓠士、猎夫梗斯一道,从衣兰岬岛的斯捺弗黎山火山口进入地底,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旅行后重返故乡,获得美名。小说出版于1864年,原作者仍为儒勒·凡尔纳。日本的三木爱华、高须墨浦于1885年将其译为《拍案惊奇地底旅行》出版。鲁迅据此日译本重译。由于日译本的错误,原作者被署为英国的威男。在中国近代的科学小说翻译中,儒勒·凡尔纳是“最引人注目、作品被译成中文最多的作家”。[8](P.167)这与日本明治年间的凡尔纳热关系密切。*参看山田敬三《鲁迅与儒勒·凡尔纳之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任冬梅《论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尽管鲁迅在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并不知道它们是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但他和当时正流亡日本且已经开始关注科学小说的梁启超等人一道成为“将凡尔纳热潮传入中国的推动者”。[7](P.92)
晚清译界以“意译”为主,处于这一时代潮流中,鲁迅在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对所参照的日译本做了大幅度地删改。《月界旅行》日译本共28章,鲁迅译为中文后,“截长补短,得十四回”。[1](卷10,P.164)《地底旅行》日译本共17章,鲁迅译成了12回。另外,鲁迅在将这两部作品译成中文时,均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语言上以俗语为主,参用文言。这一点与梁启超所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有颇多相似之处。*参看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中选录的《十五小豪杰》译后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914年,鲁迅又译过一部科学小说,名为《北极探险记》。因“译法荒谬”,即“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而被编辑“大骂一通”,[1](卷13,P.99)终未出版。今稿已佚,未知其详。鲁迅所译最后一篇科学小说是发表于1906年《女子世界》的《造人术》。这篇不足千字的小说讲的是波士顿理化大学非职化学教授伊尼他氏用六年时间成功造人一事。该文原作者为美国的路易斯·托仑。据日本学者神田一三考证,英文原著AnUnscientificStory全文发表于《国际人》杂志1903年2月号。日本原抱一庵主人将其中的一部分译成日文分别于1903年6月8日和7月20日在《东京朝日新闻》刊载。后又将前一部分收录于《(小说)泰西奇闻》(知新馆,1903),名《造人术》。此《造人术》即鲁迅译《造人术》所参照的版本,而其仅为英文原著的1/7。*参看神田一三的论文《鲁迅〈造人术〉的原作》,《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鲁迅〈造人术〉的原作·补遗》,《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与《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不同,在这篇译文里,鲁迅用文言“忠实翻译”[9](P.38)了日文原文。而鲁迅之所以选择翻译这篇小说,除其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述对科学小说的钟爱可看作原因以外,周作人附于文后的一段评语亦可作为参考:“彼以世事之皆恶,而民德之日堕,必得有大造鼓洪炉而铸冶之,而后乃可行其择种留良之术,以求人治之进化,是盖悲世之极言,而无可如何之事也。”[10](P.90)鲁迅在日本学医过程中接触到进化论并表现出兴趣,这段话与他当时的思想是吻合的。
2.周作人与侦探小说的翻译
在译完《侠女奴》后,周作人紧接着翻译了爱伦·坡(周译亚伦·坡)的TheGold-Bug,取名《山羊图》。1905年5月由翔鸾社印为单行本出版时易名为《玉虫缘》。这时的周作人仍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他翻译《玉虫缘》的底本是鲁迅从东京寄来的日本山悬五十雄“所编的《英文学研究》的一册”,“题目是《掘宝》”,[4](P.164)因当时周作人尚“不解和文,而于英文少有涉猎”,[3](P.32)故乃从英文译出。
爱伦·坡(1809—1849)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作家。他是“侦探推理小说的鼻祖”、是“科幻小说的奠基者”,[11](PP.16,24)同时还是“恐怖悬念小说大师”。[12]无论是前文提到的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还是后面将要提及的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均受到过他的影响。TheGold-Bug是爱伦·坡创作于1842年的作品。在这之前,他曾创作过同类风格的作品《摩格街谋杀案》,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篇纯粹的侦探推理小说”。[11](P.16)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一再提及的“侦探推理小说”与“侦探小说”同义。爱伦·坡刚开始创作这种类型的小说时,“还不完全具备如今已相当成熟的‘侦探小说’的各种要素”,他称之为“推理小说”,故后来亦有“侦探推理小说”的提法。[11](P.23)也正因为如此,周作人称其所翻译的《玉虫缘》是“还没有侦探小说时代的侦探小说”。[4](P.164)
《玉虫缘》写的是因家道中落而避居苏利樊岛的法国人威廉的故事。他与偶然间得到一玉虫,并在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包裹玉虫的羊皮纸上的秘密。威廉成功破译了海贼渴特在羊皮纸上留下的暗号,最后在“我”和仆人迦别的帮助下,获得巨额宝藏。周作人在该书的“绪言”中自述译此书之目的在于使“皆思得财”的“吾国之人”“读此书而三思之,知万物万事,皆有代价,而断无捷径可图”,[3](P.31)但这却像是作者译完此书后的附会之言。周作人翻译此书是更多地受到了当时中国侦探小说翻译热的影响。*当时中国的侦探小说翻译热可参看郭延礼在专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上篇”第六章“中国近代翻译侦探小说”中的论述。“在翻译的时候,《华生包探案》却早已出版,所以我的这种译书,确是受着这个影响的。”[4](P.164)因为《玉虫缘》,周作人是中国译介爱伦·坡作品的第一人。
1896年,上海《时务报》刊登了张坤德所译英国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西方侦探小说开始在中国风行,并使得其他类型的译介小说“无论在数量上和影响上都难以望其项背”。[13](P.1)柯南·道尔也成为1896—1916年间中国出版的翻译小说中占数量最多的作家。*参看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第44页中所做的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入译界,周作人亦关注过柯南·道尔。不过,他并没有翻译他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而是译了《荒矶》,遂成为首次将柯南·道尔的非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译成中文之人。《荒矶》并非侦探小说,但周作人因为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风行而译此文,故本文在此将其一并论述。
《荒矶》本名TheManfromArchangel,笔者未找到原文的创作时间及今译本。在《荒矶》的“附言”中,周作人记道,“日译易曰荒矶,今仍之”,“译者未能读日译,从原本述出”。[3](P.563)可见,周作人仍是多少参照了日译本从英文译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为英国人约翰麦微汀。因厌恶人世,“我”避居于开斯纳斯海岸一片寂寞荒凉之地,从事哲学科学研究,本想不问世事,却无意中介入了露国人濠玕尼夫与苏菲的恋情当中。濠玕尼夫的一往情深未能挽回已移情别恋的少女苏菲的心,最后两人双双葬身海天。周作人评价此文“叙惨淡悲凉之景,而有缠绵斐恻之感”,“觉悲惨甚”,[3](P.563)实非虚言。
(三)周氏兄弟与雨果
这里首先要提雨果的一部作品《见闻录》。《见闻录》是雨果“集日记、回忆、笔记、随感为一体的作品”,“记录了雨果从1830年至1885年这55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1885年雨果逝世后才“陆续发表出版(1887—1899)”。[14](第20卷,P.741)据韩南的研究,日本从1885年开始出现翻译雨果作品的潮流,主要翻译者是森田思轩。森田思轩选译了《见闻录》中的一些轶事,刊登在杂志上。鲁迅所译雨果作品《哀尘》即根据这些日文译作转译而来。[15](P.211)《哀尘》与《斯巴达之魂》一起,发表在1903年6月15日的《浙江潮》第5期,排在《斯巴达之魂》之后。这是雨果作品的“首篇中译”。[15](P.211)尽管这篇作品并非小说,但发表时仍放在小说栏内。
据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雨果文集》第20卷“游记、政论与纪实文学”,即《见闻录》一卷,可知《哀尘》为雨果1841年所记述的几件事情中的第一件。按《哀尘》译笔,文章记述了嚣俄(即雨果)与席拉覃夫人等人共进晚餐之后回家路上的所见所闻。嚣俄在等车的过程中,亲见一恶少年将一团雪塞入一女子之背。女子在还击的过程中引来了巡查,巡查将其带入警署并处以六个月的监禁。后嚣俄亲自出面作证并签字才得以解救此女子。在附于文后的“译者曰”中,鲁迅指出“彼贱女子者,乃仅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谁实为之,而令若是”,并叹道“嗟社会之穽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史》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果如鲁迅所言,我们在穆时英写于1930年的小说《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中看到了相似的情景,只不过在这篇小说里,中国女子的运气并没有《哀尘》中那个女子好,没有名人出来为她作证。韩南说鲁迅正是出于“对社会差异的认知和反应”[15](P.214)而翻译了雨果的这篇文章,并举出鲁迅后来的小说《一件小事》《祝福》和《故乡》,认为同属一类型,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1861年雨果完成其著名小说《悲惨世界》。小说第一部名为“芳汀”,此乃这部小说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而这一人物的原型即鲁迅所译《哀尘》中的这位女子。所以,《哀尘》日文译本的标题为“芳汀的来历”,鲁迅在文后“译者曰”中亦有“记一贱女子芳梯事者也”[1](卷10,P.480)之类的话。1906年周作人在《女子世界》发表译作《天鹨儿》,这篇小说原为雨果《悲惨世界》第一部“芳汀”的第四卷,大标题为“寄放,有时便是断送”,下又分为三部分:“一个母亲遇见另一个母亲”、“两副贼面孔的素描”、“云雀”。[14](卷9,P.192-207)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并未提起过这篇文章。是在史料专家的提醒和追问下,周作人才想起“可能是他译的,因为其中有英文原文(鲁迅英文不精,一般从日文转译西方小说)”,“而日文极少引用原文的”。[16](PP.41-42)由此可知,周作人是从英文转译了这篇小说。周作人曾在文中提及梁启超的《新小说》上介绍了雨果以后,非常有名,“我们也购求来了一部八大册的英译选集”。[4](P.191)《天鹨儿》可能即是据此译出。而周作人1906年创作的文言小说《孤儿记》,也是在啃雨果英译选集的过程中,“把他的一篇顶短的短篇偷了一部分,作为故事的结束”。[4](P.191)将《天鹨儿》与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雨果文集》中的《悲惨世界》第一部第四卷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出周作人在译文中去除了原文冗长拖沓的叙述,将三部分合为一部分,使得情节紧凑许多。据周作人译文所述,芳梯被情夫多罗抹无情地抛弃。在回乡途中,芳梯将女儿康雪寄放在酒食店老板覃那大家中。康雪受尽虐待,成为一只不唱歌的“天鹨儿”,即云雀。周作人在“译者曰”中说“此巴黎之秘密”,“此中国之常事”。[3](P.587)这正同于鲁迅译完《哀尘》之后“亚欧同慨”的感叹。
三、1906—1908年:《域外小说集》的酝酿期
周氏兄弟合译的小说《红星佚史》是在1907年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的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周氏兄弟选择这本书进行翻译,难逃晚清小说译介潮流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从1906年开始,周氏兄弟已经在尝试与中国晚清的译界告别了。1906年周作人在《民报》第21号发表译自俄国作家斯谛勃鄂克的小说《一文钱》即是标志。后来,这篇小说被收入《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从此时起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笔者称之为《域外小说集》的准备阶段。
(一)周氏兄弟的早期合作翻译
如前文所述,在《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前,周氏兄弟合作翻译过3部(篇)作品,即《红星佚史》《劲草》《裴彖飞诗论》。由于历史小说《劲草》并未出版,且原稿已佚,这样我们据以考察研究的就只有《红星佚史》与《裴彖飞诗论》了。
1.《红星佚史》:“文以移情”[3](P.76)观念的提出
《红星佚史》原名TheWorld’sDesire,是哈葛德(1856—1925)和安特路朗(今译安德鲁·兰,1844—1912)出版于1890年的合著小说。全书由周作人据英文翻译,而其中的诗歌则是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第三篇第七章勒尸多列庚的战歌除外,由周作人独译),出版时署名“中国会稽周逴”。《红星佚史》是周氏兄弟的首次合作翻译,1907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为“说部丛书”第8集第8编出版,1914年又编为“说部丛书”初集第78编再版。*《红星佚史》初版时间有争议,经笔者查证,初版时间应为1907年10月。
周作人之所以选择翻译《红星佚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4](P.243)哈葛德是英国19世纪后期文坛上的“一个热衷于异域探险的浪漫派小说家”,[17](P.366)他“擅长写历史题材,其小说的内容多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冒险、神秘、离奇与曲折的故事”。[18](P.70)在陈平原对1896—1916年出版的翻译小说所作的统计中,哈葛德的作品排名第二(25种),仅次于柯南·道尔(32种)。*参看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第44页)中所做的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林纾一生共翻译作品181部*此统计数字参看李家骥主编的《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前言”。,而其翻译哈葛德的作品计有25部(含二部未刊作品)*此统计数字参看邹瑞玥论文《林纾与周作人两代翻译家的译述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占翻译作品总数的13.8%。哈葛德也成为林纾翻译作品最多的外国作家。周作人难脱时代影响*鲁迅也深受林译小说影响。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对于林译小说,“出版之后”,“每本必读”,但同时又说鲁迅“对于他的多译哈葛德和科南·道尔的作品,却表示不满。他常常对我说:‘林琴南又译一部哈葛德’”!(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6页)至于鲁迅不喜欢林译哈葛德和柯南·道尔之作品的原因,许寿裳并未明确说明。,他“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觉得“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4](P.243)但哈葛德只是周作人选择翻译这本书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还在于他对另一个合著者安特路朗的关注。安特路朗是英国的作家兼学者,“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作”为名。由于《红星佚史》“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周作人“便取他的这一点”。[4](P.243)周作人对于希腊文学的兴趣于此已见端倪。
《红星佚史》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故事的延续,在商务印书馆1914年再版本的封面上标有“神怪小说”的字样。小说写的是阿迭修斯(周译,即奥德修斯)的“第三次浪游”。[3](P.75)阿迭修斯得了神的示兆,至埃及寻找意中人黄金海伦。皇后美理曼妒火中烧,幻化成海伦的模样,致使阿迭修斯受迷惑而破了誓,最终被其子台勒戈奴所射杀,死在海伦怀中。林纾曾评价哈葛德的小说,“言男女之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19](P.26)这里的《红星佚史》即是两女争一男的故事。《红星佚史》中共有诗歌36首,由于哈葛德的其他作品中并没有这么多的诗,周作人“便独断的认定”“书里所有诗歌”“是安特路朗的东西”。[4](P.243)译诗主要是模仿《诗经》或《楚辞》的体式而作,是“古雅的诗体”,而第三篇第七章中的一首,即“勒尸多列庚的战歌因为原意粗俗”,遂由周作人“用了近似白话的古文译成”。[4](P.243)
值得注意的是《红星佚史》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忠实”,“编次、布局、章节小标题全部按照原文,完全没有删改字句的情况发生,只在某些地方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稍做改动”。[20](P.65)这正应了周作人在“序”中提到的“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那句话,否则“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3](P.76)这样也就达到了“文以移情”的目的。这和周氏兄弟后来在《域外小说集》中“迻译亦期弗失文情”[1](卷10,P.168)的翻译观是一脉相承的。
2.《裴彖飞诗论》:关注弱小民族文学
《裴彖飞诗论》一文的翻译源于《摩罗诗力说》。1908年,鲁迅在《河南》月刊第二、三号分两次发表了《摩罗诗力说》,这是鲁迅“第一篇系统地介绍西欧文学流派的论文”。[2](P.196)在这篇意欲“别求新声于异邦”[1](卷1,P.68)的长文里,鲁迅详略有致地介绍了英国的拜伦、雪莱,俄罗斯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克拉辛斯基,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即裴彖飞)等8位诗人的生平及作品,称他们为“摩罗诗派”。摩罗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1](卷1,P.101)鲁迅期待中国也能有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摩罗诗力说》的最后一部分,鲁迅用不少的篇幅介绍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称赞其“所作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1](卷1,P.100)这一部分内容是中国最早介绍裴多菲的文字。之后,鲁迅即和周作人一起翻译了《裴彖飞诗论》,发表于1908年8月5日《河南》月刊第七号,署名“令飞”。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是这样回忆这篇文章的:“这本是奥匈人爱弥耳赖息用英文写的《匈加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经我口译,由鲁迅笔述的,所以应当算作他的文字,译稿分上下两部,后《河南》停刊,下半不曾登出,原稿也遗失了。”[21](P.263)虽然这篇文章仍是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是周作人帮了鲁迅的忙。大概鲁迅自己英文不好,所以特意请周作人为他口译了这篇文章。
可见这篇只剩上半部分的《裴彖飞诗论》,大致从两方面来论述裴多菲的诗。首先阐述了匈牙利的平原(文中译普斯多)对裴多菲诗歌创作的影响:“诸普斯多为状,各各殊异,多或满以麦田烟圃,及荏粟之林,多或为池沼平芜下隰,且时或茂密,时或荒寒,时或苍凉,时或艳美,大似匈加利人狂歌之性,而尤近裴彖飞”,“普斯多之影响于摩陀尔诗人者,不可掩蔽,而在裴彖飞尤然”。其次点明了裴多菲诗歌艺术上的特色:“其诗纯属客观”,“率甚短,仅以数句述境地而诗化之,言外余韵,何感于心,则一任诸读者”,“然其诗又非绝无色味,尝之泊然者”。[3](PP.590-592)由于后半部分丢失,所以这里对裴多菲诗歌艺术特色上的分析并不完全。在文章的前面有一段小引,译者说明了翻译此文的目的,“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诗人情性,与夫著作旨趣之一斑云”。[3](P.588)应该说,这篇译文是对《摩罗诗力说》中裴多菲的介绍之补充。
(二)对匈牙利文学的偏爱
《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后面均附有译文和新译预告。第一册后面的译文预告中有一条是匈牙利育珂的《怨家》《伽萧太守》,而新译预告中有一条是匈牙利密克札忒的《神盖记》(《圣彼得的伞》)。*参看戈宝权《〈域外小说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对于《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后面附有的译文和新译预告的介绍,戈宝权文见《域外小说集》,岳麓书社,1986年。由此可见周氏兄弟对匈牙利文学的钟情,可惜在后来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未能收入匈牙利作家的作品。这里要谈的是周作人出版于1908年的译介小说《匈奴奇士录》。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曾提及裴多菲的名作《民族之歌》(鲁迅译为《兴矣摩迦人》)。这首诗的写作与欧洲1848年革命有关。当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革命,消息传至匈牙利,裴多菲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民族之歌》。3月15日,匈牙利爆发革命。在首都佩斯民族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裴多菲冒雨当众朗诵了《民族之歌》,号召匈牙利人不要再作奴隶,点燃了匈牙利人民的革命热情。当时与裴多菲一起在场的,还有一位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在裴多菲朗诵完《民族之歌》后,约卡伊·莫尔宣读了事先拟好的《十二条纲领》,向奴役匈牙利的奥利地哈布斯堡王朝提出明确的要求。匈牙利革命被引向高潮。
这个宣读《十二条纲领》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是裴多菲的同学,与裴多菲交情深厚。在周氏兄弟《摩罗诗力说》《裴彖飞诗论》等文章对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进行介绍的前后,周作人翻译了约卡伊·莫尔的小说《匈奴奇士录》(周译作者名为育珂摩耳),190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匈奴奇士录》原名Egy az Isten,即“神是一位”,作于1877年,周作人系从“稍事删节”[4](P.247)的英译本转译而成。小说的主人公是匈牙利人摩那塞,之所以被周作人誉为“匈奴奇士”,乃是因为匈牙利人据说是匈奴人的后代。摩那塞携与迦勒里公爵离了婚的勃阑迦返回故乡多洛支珂,待勃阑迦归入一神教会后娶以为妻。1848年革命的战事中,在扶剌赫女郎婵那比亚的帮助下,摩那塞屡立战功。因为相信“Egy az Isten”,摩那塞始终不以杀戮为重。小说的最后,摩那塞宽恕了作恶多端的跋陀尔。在这篇“穿插恋爱政治”[4](P.247)的小说译作前的“小引”中,周作人引用了匈牙利人理特耳著的《匈加利文学史》中对约卡伊·莫尔的评价,并对文中所记的1848年战事作了简要介绍。
此后,周作人曾于1910年12月作短文《育珂摩耳传》,未见发表。[22](第1卷,PP.206-209)1911年1月,周作人还译了约卡伊·莫尔的中篇小说《黄蔷薇》,可惜迟至1927年8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周作人写了同名文章《黄蔷薇》。文中表达了对《匈奴奇士录》英译者倍因先生(R.Nisbet Bain)的念念不忘之情,说“我的对于弱小奇怪的民族文学的兴味差不多全是因了他的译书而唤起的”。[23](P.4)可以说,周氏兄弟最早进行专门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即为匈牙利文学,为《匈奴奇士录》。这比《域外小说集》中译介波兰、波思尼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文学要早。
(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1908年10月,周作人在《民报》第24号发表译作《西伯利亚纪行》,这是周作人译作中最早可见的散文作品。该文讲述俄国流人赴西伯利亚途中的悲惨情境,原为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周译为克罗颇特庚)《在英法狱中》一书中的一节。周作人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作品,是因为此时他已经受到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周作人1907年发表在提倡无政府主义的期刊《天义报》上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见周作人“与克鲁泡特金的相遇”。[24](P.173)发表于1907年9月15日《天义报》第7期的《西伯利亚之囚(读书杂拾(三))》,1907年11月30日《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的《见店头监狱书所感》,都是因为周作人读了克鲁泡特金的书后有所感发而作,文中有大段克氏原话的引用。发表于1907年10月30日《天义报》第8、9、10期合刊的《斯谛勃咢克》一文,原是介绍俄国作家斯谛勃咢克,却也提到他和克鲁泡特金同为Chaikorski党人,并转述了克鲁泡特金在其自叙传中对斯谛勃咢克的介绍,且以克氏介绍斯氏的一段原话附于文中。值得提出的是,早在1906年,周作人已经译介发表了斯谛勃鄂克(即斯谛勃咢克)的小说《一文钱》,说明周作人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早于译介《西伯利亚纪行》的1908年。后来,《一文钱》收入《域外小说集》时作者名改为斯蒂普虐支部、斯谛普虐克,在“著者事略”中,译者特意指出其为俄国“虚无论派之社会改革家”。[3](P.556)
此外,发表在1907年11月30日《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的《中国人之爱国》《防淫奇策》等文中,我们更是可以见出周作人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尤其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24](PP.165-178)同样在这一期的《天义报》中,周作人还发表了《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一文,用克鲁泡特金在自叙传中所言之意,来论述虚无主义(即无政府主义)、虚无论者与俄国革命之别。根据周作人《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中的披露,此文乃受鲁迅之嘱而作。可见,鲁迅也关注过无政府主义。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不大科学的、多有空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学生中间”“比较的更有吸引力”,“俄国有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用了漂亮的英文,做出好些书来,其中一册《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最有力量”。[22](第12卷,P.678)看来,当时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也并非仅周氏兄弟。这样,周作人译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一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 语
周氏兄弟在晚清初登译界,受译界潮流的影响,他们选择法、美、英等国的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进行翻译。虽然后来他们和晚清译界决绝地告别,但是这段早期翻译的经历无疑加深了他们对法、美、英等国文学的了解。《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中选择了英、美、法三国各一位作家的作品,而美国作家爱伦·坡,周作人在之前就译过他的《玉虫缘》。从1906年开始,周氏兄弟的翻译进入到《域外小说集》的酝酿期。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时,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并将其贯彻到《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过程中。也是在这个时期内,周氏兄弟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而这是《域外小说集》的重头戏。在《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的16篇作品中,俄国文学和弱小民族的文学占去13篇。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中,周氏兄弟选录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艺思潮的作品。他们以一种恢弘的气势告别了晚清译坛,同时宣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1](卷10,P.168)“新际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1](卷8,P.455)十多年后,鲁迅在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域外小说集》的“序”里反复提到“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1](卷10,PP.177-178)这里的“本质”,即指的是《域外小说集》所引入的“新际文潮”。而正是在早期翻译活动的基础上,周氏兄弟才做到这一点的。
可见,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对后来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不仅仅是在《域外小说集》上,一直到后来在他们各自的文学生命里我们仍然能够触摸到痕迹。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增订本):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周作人.周作人译文全集:第11卷[M].止庵编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M].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任冬梅.论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J].现代中文学刊,2012,(6).
[8]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9]神田一三.鲁迅《造人术》的原作[J].鲁迅研究月刊,2001,(9):38.
[10]熊融.关于《哀尘》、《造人术》的说明[J].文学评论,1963,(3).
[11]朱振武.爱伦·坡小说全解·序言[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12]曹明伦.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J].中国翻译,2009,(1).
[13]李德超,邓静.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源[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14]雨果.雨果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5]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6]陈梦熊.知堂老人谈《哀尘》《造人术》的三封信[J].鲁迅研究动态,1986,(12).
[17]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8]韩洪举.林译《迦茵小传》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0.
[19]林纾.林纾文选[M].许桂亭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0]邹瑞玥.林纾与周作人两代翻译家的译述特点[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2).
[21]周作人.鲁迅的故家[M].止庵校订.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22]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3]周作人.夜读抄[M].止庵校订.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24]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