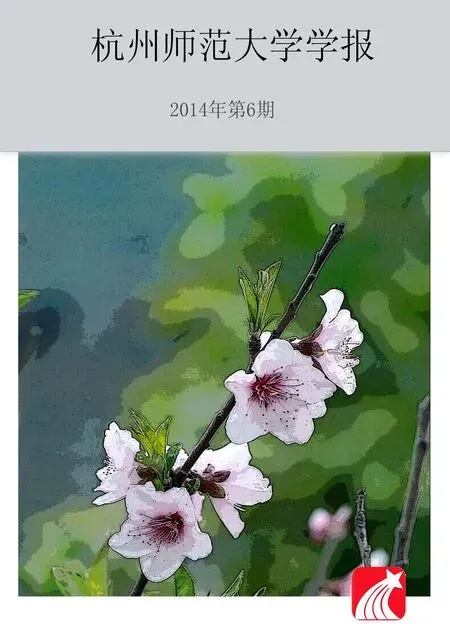黑格尔对牟宗三儒学思想的影响
陈 锐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
与19世纪俄罗斯类似,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也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康德与黑格尔是有相当不同的,康德较接近于启蒙,而黑格尔则在佛教、道家或现代新儒学中引起了更深切的共鸣,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唐君毅和牟宗三。德国哲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那种纯粹学术和历史的研究,他们是要借助其方法来解决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问题,是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以在现代世界中构建一个思想体系。他们面临的问题和黑格尔的时代是类似的,即一方面要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的科学、哲学和政治,从伏尔泰主义或启蒙运动那里寻找精神武器;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类似德国浪漫派和俄国斯拉夫主义的宗教、道德复兴和民族主义的潮流。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政治方面,正当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的时代;学术方面,正当启蒙运动之后;文艺方面,正当浪漫文艺运动之后——因此很有些相同。黑格尔的学说于解答时代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而黑格尔之有内容、有生命、有历史感的逻辑——分析矛盾,调解矛盾,征服冲突的逻辑,及其重民族历史文化,重有求超越有限的精神生活的思想,实足振聋起顽,唤醒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觅与鼓舞”,[1](P.118)贺麟说自己在1949年前是从“新黑格尔主义观点来讲黑格尔,而且往往参证了程朱陆王的理学和心学”,并认为陆王心学在20世纪上半叶之成为现代哲学的主流,也是由于体现了那个时代用内在良知去“反抗权威,解除束缚”的需要。[1](P.126)加拿大学者彼得·巴腾在其文章中,也引述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说法,将中国与“二战”后法国对黑格尔思想的兴趣相并论:“20世纪40年代末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后,法国人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蒙娜·德·波伏娃之所以对黑格尔感兴趣,是因为她深切感到,历史是一种负担。20世纪40年代,当贺麟开始翻译《小逻辑》的时候,那种全球性的破坏力也在亚洲激发了一种颇为相似的情绪。人们考察历史与人的本质。他们认为,研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对他们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大有裨益。”[2](P.72)
在思想背景上,德国古典哲学如海涅所说是“新教的儿女”,它们主要是体现了一种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的复兴运动,以此来对抗和融合来自法国的启蒙和世俗化的潮流;而中国的现代新儒家则深受佛教的影响,并最终回归到儒家传统的陆王之学。他们在对西学的了解和认同中,不是那种源自法国的启蒙和科学,而是与偏于抽象思辨和道德理想的德国哲学产生了较多的共鸣。从新儒家的前驱马一浮到唐君毅、牟宗三、贺麟等都是如此。马一浮在早年留美时对德国文学有好感,读过黑格尔,并“欲译黑格尔学说未果”。[3](P.90)他后来在复性书院时曾请国内“最早研究黑格尔哲学首屈一指的人物”张颐去讲过黑格尔的哲学。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马一浮和熊十力一样,都不满意当时有人仅仅把西学理解为器用之学的状况,并认为在西学中也存在着形而上的理论和人生哲学,既有其用,也有其本。马一浮认为,那些作为西方根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似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甥所收彼土论著百余家,略识其流别。其大概推本人生之诣,陈上治之要。玄思幽邈,出入道家,其平实者,亦与儒家为近。……凡此皆国人所弃不道,甥独好之。以为符于圣人之术。……时人盛慕欧制,曾不得其为治之迹,惊走相诧,徒以其器耳”。[4](P.350)
早期新儒家对德国哲学了解不多,尽管在内在的心灵或气质上有相通之处。到了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他们思想中理性思考和知识扩大了,但没有像以后的儒学那样更多地走向学术和政治,而是还保留着思想构建和道德的热情,这样对德国哲学的了解和共鸣增加了,黑格尔的哲学成为他们建构理论体系和思考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唐君毅被称为黑格尔主义者是有些道理的,尽管他不赞成黑格尔在政治历史中忽视个人自由的说法,但在辩证法的问题上,则较多受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如把人的精神理解成一个不断辩证发展的过程。台湾学者蔡仁厚说,唐君毅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的体系框架是模仿黑格尔辩证法的三段式的,是受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的影响:“唐先生对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有极为精深而相应的了解和体会。但他对黑格尔并不作专家式的研究和讲论, 而是取其长而去其短, 吸收黑氏讲‘精神发展’ 的智慧和理路。所以唐先生的著作, 也显示出层层推演、连环相生, 而又酥纶开合、交光互映的特色。”[5](P.503)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唐君毅说哲学辩证法的否定就是在矛盾中不断超越自身的过程;他认为西方哲学中,从黑格尔至布拉德雷最能知其义,黑格尔能知任何存在皆有其内在矛盾,此所谓内在矛盾在发展历程中,必有一自己否定之阶段,亦即自己死亡之阶段。
二
至于新儒家牟宗三,也和唐君毅一样借助辩证发展观来思考道德和文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宏大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中体现的德国哲学的影响也使得后来的一些更趋向现实的儒家人士难以接受。在牟宗三的思想建构中,他批评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努力用中国传统思想去弥补其不足,由于这个因素,他和康德哲学的关系也常常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在台湾学界曾有“不懂康德,就不懂儒家”的说法。但在另一方面,尽管黑格尔的思想对其理论建构有关键性的作用,却在研究和关注上显得不足。当然,就牟宗三个人来说,他的气质也许比唐君毅更近于康德,他处处将康德的二元论作为西方哲学的代表,对之进行仔细地翻译和研究,而对黑格尔却缺少深入的了解。他对黑格尔的认识主要是受到唐君毅的影响,“我并且因著他,始懂得了辩证法的真实意义以及其使用的层面。这在我的思想发展上有飞跃性的开辟。……我因此对黑格尔也有了好感。这都是君毅兄所给我的提撕而得的。我得感谢他,归功于他”。[6](P.99)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牟宗三对其抽象的哲学思辨并没有好感,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历史哲学。牟宗三在《历史哲学》的自序中谈到自己与黑格尔的联系时说:“吾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者,则在明‘精神实体’之表现为各种形态。吾于此欲明中国文化生命何以不出现科学、民主与宗教,其所具备者为何事,将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完成宗教之综合形态。此进于往贤者之义理乃本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而立言。”[7](P.4)
对于当时的新儒家来说,在理论上主要面临的是解决儒家天理良知与作为现象的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即如何将超越的存在与感性现实、道德与知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精神统一起来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在朱熹或黑格尔的时代也都存在过,在今天也仍然如此。牟宗三的解决办法就是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将精神或儒家的天理良知看成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其中那些对立的东西都包含在其内,都在历史中展现自己,这样就似乎避免了那种二元对立的理论困难。在解决儒家的道德精神与政治民主以及科学的关系时,牟宗三认为儒家的道德精神尽管在科学民主方面有所不足,但从精神的辩证发展来看,良知天理不会静止不动,也可在“良知自我坎陷”这样的自我否定发展中开出知识和民主。中国传统本来内在具足,只是尚未完成而已,精神要在历史中经历“对于良知本觉神智妙用之否定,因这个否定而成为政治的主体和与政治的对方之客体。在这种主客体的对立中,国家政治法律才能积极地建立起来”。[8](P.184)这样,精神在自我否定中即“不断地转进中,保持其创造性与活泼性。……它虽是要冷静下来而转为思想主体,委屈自己而转为政治主体……这在精神表现之辩证发展中,必然要贯通地有机地发展出来”。[8](P.185)
对于儒家个人的道德实践,牟宗三认为它也像黑格尔的理念在辩证发展中完成和实现自身那样,经历了那种类似三段式的过程,“故精神表现根本就是实践的。只有把自己处于道德的实践中,然后方能体会到辩证的发展”。[8](P.180)人在婴儿阶段是原始的混沌,这个精神生命,“就是辩证发展中所谓‘原始的谐和’,这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圆融不分’的绝对”。[8](P.181)然后这个最初的生命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异化出自己的对立面,这时“由自觉而显出主客之对立,就是原始谐和之破裂。这破裂就表示一种否定,对于原始谐和的否定”。[8](P.182)在这个阶段类似禅宗的“截断众流”,凸显出道德的主体,但是精神生命还要向前发展,到达合的阶段,“这‘合’就是‘再度谐和’的圆融绝对。这个‘合’就表示对于破裂而成的正反对立再加以否定,而此否定之形成是由于把‘反’的对立性,障碍性,加以消除或克服。你所以能消除或克服它,就是因为你保持住那个‘正’”;[8](P.182)“这就是‘良知天理’的繁兴大用(成物),而其所成之物亦就是实现良知天理之资具。此就是儒家的本末圆融之‘盈消’,而为辩证发展所证实。这在禅家,名之曰随波逐浪,经过截断众流,盖天盖地后而来的‘随波逐浪’,这表示一种大而化之、圆通无碍的境地(佛家宗旨虽别,而工夫的辩证发展则同)。黑格尔名之曰‘绝对’,表示‘合’的圆融绝对(程明道说动亦定、静亦定、亦就是本贯末、物从心的绝对定境)。……黑格尔从精神发展上讲辩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最恰当”。[8](P.183)
三
尽管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以此来解决中国文化和世界的问题,但一直面临着诸多争议。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黑格尔的那种辩证发展本身就包含着神秘的因素,以至那些较为理性和现实的人总是觉得难以接受。那种“良知自我坎陷”说从知性的角度来说是难以解释的,但如果将之看成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内在否定和发展的话就没有什么新奇的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牟宗三尽管借助黑格尔的辩证发展观来构建自己的体系,但他自己的气质却与黑格尔有距离,或者说他尽管批评康德的不足,但他在气质上比唐君毅更近于康德,除了那个辩证发展的框架外,在思考道德和文化问题时则更偏好那些类似康德的知性的概念分析,他是如徐复观所说的“智者型的儒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对牟宗三的思想特色及其面临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总的方面,他对黑格尔缺少深入的研究,“吾一直未正式去细读他,去一句一句去研究他,乃是在师友之提撕与启迪中渐渐虽未正式研究他而却能知道他嗅到他”。[6](P.103)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牟宗三所了解的主要是康德,而对浪漫派、黑格尔思想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缺少了解。 牟宗三晚年的《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总结一生学术,对西方哲学进行系统梳理,其中将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作为主线,认为 “康德以后的哲学都由康德开出……因为在康德的哲学内,一切哲学的问题,哲学的论点都已谈到”,[9](P.39)“德国方面康德以后的哲学承之前进者,亦不必能是相应地承之而前进。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俱不真能相应地承之而发展。”[9](PP.72-73)
康德在反对浪漫派的神秘的想象时反复强调哲学要追求清晰的形式的知识,认为“这种东西毕竟是哲学的最主要的任务”,[10](P.411)牟宗三在批评康德二元论的同时则对康德的知性分析保留了相当的认同,并认为黑格尔在这方面有所不足,没有“以分解作底子”,没有像康德一样“分解所以标举事实,彰显原理,厘清分际,界划眉目。故哲学的思考活动常以此为主要工作。但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注意与贡献却甚少。他直接以辩证的综合出之。故读其纯哲学方面的书者,觉其所言好像是一个无眉目无异质的混沌在那里滚”。[8](P.140)牟宗三尽管说黑格尔辩证法的优点是将精神和历史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辩证法不同于康德的知性,“所以辩证法是动的逻辑,而形式逻辑是静的。……它所以是动的,乃因为它根本是由主动的创造的理性发展,而且还要统驭知性、贯彻知性,而见其为一发展,所以它才是动的”。[8](P.179)但他又认为其《大逻辑》不是从康德的知性逻辑范畴讲起,而是从“空洞无物”的上帝或绝对进行推演,不够清晰,不是好的哲学家,只是历史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的综合’之在纯哲学的表现却失败,令人无法接近相从”。[8](P.142)
由于牟宗三思想的上述认识,导致他在批评康德的同时也保留了那种类似康德的二元论的形式。康德本人的气质接近启蒙运动,爱好理性和秩序,体现了科学家的品格;而黑格尔的思想却与浪漫派以及德国传统中的神秘主义、民族主义有更多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尽管批评康德的二元论,要用中国传统思想去补西方之不足,但他未能理解那种“消化康德而归于儒圣”[11](P.152)的努力在黑格尔那里实际上早已被多方面尝试了,那种“人虽有限而可无限”、“人可有智的直觉”、“良知坎陷”等说法尽管复杂晦涩,但其内容以及思路从东西方历史上的神秘主义传统来看,并没有多少新颖之处。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将道德与幸福、信仰与科学、无限与有限、物自体与现象分开,因此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难。而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消解这种知性的二元论,将精神和自然整合为一个无限辩证运动的过程,或者说将神秘与理性、浪漫派与启蒙运动、东方的“无”和西方的“有”统一起来。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也和实践的感性、冲动、嗜好等相对立。完善的道德只能在彼岸,因为道德假定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差别。道德是根据普遍规律对于感性情欲的斗争”。[12](P.292)康德为了解决这种对立,将其统一归于至善、审美判断和上帝,但“那种结合本身仍然只是一个彼岸,一个思想”。[12](P.292)黑格尔说:“善与实在的这种同一性就是理性的要求。……善与世界的对立和矛盾是和这种同一性正相反对的;因此理性要求必须把这个矛盾扬弃,并且要求一个本身至善并统治世界的力量。这就是上帝; 这就是上帝在康德哲学中所占的地位。要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却有上帝存在的要求。我们有两个方面,世界与善。德性或道德只有当它在斗争时才是善的;它发现这个对立就这样被设定了,而另一方面又有必要去寻求两者的谐和。……但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是上帝?说上帝是超感官的并没有多少意义”;[12](P.304)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其历史哲学是和整个思想不可分的,或者说是辩证发展在历史中的特殊运用而已。牟宗三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纯哲学中是失败的,这绝不是偶然的,那种认为其辩证法只适用于历史和实践领域的想法实际上也只是重复了20世纪一些西方的说法而已。牟宗三未能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中的神秘主义以及其与东方的关系,或者说,他的儒家的道德立场也使他很难真正体验那种贯穿于东西方历史中的超道德的神秘境界。
黑格尔对康德二元论的消解源于德国的神秘主义传统,与中国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也有相通之处,对此牟宗三也有所意识,并反对使用神秘主义这个词。康德从理性和科学的立场出发,不喜欢这种神秘主义,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批评神秘主义,认为在反对经验主义的同时,实践理性“这个范型也防范住实践理性方面的神秘主义”,[13](P.78)当然在那时大革命还没有爆发,康德还没有像1795年的文章中那样对新起的浪漫派的神秘热情激烈批评,还认为神秘主义的危害没有经验主义那么大,“因为神秘主义与道德法则的纯粹性和崇高性是可以互相融和的……在另外一方面,经验主义却把意向的道德连根拔去”。[13](P.78)对于康德的这些说法及其与黑格尔的差别,牟宗三的想法是复杂而微妙的,在总体上,他也看到了“人类的思考历程,大体都可以概括在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之下……在西方哲学家中,只有黑格尔不是采取分析的路子,他所采取的是辩证的方式。所谓辩证的方式,就是消化分别说所建立的那些观念,然后用辩证的方法把它统而为一。不过在他表示辩证的统而为一的过程中,他也随时有分别的解说”,[14](P.313)“关于非分解地说,除了黑格尔的哲学以外,还有另一种形式,就是西方哲学中所说的神秘主义(Mysticism)。神秘主义当然没有分别说,不但没有分别说,而且所谓‘神秘’根本是不可说。可是神秘主义在西方哲学中并不能成一个正式的系统,只是有这么一个境界而已,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成气候的系统看。然而这种境界在东方哲学里,即可以得到正视,可以独立的展示出来;而且东方哲学大部分的功夫都放在这上面。那么,是否还能用西方‘神秘主义’这个辞语来表示东方的这种思想,是有点问题的。……东方的哲学思想,你要说它是神秘的,它也可以是神秘的;‘神秘’这种含义在佛教经典中到处出现……而这类的话,你是否可以用西方的mysticism 来解说呢?”[14](P.314)牟宗三认为,东方哲学中存在着那种康德所批评的神秘主义;在黑格尔那里,“此即是辩证的非分别说,这就好比禅宗所表示的方式一样”。[14](P.317)牟宗三不喜欢神秘主义这个词,也反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以神秘主义来概括孟子、庄子与《中庸》《易传》之思想;当时我们看到这里就觉得很不妥当。因为孟子的思想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思想很清楚地呈现出来,怎么可以用‘神秘主义’一句话就把它给定住了呢?这种说法是很不妥当的。所以西方的mysticism一词,并不适合于中国哲学”。[14](PP.314-315)牟宗三在这个问题上赞同梁漱溟的说法,认为“梁漱溟先生指出这不是神秘主义而是真正的理性所在”[14](P.315)“在东方哲学中,以儒家之思想来与康德相比照,儒家思想是以道德为主,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儒家以仁为主,仁是理性;那么由仁所充分展开之理性,是否还可以用西方之神秘主义(包括康德所批评之神秘主义)来解说,似乎很成问题”。[14](PP.316-317)
四
在这里,牟宗三确实也触及到了思想的最深之处。他也意识到神秘主义会将一切确定的东西化为虚无,儒家的道德理想驱使他必须要保留一个终极和确定的存在,在这点上他和康德是类似的,而黑格尔的哲学以及中国传统的道家和佛教所追求的却是超道德的境界。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有”和“无”没有哪一个是绝对的开端,在否定和肯定这两者中没有哪一个是优先和独立存在的,在神那里也包含着否定和活动性,黑格尔在谈到德国历史中的神秘主义者波墨时称赞其思想的深刻性,即如何努力将肯定和否定这些绝对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在神的内部把握消极方面的恶和魔鬼。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发挥了波墨的这种思想,即认为神本身也包含着否定的东西,善和恶不可分离:“上帝的生活和上帝的知识因而很可以说是一种自己爱自己的游戏;但这个理念如果内中缺乏否定物的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它就沦为一种虔诚,甚至于沦为一种无味的举动。”[15](上册,P.11)“但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15](上册,P.21)
在唐君毅和牟宗三的思想中,尽管用辩证法来解释和包容那些否定的东西,让良知天理在类似辩证法的自我坎陷和否定中走向现实,但在最终仍然把肯定作为终极的目标和存在,而否定和矛盾则不过是次要和辅助的。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传统儒道思想作比较,认为儒家虽然承认现实世界和生命意识中的矛盾、冲突和苦痛,但最终的目标仍是要到达一种较高的目的与和谐,“即于其他人物之苦痛失望,必有所不安与不忍,则此其他人物矛盾冲突感,即成为吾所原则上欲加以化除,而使其发展生化之历程,一直畅遂,而归于内在的和谐者。由是而吾人诚透过吾之仁心所发出之情,以观万物之矛盾冲突感,亦为吾心之求致中和于其上之场所。因而此矛盾冲突感,亦非其他人物所必然的须具有者,亦非其他人物之本质的属性”。[16](P.120)总之,唐君毅认为黑格尔的“乃恒否定其自己,或自己与自己相矛盾”的“辨证的宇宙观,亦非中国儒道之二家所取”。[16](P.119)
在这点上牟宗三也与唐君毅类似,在《论“凡存在即合理”》一文中,他将黑格尔的“理性”误解为与现实不同的正面价值,将“理性的狡计”理解为道德精神在曲折发展中以完成自身的过程,“人不能常惺惺维持其向上精神与正面的文化理想……假借毁灭之一曲折来解决来完成,这是人间的可悲。黑格尔名之为‘理性的诡谲’(cunning of reason)。中国人以前名为‘天道之权变’”。[8](P.159)在谈到朱熹与陈亮的差别时,他认为朱熹的道德判断忽视了历史和否定性的东西,因此要在辩证发展或良知坎陷中容纳和解释那些否定性,“朱子对于三代以外的断定,只是抹杀。所以他只能说正面的价值,不能说负面的价值。就是说,他的断定不是历史发展精神表现中的估价”。[8](P.153)由此他承认陈亮的历史思想以及与朱熹辩驳的意义,认为陈亮要为汉唐争地位,以为“汉唐于默默不觉中对于道亦略有所表现,不能吹毛求疵,一概抹杀”。[8](P.150)但是牟宗三认为陈亮的学力不足,因而必须“把以前的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两种综合地统一起来”,但是在牟宗三所理解的综合统一中实际上仍然以道德判断作为优先和主要的东西,而历史和否定只是从属和辅助的,“只有在这个综合观点下,才能曲线地间接地说‘凡存在即合理’。盛世、治世、正面的,当然直接说它合理。这句话的问题单在衰世、乱世、负面的一面。就此面说,说它合理,并不是说它本身是对的,是合理的。它本身仍是罪恶,仍是邪恶。所以说它合理,一定是曲线地间接地说。而且说它合理亦只是估定它的负面价值……而所谓负面价值亦不是就其自身言,乃是就其对于未来的‘正面的’之关系言。……这个意思只是:‘堕落不深,觉悟不切’修道上的话应用于历史。……但是,人不是神,所以历史、文化、价值(正面的,负面的),这都是人间的事,不是神的事。若只如朱子所表现的道德判断,则必须人是神,若不是神,便不必说了”。[8](P.154)由上可见,牟宗三的思想尽管具有辩证发展的框架,但终极的道德价值和神本身却并不包含否定,否定对于神来说终究是外在的东西,而在黑格尔或神秘主义传统中,上帝和理念中本身包含否定性和恶,善和恶在精神的运动中也互相过渡。
因此,对牟宗三或唐君毅来说,他们虽然要用中国传统儒学和佛教的思想来弥补西方理性的二元论的不足,但他们在建构思想体系时仍然保留了不少那种黑格尔所批评的知性思维或二元论的成分,在对神秘主义的理解或体验上仍然是不彻底的。当他们高扬儒家的道德价值,来对抗西方科学、理性主义和世俗化的潮流时,在理论上都仍然多少面临着那种康德的二元论的困难,也就是普遍的道德意识和现实存在、历史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不仅是康德哲学,几乎人类所有的宗教及道德学说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面临类似的问题。历史上那些神秘主义思潮之所以始终存在,正是在于能够包含消解二元论的要求。就牟宗三而言,儒家的道德立场使他更偏好人类的理性和现实秩序,使他像康德那样站在地上来仰观无限的星辰,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从神、天上或世界历史来俯视人间,不是从无限和绝对的存在来推演出有限和相对的现实世界。因此,当牟宗三思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等许多问题时,其立足点仍然是那种现实的差别和知性的分解。例如说,当牟宗三认为中国在“政治的主体自由”和“知性主体”的理解形态上有不足,而西方文化生命一往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并要用中国传统哲学去补充西方二元论的不足时,他不知道这正是黑格尔所批评的知性的外在的比较和统一,也是中国哲人所说的文化上的体和用的分离。在这一点上牟宗三甚至不能像马一浮那样相信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一不异,也未能像钱锺书那样强调“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就唐君毅、牟宗三这些新儒家来说,他们在看待世界时仍然像康德那样抱有那种现实的伦常秩序和终极的价值理想,追求“各欲通过其一时之阻碍,以一直成就其自己……以成就人物为事”[16](P.120)的个人道德的完善,而不可能诉诸那种彻底的宗教神秘主义或黑格尔所说的真的无限物,否则他们就不是儒家了。而在黑格尔那里,所关注的是普遍的理念和世界历史,其“理性的狡计”中的理性本身就包含着否定性,而不等同于牟宗三所理解的正面价值;同时,道德在黑格尔那里也只是理念发展中的有限的环节,而不是最高的存在和目的。德国学者G·G·索伦说:“神秘主义者甚至不回避这样的推论:在更高的意义上,上帝中有恶的根源。”[17](P.13)对于波墨来说,善和恶在神那里互相过渡和统一,是“一切对立在神中的联合”;在黑格尔那里则体现于概念的运动和世界历史中。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那种“德行”在世界进程中也只是下降为一个有限的环节,“在德行的意识那里,各人私有的个体性必须接受普遍、自在的真与善的训练约束。……在世界进程里,个体性的态度与它在德行意识里的态度恰好相反,它现在把自己当成本质而使自在的真和善屈服于自己之下”。[15](上册,P.252)“个体性在寻求快乐和享受的过程中找到了它自己的复灭,并从而满足了那普遍的东西”,[15](上册,P.253)“对于德行的意识,普遍只在信仰中或潜在地是真的,但它还不是现实的普遍性”,[15](上册,P.254)“这种普遍的东西为了它自己取得生命,能够运动,就需要个体性原则,并在个体性原则中取得它的现实性”。[15](上册,P.255)在唐君毅和牟宗三那里,矛盾和冲突只是到达最高的善与和谐的条件,仍然是要被克服的对象,普遍的善与现实世界仍然是不同的东西,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善本来被当作是自在或潜在的东西,与存在着的东西相对立”。[15](上册,P.257)但黑格尔的辩证法旨在消除一切的二元对立。对于他来说,“善和恶是不可分割的”,[18](P.144)“思维于是把它们的这种差别以最普遍的方式加以固定,那就是,固定为绝对对立的善与恶,而善与恶被看成是天壤悬殊、绝对不能变成同一个东西的。但是这种固定的存在却以向对方直接过渡为其灵魂”。[15](下册,P.44)
五
在东西方各种宗教和道德哲学中,神秘主义往往是最深的源泉,也是理论上最根本的难点所在,它在20世纪中国也少有专门的研究。冯友兰曾对传统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有过论述,但其理解仍然像黑格尔所批评的知性思维一样,即是将神秘看成是与理性不同的,无法用逻辑、语言来认识和表达的一种负的方法。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负的方法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19](P.394)新儒家方东美和牟宗三一样,要用中国的和谐智慧挑战西方受二元对立问题所困的分裂思维方式,他对神秘主义这个词也不像牟宗三那样排斥。在《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中,他引述怀特海的话说:“哲学是神秘的。神秘主义直接洞见了不可言说的深奥。但哲学的目的在于将神秘主义理性化,而非将其消解。”[20](P.213)康德的知性哲学类似于儒家,具有现实感,其目标是道德自由,而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却指向那种超道德的境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超道德的境界论主要体现在道家和佛教中。在庄子《天运篇》中,“仁义,圣王之蘧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在宋明儒学中,尽管批评佛道的空无,现实感增加了,但仍然涉及神秘主义的问题。在程明道《识仁篇》和《定性书》中,也多少包含有一种超道德的神秘主义的思考:“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圣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岂尝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尔?若善者亲之,不善者远之,则物不与者多矣,安得为天地?”在程明道看来,即使是庄子的“逍遥”与“齐物”最终也不能脱离现实的存在;“而庄周强要齐物,然而物终不齐也。尧夫有言‘泥空终是著,齐物到头争’。此其肃如秋,其和如春”。[21](PP.17,33)
但如前所说,神秘主义虽然有助于解决理论上的困难,但是不能保证那种类似康德哲学的道德庄严,神秘主义表现的是超道德的天地境界,但人的道德理想却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开端。牟宗三的哲学触及到了这些问题,因此他在最终必然要保留一个正面的价值理想。事实上,黑格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神秘主义本身的危险或困难,因为任何理论涉及现实秩序时,都需要知性意义上的绝对的肯定性,而不能容许那种神秘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因此对于黑格尔的思想来说,也像海涅一样不能被完全等同于神秘主义,因为毕竟还要保留神和人、善和恶的现实差别,就像他强调用理性思维去认识最高真理一样。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为斯宾诺莎所受到的泛神论和无神论的攻击辩护,即认为虽然在斯宾诺莎的无限的实体中,善和恶的差别消失了,但当涉及样式和现实的差别时,则维护了道德的尊严,因为那种善恶只是在现实中、在神与人的差别中,“在这里,人与神的区别存在的时候,本质上亦即是善与恶的区别存在的时候。因为人本来就是这样,有善恶的区别,就是人所特有的命运。假如我们仅仅着眼于斯宾诺莎主义里的实体,我们在里面就找不出善与恶的区别。……但假如我们更注意他的体系中论及人、和人与实体的关系,即论到恶及恶与善的区别的地方……我们会钦敬他的以纯粹对神的爱为原则的高尚纯洁的道德观。而且会深信高尚纯洁的道德就是他的体系的后果”。[22](P.10)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也区分了两种情况:即认为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需要一个绝对肯定的开端,但从思想本身的要求来说,则否定就包含在肯定中; “但是关于恶的渊源问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否定的东西怎么会进入肯定的东西之内,如果我们假定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是绝对肯定的东西,那么,我们无论怎样穿凿,也不能在肯定的东西中寻出否定的东西来,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在它的方面是容许恶的,这就等于把这种否定的关系归诸神,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也是毫无意义的。在宗教神话的观念中,人们不去理解恶的渊源,也就是说,不再从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之中去相互认识。……但是,这种说法是不能满足思想的,因为思想要求某种理由和必然性,并把否定的东西理解为本身源出于肯定的东西。……如果我们死抱住纯善——即在它根源上就是善的,那么,这是理智的空虚规定”。[18](P.145)在这里,黑格尔将思想与世俗宗教相区别,既承认世俗的需要,又保留了自己的思想。牟宗三则显然不同,他始终关心的是某种正面的价值,认为“依西方正宗的哲学系统说,事物之‘被知性’(亦曰观念性),现实性,合理性,三者是合一的。上帝有两种事物不能创造,亦即有两种东西不能在神心的涵养涵摄中,一是矛盾的东西,一是罪恶。因此,在现实宇宙中,凡是一个‘有’,一个存在,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都有它在神心中的意义与价值。哪怕是一草一木,一个苍蝇,一个粪蛆,也是一个正面的有。凡自相矛盾的必归于虚无(是零)”。[8](P.149)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即可理解牟宗三为何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理解为通过曲折和坎陷以达到正面价值了。
[1]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彼得·巴腾.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J].哲学分析,2013,(3).
[3]丁敬涵.马一浮先生遗稿三编[M].台北:广文书局,2002.
[4]马一浮.马一浮集:第2册[M].丁敬涵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5]蔡仁厚.唐君毅先生的生平与学术[C]//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6]牟宗三.五十自述[M]//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卷.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
[7]牟宗三.历史哲学[M].台北:学生书局,1988.
[8]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1]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4]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G·G·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0]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2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2]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