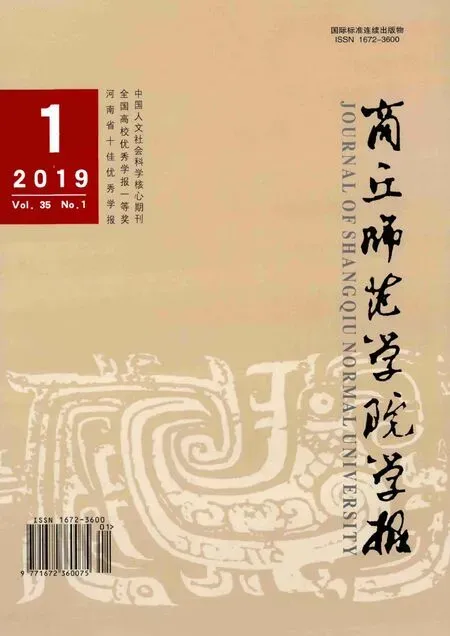西方汉学界关于庄子哲学之神秘主义性质的论辩
徐 强
(大连理工大学 哲学系,辽宁 大连 116024)
在西方汉学家看来,庄子哲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往往带有比较浓厚的神秘色彩。比如,它追求天人合一或者与道合一,主张通过个人修养而最终达到一种终极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却很难用语言来说清楚;在认知过程中,它推崇直觉、体验,不太重视理性分析或清晰的逻辑表达。庄子哲学由于更关注个人,更加个人化,这种神秘性的特质就更容易见到;另一方面,《庄子》文本自身的特色——书中充斥着寓言或卮言之类的具有荒诞色彩的语言表达风格——更加强化了这一特征。所以,考察西方汉学界对庄子哲学的研究,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研究者用神秘主义(mysticism)来理解庄子哲学。那么,庄子哲学究竟是否具有神秘主义的性质呢?西方汉学家对这个问题又有哪些代表性的看法呢?
首先来看何谓“神秘主义”。总体而言,“神秘主义”并不是一个意义清晰的概念,目前存在着对它的多种不完全相同的理解,而这些理解可能导致对庄子哲学是否是神秘主义的不同判定。关于神秘主义,美国布朗大学宗教学与东亚研究专业罗浩(Harold D.Roth)教授在《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一书中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说明。他认为,神秘主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可以包括诸如神秘体验、神秘写作、神秘技巧以及神秘语言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极为关键的是神秘体验,这种体验,通常具有如下特征:不可言说性;可知性;易逝性;被动性;有多种解释的对“一”或者“一体”的感觉;正常的智力活动的终止,或者用一些更为高级的或本质上不同的智力形式(如直觉)代替它。与神秘主义密切相关的还有神秘写作、神秘技巧、神秘语言等。神秘写作涉及“这样的文本,它讨论通往领会终极知识的道路,这种知识是每一个特定宗教不能不提供的;它还包含了关于这种知识的本质的陈述”[1]77。神秘技巧则可以包括诸如“入定”(meditation)与“意念”(contemplation)等修炼活动。神秘语言则是指在神秘修炼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通常只是对那些熟悉正在谈论的体验的瑜伽修炼者是可理解的”[2]101。根据不同的标准,神秘主义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神秘体验的基本样式,可以分为内向的神秘主义和外向的神秘主义;根据神秘主义体验中被统一的东西或“客观对象”,可以分为有神论的(theistic)神秘主义和一元论的(monistic)神秘主义;等等。
西方汉学界对于庄子哲学之神秘主义性质的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多数学者认为,庄子哲学是一种神秘主义哲学,或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只不过,对于庄子哲学的神秘主义究竟是何种类型的神秘主义,以及其神秘主义的理论特点,学者们的理解则不甚相同。
一、李亦理:在世或入世的神秘主义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李亦理(Yearley Lee)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神秘主义,即在世/入世的神秘主义(intraworldly mysticism)和一元的/出世的神秘主义(unitive/escapist mysticism)。李亦理认为,庄子哲学的神秘主义是入世的神秘主义,因为庄子的修养目标并不是要与某个不变的、一元的原则合一,而是要完全地参与到自然界之中[3],这样的人可以做到“其心若镜”。他不离开这个世界,却可以达到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与内在于世界的神秘主义相对的是逃避主义的或出世主义的(escapist)神秘主义,也称作一元的(unitive)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的特点是追求与某个不变的、一元的原则相“合一”,为了达到与这种不变的原则合一,它强调修行者需要离开世界,不参与世间的俗务,不被凡俗之事所干扰,这样才可能达到某种最终极的神秘主义的状态或境界。在李亦理看来,正是庄子哲学的这种在世/入世的神秘主义特征,使得它与西方的一些一元的/出世的神秘主义体现出明显的不同。
二、罗浩:双型的神秘主义
罗浩是美国汉学家,他在《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一书中主要关注的是道家的神秘主义传统。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道家思想起源于《管子·内业》或《内业》所代表的传统。不同于把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源头的传统看法。罗浩认为,道家学派源自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内在修炼,用他的话说就是,“它们来自于一个基于内在修炼的共同传统的一部分”[2]13。所以,罗浩对庄子哲学的研究,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关注庄子的内修层面或修炼层面,以从中找到有关神秘主义或神秘修行的论述。
罗浩认为,庄子哲学中有一种双型(bimodal)的神秘主义经验[4]。所谓双型(bimodal)的神秘主义,主要立足于英国哲学家史泰斯(W.T.Stace)对神秘主义的划分。史泰斯把神秘主义分为两种:内向的神秘主义(introvertive mysticism)和外向的神秘主义(extrovertive mysticism)。其中,“外向的是通过个人的感官向外看,该个体看到,在他与世界之间有基本的一致,同时他还觉察到了一与多,一体与多元”[2]93;“内向的神秘体验向内看,完全是一种一体的体验,即对于统一的或如一些学者(福曼与其他人)所称的‘纯粹的’或无目的的意识的体验。”[2]94双型的神秘主义就是兼具这两种类型之特点的神秘主义。
依罗浩之见,庄子的“大知”或对直觉知识的接受,来自于沉思的实践。立足于沉思的实践行为,罗浩称此行为为“内修”(inner-cultivation)。这种实践包括一系列行为,例如静坐、调息,直至身心俱静,而意识逐渐被空掉或忘掉,如《庄子》中所说的“坐忘”“心斋”。如果能够修养到最高或最终极的层次,那么这种不断做各种否定的修行行为可以让修行者最终直接体验到道[4]。“心斋”和“坐忘”都是以自我否定的方法进行的内在修养行为。通过这种修养行为,日常的感知和思想都被从意识中去除,修养者由此达到与道合一,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大通”。这就是史泰斯所讲的“内在的神秘体验”。
罗浩进而指出,对庄子而言,达到这种体验还不是他的最终目标。《庄子》中有“因是”和“为是”两种类型的认知,所谓“为是”是指局限于一种固定的认知模式,并且僵硬死板地固执于这种认知方式,而“因是”则不固守一种立场,修养者能根据不同情况自发地调整,此即庄子所言之“明”,而这种“明”就是一种神秘的直觉的知识。庄子进一步认为,丢掉一种固定的认知,就是抛弃对自我的固执,所谓“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齐物论》)。丢掉自己,摒弃了选择与偏见,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因是”。罗浩把这种模式称为“外向的神秘主义”,而这种神秘主义的终极指向则是与道合一[5]。不同于此,日常的“为是”常常区分、辨别事物,并基于区分而有所偏好或选择。只有道才能通万物、一万物,故庄子所谓“大知”“明”都侧重于道的视角,由此视角观万物,则万物各是其所是,个体对万物也就没有了偏好偏见,而至于万物平等,此即所谓“道通为一”。因为庄子强调个体应在自身与外物的关系中体验这种神秘主义,所以罗浩称之为“外向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道毕竟不能被作为认知的对象,它只有在我与外物间的界限消失之后才能被体验或把握,而我与外物间的界限的消失又必然会表现出神秘的特点,故而这是一种“外向的神秘经验”。在《庄子》中,“与道为一”的神秘经验又被描述为“同于大通”。一旦个体在这种境界中去除或忘掉了自身,从而回到多元的日常生活世界,那么他便不再固执于自我,“因是”的经验也就会出现,这个过程所体现的是由“以自我为中心”到“以道为中心”的转变。
总之,罗浩认为,庄子哲学中存在着双型(bimodal)的神秘主义体验:“第一种类型是内向的一体意识,那里修炼者完全与道合一”,“第二种类型是已经转化的外向意识,那里修炼者回到了现实世界中,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保持先前在内向模式中体验到的、对于统一体的深切的感受。这个体验需要有这样的生活能力,即在世界上不受个体自我有限的带倾向性的观点的束缚。”[2]99-100把握《庄子》中的这两种神秘经验对于理解庄子哲学的其他主题至关重要。例如,庄子在自然观上强调自然而然,强调圣人不需主观自我意识而自发反应,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之中,他都能自然而然、自发地立足于道。这本身就是一种神秘体验,或者说,从神秘主义的视角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三、史华慈:不排斥“秩序”的神秘主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也认为,庄子哲学是一种神秘主义。不过,史华慈对神秘主义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神秘主义有如下特征:认为存在一个人类语言所不能言说的终极实在;认为人类语言所不能言传的终极实在是人类世界一切意义之源;假设具有有限性的人类或某些具有有限性的人类能够达到“一”(终极实在),或能够与实在的终极基础取得某种神秘主义的合一。同时,“神秘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获得世俗个体存在的幸福。这里无法找到个体存在本身具有无限价值的观念。……事实上,芸芸众生就像一滴水一样被重新吸收到了终极的汪洋大海之中,此乃值得心仪的圆满”[6]202。基于这种判定标准,史华慈认为,庄子哲学可以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学说。
在《庄子》中,有很多关于神秘主义的体验或神秘主义的顿悟状态的描写。例如《齐物论》开头描写“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就是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恍恍惚惚的体验。至于《庄子·人间世》所讲的“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史华慈认为,其中的“气”即为形而上的神秘主义实体。此外,《达生》篇中的承蜩老者以及造钅豦者的故事,则都蕴涵着神秘主义的技巧。
史华慈同时指出,庄子哲学的神秘主义具有自身的特点,涂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例如,他认为老庄道家的神秘主义内在地包容了为西方神秘主义所拒斥的“秩序”观念。因为在西方的观念中,“非人格化的秩序”或“结构”恰恰是一种与神秘事物相对立的存在,神秘主义很难与“秩序”观念相容,而庄子却恰恰“借助于‘秩序’的暗喻而达到神秘主义的境地”[6]205。再如,道家的神秘主义并没有在具有确定性质的、个体化的和对待的世界与那个终极的非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作为一切意义之源)之间划分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认为两者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一方面追求与终极的“道”合一,同时也肯定个体化的现实世界,或者如史华慈所说:“自然驻留于‘道’之中,在自然之中,非存在和存在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就其‘非存在’方面而论,自然的‘无为’方面是‘道’的显现,自然藉此而驻留于‘道’之中。”[6]210而在西方的神秘主义中,个体化的世界与终极的非存在的世界是对立的,相比之下,关注存在与非存在领域的关联则是道家式神秘主义的重要特色。
庄子的神秘主义之所以体现出如此鲜明的特色,史华慈认为实际上是与它们立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或说它们都分享了传统的共同的文化取向,那就是一向重视秩序,普遍地追求一种秩序感,不管它是自然界的秩序,抑或是社会的秩序。我们知道,指出“人的有限的自由”是史华慈治思想史的基本理念,在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他总是一方面考察共享的文化取向对于思想者的限定作用,同时也注意思想者在这种共享的文化取向或问题意识之中自觉和能动的反应。可以看出,史华慈学术方法的这个特点在他对道家神秘主义的研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四、史怀哲:伦理的和肯定生命及世界的神秘主义
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是德国哲学家、神学家、人道主义者,他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把庄子视为神秘主义者,并且指出庄子哲学是伦理的和对生命及世界持肯定态度的神秘主义。
史怀哲认为,庄子同道家学派的老子、列子一样,都不主张通过经验去获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们曾经试图采取经验主义的道路,进而发现这条路根本走不通,而是因为道家哲学作为一种神秘主义思想,同婆罗门神秘主义一样,相信真正的认识是通过体验忘我的癫狂的状态才能够获取的,所以他们都贬低一切通过自然的方法获取的知识。所以,在道家神秘主义和婆罗门神秘主义那里很少有对于客观世界的探讨。人自己是什么,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意义又是什么,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体验忘我的癫狂状态而获得理解和领悟的[7]57。正是因为庄子哲学是一种神秘主义思想,所以它很关注神秘主义的修养或技巧的问题。《庄子》中的很多寓言故事都描述了通往道所必需的集中意念、专注于内心世界等修炼方法。此外,为了表现出外在认识的不可靠,庄子甚至认为人根本不可能完全地区别梦境和现实。例如,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无思无虑始知道。”(《知北游》)“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在史怀哲看来,这些话显然都体现着神秘主义思想的特点。
对于老子、庄子哲学中的核心观念“无为”,史怀哲同样认为弥漫着神秘主义色彩。他说:“道家理解的积极方面的无为而治是指人们不是通过在现实世界中做出一定的行为从而迷失自己,而是达到最深层次的聚集、内在性和纯粹性,并从自身焕发出来的、能够感染他人的、在精神力量层面上的东西。”“最终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于,人不再按照人的计划而有意图,而是必须要成为决定客观世界变化的力量的一个器官。人们要放弃的不仅仅是作为,更多的是要放弃为达到某种目的的理智的思考。单纯通过内在的感觉就可以得出结论。跟着内在的调节和制约的自然力的神秘的灵感启发去走,就像一口钟一样,当别人敲打的时候,就会跟着响起来,这样,人的行为方式就是正确的了。”[7]61无论是强调达到最深层次的聚集、内在性和纯粹性,还是强调人们需要放弃理智的思考、跟随神秘的灵感启发,都体现着庄子哲学的神秘主义性质。
在史怀哲看来,庄子哲学不仅是神秘主义,而且是一种伦理和对生命及世界持肯定态度的神秘主义。他认为,与印度的婆罗门神秘主义相比,道家或庄子的神秘主义要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因为“其他所有的神秘主义都来源于对生命和对世界的否定,因而也都不包含伦理的特征,而道家思想在建筑在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之上,并致力于获取伦理的特征。它就像一曲前奏,但在其中已经完全孕育着整篇交响曲的主题。因为其中包含着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的伦理精神,所以它自然释放出这样的魔力”[7]61。也就是说,虽然同为神秘主义,但庄子和道家的神秘主义却表现出独有特征:这种神秘主义对生命和世界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因而是更为积极的,因此可能也就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五、莱格:非神秘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想
西方汉学界的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庄子哲学是神秘主义,但也有学者否认这一点。例如,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宗教系的罗素·莱格(Russel D.Legge)在《庄子和自由的人》(Chuang Tzu and Free Man)一文中指出,通常人们认为庄子思想是一种神秘主义思想,他着重关注个人的奴役状态以及如何获得自由,而不太关注社会秩序的问题[8]。因为庄子不太关注人类社会,而更关注个人生活,所以他主要是向个人而非统治者或治国者言说。关于个人生活或个人的精神自由,庄子则希望通过与道合一的神秘经验而达到。所以顾立雅(H.G.Creel)说,庄子是沉思性的,而老子是目的性的,因为与庄子相比,老子更关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问题。但是,莱格认为庄子哲学并非神秘主义,相反,庄子是一个敏锐的政治思想家,他建立了一套生活观念,这套生活观念如果能被在位者或者有影响力的人接受,就不仅能给他或他们带来自由和快乐,而且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解放和幸福。换言之,庄子关注社会秩序,个人精神自由并非庄子思想的最终目标,而仅是一种手段和途径,其目的是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8]。
六、与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比较分析
上文的介绍和解析表明,西方汉学界在庄子哲学是否具有神秘主义的问题上多数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庄子哲学到底是何种类型的神秘主义,学者们的看法却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除了我们已经介绍的诸种观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评论翟里斯(Herbert A.Giles)的《庄子》翻译时指出:庄子是神秘主义者,对于他来说,生活的目标是消除自我意识,从而成为一种更高的精神启示的无意识媒介。实际上,庄子身上集中了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几乎所有欧洲玄学或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9]274。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于此类看法不再作详细介绍。
如果把西方汉学界关于庄子哲学之神秘主义性质的研究与国内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单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大致来说,国内学者对于庄子哲学之神秘主义性质给出明确判定的不是很多。在诸多研究庄学的学者中,以神秘主义界定庄子哲学的情况也不常见,而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比较少。其原因固然在于神秘主义本是一个西式的概念术语,一些学者本来就不喜或不倾向于用西式的概念硬加诸庄子,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学者们认为用神秘主义很难合理地把握庄子哲学思想的实质。陈绍燕是为数不多地较为关注并且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不过其看法的特点在于把庄子的神秘主义同其怀疑论、相对主义放到一起,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讨论。陈氏的核心观点是:庄子的怀疑论或相对主义不是根本的,其理论归宿在于神秘主义;怀疑论、相对主义仅仅是实现其神秘主义的工具或手段[10]。这有点类似于张岱年的看法:“庄子的认识论中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观点,但最终归宿是神秘主义、道是可知的,‘无思无虑始知道’(《知北游》),最高的境界是‘体道’,‘与天为一’。”[11]
与西方汉学界相比,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学者通常缺少对神秘主义的深入说明,而大致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他们多是比较随意地将庄子哲学归结为神秘主义,似乎神秘主义是一个自明的概念。比如,陈绍燕在其《神秘主义是庄子认识论的归宿》一文中,甚至没有对什么是神秘主义作出任何界定和说明,就直接把庄子思想定性为神秘主义。其次,对于神秘主义理论自身是否也有内部的某些差异,可以细分为哪些具体的类型,以及庄子哲学应该更明确地归属于哪种类型的神秘主义等问题,相对而言都缺少深入的分析说明。
不同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西方汉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比国内要高,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相对而言也比较多。其次,西方汉学家对神秘主义的内涵通常都有比较明确的认知和自觉的思考,多数学者能对这一概念作出比较清晰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庄子哲学的神秘主义性质问题。再者,西方学者往往不仅强调庄子哲学的神秘主义性质,而且对神秘主义有非常细致的梳理和分类,对庄子哲学属于何种类型的神秘主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这为我们深入理解庄子哲学的理论特质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前提。
西方汉学家普遍将庄子哲学界定为神秘主义,由此我们看到,作为西方学者的汉学家固有的知识观念对于他们理解《庄子》文本所起的潜在作用。这里,“神秘主义”构成了他们理解的基础和框架,成为其尝试着把握《庄子》的工具。通过将《庄子》界定为神秘主义文本,他们获得了一种对于《庄子》的相对熟悉感。不过,这一点恰恰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西方汉学家只是借助于道家或庄子在阐述自己的神秘主义思想,而这种神秘主义与道家或庄子本身是无关的[12]。本文认为,西方汉学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将庄子哲学看成具有神秘主义性质,还是有一定的理据和价值的。以神秘主义界定庄子哲学,其意义不仅仅是给庄子加上了一顶“神秘主义”的帽子,这种界定揭示出中西思想和文化中面对着一些类似的问题存在着共同的经验或理解,只不过基于不同的文化取向,中外学者对这些问题持有不甚相同的答案。从另一角度说,西方汉学家在考察中国思想中的神秘主义时,指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神秘主义,这既丰富了神秘主义的传统,又丰富了整个人类共同的经验,从而成为我们作为人类应对相关问题的共同思想资源,这无疑有助于展现出庄子哲学之世界性或普世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