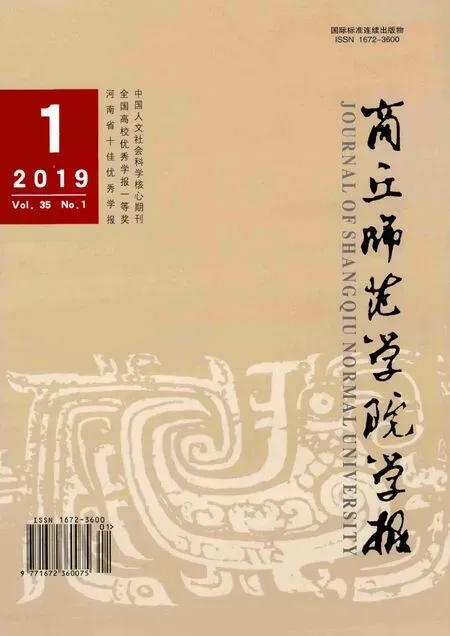从“平等”到“一体”
——论庄子的天下观
王 威 威
(华北电力大学 国学研究中心,北京 102206)
“天下”是中国古代政治论说中的特有观念,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形成和演化进行了细致梳理。虽有分歧,但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天下”一般被看作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狭义的“天下”等同于中国或九州,广义的“天下”指九州加上四海,甚至可以扩展到天覆地载的所有区域,与此关联的是五服制度、朝贡制度以及华夷之辨。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天下观的理解则深受列文森的影响,他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天下”是一个价值体,而“国”则是一个权力体[1]84。张其贤在《“中国”与“天下”概念探源》中重申“天下”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列文森以“天下”为文化价值体系是源于对黄宗羲、顾炎武观点的误解[2]。赵汀阳则提出古代中国的“天下”兼有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心理意义上的“民心”和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一家的理想[3]27-28。史学界、哲学界甚至政治学界关于“天下”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历史中的“天下”和儒家思想中的“天下”,而事实上,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先秦思想中有着关于“天下”的丰富多样的看法,其中,道家的“天下观”独具个性,尤其值得重视。本文将以《庄子》内篇为研究对象,探讨庄子关于“天下”概念之义涵、“天下”的现实存在状态及本真情态的看法,并梳理出庄子关于如何“治天下”这一问题的回答。
一、“天下”之义涵
“天下”一语在《庄子》内篇中出现近三十次,具体所指有所不同。“天下”从字面意义看为“天之下”,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万物(包括人类)存在和生长的空间,与“天地之间”所指相同。由此意义又可引申指存在于天地之间的物(包括人类)之全体,如《应帝王》中有“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之说,“功盖天下”与“化贷万物”相对应,意为功德广被天下,化育施及万物,“天下”与“万物”均为明王化育之功德所施及的最广泛的对象,所指相同。“天下”可指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万物之全体,甚至可包括天地本身。《齐物论》中有“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的说法,庄子在消解了“天下”之内的秋毫、太山的大小之别和殇子、彭祖的寿夭之别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可见“天地”与“万物”均可包含于“天下”之内。而“天地”与“万物”又构成了庄子思想中与“道”相对的“物”的世界。《大宗师》中讲:“藏小大有宜,犹有所循。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循,是恒物之大情也。”无论是小物还是大物,藏于何处都有所依循,而不藏则无所循。“藏天下于天下”指天下所包含的“物”均以自身的面貌存在和变化,而毫无隐藏和抗拒,这是“物”之实情。《逍遥游》中有“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同时又讲到“孰肯以物为事”,“天下”与“物”所指相同。以“天下”为一地理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之共性。虽然其所指区域的大小有所区别,而以“天下”为天地万物之全体应是庄子天下观的特别之处。
庄子对“天下”意义的这一理解承自老子。《老子》第一章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五十二章讲:“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通过相互对照可知,“天地”“万物”“天下”实际所指相同,均为“道”所生成的天地万物之全体,是无形无名之“道”所生的有形有名之“物”。而且,庄子也继承了“道”为天地万物之来源,即“天下”之来源的观点。《大宗师》中讲道: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这一段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来源,是无为无形的真实存在,不能通过人的感官来认识,这些观点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但庄子强调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与老子认为道“先天地生”有所不同。“道”“自本自根”,而天地万物的存在和变化则以“道”为根据,《大宗师》中就提出“道”是“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
此外,“天下”在《庄子》中亦指一政治共同体。“治天下”在内篇中出现4次,“为天下”出现1次,“天下治”出现2次。在《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中,尧讲道:“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回答:“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这个尧想要让给许由的“天下”,作为“治”之对象的“天下”,许由认为于自己无所用的“天下”,就是一个拥有治理者、拥有居住于其权力所覆盖地域中的民众的政治共同体,这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天下”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之意义。《逍遥游》中还讲道:“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天下”与“海内”相对而言,可见此“天下”指“四海之内”。这一对“天下”的理解应是庄子对战国中期天下观的接受。渡边信一郎就提出:“战国中期至于汉初,天下乃是‘四海之内’方三千里的领域,是由九州所构成的天子的统治领域。”[4]48
值得注意的是,《逍遥游》中讲:“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齐物论》中也讲道:“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在庄子的思想中,与“天下”“海内”相对的“四海之外”是“神人”“至人”的遨游之所。《逍遥游》中有“以游无穷”,“游乎尘垢之外”,《应帝王》中也有“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体尽无穷,而游无朕”。“无穷”“尘垢之外”“六极之外”“无何有之乡”“圹埌之野”“淡漠”“不测”“无有”“无朕”所指均为无形、无限的“道境”。《大宗师》中许由先言道:“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后又讲:“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所指正是“道”,此段文字明确了“所游”为“道境”。如此看来,“四海之外”就是无形、无限的“道境”,“四海之内”则是“物”的世界。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共同体之“天下”可以囊括“物”的世界,与作为天地万物之全体的“天下”所指实际并无不同,只是在讨论政治问题的语境之内所发生的意义转化,或者说是“天地万物之全体”在政治视域中的体现,作为“治”之对象的“天下”实际即是“天地万物之全体”。可见,庄子虽然对当时的天下观念有所吸收,但他对“天下”的理解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
二、“天下”之本真情态
“天下”是生于“道”、以“道”为依据的天地万物之全体,这是庄子之“天下”的首要意义。那么,“天下”又是以怎样的状态存在的呢?首先,这是一个万物各具个性、千差万别的“天下”。《齐物论》开篇子綦向子游解释何为“地籁”时讲道: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陵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讠高者、叱者、吸者、叫者、讠豪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大地呼气而生风,风吹孔窍,万窍怒吼。孔窍之形态千奇百怪,发出的声音也是各不相同。此段以极其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出孔窍及声音的千变万化,实际所指为天下万物的差异性。万物各不相同,却都是自己如此。道虽生万物,但并不做万物的主宰。《齐物论》在解释何谓“天籁”时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吹万不同”即风吹万窍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这段文字强调“使其自己”“咸其自取”,认为不同的声音是自己产生、自己停止的,实际是要表达“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自己如此”的观点。“自己”“自取”是“自然”的不同表达方式。“怒者其谁邪”则以反问的语气否定了“怒者”的存在。也就是说,庄子认为各不相同的事物之存在及各自之变化皆是自己如此,并不存在一个万物之外的鼓动者来主使这一切。
人作为万物之中具有认识能力的特殊存在,会将他人、他物作为认识的对象,对其进行是非判断,这就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认为之所以对事物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是因为每个认识主体都有“成心”。《齐物论》讲: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无论是聪明之人还是愚笨之人,作为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了“成心”。每个人均以“成心”为师,执一己之偏,也就有了是非判断的存在。与“地籁”和“天籁”相区别的“人籁”即指各种是非争论。“人籁”为比竹之音,比竹本空洞无心,没有任何感情,因为演奏者心中有喜怒哀乐,所以比竹之音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感情。在庄子看来,物本无是非,就似比竹本是空虚,没有情感;人从“成心”出发、从“我”的立场出发对事物进行是非的判断,就似演奏者利用比竹奏出不同的乐声,表达不同的感情。每个人的“成心”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对相同的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是非判断,并都肯定自己而否定他人,于是引起无穷的争论,此即“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人们对相同事物所作出的是非判断不同,确定谁是谁非的标准至关重要。《齐物论》借啮缺和王倪的对话探讨了这一问题: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庄子否定存在适用于所有物的共同标准,就是说,我们无法以一个确定的标准来判定每个事物的“是”和“非”,那么,就没有一个标准的“是”和“非”来衡量不同的认识主体对事物不同的是非判断的真伪、正误,如此,“知”与“不知”也就不能确定。人与各种动物分属于不同的类别,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因而对处、味、色的喜好和选择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并不能够确定谁的喜好和选择是正确的。庄子通过“正处”“正味”“正色”无法确定来论证“判断哪种是非为真的标准并不存在”这一观点。
《齐物论》中又讲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然”指事实的存在状态,“可”是价值判断。“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这是说一切事物都有着各自的存在状态,一切事物都有它应该被认可之处。如陈鼓应所讲:“‘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即是肯定各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及其独特的价值。”[5]也就是说,各个事物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完全否定,这是对万物平等的承认。因此,我们应该抛弃由“成心”出发而形成的对人、事、物的各种是非判断,而将万物千差万别的本来状态呈现出来,这就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庄子的论说并没有停留在否定“是非”、承认差别这一层次。他认为,天下万物各具特性,彼此有分,却又相互依赖。《齐物论》中讲“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万物有“彼”和“我”(“此”“是”)的分别和对待,正是在“彼”和“我”的分别和对待中确认了自身的存在。但是,“彼”与“我”(“此”“是”)的分别并不具有确定性。《齐物论》讲: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
在物的世界中,事物之间都互为“彼”“此”。从自己的角度看,自己是“此”,他物为“彼”。若以他物为“此”,则他物以外的他者也是“彼”。而且,事物本身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随起就随灭,随灭就随起,事物的任何性质和存在状态都是暂时的、相对的。也可以说,事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没有确定性,因此,认识到万物的差别和个性并非最高的认识,也就是说并非对“天下”本真情态的最终把握。
庄子在《齐物论》中将人的认识分为不同的层次: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最高层次的认识是对“未始有物”的“道”的体认;其次是认识到有物存在,但是物与物之间没有分界;再次是认识到物与物之间的分界,但并未对物进行是非判断;及至对物有了是非判断,道就已经亏损了。世俗之人执着于对万物的是非判断和是非之争,就处于“是非之彰,道之所以亏”这一层次。前文所讲到的不对万物进行是非判断,使万物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出来,就处于“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这一层次。这一层次虽非最高,但是仍属于“道”未亏损的情况。从“道”的视角来看,多样的事物都来源于“未始有物”的“道”,他们之间的分别和隔阂可以被打破,可以相互会通而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这一层次。这是对物世界的最高认识。庄子提出:“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细小的草茎和高大的木柱,丑癞的女人和美丽的西施,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事物,都可以由“道”而会通为“一”。庄子经常在描述万物之千差万别之后又将其千差万别归而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
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
万物有“成”有“毁”,有“大”有“小”,有“寿”有“夭”,这是从万物差别的角度去看,而如果从万物的共同之处来看,万物可以融为“一体”。
《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生动形象,为我们所熟知,其中的深意却也不易领会: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非常真实快乐的样子,并不知道自己是庄周。当他醒来之时,知道自己是庄周而不是蝴蝶。在庄子思想中,“梦”与“觉”可以分别代表“真”与“伪”。人们都认为梦中为虚妄,觉时为真实,而庄子却认为当人有了大觉悟,才会发现我们以为的清醒和真实是虚假的。庄子在清醒之后,认为自己和蝴蝶一定是有分界的,这并非真实,而他在梦中所感受到的,自己变成了蝴蝶,才是世界的真实。他所要表达的正是自己与蝴蝶可以转化、会通的思想,就是他所说的“物化”。从根本上来看,我与蝴蝶本无分别,我与天地万物均是“一体”的。
至此可见,“天下”包含了有分别、有个性、自然而成的“物”,万物各不相同却均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而没有是非贵贱之别,可以说,“天下”所含之万物是平等的。万物之间相互依赖,“彼”和“此”并无截然确定的分界,万物均处于流转变化之中,而从道的立场来看,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可以被打通,“天下”于是成为没有分别的整体。
三、“治天下”与“天下治”
庄子在《逍遥游》中讲“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虽然天下之人都急于求得天下大治,但体道之神人并不把治理天下当回事。该篇又讲:“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神人所留下的尘垢和糟粕,就能铸就儒家所推崇的圣王尧和舜,但神人并不在意治理天下之事。《应帝王》中的“无名人”回应“天根”如何“为天下”之问:“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庄子并不关心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但他也同“无名人”一样不得不回答这一问题,他的回答集中于《应帝王》篇的几个寓言之中。在这几个寓言中,庄子分别对德治、法治、智治等治理天下的方式进行了批判。虽然各个寓言所针对的对象不同,论述的重点有所差异,但其中也有着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
首先,最理想的君主不应以“治天下”为重心,“天下”只是“外”,专注于“治天下”犹如“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以达到“天下治”。“天下”虽大,也只是有限的“物”而已,而这几段文字中所出现的“六极之外”“无何有之乡”“圹埌之野”“淡漠之境”“无穷”“无朕”“不测”“无有”都是指无形、无限的“道境”。在庄子看来,理想的君主只需修养心灵以达到体道的境界,就可达致“天下治”。
其次,庄子认为,理想的君主修养心灵以达到体道的境界,并不需要他去治理天下,天下自然就会变好,这是对百姓自治能力的充分认可。在老子思想中,君主需要通过“无为”来约束自己权力的使用以保证百姓的自然发展,但并非毫无作为。《老子》第六十四章讲“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君主对万物和百姓的自然发展发挥了辅助作用。而庄子认为,百姓就像“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完全具有自我保存和发展的能力,并不需要被君主治理。
最后,庄子反对君主以“仁”“法”“智”等手段来治理天下,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君主使用权力的具体方式不同,但有虞氏的“藏仁以要人”,日中始传授给肩吾的“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本质上都是将自己的专断意志强加于百姓,都是对百姓自然发展的干涉。他所赞赏的是泰氏的“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无名人所讲的“顺物自然而无容私”,这是不以自己的意志、私见强加于百姓的表现。
庄子对各种治理方式的激烈批判和对君主使用权力的正当性的消解,使一些学者提出庄子有“无君论”的立场。如崔大华提出庄子社会批判的理论立场可分为无君论、无为论、反朴论,并讲道:“庄子的无君论,作为一种思想,尚是缺乏理论形态的、比较朦胧的阶段;而作为一种情感,则是非常鲜明强烈的。”[6] 233-237“无君论”应是一种主张君主存在本身就不具有正当性的理论。实际上,庄子对有为之君的批判并不能得出他主张“无君”的结论,而且在以上所论内容中,庄子仍然为我们塑造出了泰氏、明王等理想君主的形象,并非认为任何类型的君主的存在都只有负面价值,都没有正当性。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庄子讨论如何治理天下这一问题时,讲到“顺物自然”,“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这也说明作为治理对象的“天下”不仅包含民众,而且包含了“物”之全体,而“天下治”的理想状态则是物之“自然”“自喜”。在认识活动中,庄子要求人们放弃“成心”而使万物之本真情态得以呈现;在治理活动中,庄子要求君主放弃权力的使用而使万物以自然的状态存在和发展。
此外,庄子思想中“天下”与“国”的关系尤其特别。“国”只出现于庄子所设置的寓言场景之内,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如鲁国、晋国、卫国等。《德充符》篇一寓言中的孔子讲道“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亦是对各个诸侯国构成“天下”这一现实的反映。但庄子却并未探讨过如何治国的问题,在其对“治天下”问题的讨论中,也并未有“国”的出现,似乎庄子思想中理想之“天下”并没有“国”的存在,或者说,“天下”之中的“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已经消除,这正可对应作为天地万物之全体的“天下”之中“物”与“物”之间界限的消除。
四、结论
“天下”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万物(包括人类)存在和生长的空间,又可指存在于天地之间的物(包括人类)之全体,甚至可包括天地本身。无形之“道”所产生的“物”之全体(即天地万物)是庄子之“天下”的首要意义。“天下”包含了有分别、有个性、自然而成的万物,万物各不相同却没有是非贵贱之别。万物之间相互依赖,且处于不断的流转变化之中,彼此的界限并不确定,而从道的立场来看,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可以被打通,“天下”于是成为无分别的整体。“天下”在《庄子》中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作为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天下”与作为天地万物之全体的“天下”所指实际并无不同,只是在讨论政治问题的语境之内所发生的意义转化,作为“治”之对象的“天下”实际即是“天地万物之全体”,“天下”之内并无“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存在。庄子对“德”“法”“智”等治理天下的方式进行批评,认为“天下”并不需要治理,君主应该实行真正的无为之治,任由万物自然地存在和发展,即可实现“天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