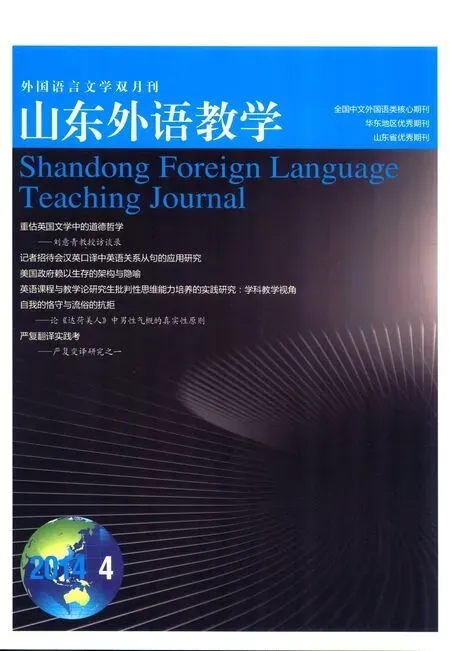自我的恪守与流俗的抗拒
——论《达荷美人》中男性气概的真实性原则
隋红升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自我的恪守与流俗的抗拒
——论《达荷美人》中男性气概的真实性原则
隋红升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在分析当代著名非裔美国作家弗兰克·耶比代表作《达荷美人》中纳瑟努这一男性人物形象时,我们发现,该作所书写的男性气概模式打破了西方文化和社会在男性气概认知、建构与实践方面重刚轻柔、重外在轻内在、重流俗轻自我、重王道轻人道等二元等级秩序,体现了相当的人性高度和人道主义精神。而纳瑟努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在认知、建构与实践男性气概过程中秉承了一种“真实性”原则,坚持了对自我与良知的恪守与对性别流俗观念的抗拒。结合莱昂内尔·特里林和查理斯·泰勒等学者的“真实性”理论,本文将对该作书写的这种男性气概的思想内涵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进行深入分析。
弗兰克·耶比,《达荷美人》,男性气概,真实性
1.0 引言
弗兰克·耶比(Frank Yerby,1916-1991)是当代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平生创作了33部小说,大多数作品都是畅销之作。其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其中三部小说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截至到2011年,其小说在全球的销售量突破六千万册,是拥有读者最多的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然而,与他在广大读者中的接受现状不相称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美国文学评论界一直倍受冷遇。其原因大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他很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白人,这让很多学者深为不满;二是其创作被定性为大众畅销书,被认为缺乏文学价值;三是其创作缺乏对种族话题以及黑人解放运动的关注。对于耶比在学界所受的冷遇,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为之鸣不平。达尔文·T·特纳(DarwinT.Turner)就曾明言“一个在20年内创作出20本书并且大多数都是畅销之作的小说家是值得我们略微关注一下的”。(Turner,1968:570)特纳认为,作为一个传奇小说家,耶比的创作成就可以与大仲马、斯科特和库伯等作家比肩。在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时代,特纳的呼吁当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然而,随着当代非裔美国文学创作政治正确性的淡化及其创作主题与叙事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再加上文化批评的兴起,耶比小说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开始得到重视。从20世纪末到现在,在多部重要的非裔美国文学综合性研究文献①中,耶比及其小说创作都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葛温德林·摩根(Gwendolyn Morgan)回应了20年前特纳的呼吁,认为美国评论界应当“放弃偏见,真诚地对他的大量作品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转引自Pratt,1999:505)
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耶比小说在破除南方白人贵族神话方面所做的文化贡献及其小说所蕴含的被评论界所忽略的种族话题。特纳认为耶比在其反浪漫(anti-romantic)故事中无情地暴露了美国白人神话,揭发了南方贵族并不光彩的过去及其充满罪恶与血腥的发家史,抨击了他们所缔造的种种神话的虚伪,而且他认定对美国神话的“讨伐最终将被看作是耶比对美国文化的主要贡献”。(Turner,1968:572)吉恩·加瑞特(Gene Jarrett)则通过对耶比的成名作《哈罗大宅的福克斯一家》(The Foxes of Harrow,1946)的分析,探讨了耶比小说中倍受忽略的种族话题,认为在该作“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手法塑造了斯蒂芬·福克斯(Stephen Fox)这一人物形象,表达了种族和解的可能性,而这也是二战以来非裔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Jarrett,2006:63)就研究的文本来看,学界关注最多的是耶比的成名作《哈罗大宅的福克斯一家》,而被评论界公认为耶比最佳作品的《达荷美人》(The Danomean,1971)以及贯穿其始终的男性气概话题却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通过对主人公纳瑟努(Nyasanu)这一男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发现,《达荷美人》在男性气概书写方面体现出一种独特视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模式。首先,在男性气概的认知方面,该作所书写的这种男性气概模式不再片面地把勇武、强硬和理性等因素看作是其决定性的判定尺度,而是为其注入了慈善、仁爱与感性等因素,从而使男性气概的内涵有了更多的人性色彩。其次,在男性气概的建构与实践方面,这种男性气概模式与战争和杀戮保持了一定的批判距离,体现出对生命的珍视与热爱,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精神。最后,纳瑟努之所以能够实践这种富有人性高度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男性气概模式,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了一种“真实性”(authenticity)原则。对此,我们将援用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和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学者的“真实性”理论对主人公男性气概实践的行为逻辑进行深入分析。
2.0 主人公男性气概体系中的人性高度
虽然我们很难给男性气概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就传统男性气概的话语体系来看,勇敢、强硬、坚韧、进攻性和毅力等特性一直都是传统男性气概的基调和性别规范。哈维·C·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把男性气概看作是一种德性(virtue),而这种德性的基石则是“勇敢或绅士风范”(courage or gentlemanliness)。(Mansfield,2006:xii)根据曼斯菲尔德的考察,“在希腊文中,男性气概(andreia)一词同样被希腊人用来指勇敢(courage),一种控制恐惧(fear)的德性”。(同上:18)然而遗憾的是,传统男性气概话语体系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在强调勇敢、强硬、坚韧、进攻性和毅力等特性的同时,否定了男性个体的情感需求与表达,贬斥了个体的同情之心与悲悯之心,把这些看作是女性气质的性别规范,从而具有非人性的特点。
可以看出,在《达荷美人》所再现的19世纪非洲部族社会性别文化价值观念中,勇敢与坚强同样是评判一个男性是否具有男性气概的决定性标准,也是主人公纳瑟努男性气概的主基调。在他的人格体系中,勇敢、刚毅、果断是他一贯的精神品质,从来没有含糊过。他在接受割礼以及在一次敌强我弱战役中单骑救主的勇敢表现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这些“刚性因素”之外,纳瑟努的男性气概体系中还有慈柔的一面,感性的一面,富有同情心和悲悯情怀,体现出的是一种刚柔相济的男性气概模式。
一方面,他珍视情感,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他而言,友情与亲情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一点从他对好友卡杜努(Kpadunu)和父亲的真挚情感中就可看出:“他无法想象没有卡杜努或父亲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地方将会是废墟和荒原,空无,贫瘠,匮乏,没有智慧,没有援助,没有慰藉,也没有欢乐。”(Yerby,1971:213)②
另一方面,他外刚内柔,富有同情之心和悲悯情怀。在纳瑟努的父亲眼中,儿子是“一只年轻的雄狮,但同时有着一颗比少女还温柔的心”。(P172)在与麦克西人(Maxi)的一次遭遇战之后,看到士兵们为了向国王邀功迫不及待地把射杀的敌人头颅割下时,他禁不住呕吐了起来。他这种仁慈的表现也引起了同伴陶格拜迪(Taugbadji)的注意,后者对他的评价也说明了其男性气概柔性的一面:“你永远不是做一名战士的料,纳瑟努。你的心像女人一样仁慈,我的兄弟!”(P166)对此,他毫不避讳地说:“我与其说自己是个男人,倒不如说自己更像个女人。”(P167)。在大多数男性极力与女性气质划清界线、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男性形象之时,纳瑟努却反其道而行之,毫不在乎地称自己更像女人,坦率地承认自己身上具有女性气质,非常耐人寻味。
3.0 主人公男性气概体系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男权文化话语体系中,战争往往是男人的领地,也是考验、证明和实践男性气概的重要形式与场所。很多时候,战场上的英雄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男子汉,他们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也几乎是男性气概的代名词,有人认为“男性气概在战争、尤其在危难之时对国家的保卫过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展现”。(Mansfield,2006:75)这种观点从古希腊时期就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战场是展示男性气概或勇气的最佳场所”。(转引自Mansfield,2006: 75)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有人甚至担心长久和平的生活会让男性变得“女性化和柔弱无力”,而“只有不断经受战争的洗礼,那种开疆拓土式的男性气概才能得到恢复”。(Kimmel,2006:76)不能否认,在国家和民族遭受侵犯之际,无论军人还是平民百姓都需要一种挺身而出、视死捍卫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精神和气概。然而,简单地把战争、暴力甚至杀戮作为建构和证明男性气概的手段则是荒谬之极,有很大的误导性、潜在的破坏性和反人道性。
起初,与《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1895)中的主人公亨利·弗莱明(Henry Fleming)一样,在传统男性气概话语体系所炮制的战争神话的蛊惑下,纳瑟努对战争抱有一定的憧憬和幻想。战争神话所鼓吹的勇气、荣耀等字眼对他还存在一定的诱惑力,让他希望成为受人敬仰的战争英雄。因此,当新婚不久的他被国王召集过去参加一次战争时,他摩拳擦掌,雀跃不已。他一直都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梦想着“有朝一日,他,纳瑟努,男人中的男人,胸前挂满了由他宰杀的敌人的牙齿所做成的项链,大步走向前去,把亲手割下的头颅奉献给国王”。(P135)看得出,此时他对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对象、战争的后果等问题丝毫没有考虑,头脑中只有对战争的幻觉。这种幻觉也是长期以来人们一贯把战争与男性气概联系在一起的后果。难能可贵的是,纳瑟努很快摆脱了对战争的痴迷,不再受战争神话所蛊惑,而是听从了自我与良知的召唤,对战争的血腥、残暴和非人道等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挚友卡杜努起到了相当的引导和启蒙作用。在对麦克西部落的战争尚未开始之际,卡杜努就似乎有意给纳瑟努的战争热情泼冷水:
唉,我的兄弟,我真不想做嗜杀成性的野蛮族群中的一份子,可我们这些达贝利的子民们偏偏属于这样的一个族群。很难想象地球上有哪个地方人与人之间不再以一个原本就子虚乌有的神的名义或者其他的随便什么原因而互相残杀。在那些地方国王们能用仁爱治国,而不是动辄就出兵攻打自己的同胞,眼看着他们被饿死或砍死。(P139)
显然,卡杜努对战争的本质看得比纳瑟努透彻得多。在他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来自一种尚未泯灭的人性,来自对生命的珍视与尊重。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批判了战争神话和英雄主义所掩盖的对生命的漠视和残忍。在他看来,在战场上大开杀戒、以杀人为荣的男人不但算不得英雄好汉,甚至连野兽都不如,这一点从他对纳瑟努说的一番话中就可看出:
我要让我们成为男人,纳瑟努!你也许会说,哈!你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哪些被捆绑的、嘴巴被塞住的囚徒们被屠杀,因为男人们本性如此,他们就是要这么做!这就是你要说的,对吗?我在问你,我的兄弟,这就是你心里所想的,对吗?但我要说,森林中没有哪个野兽——即使最凶猛的豹子也不会——以杀戮为乐!(P140)
可见,在卡杜努眼中,暴力不应该成为男人的本性,杀戮行为更无多少英雄气概可言,也不值得称道,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罪恶。他的这番话使纳瑟努幡然醒悟,意识到这种对生命任意宰杀和屠戮的非人道性,是天理难容的。因此,在与麦克西人之间的一次遭遇战中,当纳瑟努为了救孤军奋战的同伴陶格拜迪不得不开枪打死了一个麦克西人时,他不但没有一般战士射杀敌人后的喜悦与成就感,反而觉得自己犯了罪:“看到朋友身处险境时所感受到疯狂与杀性消退后,他感觉糟透了,他杀了一个人,他谋杀了一个手里拿着锄头的农民,而且是从20码的地方用火枪射杀的。”(P166)当纳瑟努看到他的妹妹阿罗巴(Alogba)——也是国王御用女兵的一员——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战俘并从中获得一种变态的快感时,他怒不可遏,冒着被国王重罚的危险,上前制止并痛打了她。在他眼中,任何对生命的践踏与侮辱都是不可容忍的。在此,纳瑟努的男性气概体系中除了悲悯、仁慈与同情等柔性因素外,更多了一份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惜,这也让他的男性气概体系增添了一种宝贵的伦理维度和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
4.0 主人公男性气概实践背后的“真实性”原则
纳瑟努之所以能够使其男性气概富有人性高度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因为他在认知、建构与实践其男性气概过程中坚持了一种真实性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内在自我的忠实与对流俗抗拒,这种真实性原则构成了其男性气概实践背后的行为逻辑。
根据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真实性理论,真实性原则其实就是“对本真性的恪守和对社会习俗、甚至那些很有可能被我们当成道德之律条的不断抵抗”。(Taylor,1991:66)用伯纳德·W·贝尔(Bernard W.Bell)的话说,“真实”是指“对限定性物质条件的超越和克服以及对社会和道德约束的僭越和违抗”。(Bell,2004:42)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而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在很多时候,男性个体在建构与实践其男性气概时,他往往很难诉诸于内心真实的自我,而是被一种随波逐流的人格所左右。正如特里林所说的那样,这种随波逐流的人“时刻关注着他的同伴或文化机构所发出的信号,甚至到了根本没有自我的地步,成了一个复制品和冒牌货”。(Trilling,1972:66)也就是说,大多数男性在建构和实践自己男性气概过程中没有忠实于自我与内在主体判断,而是过多地在乎他者的眼光,对陈规陋俗缺乏抗拒的勇气。
我们发现,纳瑟努这一人物形象没有盲目遵从主流性别文化对男性气概的种种片面、单一和狭隘的规约和界定,而是根据自我、良知与真情实感来认知、建构与实践自己的男性气概,体现的是一种真实性原则。这一点从他对妻子唐百薇(Dangbevi)的告白中就可看出:
不要把我当成了动物或者一个被色欲支配的奴隶,那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是男人,唐百薇。你可能还不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男人也是有灵魂的生命体,不知道他的生命充满了怎样的梦想、激情、温柔、才智、痛苦以及少有的欢乐!你不知道一束月光就会让他心神荡漾,一首乐曲就会让他忘记一切……。(P243)
这段告白也是对“真实的”男性气概内涵的经典诠释。从这段告白中我们可以看出,纳瑟努在男性气概的认知方面没有遵从性别文化长久以来为男性气概打造的种种刻板印象,没有把“具有侵略性”(aggressive)、“强硬”(hard)、“专断”(assertive)、置身事外(aloof)、“冷酷”(cold)、“寡言”(laconic)和坚韧克己(stoic)等流俗观念 (Mansfield,2006:23)作为男性气概的性别规范,而是充分肯定了被流俗贬斥为女性特质的种种情感与精神要素的人性价值,把男性看作是着梦想与激情、温柔与才智、痛苦与欢乐、感性与灵性的生命体。
然而,从男权文化赋予男性气概的种种性别规范来看,纳瑟努对男性气概的诠释显然非常“性别不正确”。但有趣的是,对流俗的性别规范毫不在意的他,却凭着他内在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力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正如他的妻子对他所评价的那样:
你一点也不残忍。就算你想使自己变得残忍,你也无法做到。而恰恰是你的温柔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勇敢而且强壮,那些大型野兽也都个个勇敢强壮。但你除了勇敢强壮外,还富有智慧,能够时刻保持清醒,而且你还能做到安静持重。(P406)
这显然是关于真正男性气概内涵的又一段经典表述。尤其这段话出自一位女性之口,更是发人深省。这段话从女性的角度响应和肯定了纳瑟努所认知、建构与实践的男性气概的人性高度与人道主义精神,与前者构成了一种两性间的“召唤与回应”(call and response)式对话关系,昭示了这种男性气概模式在促进两性和谐方面的重要意义。
这也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男性气概真谛的反思。按照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对男性气概的种种流俗规范,纳瑟努似乎不具备男性气概。然而,他对诸多传统性别规范的抗拒与对自我真情实感与良知的恪守反而让他拥有了真正的男性气概。与他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卓越勇气相比,这种对他者眼光与传统流俗公然蔑视的勇气更是难能可贵。相比之下,那些对陈规陋俗和僵化的性别规范不敢质疑与抗拒、过度在意他者眼光、缺乏自我与主体判断的男性是无法真正拥有男性气概的。他们所拥有的男性气概与其说是一种勇气,倒不如说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被人耻笑的恐惧。
5.0 结语
通过以上几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小说《达荷美人》的主人公纳瑟努践行的这种男性气概模式打破了西方文化和社会在男性气概认知、建构与实践方面重刚轻柔、重外在轻内在、重流俗轻自我、重王道轻人道等二元等级秩序,体现出相当的人性高度和人道主义精神。纳瑟努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在认知、建构与实践其男性气概过程中秉承了一种“真实性”原则,坚持了对自我、良知与真情实感的恪守与对性别流俗观念的抗拒。可以说,该作书写的这种男性气概体现了一种由外到内的转向,无论对当今人类男性气概的认知与建构,还是对当今学界的男性气概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于当今人类男性气概的认知与建构而言,这种转向提醒人们要更多地关注男性气概的内在人格与精神品质,关注人性的多元诉求,使男性气概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性别规范和流俗的遵守与服从上。显然,这种转向为危机重重的当代男性气概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其走出困境提供了有益启示。对于当今学界男性气概研究而言,这种转向提示我们不能过多地局限于R·W·康奈尔等男性气概学者强调的的权力关系研究范式,而要同时关注男性气概研究的伦理维度,本文所援用的“真实性”理论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
注释:
①这些文献主要包括上个世纪末出版的《牛津非裔美国文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1997)、《当代非裔美国小说家》(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ists,1999)与本世纪新近出版的《非裔美国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2007)和《剑桥非裔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2011)等著作。
②下文引此书均为笔者翻译,只标注页码。
[1]Bell,B.B.The 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Its Folks Roots and Modern Literary Branches[M].Amherst and Boston: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4.
[2] Jarrett,G.A.“For Endless Generations”: Myth,Dynasty,and Frank Yerby's The Foxes of Harrow[J].TheSouthernLiteraryJournal,2006,39(1):54-70.
[3]Kimmel,M.S.Manhood in America:A Cultural Histor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Mansfield,H.C.Manliness[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5]Pratt,L.H.Frank Garvin Yerby[A].In E.S.Nelson(ed.).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Novelists[C].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1999.505-511.
[6]Taylor,C.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7]Trilling,L.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8]Turner.D.T.Frank Yerby as Debunker[J].The Massachusetts Review,1968,9(2):569-577.
[9]Yerby,F.The Dahomean[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Inc.,1971.
Commitment to Selfhood and Defiance Against Stereotypes: On the Authenticity Principle of Masculinity in The Dahomean
SUI Hong-s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While analyzing the male protagnist Nyasanu in Frank Yerby's masterpiece The Dahomean,we find that the model of masculinity written in this novel has broken such hierachical orders which prefer hardness to tenderness,external to internal,externality to internality,stereotypes to selfhood,and hegemony to humanity in we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and demonstrated considerable humanistic concern and humanism.One reason why Nyasanu could do this is that he practices an“authenticity”principle,committed to his selfhood and conscience and defying against the prevalent gender stereotypes.In light of Lionel Trilling and Charles Taylor's theory of authenticity,this paper undert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asculinity ideology in the novel and the behavioral logic behind it.
Frank Yerby;The Dahomean;masculinity;authenticity
I106
A
1002-2643(2014)04-0080-04
2013-11-1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非裔美国文学中的男性气概研究”(项目编号:12BWW05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从片面表征到多元建构——黑人男性小说家笔下的男性气概研究”(项目编号:10YJC752037)阶段性研究成果。
隋红升(1972-),男,汉族,山东诸城人,文学博士,副教授,博士导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和性别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