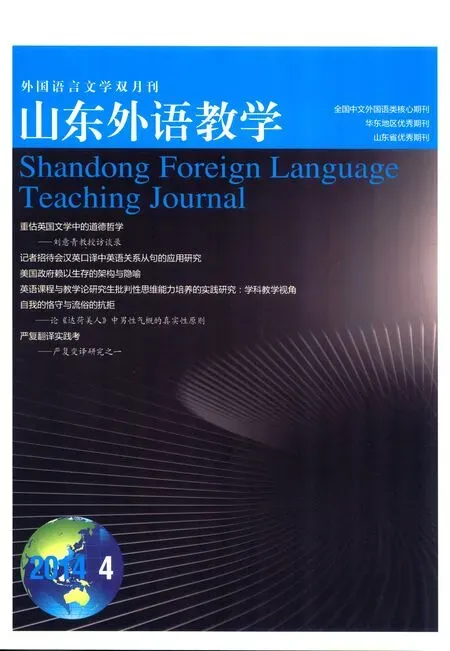重估英国文学中的道德哲学
——刘意青教授访谈录
邹赞,欧光安
(1新疆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2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 832003)
重估英国文学中的道德哲学
——刘意青教授访谈录
邹赞,欧光安
(1新疆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2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 832003)
本文是对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的访谈录。作为国内英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刘意青教授以英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为线索,聚焦于18世纪英国小说,深入探析了英国文学中的道德哲学。此外,刘教授结合文学批评实践,详细区分了道德哲学与道德说教,并对国内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以及多元文论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当下困境提供了独到见解。
道德哲学;道德说教;18世纪英国文学;多元文化主义
邹赞、欧光安(以下简称邹、欧):刘老师您好,感谢您再次接受我们的访谈,本次话题将围绕英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道德维度展开。您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令尊刘世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您对专业志趣的选择是否得益于您的家学渊源?
刘意青(以下简称刘):我之所以考上英语专业或者说后来从事英美文学的研究,还是有偶然性的。我中学6年学的都是俄语,高考时报的第一志愿也是俄语专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录取到了英语专业。既然被英语专业录取了,那时候又是国家分配工作,所以毕业之后就从事了英语文学教学与研究。当然家庭的影响还是有的,毕竟我父亲是英语教授,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回来,他在大学念的是欧洲中世纪语言文学,主要研究乔叟和Philology(语文学)。在我刚开始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指点了我,让我走文学路,一开始让我读大量的简易英文读物,培养语感,也由此对英语产生了兴趣。后来我父亲又到北大来做讲座,当时北大、北外云集了一批优秀的英语教授。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最终走上了英语文学的道路。
邹、欧:您常常自称属于“常识学派”(School of Common Sense),其实这并非一些人所误解的“自谦”,“常识学派”确确实实存在,是英国近代一脉重要的哲学思潮,以苏格兰哲学家T.里德和D.斯图尔特为代表。您的这种自我表述一方面是对英国“常识学派”的当下回应,另一方面可能更多地基于对多元文论话语游戏(能指狂欢)的一种批评,是这样的吗?
刘:我说自己属于“常识学派”,这是一个玩笑话(笑)。我也不是那么认真地称自己就是常识学派。为什么说是个玩笑话呢?这是指我当时的一种态度,就是反对在文学研究、哲学或理论上故弄玄虚。实际上苏格兰的常识学派,强调要通过某种明确的道理去认识事物,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理念。他们宣扬的是,人生来头脑里面已经具备了认识事物的简单道理的能力,人天生就有这种常识性的能力,因此和洛克的经验论是相对的。苏格兰常识学派可不是我戏称自己是常识派那么简单。我同意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很多事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道理来解决。而现在,各种后现代文论流于话语游戏,可谓繁复晦涩。又比如说语言学,明明原来就有现成的简单词汇,现在被换成了比较大的词汇,但说的是同样一个问题,最古老的东西其实都还在里头。虽然现代语言学有自己的许多理论,但的确存在用复杂新奇的词汇表达原来就有的一些语法和语言道理的现象。
邹、欧:洛克的经验论认为人一出生之后,其思维是一张白板,随着经验的积累,知识就产生了。我们感觉休谟是在霍布斯和洛克的基础上,更强调道德。休谟在其哲学著作中认为道德在知识的积累中至关重要。比如18世纪著名的小说家斯特恩,他对洛克的观念联想学说做了一种游戏性解读,很可能斯特恩受休谟的影响更大。
刘:是这样,不过洛克认为在认知论中有一个升华的阶段,他在《人类理解论》中的理论还是比较复杂的。他从各个方面探讨了人类从感觉如何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并且从方式和性质上做了很多区分,有趣的要数对“观念联想”的论述。洛克思想中最基本的层面,与17世纪的霍布斯的思想存在着显著差异。霍布斯认为,人生来就是恶的,邪恶已经在人的体内,所以必须用法律把它管起来。但是如果按照洛克的观点,人本来就是一张白板,人生来是可善可恶的。那么人实际上就是可塑的,因此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而霍布斯强调的是法制。两个人各有其理。对人而言,教育确实重要。而人又存在欲念,那么要是没有法制,也是不行的。所以说他们的观点具有互补性。
当然霍布斯和洛克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但他们基本上不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谈认识。所以说在认识中道德的理念被提出的时候,宗教中的善与恶等理念就已经介入了。这样一来,道德就不纯粹是认识论的问题了,它具备了一些超出简单认识论的更高层面的意义,或者说,它更复杂,它有习惯俗成、社会压力,还有宗教的影响,各种东西都加进来了。
邹、欧:文学自古以来就不是“真空式”存在,一定程度上始终承载着某种社会道德观念、伦理价值等意识形态符码。文学批评也是如此,社会历史批评、道德——伦理批评、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共同构筑起文学批评的立体构架。中国文学素来有“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西方诗学也绵延着对理性精神和道德传统的重视,但由于受到20世纪后现代文论的冲击,反权威、解构真理、挑战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狂躁热潮压抑了文学批评所承载的道德哲学,甚至将严肃的道德哲学与拙劣的道德说教混为一谈。这样一来,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谈论“真善美”就是在宣扬陈词滥调,探析文学中的道德主题就容易联想起元代四大南戏或者明代拟话本里酸腐露骨的道德说教。请您介绍一下道德哲学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区别。
刘:这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我想说的是,文学是承载道德的,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即便到后现代,人们常说文学中充斥了颓废、魔幻、荒诞、性自由,它里面还是有道德的因素,这是没法摆脱的。所以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开始,就重视文学的两个功能,一个是to instruct,即教育和教导,还有一个是to delight,就是使愉悦。文艺应当同时具备愉悦和教导两项功能,这种说法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推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to instruct和to delight的内容在变,它辐射的范围、含义和方式都在变。比如说,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末期,以但丁的《神曲》为例,它是怎样的to delight和to instruct。到了莎士比亚时代,这两项功能的内容就又很不一样了。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融汇了很多荒诞和搞笑的东西,那么它的愉悦和教导功能的表现方式也将大相径庭。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运作模式都不一样。到了后现代的图像时代,甚至吸血鬼也可以有to delight和to instruct的功能了,而回想17、18世纪甚至中世纪,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学的这两个功能永远都是存在的。人类之所以存在,就是它必须具备一些正直的理念,这些理念不管是用吸血鬼的形式还是用福尔摩斯的形式包装,最后还是“愉悦”和“教导”两种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作用,这是我的看法。
其次,说教和文学的教导是很不一样的。所谓的说教,就是当创作者把一个政治理念强加给文本使用的艺术手法特别拙劣的时候,作品的愉悦程度就大大下降,这时候的“教导”功能就变成说教了。说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使用简单化的政治手段干预艺术创作,比如白桦的小说《苦恋》。
倘若回顾英美文学的进程,道德说教也是存在的,例如18世纪英国作家理查逊强调年轻姑娘们一定要守身如玉,不要堕落,不要成为别人的情妇,不要当妓女,否则你就完蛋了。怎样才能达到艺术性和教育目标的结合,始终是考验作家的一块试金石。18世纪的英国,说教的问题干脆变为行为书,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社会比较无序,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人们开始疯狂追逐物质利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所有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都是道德家。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人的小说都没有简单地说教,而是热衷于出一种书叫conduct book(行为指南),教给雇主们怎么管教徒弟,姑娘们怎么给不同的人写信,姑娘们怎么选择婚嫁等。这些作家明确地把它从文学作品里分出来,变成一个通俗读本,就是指导读者的行为,这种情况就是完全的说教了。所以,在当时说教和教导也是有严格区分的。一般来说,会造成简单化的说教跟这个社会是不是民主,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或者中央政府和掌权的人是不是高压有关系,所以道德说教往往和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情形也和人们对理论的认识过于简单粗暴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过去简单地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从苏联那里照搬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僵硬教条。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人物必须归属黑白分明的不同阵营,不允许中间人物的出现,有缺点的、模棱两可的人物形象是要遭受严厉批判的,这种情形就是后来被西方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充斥着道德说教的作品往往只注重政治目的,全然不顾艺术性,结果恰恰适得其反,这种作品都是不能持久的。
邹、欧:一国文学的发展往往与当时社会的思潮紧密相关,例如文学作品中道德的表现就与当时流行的哲学、伦理、宗教等因素关联密切。更具体地说,作家的宗教身份会极大地影响其作品中道德主题的呈现,例如弥尔顿的清教主义身份,斯特恩的英国国教身份,这种身份与作品的对应在20世纪之前的英国文学中显而易见。而到了20世纪之后,这种宗教身份又与其它各种身份交织在一起,形成作品错综复杂的道德表现。您能从17、18世纪英国文学大致的发展方向谈谈文学作品中道德的表现吗?
刘:这个问题涉及作者宗教身份对于创作的影响,除了你们提到的斯特恩和弥尔顿,比较典型的还有斯威夫特,他本人是英国国教神职人员,曾在都伯林三一学院接受训练,原计划在伦敦呆下去,但安妮女王不喜欢他。斯威夫特是托立党人,但是当时的执政党由托立党换成了辉格党,所以没有人替他说话。最后他只好回到爱尔兰,但一直持笃定的国教观点,在这方面代表他观点的著作是《一只木桶的故事》。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个大的宗教寓言。小说从一个寓言开始,人物关系复杂,内容非常丰富。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一位老父亲临死之前把他的三个儿子叫到床边,给每个儿子留了一件外套,大儿子叫做Martin,二儿子叫做Peter,三儿子叫做Jack。从名字本身来看,Martin是一个比较高贵的名字,Jack常常是通俗和身份地位低的代称。老父亲告诉三个儿子要好好使用这三件外套,并保存好。等到父亲一死,大儿子马上就在他那件衣服的袖子上补上花边,缀上花,搞得十分华丽花哨;二儿子什么都没改,维持原样;小儿子嫌衣服长了,就把下面给剪了,然后又做了许多简化的修改。斯威夫特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代表三种宗教,大儿子象征天主教,因为他很繁杂,注重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小儿子代表清教,就是当时斯威夫特极其反对的 dissenters (持异见者)。很显然,这是斯威夫特在宣扬他的国教立场,他认为其他两个宗教都不行。笛福也是如此,他甚至写了一个行为准则书叫做《基督教的婚恋》,写三个姑娘,一个嫁给了天主教徒,一个嫁给了清教徒,一个嫁给了国教徒,嫁给清教徒的那位过得最好,婚姻最幸福,因为笛福是个清教徒,这当然是在宣扬创作者的宗教立场。相比而言,理查逊虽然是一个清教徒,但他并没有大肆鼓吹清教,原因在于他比笛福小很多,他出生在宗教论战和排挤持异见者之后的时代,所受的宗教排挤比较少。但是他推崇实用主义的清教观念,例如要勤恳,要用美德换取更多的好处等。而菲尔丁又不一样,他信仰国教而且是贵族出身,所以他的小说并没有宣扬实用主义,但他强调人要诚实、仗义,要有同情心,最痛恨搞阴谋诡计和两面派。弥尔顿是个特例。弥尔顿在写《失乐园》和《复乐园》的时候,清教革命已经失败,王朝已经复辟,但弥尔顿的内心尚未平静下来,于是在塑造撒旦造反的形象时,不自觉地羼入一种清教革命的勇气。这样的塑造事实上也是诗人的艺术需要,因为撒旦在从天堂堕落到地狱之前,代表着光明,是光彩照人的天使。撒旦不可能从天上一掉下来就变成了蛇,因为神性还在他身上。从诗歌本身的艺术创作规律来说,撒旦的性格也不可能造反后就立刻屈服,所以,诗歌有必要表现撒旦对上帝慷慨激昂的指责。这样一来,倘若有人认为弥尔顿是在赞扬撒旦,那就太简单化了。弥尔顿尝试书写一部人类的史诗,他在写作时已经跳出了简单的宗教派别和阶级立场。我们不能认为弥尔顿仅仅因为坚持清教立场,所以写了三部史诗,弥尔顿创作的是了不起的人类史诗,是一部关于上帝造人的宏大史诗,超越了我们人类世间的林林总总、琐琐碎碎的斗争。倘若真正将弥尔顿作品中所有的卷册都读下来,就会明白弥尔顿是怎样写撒旦慢慢堕落的,撒旦煽动这些人造反,跑到乐园里面去引诱夏娃和人类犯罪,以报复上帝。我想借这个机会说一下,不要误认为弥尔顿是在以清教主义的身份来写《失乐园》和《复乐园》。不管是清教、天主教,还是国教,其实都是基督教。弥尔顿在这个大的立场上对上帝的态度是不变的,并没有受到政治立场的干扰。当他写上帝造人这个伟大史诗的时候,他是崇敬上帝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样一部恢弘的史诗巨作中,弥尔顿的清教思想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它一方面不同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因为后者强调清教思想所宣扬的“要勤奋、要发家”等理念;另一方面,弥尔顿也和理查逊不同,理查逊的《帕美拉》自始至终都在宣扬一种待价而沽的实用清教主义。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判定某位作家的政治或宗教身份就一定会反映在他的作品里。这些跟这个作家写什么样的作品、当时的处境、要完成什么样的工程都是有关的。愉悦和教导这两大目标在文学中永远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方式、内容或者层次不同,不能简单化处理。至于作家的政治或宗教身份一定会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我认为这不是必然的。
邹、欧:对英国18世纪文学的研究在以前一度被忽略,自20世纪中期以后在国际学术界逐渐被重视。在我国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起步,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18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小说,其中表现出的道德维度都和宗教有关,比如斯特恩和理查逊小说中呈现出的不同道德主题,就可以追溯到英国国教和清教之间的斗争。此外,以洛克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以休谟和贝克莱为代表的道德哲学派别,他们的思想对当时的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您认为我们在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时还需要注意哪些因素?
刘:英国的18世纪实际上是一个一贯被我们忽略了的世纪,它夹在莎士比亚、弥尔顿几座高峰之后,后面是浪漫主义,再加上维多利亚小说,它处在夹缝中间,显得支离破碎。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世纪充分地研讨过,而且极大地忽视了这个世纪的重要性。
事实上,18世纪作为英国从商品经济即从资本主义初期到盛期的一个过程,思想、理论的生产与流通十分活跃,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经济和大都会涌现,农村人口大举迁入城市,小说和书市开始在都市出现,整个情况与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非常相似。可以说,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不仅对英国文化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同时对现阶段中国的社会情境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英国18世纪的几个主要思潮,包括洛克的理性主义,还有休谟、贝克莱的道德哲学,我在《英国18世纪文学史》(2006)那本书中,专设一章讨论苏格兰的道德哲学,比如几个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也包括刚才说的常识学派等等。18世纪是一个思想活跃、百花齐放的时代。如果要好好研究18世纪,首先就要弄清楚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和道德哲学,还需要弄清楚文学是怎么从新古典主义转到了现代小说等等,当然还涉及市场经济、书籍市场等很多方面的东西。
至于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应该注意哪些因素,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英国现代小说的兴起,这是18世纪的专利。我始终认为早期小说的兴起,小说家实际上都是实验派。实验派并非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独有现象,早期小说兴起的时候,理查逊实验用书信体小说写女性心理,菲尔丁写全景小说,展示主人公游遍了整个英国社会。菲尔丁的小说不是心理小说,突显动作维度,他们两人引领了后来英国和美国两大派别的作家。一般认为伊恩·瓦特的说法比较公允,他把理查逊定位成心理小说的始祖,其后就是亨利·詹姆斯、乔伊斯等人,而菲尔丁则引领了狄更斯,其后是写了《印度之行》的福斯特等,当然还有萨克雷。我还有一个看法,就是不要以为所有的后现代的东西都是新的,其实在18世纪的英国小说里都能找到后来几乎所有小说里的新的因素,只是这些因素变得更加强烈了,或者是采用了更多的手段和技巧,愈加显得复杂玄虚。但一些基本的因素在18世纪英国小说里都能找到原型,比如说理查逊书信体小说中的双轨叙述技巧,两个人互相写信,另外两个人也相对写信,彼此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却提供了四个不同的视角。后来这种写法就很时髦,比如布朗宁的代表作《指环与书》就是例证,一个谋杀案通过6个叙述人从不同的视角讲述,所以到最后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的东西,而不是以情节取胜了。这种叙事策略在后现代文学里比比皆是,莱辛的《金色笔记》就是从各个角度来写发生的事情。要是把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好了,也就为研究后面的文学奠定了基础。
因此,我觉得应该充分重视18世纪作为小说的源头,以及作为英国资产阶级理论和认识论源头的独特意义。洛克、伯克、休谟的思想,苏格兰的文艺复兴、启蒙意识形态等,都值得认真研究。
邹、欧:以马修·阿诺德、F.R.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批评注重突显道德哲学的意义,致力于重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秩序。尽管利维斯在批评实践中吸取了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但始终与新批评派保持明显的距离,自觉羼入并张扬文学文本的道德意涵,他在《伟大的传统》中设定的经典序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英国自由人文主义批评由于被扣上“保守主义文论”的帽子,其自身积极意义以及对于当下文化情境的参照意义常常被忽视,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刘:阿诺德和利维斯都属于西方人文传统系列中的精英。阿诺德为了国家和社会安定,主张吸收传统人文经典里的精华部分,主要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化的道德约束。我们有必要将利维斯和新批评作明确的界限区分,新批评有一阵特别强调技巧,反对把历史背景和作家立场裹进来,有点排斥社会和历史文化因素而专门从艺术技巧去研究文学的意味。利维斯要强调“伟大传统”的时候,他实际上试图达到与阿诺德同样的目的,即把英国领回到伟大的文学传统里来,从而确保英国社会兴旺不衰,这其中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诉求。利维斯一方面自觉与新批评保持距离,一方面又不能丢掉和批判新批评,因为新批评的方法永远是我们穷尽文本、构造文本继而批评文本的必要工具。我的看法是,只要从事文学研究,就多少要用到新批评。尽管后现代惯于翻陈出新,新批评看似不再时兴,但具体的文本批评实践始终都未曾真正离弃过新批评。
邹、欧:我们习惯上用多元文化主义来图绘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地形。在众神狂欢、杂色纷呈的表现背后隐藏着关于普世价值,关于新人文精神,关于全球对话主义的深度思考,这些思考同样是英语文学课堂教学必须履行的任务之一。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在接续传统英语文学教学的文本析读法的同时,有效传输一种适应于现时代的新型道德哲学?
刘: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人们使用这个词汇来认知和图绘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众神狂欢也好,杂色纷呈也罢,其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我想从这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坚信文学从来都不曾脱离“愉悦”和“教导”两个功能,关于“人人平等”、“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也未曾真正缺席过。后现代鼓吹反权威、自树真理,在人人平等的问题上可能有点走极端。这种极端具体表现为“过度”,即平等到了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应该把握一种度量,因为人都是社会人,每个个体的日常习性都会有意无意影响到他人。拥有一个普世价值是很有意义的,但具体践行的时候也会遭遇诸多管制。多元文化主义也容易走向反政府管理的另一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西方就开始反思多元文化主义了,所谓多元主义,其实存在一个荒唐的逻辑,即所有的构成脉络都积极向中心进发,梦想着成为又一个中心。宗教问题、女权主义、族裔政治等等都遭遇了类似困境。
普世价值还是有很多内容的,比方说强调人的尊严。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这方面比起西方来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不能简单化地生搬硬套,我们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应当好好地把外国文学每个阶段文学里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哲学道理、道德观念吃透,真正弄清楚,而不是瞎忽悠,空口喊大词汇。身处一个非常浮躁的现实情境里,我们应当坚守学术的底线,潜心专研,真正进入文本的内部,发掘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与审美内涵,从而传达一种适用于时代的道德哲学。
邹、欧:我们最后想表达一点自己的想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常常处于一种流动的、旅行的状态之中,经历着跨民族、跨文化、跨时空的挪用和改写,其所负载的道德寓意也在不断遭遇着解构与重构,比如《圣经》里大逆不道的“该隐”到了拜伦的笔下,摇身一变成为被歌颂的反抗英雄,英国文学长廊里这样的例子很多。这自然牵系到另一层面的问题,即文学经典通过成功改编传统形象以表达契合于时代情境的道德主题,我们把这种现象命名为道德主题的“在地性”,这可能也比较好地印证了前一个问题。
刘:确实如此,你们的想法事实上已经成为很重要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课题了。
邹、欧:谢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述。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向您请教加拿大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
[1]刘意青.英国18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语料库与口译研究专栏 (主持人:胡开宝)
主持人按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学界相继建设平行语料库、翻译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开展翻译共性、译者风格、翻译规范、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等领域的研究。然而,相比较而言,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却相对滞后。一方面,与笔译语料库相比,口译语料库的建设面临语料转写费时费力,口译副语言特征(paralinguistic features)的描述比较困难等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口译语料库不能反映目光接触和语调等副语言特征,其应用价值往往受到质疑。尽管如此,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仍然取得长足的发展,以欧洲议会口译语料库(European Parliament Interpreting Corpus,简称为EPIC)和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the Chinese-English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orpus,简称为CECIC)为代表的数十个口译语料库相继建成,并应用于口译语言特征、翻译规范和译员翻译风格等领域的研究。事实上,在口译研究中运用语料库,人们可以基于大量口译事实及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深入开展一系列口译课题的研究,为建立实证、科学的口译理论提供重要的物质前提。
本专栏选辑的三篇文章涵盖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的不同领域。胡开宝、谢丽欣运用语料库方法对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英语关系从句的应用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英语关系从句的应用频率显著高于政府工作报告英译,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的译员比政府工作报告的译者更倾向于将并列的两个汉语单句、名词短语和普通汉语单句等汉语结构译作英语关系从句。不过,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比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更倾向于将汉语关系从句译为英语关系从句。邹兵、王斌华归纳了口译语料库中副语言信息的转写及标注应注意的问题,并从标注工具、标注步骤和后期建设几个方面探讨了口译副语言信息的转写及标注方法。作者强调基于口译语料库开展口译研究的意义已经得到口译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其应用前景尚待进一步拓展。未来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应关注口译产品的口语体典型特征以及与口译特有的认知处理过程紧密相关的副语言信息。潘峰对于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模糊限制语的应用进行语料库考察,发现记者招待会口译英译语料比政府工作报告英译语料显著多用模糊限制语,这一现象既与模糊限制语在记者招待会口译活动中所能执行的功能有关,即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也与汉语书面语中程度副词的语义退化有关。此外,汉语源语的影响不应忽略。
Reconsidering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British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u Yiqing
ZOU Zan,OU Guang-an
(1.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6,China;2.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3,China)
This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u Yiqing,an outstanding scholar in the academic fields of British literature,Canadian literature and Bible studies.In the interview,Professor Liu starts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ritish literature,and intensively analyzes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British literature with the focus on English fictions in the 18th century.Besides,Professor Liu specially differs moral philosophy from moral preaching.She also offers deep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British literature in the 18th century in China,diversified literary theories,and the problems of diversified literary theories and multi-culturalism.
moral philosophy;moral preaching;British literature in the 18th century;multi-culturalism
I109
A
1002-2643(2014)04-0003-05
2013-01-10
本文是石河子大学人文社科中青年人才培育基金项目(项目编号:RWSK12-Y12)。
邹赞,男,汉族,湖南衡阳人,北京大学博士,新疆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文化研究。
欧光安,男,湖南武冈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