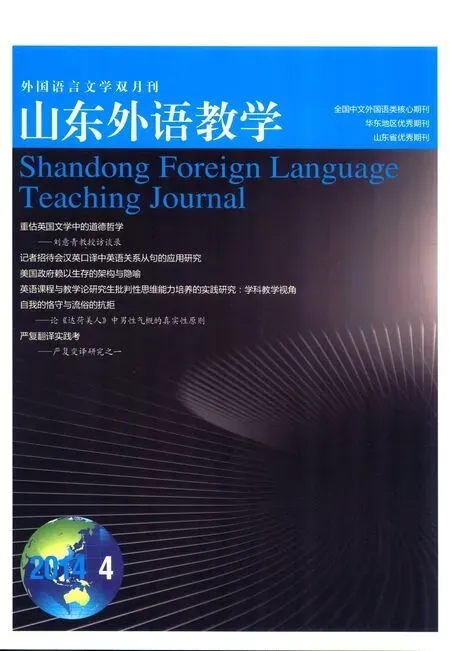“间质空间”阈限下的文化身份认同
何新敏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间质空间”阈限下的文化身份认同
何新敏
(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霍米·巴巴认为,后殖民文化就是一个“混杂体”,差异文化在一个交叉位置“间质空间”相交汇,在冲突与交往中,经过不断的“间性协商”而产生互融、互渗与共存。《中途》的主人公鲁特福德在贩奴途中就生存在一个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相交汇的空间,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双重夹击使他陷入文化身份的困惑而处于“中间”状态,随着与黑人交往的深入,他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逐步觉醒,最终摆脱不确定身份的困境,找到自我并超越自我,成为一个具有混杂文化身份的人。
间质空间;混杂文化;间性协商;文化身份;认同
1.0 引言
查尔斯·约翰逊的长篇小说《中途》是美国文学史上继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根》之后又一部叙述贩卖黑人奴隶历史的经典之作。小说发表之后,立刻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关注。《华盛顿邮报》认为这部小说“极具讽刺意味和高超智慧”;《今日美国》评论说,它以戏剧性的方式讲述了黑人和白人文化的融合。约翰逊自己也认为,这“是一部艺术性和知识性都很强的小说,它使我们能够作为有文化的群体而摆脱狭隘的抱怨,转向广泛的欢聚”。(转引自江宁康,2008:234)小说生动地讲述了贩奴途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揭露了美国资本积累的血腥与罪恶。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文化相交汇的“间质空间”,详细地描绘了处于命运转折中的主人公鲁特福德在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的碰撞中性格的多变和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揭示了“混杂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互动与杂交的基本特色,身份认同是一个与历史有关的、复杂而持续的协商过程。
后殖民文化批评家霍米·巴巴认为,后殖民社会是由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历构成的杂交体,任何族群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他们处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同参与了形成自身文化特征的过程,最终形成的文化就是一个“混杂体”。具有差异性的民族文化在一个“充满矛盾的”“混杂的”和居间的空间,即“第三空间”相交汇。霍米·巴巴借用艺术作品的隐喻“间质空间”的概念来描绘这一空间在不同文化相互连接上所起的协调作用。“间质空间”是指“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交融和相互趋同的交叉位置”。(任一鸣,2008:53)在这一空间里,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差异文化的“间性协商”,在双方的对抗与交往中不断变化,最后产生对差异文化的相互“默认”。(同上:53)不同文化在这里自由穿梭,文化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生活在这一空间的人因地域的“移位”、文化的“错位”而处于边缘生存的状态,“流放”就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他们往往产生归属上的失落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漂泊无根、无处安身使他们对“家”有着强烈的渴求,希望找到心灵的依托,身份得到认同。《中途》的主人公鲁特福德在贩奴途中心灵和精神上就经受着身份迷失痛苦的折磨,在黑、白文化张力的相互作用下,他经历了自我文化身份迷失的困惑、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最终找到自我并超越自我,实现了跨越种族界限的混杂文化身份认同。
2.0 自我文化身份的困惑
在后殖民语境中,萨义德用“流放”来描绘被殖民者文化归属上的失落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流放”是指地域、种族意义上的流放,处于流放状态的人,往往经历着文化身份上的困惑和心理上对“家园”的渴望。鲁特福德就是一个被流放者。自幼随父被卖到南方种植园,远离故土、被人奴役的苦痛在他幼小的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有幸在奴隶主死前赠与他自由人的身份,燃起他生活的希望。于是,他便满怀希望只身来到新奥尔良,期盼能像白人一样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可陌生的城市并不接纳他。虽然他是个自由人,但他奴隶的身份并没有一下子消失。他既无法延续原来奴隶的身份,又很难融入新的环境,成为一名无根的漂泊者。他以前是农场的黑奴,现在又成为城市的黑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感到无助和绝望,只能靠偷窃、赌博度日。为了让债权人忘掉自己和给伊莎多拉几个月的时间重新考虑结婚的建议,他出海远行,偷偷登上了前去非洲装运货物(黑人)的“共和国”号,幻想能享受航海的自由和快乐。但事与愿违,他途中的经历大大出乎预料,3个月的海上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次航行成为他重塑自我、寻找文化身份之旅。
作为一个新获自由的黑人,从小生长在美国,并接受过良好的西方文化教育,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当做船上的一名船员。可白人船员并不承认他的身份,他们也不信任他,仍把他看做是地位卑劣的黑奴。到达西非港口班加朗的第一天,大厨斯奎布就警告他不要四处走动,否则奴隶贩子会把他当作非洲黑人抓去卖掉,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一个船员。他与其他船员的疏离立时可见,因肤色不同而被排除在白人船员之外。后来船长雇他做眼耳,密切关注船上黑人和船员的举动,但也没有真正相信他。以大副为首的船员密谋哗变,试图推翻船长,他们拉拢鲁特福德为帮凶,偷偷卸掉船长枪里的火药,即便如此,大副等船员仍认为,“他就是一个小偷,偷窃是他的本性”。(Johnson,1990:91)在白人眼里,偷窃、赌博、无所事事等陋习是黑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他始终改变不了黑奴的身份。然而,船上的非洲阿尔穆塞里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黑人身份。虽然皮肤和他们一样黑,但阿族人把他和其他船员一样看做是他们的敌人,仇视、憎恨他。身份的不确定性使他成为性格分裂的人。他一方面要讨好船长和大副,试图得到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又主动教恩贡亚马英语,设法与阿族人拉近距离。但最终也未能如愿,没人把他当自己人。“中间人”的身份使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是白人殖民者,另一边是黑奴阿尔穆塞里人,在黑白两个群体之间游动,使他对自己的身份越发困惑,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黑人还是白人。
鲁特福德同时还经受着文化上被“流放”的困扰。他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能读会写,但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没给他平等的机会,失业流浪,成为城市的黑奴。可当他面对阿尔穆塞里人时,对他们的文化又感到陌生和吃惊。他觉得他们说的是奇怪的话,那“不是真正的语言”。(Johnson,1990:77)他们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简直不可思议,甚至生病了也不用吃药,能够自愈。非洲人原始的生活方式让他觉得新奇,感到震惊。西方和非洲文化巨大的反差带给他强烈的文化的“错位”感。鲁特福德既非白人,却成长在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尽管长着黑色的皮肤,可阿尔穆塞里人又不承认他。这种既不白又不黑的混杂文化身份,始终使他无法将自己整合为一个单纯的统一体,时常处于自我身份的怀疑之中。(王岳川,1999:63)
游移于两种文化身份之间心灵无所归依的痛苦自然使他产生想“家”的念头。文化身份的困惑必然产生心灵的流放,心灵流放的必然后果便是对“家”的渴望。鲁特福德是一个“错位”的非洲人,早已远离非洲根基,被流放在西方文化的边缘,但又与西方文化之间保持批评距离。在“共和国”号上,当鲁特福德的文化身份遭受质疑、被人排挤之时,他万念俱灰,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我只想有个家”,他多么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一个能让他安心生活的“家园”。可作为一个昔日为奴今日漂泊的流放者,流放是他必然的生存方式,不确定的身份带来的还是“无家可归”。对鲁特福德来说,“家”仅仅意味着他的归属,摆脱“中间人”的境地。他丝毫没意识到,自从登上“共和国”号的那刻起,他就不可能拥有一个“家”。“家”只是一个幻想,是一个在他失望、痛苦时“想要的地方”。
3.0 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
霍米·巴巴指出,文化身份不是来源于自身的某种稳固不变的东西,而是产生于与他者的差异之中。文化身份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已经存在在那里的东西,它是一个被建构的、可变的、流动的过程性的东西。(贺玉高,2012: 131)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关系并非“他者”与“自我”简单的对立关系,它们也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而是两者之间互为依存、不断变换的不稳定的关系,难以用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来解释。它们在一个假定的“第三空间”交汇,在冲突与交融中进行“协商”,从而达到互渗、互融,使对立关系转化为文化的渗透与认同,将对立的冲突转变为身份的改变。几个月的航行对于生存在这一特殊空间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互相改变彼此的过程。鲁特福德在与白人和黑人的交往中,自己的文化身份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初,他自以为自己是“共和国”号上的一位船员,和其他白人船员一样都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者,并且他否认自己的黑人身份,试图和白人船员站在一起。但白人船员并不承认他西方人的身份,仍把他看做一个黑奴。外表上他与船员疏离;而在内心里他又排斥与阿尔穆塞里人的种族关系。但非洲人的血脉是永远消除不掉的,他也曾告诫自己“他们不是黑奴,他们是阿尔穆塞里人”。(Johnson,1990:76)实际上,他就是一位离开“非原始起点”的被“移位”的非洲人,他与阿尔穆塞里人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滞差”,使他与阿族人处于失衡的状态。他长着黑色的皮肤,可又深受西方文化的侵染,两种文化在他内心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而正是这种文化差异和碰撞,使得异质文化之间得以沟通和转化。双方经过“间性协商”,互相对话、交谈和商讨,使文化权利在双方之中达到一种均衡的发展和认同,并对双方加以制约和协调。(王岳川,1999:65)
鲁特福德在与阿尔穆塞里人的相处中,对他们的文化渐渐有了深层的认识和尊重,对自己认同的西方文化的权利作用也逐渐削弱。他主动向阿尔穆塞里人恩贡亚马学习阿族人的语言,打听他们祖先的历史。在不断接触中,他越来越敬仰他们的祖先,尊重他们优秀的文化传统,对船上黑人的悲惨遭遇也越来越同情。特别是当他被叫去将一个黑人的尸体扔进大海而手上仍留下一块腐烂的血肉时,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刺激,内心深深地被刺痛,他对白人殖民统治的合理性开始动摇,对奴隶制度产生痛恨。于是,他改变了对黑人的态度,主动与他们接近,试图赢得黑人的信任。这些变化说明鲁特福德的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和人性、良知的显现,他认识到贩卖黑奴的非人性和奴隶制度的残暴。因此他参与了阿族人的暴动,推翻了船上白人船员的统治。尽管他的黑人意识有所觉醒,但他终究摆脱不掉西方文化霸权地位的影响,对白人仍抱有幻想,游移不定的双重性格再次表现出来。他既同情黑人,又不想伤害白人。在黑人控制了船只之后,他又劝说阿族人不要杀死受伤的船长和大副,再次扮演了调停人的身份,在黑人和白人两个群体间斡旋。鲁特福德不确定的性格特征正是萨义德所谓的“夹缝人”生存本能的必然选择,是在尴尬处境中唯一的出路,也是两种文化碰撞产生的后果。在西方白人文化与非洲文化发生冲突时,面对优势文化他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面对弱势文化他不禁又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又要保住优势文化的地位。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不可能一下子放弃,完全站在被压制的“弱势文化”一边。最终,他选择一条折中的办法,既顾及到黑人的面子,又保全了白人。实际上,这是两种文化相互协商的结果。
黑人小女奴巴莱卡母女加速了鲁特福德身份意识的转变。在“共和国”号船只几乎被毁的危难时刻,他答应巴莱卡的母亲收养这个8岁的小女孩,后来又给予她悉心的照料,和她聊天,培养他们之间的感情,最终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这说明他与阿尔穆塞里人血缘上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也是他民族文化身份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鲁特福德不再拒绝自己非洲人的身份,他觉得他的哥哥很像恩贡亚马和巴莱卡,并对斯奎布说,“我很可能来自阿尔穆塞里人的部落”。(Johnson,1990:109)虽然他没有明确承认自己是非洲人,但态度的转变足以说明他价值体系所发生的变化,他在思考在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对于一个处于迷茫状态的人来说毕竟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在霍米·巴巴看来,这种心灵扭曲的接受者,由被动到主动,由压迫感、屈辱感到逐渐适应,这应该是身份认同的基点。(王岳川,1999:64)
4.0 混杂文化身份的认同
黑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是生存在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种族占统治地位的美国黑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不仅是生理的本能,还包含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文化身份是每一个族群或个体的立足之本,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点的标志。身份认同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一种认识视野和立场。”(习传进,2007:220)换句话说,文化身份认同是每一个族群和个人生活的依赖,归属感的寄托。因此,文化身份认同是生活在边缘社会的美国黑人一直追寻的目标,也是民族主体性的诉求。对于非裔美国黑人来说,文化身份认同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弄清楚“我是谁?”“我与谁认同?”在对黑人充满敌意和偏见的美国社会,黑人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受歧视,而且身心和精神上遭受无以言说的痛苦的折磨,他们往往迷失自我,处于迷茫疏离的生存状态,“双重意识”是典型的心理特征。“每个黑人都有两个灵魂,两种思维,两种难以调和的竞争和在一个黑色躯体内的两种思想的斗争。”(同上:7)“双重文化”传统同化与分离持续的张力使他们陷入迷茫痛苦的深渊,既不白又不黑的身份使他们缺乏安全感,时常因“无家可归”而困扰。这种生存状态激发他们强烈的寻根的热望,希望得到认同,找到归属。他们一方面渴求认同白人文化,同时又希望维持黑人文化传统的独立性。这种“新黑人”希冀得到的文化身份已经超越传统黑人的寻根认祖,虽然他们有强烈的寻根的愿望,但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社会环境已经决定他们是无法回到“原始的起点”,只能在新的环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萨义德(1999:427)认为:“人类文化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织、汇合的生存空间,各种文化的相互作用留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任何纯粹的、绝对的、本真的族性也是不存在的,“杂交性”是多元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后果。生存在“间质空间”里的黑人也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根据具体的文化语境建构自己的身份,实现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并存的主题体验,继而出现文化身份的杂交状态。
鲁特福德的文化身份认同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重新建构身份的过程,这是多元文化“间性协商”的产物,是“混杂文化”的体现。返航途中,鲁特福德就开始周旋于以船长为代表的白人文化和以恩贡亚马为代表的非洲文化之间。两种文化的持续夹击在鲁特福德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求生的本能使他的性格和思想观念随环境变化而改变。在费尔肯船长的劝解和教诲之下,他默认了西方主流文化宣扬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也表现出对船长分裂的忠诚。在黑人哗变掌控“共和国”号之后,他还设法保全船长和大副的性命。他也接受了西方文化倡导的赎罪、忏悔等文化价值观。这说明白人文化对他的影响和与主流文化认同的愿望。但他同时又表现出对非洲文化的尊重。恩贡亚马向他讲述了阿尔穆塞里人祖先的故事和他们古老的文化传统,他的心灵受到洗礼,他对阿族人信奉的神、文化传统、生活态度以及他们的自尊等表示敬意,不能容忍自己再去伤害他们。受阿族人神的教化,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参与贩运黑人奴隶的举动感到耻辱和自责。所以,当船长请求他续写航海日志时,他欣然答应。但他不愿意按照船长的吩咐,而是要按自己的意愿,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世人。拿起笔来书写历史成为他身份转变的转折点,他要亲自把美国这段丑陋的历史公布于众,这说明鲁特福德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已经摆脱“中间人”左右逢源的境地,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这是对以船长为代表的白人主流文化霸权的消解,也是边缘文化走向前台的标志。
特别当鲁特福德在船舱底层亲眼看到船长贩运的阿尔穆塞里女神时,他顿时醒悟,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本性苏醒了。在女神面前,在黑暗的船舱里,他如真如幻地看到了20年前父亲的身影,看到了面对猎奴者父亲英勇不屈、顽强高大的形象。20年来对父亲抛弃幼子独自逃跑所怀有的仇恨一下子烟消云散,所有的怨恨顷刻间转变成无限的敬意,他觉得那个站在他面前的阿尔穆塞里人祖祖辈辈敬奉的神灵就是他的父亲。他从阿尔穆塞里人的文化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确认了长期困扰自己的文化身份,承认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非洲人。非洲裔文化身份的确认更加坚定了他与贩奴者决裂的决心,加深了对他们卑劣行径的痛恨。在船只遇难被救起之后,他拒绝接受流氓泽林盖巨款收买他的条件,而是当众揭露他贩卖、残害黑人奴隶的罪恶行径。鲁特福德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表明他已建构起黑人的主体性,实现了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找到了个人赖以生存的民族之根,心灵之魂。
正如鲁特福德自己承认的那样,这次航行使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鲁特福德。这种变化是无法抗拒、不可回避的,也是双重文化相互作用、不断“协商”后产生的。“共和国”号狭小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文化相交汇的“第三空间”,作为“中间人”的鲁特福德游移于两种文化之间,两种文化的碰撞必然产生相互间的融合。无论是白人文化还是黑人文化在这一特殊空间内是很难保持原来各自的独立性,它们只能在差异中共生共存。船长的教诲、大副的身体力行使他认识到西方白人文化、西方宗教中邪恶与真诚友善并存;从黑人的言谈举止中也认识到非洲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为在危难之时大副主动捐躯延续他人性命而感动,也为阿尔穆塞里人的顽强不屈而表示敬意。鲁特福德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是典型的“混杂文化”的结合体。最终,他摆脱了单一文化的狭隘与偏见,实现了超越国家与种族的混杂文化身份认同。他要求泽林盖答应供养三个黑人小孩,这说明他已经跨越了不同文化的疆界。小说尾声约翰逊交待,鲁特福德打算与伊莎多拉回到伊利诺伊南部农场定居,建立起自己新的“家园”。这象征着新生活的开始,也是航行途中文化身份认同过程的结束,是心灵归属的结果。
5.0 结语
鲁特福德命运的转变,文化身份的寻找与认同模式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差异文化的相互依存指明了方向。这既是约翰逊对处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文化关系所进行的哲学思考,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一个启发性的模式。约翰逊既反对白人标榜的二元对立的观点,也不赞成白人文化之上的强权哲学,而是主张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共生共存的一种中庸之道。他通过塑造鲁特福德这样一个“新黑人”形象,借此告诫人们,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在特殊的语境之下经过不断的“协商”是能够交融,从而消解西方中心霸权思想,使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趋于并存。这也是霍米·巴巴“间质空间”理论所阐释的观点。文化差异是当今世界不可回避的事实,民族文化存在于差异性之中,“混杂文化”是当代文化存在的状态。因此,萨义德提倡人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不同的文化差异。(王岳川,1999:3)
[1]Johnson,C.Middle Passage[M].New York:Scribner,1990.
[2]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贺玉高.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江宁康.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6]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7]习传进.走向人类学诗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非裔美国文学批评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Liminal Space”
HE Xin-m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Homi K.Bhabha argues that the post-colonial culture is continuously in a process of hybridity,and that cultures meet in a liminal or in-between space.He also suggests that with a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transvaluing,cultures interact,transgress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The protagonist,Rutherford,in Middle Passage inhabits such an in-between space on the voyage of slave trading.Challenged by both western and African cultures,he gets confused for lack of an essentialized or fixed identity.With constant interactions with the black,he begins to be awake to his black identity,and more than that,he even leaps over the borderlines between races,and ultimately constructs his hybrid identity.
liminal space;cultural hybridity;liminal negotiation;cultural identity;identification
I106
A
1002-2643(2014)04-0090-04
2013-09-06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当代非裔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2YJA752019)、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当代非裔美国作家查尔斯·约翰逊研究”(项目编号:QSY13023)和中南民族大学中央专项“当代非裔美国小说新历史主义话语研究”(项目编号:CSZ13007)的部分成果。
何新敏(1965-),女,汉族,河南南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