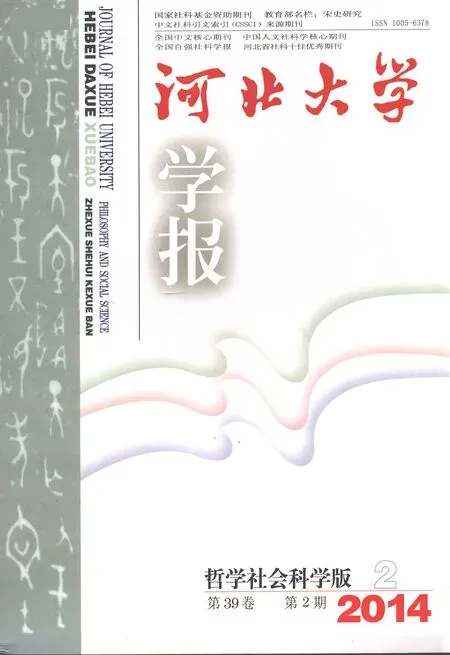李长之画论研究与中国艺术理论的现代转换
刘 洁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相继出现了三部旨在整理并讨论中国古代画学思想和理论价值的重要论著,李长之的《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是其中格外另类的一部,因为著者极其自觉而明确地将研究重点落在“体系”的发现与建构上。长期以来,这部体系化著作一直被定位成极端西化和不符合中国文化逻辑的教条之作[1]。但是,也有少数学者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认为“在四十四年前,作者李长之先生以体系的——哲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画论和中国绘画,……能以全新的观点与方法,讨论中国绘画的意义和价值,不论他的理论是否全为后人所赞同,他超越传统窠臼的见识与独特的见地,尤其在那战乱频仍,颠沛流离的时代,更加难能可贵”[2]。笔者对此十分认同,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画论体系与批评》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以体系性思维整理国故,它更为深远的旨趣在于重新激活民族文化系统中未曾充分生长的本有元素,并以此实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这并非是简单的西化,而是中国艺术理论挣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积极探索和勇敢尝试。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艺术理论近百年的现代转换历程中,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应被忽视。
一、传统画论现代转换的重要实践
关于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问题,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要议题。“失语”和“重建”成为最频繁使用的关键词。钱中文、曹顺庆等大量学者开始积极投入到“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工作中,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就。然而,这种“失语”和“重建”问题并不仅仅是世纪之交才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理想,它其实贯穿了中国文论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王国维、宗白华、钱钟书、朱光潜、李泽厚等诸多学者无一不是在“失语”即借鉴西方理论话语的过程中“重建”起中国现代理论话语的实践者。如果我们能把李长之的艺术理论研究放在这样一个整体历程中去考察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去简单地质疑其理论上的西化,而他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也会清晰地突显出来。因此,玛尔霍兹、温克尔曼、歌德、席勒等之于李长之的意义,便与叔本华之于王国维的意义、康德之于宗白华的意义、甚至马克思之于当代中国文论的意义,并无根本的区别。
但是,李长之的与众不同则在于,他格外关注西方的重视逻辑明晰性的治学思维和建构完美体系的理论意识,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理论恰恰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精确的范畴、明晰的体系正是未来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样态。如果说,对于西方理论,王国维、宗白华等人更多地是一种内在观念的吸纳,那么,李长之则更多地是一种对理论表达方式的外在吸纳,其目的不是以西方观念置换或改造中国观念,而是找到比我们以往更加适应时代的理论话语表达方式。当然,这个方式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形式或组织结构的问题,其间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现代性的治学思维和话语方式。正如李长之在《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的《导言》中所说:“通常那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态度,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所谓不可以言传,是本没有可传呢?还是没有能力去传?本没有可传,就不必传;没有能力去传,那就须锻炼出传的能力。对于中国旧东西,我不赞成用原来的名词,囫囵吞枣的办法。我认为,凡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就是根本没弄明白,凡是不能用现代语言表达的,就是没能运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弄明白。中国的佛学,画,文章,……我都希望其早能用现代人的语言明明白白说出来。本篇之作,这也是其微意之一了。”[3]240在这里,李长之表述得非常清楚,这部著作的旨趣之一就是要对传统画论进行现代转换,其重要的途径就是使用精确的现代语言将含混不清的古代名词即概念、范畴表达得更清楚、更明了。同时,他还说到这部著作的另一旨趣:“国人对于中国画论的中国画,在过去从历史的——实用的观点去整理者多,从体系的——哲学的观点去整理者则少。现在此作即从后者出发,作一个初步的尝试”“我们可以在好像没有头绪的画论中,找出一个体系来,并且因而可以看出中国画在艺术上之究竟的意义和价值来。”[3]239显然,李长之要对经验语录式或史传著录式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中国画论进行一次大胆的体系化重建,即用一种具有系统性的现代思维方式来重新审视和表述中国画论中对艺术本质问题的那些思考,这一思维是非时间性和非经验性的,因此它将呈现中国传统绘画和传统理论的总体风貌和本质特征。应该说,这正是典型的现代理性思维,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建设的基本话语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理论话语的现代化表达方面,李长之比他的前辈比如王国维、宗白华等似乎走得更远一些。
尽管李长之在《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这部著作中主要尝试的体系方案是一种来自德国理论家玛尔霍兹《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和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的西方方案[3]239,但是在另一篇重要的论文《唐代的伟大批评家张彦远与中国绘画》中,李长之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中事实上也存在着可以和西方比肩的体系性著作,即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他指出这部著作在理论及方法上都堪称典范[3]456。但是,他也不无遗憾地论道,在张彦远之后,无论是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还是米芾的《画史》,都要比张彦远平庸得多,前者“关于纯理论的成分渐少,而关于实践上的叮嘱加多,……但这却是以后中国画论的趋势”。而后者“则更为琐碎,倘若我们要找点点滴滴的精辟之处,虽未尝没有,只是那气魄和系统,却更要输与张彦远多多了”[3]474。可见,李长之的对中国画论的体系化尝试并非是一种纯粹西化的方案,他是在西方和古代即空间和时间的两个维度上去寻找可以引领中国理论走向全新领域的合法路径。同时,李长之的立场始终是一个现代的中国的立场,是一个跟西方跟古代都保持着一定距离的现实立场,因此,基于这样的立场所提出的现代转换方案,即使在观点上有一些幼稚或偏激,其整体思路却是不应受到质疑的。
二、充满时代精神的体系建构
李长之的《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是从艺术的三个要素入手去努力发现理论体系的,这三个要素即“一、主观——就是创作者的人格问题;二、对象——就是艺术品的取材问题;三、用具——就是创作者所借以表现艺术品之取材的手段问题”[3]239。全书结构也正是以此为主体,同时另设“中国画论中之一般的艺术问题”一章进行系统总结。李长之所谓“发现”了中国画论的思想体系,并不是指这个功能性的结构形式,而是指他在这个结构的引导下所找到的一种我们民族曾经拥有且一以贯之的绘画精神,即以“壮美”为主要审美形态的艺术精神,“壮美性……这乃是中国画的真精神和独特处”[3]257。在李长之看来,无论是主观方面还是对象方面抑或是用具方面,中国画的要求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壮美”性,而不是“优美”性。
李长之首先论道,“在主观上看,中国人对于画所要求的,是三点,一是要求男性的,二是要求老年的,三是要求士大夫的”。因为,中国画反对悲观色彩、琐屑、闺阁之气等近于女性气质的美;中国画在技术和内容上都是要求纯熟、精湛、老到、苍劲,而反对的则是幼稚、嫩弱;中国画还反对匠气、凡气、市井气、俗气,反对院工、作家和北派等等与士大夫的精神相背驰的绘画风气。中国的士大夫“把绘画的种种方面使其趋于单简”。在李长之看来,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画的美学特征是一种“壮美”,而 不 是 优 美[3]241-257。其 次,李 长 之 认为,中国画在对象上并不是漫无选择的,相对于人物,山水自然更能够体现士大夫的精神追求,而植物中的梅、兰、竹、菊更能代表士大夫的人格德性,所以“严格地说,中国画没有写生。虽然当前画的是事物,其实不是事物,乃是人生经验,又不是原料式的人生经验,乃是人生经验而经过组织,经过提炼,经过理想化者”。因此,在对象上中国画的“非写实”特征和“形而上”追求,在美学上也都是属于“壮美”一类[3]258-264。最后,李长之认为中国画在用具即艺术手段方面也是趋于壮美的。他非常赞同清人所谓“气韵由笔墨而生”的观点,指出中国绘画正是因为注重笔墨工具而忽视对象,所以才能达到对单纯而统一的“壮美”的表现。而由笔墨所至的“气韵生动”也正是充满生命壮美性的艺术最高境界[3]265-286。
总之,在李长之的发掘中所显现出来的具有整体性的中国画论体系,是一个以“壮美”为核心审美风格和审美理想的、将主观(人格)与对象(自然)及用具(笔墨)三个艺术要素成功结合的、纯粹形式主义(气韵)的美学系统。正像李长之所强调的这个系统具有趋简的倾向一样,他对它的描述和建构也是异常的精炼和简洁。李长之所言的“壮美”是一种与“优美”相对立的审美范畴,它以“单纯,统一,简净,高超,而庄严”[3]302为基本特征。
李长之的“壮美”范畴实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康德早期哲学;二是中国儒家思想。1936年李长之曾评介并翻译了康德的早期论文《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中的前两个部分,即《论优美感与壮美感之不同的对象》和《论人类之一般的壮美性与优美性》。根据李长之的译文,我们知道,康德认为,能够引起审美主体壮美感的对象往往具有单一纯净、古老悠远、高大幽深等特征,而人格的真实坦诚、单纯高贵,也是一种壮美。李长之认为中国画在对象上的单纯,在精神上的高贵,在工具上的趋简与康德所谓的壮美的确一致,可见其影响。同时,李长之也非常认同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刚性气质,孔子刚强,热烈,勤奋,极端积极的性格便是一种壮美的人格,而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更是中国艺术壮美精神的最好概括。很显然,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李长之是试图在理论上鼓舞起时代的热望与民族的精神。
三、文艺美学建构中的重要著作
文艺美学是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勃兴起来的一门学科,它的提出是对长期以来的泛滥于中国文艺研究中的阶级斗争工具论、唯意识形态论以及唯认识论等严重忽视文艺自身审美特征这一恶劣现象的反拨[4]。但是,文艺美学的学科名称及建构理念,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出现在李长之的多篇论文中。因此,李长之实际上是中国文艺美学的第一位建构者,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5]。李长之的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于古典经验论和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新的文艺研究方法,即体系性的哲学美学的方法。他认为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批评以及文艺教育,都要始终坚持美学价值第一位的原则。体系性的提倡主要是针对经验论来说的,而美学价值的标举则是针对当时格外火热的两种研究方法即心理学和社会学而言的。当然,他并不是否定和反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而是强调它们应该在美学方法之后,即文艺美学理当是文艺研究的首要方法论。
在《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这部论著中,李长之明确地实施了这一主张,不仅以体系性重新构建了经验论式的中国古代画论,而且更以一种哲学美学式的方法对中国画论中所体现的美学追求和文化价值进行了独到的阐发。比如此论著的第五章《中国画论中之一般的艺术问题》,李长之将中国画论中关于艺术的形而上思考加以提炼,对文艺美学方法论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在这部分,李长之的探讨包括:艺术与大自然,艺术与实生活的距离、艺术与道德、天才问题、个性论、创造与模仿、创作原理、完整的艺术品之要求、艺术上之失败、艺术上之浅薄、创作与批评、艺术之时代划分等共是11个方面,尽管每个方面的论述都不是充分展开的样态,但其简练中亦不乏真知灼见。
但是,李长之的《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恐怕也并不仅仅在于整理国故,甚至也不止于对艺术理论进行一种现代性转换,它还有更为根本的一个意义,即将艺术的美学价值的评判与讨论引领到文艺研究的首席地位上来,而这种文艺美学的方法实际上正是中国近现代学者进行现代转换时最为切实的策略。因此,对于《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的考察,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部专门的艺术理论著作来读,而是将其放在中国现代美学和中国文艺美学的建构历程中去看,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且充分地认识到李长之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
[1]罗世平.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整理与研究[J].朵云,2007(66):7-30.
[2]何怀硕.近代中国美术论集:第六卷[C].台北: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1:55.
[3]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杜书瀛.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J].文学评论,2003(4):149-164.
[5]刘洁.李长之与中国文艺美学的“现代”建构[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3(16):133-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