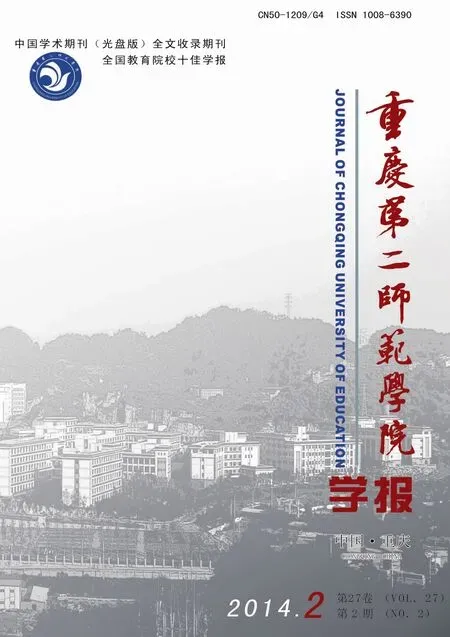论英汉词汇重叠的象似性理据
杨 双
(黄淮学院 外语系,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一、语言重叠式的象似性研究
象似性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哲学家、实用主义和符号学的创始人Peirce[1]在他的符号三元组合概念中提出的。Peirce的象似符反映了能指和所指之间可能出现的一种指称关系,是指由其自身的特征来表示另一事物的符号,即形式与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象似性。国内外语言学家普遍承认语言符号具有象似性,象似性是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即语言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有论证理据的。
把象似性引入语言重叠式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家的重视。由于重叠式在不同语言中有共性存在,通过对不同语言的研究和观察,可揭示重叠式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非任意性联系。较早注意到这点的是Sapir[2],他在对既无亲缘关系又无地缘关系的美洲印第安语言、非洲、大洋洲语言的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多种语言中的重叠现象含有“不证自明的象似性”。Lakoff & Johnson[3]也认为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的所有的“重复现象”都是“形式越多、内容越多”原则的例证。Moravcsik[4]指出语言的重叠式是“形式机制的拟象用法”,各种语言的重叠式经常负载的最为明显的意义是“量的增加”。Hiraga[5]则将语言的重叠现象作为“数量象似性”实例进行阐释。
英汉两种语言都以其自身的语言体系选择了自己的重叠形式,特别表现在词汇重叠的现象上。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词汇重叠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理据的,可以说词汇重叠是象似性的一种体现,有认知上的象似性根源,是人类认知规律的语言外显形式,用象似性理论去分析词汇重叠现象是可行的。
二、英汉词汇重叠的象似性理据
语言具有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篇章等多个层面,象似性可存在于语言的不同层面,考察语言符号象似性不可只从分析某一个层面得出的结论。对于英汉词汇重叠这一语言现象,也可从不同层面进行探讨,语音、词汇、句法这三个层面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语音层面的象似性
1. 重叠的拟声词
拟声词中词汇重叠占多数,通过重叠的形式,拟声重叠词加强了一般拟声词所具有的表现力,与其音韵特征共同创造意境的声效,使语言达到更加生动和形象的效果。英语中的拟声词有很多是重叠词,通过音节的复制或部分复制构成的,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感。如摹仿水的声音:沸腾声hubble-bubble,滴嗒声drip-drop,下雨声pitter-patter;模仿金属的声音:叮当声ding-dong,jingle-jangle;模仿敲门的声音:rat-tat,tap-tap;模仿钟表滴答声:tick-tick,tick-tach;模仿动物叫声类:狗吠bow-wow,猫头鹰的叫声tu-whit,tu-whoo,夜莺的叫声jug-jug,鸭叫声quack-quack;也有模拟人类语言的声音:hush-hush 秘密的,hurly-burly 喧闹。
汉语中的拟声词也常常采用重叠的形式。与英语中的拟声叠词相比,汉语叠字拟声词形式更加灵活丰富,有两字格的如“嗡嗡”、“呜呜”,有三字格的如“啪啪啪”、“呼噜噜”,也有四字格的如“劈劈啪啪”、“咕嘟咕嘟”等。这些词有的纯粹摹拟自然的声音,有的表示声音的一个自然段落,有的表示声音的连续或重复,有的表示声音的杂乱。以自然声音的模仿为例,模拟水声:哗哗、汩汩、潺潺淙淙、哗啦哗啦、咕噜咕噜;模仿金属碰撞声:丁零零、叮当叮当;模仿人的说话或笑声:喋喋、叨叨唠唠、喃喃、嘟嘟囔囔、啧啧、叽叽喳喳、呵呵、嘻嘻哈哈;模仿动物叫声有:嘁嘁喳喳、喔喔、呱呱。
2. 重叠的音素与声调
英语中有不少音素与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有直接联系。音素并非对自然声音的直接模拟,而是引起人们心理的联想,引起一种运动的感觉或者某种物质与精神特性的感觉。换言之,音素构词使音与某种象征性意义发生联系从而产生音与义的联想。在英语词汇重叠中,音素与意义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联系,音素也会影响意义。如英语中的shm-重叠,音素shm-加在重复词词首,代替第一个辅音字母构成特殊重叠词,表示一定程度的轻视或语义消解。shm-重叠词一般即时构成,属于口语或儿语,它的发音可使人联想到与儿语有关的相似声,例如baby-shmaby,car-shmar,marry-shmarry,doctor-shmoctor等。
英语是拼音文字,音素或音位可以影响词义,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与之不同。汉语可以通过声调来影响重叠词的意义,相当于Lyons[6]阐述的“超音质特征”(prosodic features),即伴随言语的语调升降或重音模式具有相当大程度的象似性。声调的轻重变化与词汇重叠的意义有联系,可以说形式元素的构型与概念元素的构型呈现一种同构关系。例如,汉语中动词的AA及ABAB重叠式,如“看看”和“考虑考虑”的第二个及第四个音节都念轻声,发音较短较轻,其意义是动量及时量的减弱;而AABB重叠式,如“打打闹闹”和“修修补补”各音节都念原调,发音较重较长,其意义则为动作时间的延长或不断重复[7]。
(二)词汇层面的象似性
1. 重叠的摹绘词
词汇重叠可对人类行为,客观世界存在事物的形状、状态及面貌进行模拟。词汇重叠拟态的性质比较强,原来没有这一特点的词语构成重叠词后便增加了这种性质。英语中的词汇重叠有的模拟形状,主要对大小、弯曲、长短、凹凸等方面的临摹,如 teensy-weensy 小小的,zig-zag 之字形状,criss-cross十字形,jing-bang 团状的物体,convex-convex 双凸面的;有的模拟行为状态,如hurry-scurry 慌慌张张,shilly-shally 犹豫不决,dilly-dally 磨磨蹭蹭,titer-titter 上下晃动,wig-way 摇摇摆摆,harum-scarum 冒冒失失,niminy-piminy 做作、扭捏;有的使人产生与词形相似的联想,如 roly-poly展现孩子圆滚滚、胖乎乎的可爱样子,niddle-noddle 可联想到打盹时不断点头的情形,lovey-dovey勾画出一幅情人道别时情意绵绵的景象,lardy-dardy 展现无精打彩装扮成花花公子的样貌,holus-bolus 则把一口吞下的情形还原出来。
作为方块字的汉字源于象形和会意,属于表意文字,常常以其形表义,因此其书写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不证自明。汉语中的词汇重叠也不例外,常常用来摹色、摹味、摹形、摹状等,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增添了音韵美、强化了形象意义。常见的摹绘色彩的叠词有:白茫茫、红彤彤、金灿灿、绿油油、黑漆漆、花花绿绿;摹绘气味的叠词有:香喷喷、热辣辣、臭烘烘、甜蜜蜜;摹绘形状的叠词有:直挺挺、圆滚滚、瘦嶙嶙、乱蓬蓬;摹绘状态和样貌的叠词有:热呼呼,粘糊糊、笑嘻嘻、整整齐齐、龌里龌龊。
2. 语义重叠词
语义理据指根据其原有意义推断出其新的或衍生的意义。有些英语中的词汇重叠是通过语义的引申和比喻而产生的。如英语中的重叠词goody-goody 借用对“good”的儿语化,指人表面上好而本质伪善的伪君子。再如,filp-flop (又作filp-flap) 是flip 的重叠,原指在空中翻转的动作,引申为方向、观点、态度的突然改变。一些常用表达方法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沿用语义和通过语音讹化形成重叠词。最典型的例子是shilly-shally,最初人们表示犹豫迟疑时常说“Shall I ? Shall I ?”逐渐讹化成“shill I ? shall I ?”在现代构成重叠词shilly-shally。
(三)句法层面的象似性
英汉词汇重叠在句法层面的象似性可以从数量相似性来解释。语言的使用者把他们对世界感知的方式和过程映现在句法上,词汇重叠式中形式与意义对应的普遍性也可以看作“形式越多、内容越多”数量象似性的一种特殊反映。更多的相同的形式(词汇重叠)代表更多的相同的内容(名词复数为多量、动作重复为性状增强等)。在句法层面的词汇重叠,可以说是通过词汇形式元素的重复出现以图样的方式反映了意义元素的复现。
英语中单音节拟声词模拟一次声音或动作,如:beep, bomb, cock, crack, pop, plop, sizz等。而重叠拟声词则模拟反复,多次性声音或重复的动作:quack-quack, puff-puff, zip-zip, flick-flick等。汉语中也常常使用词汇重叠来加重语气,扩大概念量,能表达某种状态和程度的加深。如“绿草萋萋,白云冉冉,彩蝶翩翩”中,“萋萋”使青草绿的性状加强,“冉冉”使白云的动态增加,“翩翩”使动作更加形象,使次数增多、程度加强、意旨深化。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目前运用中的英汉词汇重叠从象似性的角度进行了动态的考察,用象似性的理论进行论证,肯定了象似性在英汉词汇重叠中的体现,进而对象似性在不同语言中和不同层面中的方式及程度差异进行探讨。英汉词汇重叠不仅通过模拟声音、摹绘形状展现了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而且还通过语义理据、句法上的数量象似性揭示了语言符号与人类思维规律的关系。本文在展现同一语言现象词汇重叠在英汉两种不同语言中和具体语言层面中的象似性的方式和程度差异的同时,论证了象似性的普遍性规律,为英汉词汇重叠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
参考文献:
[1]Perice, C.S. Philosophical Writings[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2]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3]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4]Moravcsik, Edith A. Reduplicative Construction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3.[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5]Hirage, Masako K. Diagrams and Metaphors: 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5, (22): 5-12.
[6]Lyons, John.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积累AABB式拟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