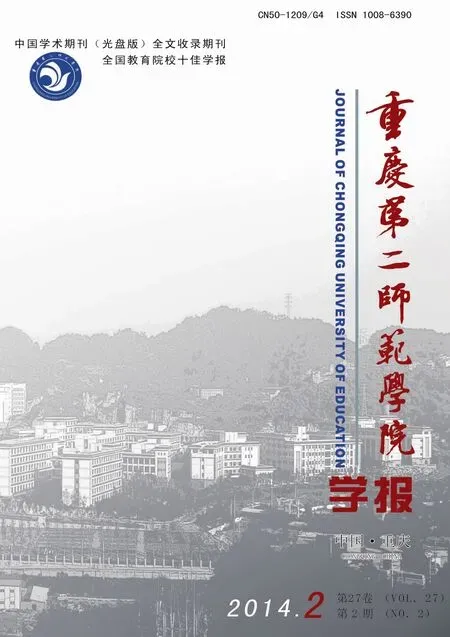批判与超越: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主—奴辩证法”
李贞元,程和祥
(1.南京大学 哲学系,南京 210023;2.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精神现象学》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关键和秘密,而这个关键和秘密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种“否定性的辩证法”表现在贯穿整部《精神现象学》的“异化”或“自我意识的异化”这一概念上,而这又集中体现于《精神现象学》的第四章第一节——在这一节,黑格尔提出了“主—奴辩证法”。在对黑格尔的这一思想的解读过程中,显现出一些浅薄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在这些观点的包装下,“主—奴辩证法”成了俞吾金所说的“哲学神话”,即“主人成了奴隶,而奴隶则成了主人”。[1]66基于唯物史观,从感性活动的视角对“奴隶”和“主人”的处境进行分析,以及对“主—奴辩证法”的历史审视,将表明奴隶对主人的颠覆具有偶然性;并且所谓的“主人变成奴隶,奴隶变成主人”,也不符合黑格尔的原意。
一、“主—奴辩证法”的神话
按黑格尔的原意,在争取承认的生死斗争中,一方冒着生命危险,获胜后成为主人;另一方因对死亡的恐惧而把自身的命运交由对方决定,被对方蓄为奴隶。在主人的权力支配下,奴隶投入到陶冶事物的劳动之中。在劳动中,他摧毁了曾经令他发抖的异己的存在物,“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2]131而主人只是尽情享受,在享受中他成为一个“非独立的意识”。对这种“独立性”和“非独立的意识”的理解,学者们莫衷一是。在肯定“恐惧”和“劳动”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当奴隶获得独立性而主人成为非独立的意识时,主—奴关系开始反转:“主人成了奴隶,而奴隶则成了主人。”[3]117
然而,这种理解过于主观,它肯定了“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中,恐惧和陶冶事物的劳动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但对于奴隶的恐惧和劳动,缺乏科学客观的分析。
首先,它没有看到恐惧的负面意义。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在于他恐惧死亡,即他宁可放弃超越自然层次的自由,选择作为物而活着。因为恐惧,奴隶在一切异己的存在面前都害怕得发抖,从而不能将一切事物都看作满足其欲望的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对象,他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欲望与其对象之间的自然关系。他在恐惧中开始否定自身的自然存在,潜在地意识到自己是一种自为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使得奴隶成为奴隶的恐惧感,也开启了奴隶的自我确证之路。但是,奴隶对死亡的恐惧除了具有黑格尔所说的正面意义外,还有严重的负面后果。这种“曾经浸透进他的内在灵魂,曾经震撼过他整个躯体”[2]130的恐惧会导致奴隶处于焦虑状态,长期的焦虑会禁锢奴隶的思维,使奴隶变得麻木和神经质,他“目瞪口呆,而意识也得不到提高与发展”。[2]131
其次,它忽略了现实劳动的消极方面。在黑格尔看来,在恐惧中奴隶所达到的对自为存在的潜在的自觉只不过是智慧的开始,而真正地完成这种智慧,还需要由劳动来实现。对于奴隶而言,“一切‘现状’都不‘符合’‘自己’的‘本质’,都是要‘改变’的”。[5]20劳动不仅改变了奴隶的依赖意识,而且还是对恐惧的否定——通过劳动,呈现在他面前的令他恐惧的异己的存在都被他改造了。但是,黑格尔虽然“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6]101理解为人在劳动中的对象化和异化,并且扬弃这种外化的自我生成。但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没有把劳动看作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受其哲学体系的制约,黑格尔把“劳动”桎梏在绝对观念的牢笼之中,忽视了劳动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因而,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只看到精神劳动的积极意义,而没有看到现实劳动的消极方面。在奴隶社会或存在奴役的地方,主人驱使奴隶从事的都是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劳动。一方面,对于这些强制性的、重复且乏味的劳动,奴隶不仅毫无兴趣,还常常通过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和逃亡等方式与主人进行抗争。对于此类劳动,谈何“陶冶与教化”?所谓的劳动美学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繁重的、屈辱性的、危险性的劳动严重威胁着奴隶的身心健康和生命。不少奴隶常常在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悲惨地死去,又如何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如何对主人的地位进行挑战?
最后,恐惧和劳动这两个环节是相互关联的。对奴隶而言,“在恐惧中他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潜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2]131“没有服务和听从的训练则恐惧只停留在外表形式上,不会在现实生活中震撼人的整个身心。没有陶冶事物的劳动则恐惧只停留在内心里,使人目瞪口呆,而意识也得不到提高与发展” 。[2]131同样,如果奴隶一直处于恐惧和焦虑的阴影中,那么,奴隶就不能很好地从事改造自然、陶冶事物的劳动,这样,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就不能“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2]130因此,那劳动着的意识便难以达到“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
二、主人和奴隶——基于实践的视角
对“主—奴辩证法”的认识,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主—奴辩证法”“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7]54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56换句话说,对“主—奴辩证法”的认识,要始终站在现实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从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理解它、把握它。立足于此,可以发现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存有诸多疑问。
一方面,黑格尔对奴隶的处境的理解,有两点值得怀疑。
首先,黑格尔认为,劳动节制了奴隶的欲望。但是,他没有深刻地洞察到,现实中奴隶的劳动不仅仅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更多时候被迫压抑自己的欲望,而极度的压抑在一定程度上会摧残奴隶的身体并扭曲奴隶的心理,使奴隶处于接近崩溃的病态和疯狂之中。
其次,当奴隶在主人的权力支配下投入到劳动中去的时候,其体能、技能和性格都必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和奴隶的独立意识的确立并没有必然关系——奴隶有可能变得麻木不仁,也有可能更加依赖主人。整个人类历史表明,作为整体的奴隶阶级的觉醒和独立意识的获得乃是外在的或从内部成长起来的先知先觉者对广大奴隶自觉地进行教育甚至灌输的结果。单纯的劳动有可能导致某一个奴隶产生独立意识,并且这种独立意识会逐步成熟,但是仅仅单纯的劳动就导致整个奴隶阶层产生独立意识却是一种痴心妄想。
另一方面,黑格尔对主人的论述也有失偏颇。黑格尔这样写道:“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把他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2]128在这里,黑格尔把主人仅仅理解为奴隶劳动成果的享受者。实际上,主人在现实活动中扮演着多个角色,远比一个单纯的享受者丰富得多。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主人都沉溺于享受。主人在追求享受的同时,也试图维持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以使自己在物质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且,主人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强加给奴隶后,并不是所有的主人都“无所事事”地饱食终日,主人中的精英阶层会用从奴隶那里掠夺过来的时间去构建适合于主人利益的意识形态,“以麻痹并消解可能会在奴隶中间慢慢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1]67换言之,主人不仅仅在物质上支配奴隶,还试图从精神上给奴隶套上枷锁,决不会坐以待毙。
第二,主人也会用掠夺来的时间去自由地学习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知识,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陶冶个人的情操,使自己得到全面发展。对于日夜都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纠缠的奴隶而言,主人这样的学习方式和发展方式是他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另外,主人的这种学习和发展策略也可以看作是对奴隶反抗的全面防范和戒备。在谈到资本家的财富时,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8]218又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8]225把马克思关于资本家的观点运用到主人身上,也是适当的。这样,黑格尔把主人仅仅设想为纯粹的消费主义者只不过是一种偏见。
总之,在“主—奴辩证法”的神话中,主人是只知道痴迷于享受而一无是处的白痴。与此同时,奴隶则被精心打扮成了真正的智者和命运的宠儿。通过劳动,奴隶摆脱了对主人的依赖,而主人反过来依赖奴隶。但是,这又如何解释人类的历史?
三、对“主奴辩证法”的历史审视
重新理解“主—奴辩证法”,我们需要对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作一番历史考察。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启示我们,对“主—奴辩证法”的历史考察应该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出发。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出发去审视“主—奴辩证法”,完全是由现实的社会实践所激发和规定的,因为从“事后”开始思考,无非是说明“思维应该在实践的最高端和发展的最前沿”。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着眼于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社会总体历史进程作了一个深刻的划分与展望。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奴关系”刻画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特性,存在于“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之中,当该社会形态终结之后,人成为“生产当事人”,但奴隶并没有成为主人——奴隶仍然是奴隶,但主人不再是人,而是外在于曾经的主人和奴隶的物——他们所赖以生活和维持生产的物。换句话说,当作为整体的奴隶阶级颠覆主人的统治,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之后,又被“物”所奴役。至于马克思许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依旧还未到来——即使到来,奴隶也只是“社会自由人”,不是“主人”。由此观之,立足于现实的历史,奴隶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对主人进行统治。所谓的“奴隶变成主人,主人成为奴隶”没有历史依据,根本不具备普遍性。有鉴于此,尼采拒斥“主—奴辩证法”。与马克思不同,在尼采看来,奴隶的胜利只是一种极其偶然的个别结果,具有主人气质的超人完全可以再次取胜。尼采认为,奴隶永远是奴隶,它不可能“升华”为主人,主人也永远是主人,它不可能沦落到奴隶的自保状况。“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本身并非辩证的关系。那么谁是辩证法家,谁使这种关系辩证化了呢?是奴隶,是奴隶的视角和属于奴隶视角的思维方式。[9]14”或者,“辩证法仅仅是那些不具备任何其他武器之人手中的自卫手段”。[10]49
四、回到黑格尔——生死斗争
实际上,根据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安排,奴隶并没有在现实中冒生命危险去实现自己的自由,而是倒向了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与基督教主义。
在斯多葛主义中,奴隶只是在思想中承认自己的自由,他以口头议论的方式调和自己的奴隶地位与抽象的思想自由,而口头自由与现实处境的冲突,驱使着奴隶走向怀疑主义;在怀疑中,奴隶否定一切外在的存在,包括他在现实世界中的奴隶地位,这种怀疑使得奴隶走向虚无主义,其中一些人会选择自杀,而活下来的虚无主义者选择了基督教主义;在基督教主义中,对于作为教徒存在的奴隶而言,“自由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词,一个简单的抽象理念,一个无法实现的理念,就像在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中那样。自由是真实的,自由真实地存在于超越之中” 。[11]55
但是,归根结底,斯多葛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以及基督教主义者都是奴隶。因为他们在死亡面前哆哆嗦嗦,不敢冒着生命危险与主人作斗争,因而不能改变他们自身的奴役处境,终究只是奴隶。“在生死斗争中,人成为其对手的奴隶是因为想不惜一切代价保存生命,人成为上帝的奴隶也是因为想避免死亡,想作为教徒在自己身上寻找一个不死的灵魂” 。[12]81但人终究是要死的,“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 。[2]21“正是人自愿地接受在为了纯荣誉的斗争中的死亡危险,甘心死亡、并通过语言揭示死亡,人才成为人” 。[12]642毕竟,是死亡形成了植根于自然之中而又凭借人的精神而振拔于自然之上的人,是死亡令人“走向他自己的最后命运”。也只有这种“朝向死亡的存在”,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被置入了先有之中。“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就其存在来说本质上是将来的,因而能够自由地面对死而让自己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抛回其实际的此之上,亦即,作为将来的存在者就同样原始地是曾在的,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能够把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自己本身之际承担起本已的被抛状态并在眼下为‘它的时代’存在。只有那同时既是有终的又是本真的时间性才使命运这样的东西亦即使本真的历史性成为可能。”[13]435-436
奴隶真正应该做的,是接受死亡的事实,“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4]1483-1490只有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与主人作斗争,奴隶才能被承认为具有独立性的人。“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的真理性。”[2]126也就是说,仅仅意识到自身的自由是不够的,充其量只是像一个主人,一个假主人。“但是,真主人杀人:他为了得到承认进行斗争。”[12]97
五、小结
基于唯物史观,从感性活动和历史的角度,对“主—奴辩证法”进行分析,以及立足于原文的解读,都能够证明:从“主—奴辩证法”中解读出“主人成了奴隶,而奴隶则成了主人”,将“主—奴辩证法”制造成哲学神话,纯属误读和亵渎。毋庸置疑,“主—奴辩证法”作为黑格尔青年时期最深刻、最神圣的思想之一,影响深远:马克思把“主—奴辩证法”中的承认论题和劳动论题结合起来,并深入思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承认问题——“对马克思来说,主奴关系的核心无疑就是阶级斗争,承认问题的关键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5]90欲望、死亡和承认等概念也被科耶夫发掘,成了他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主—奴辩证法”进行透视的重要主题,从而为之后的诸多流派提供了可汲取的思想资源——“欲望主题在萨特、德里达、福柯、拉康、德鲁兹等人那里得到了极其绚烂的发挥;死亡主题使海德格尔通向法国成为可能,进而在列维纳斯那里得到最强有力的回应”;[16]5至于承认主题,在德国由霍耐特继承,并在流行于英语世界的后殖民理论思潮中得到了某种异乡的回响。
参考文献:
[1]俞吾金.走出“主奴关系”的哲学神话[J].东南学术,2002,(2).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陈伟.片面承认的全面化——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J].理论界,2008,(1).
[4]陈良斌.“主奴辩证法”的扬弃与承认的重建——从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论到马克思的承认理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10),22(5).
[5]叶秀山.关于“自由”与“必然”——研讨黑格尔哲学断想[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1).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M].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0]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A. Koje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M].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12]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张盾.马克思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7),47(4).
[16]张亮.欲望、死亡与承认:科耶夫式黑格尔哲学的三个关键词[J].江苏社会科学,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