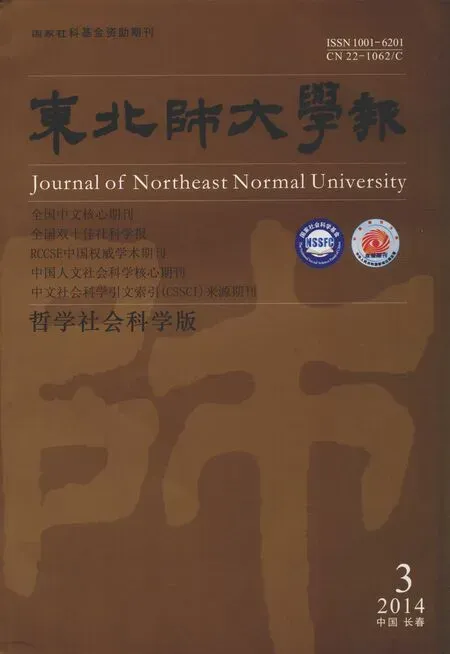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的特异性探究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2)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台湾成为日本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从此开启了日本的海外殖民统治。日本殖民地的语言政策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在一元化的组织性、计划性、实行力及一贯地行动方针或系统式的立法措施上,明显落后许多。但是,另一方面,在世界的殖民地语言政策史上,日本的政策可说是极为特殊的。帝国主义各国在百年甚至数百年所做的事,日本在短短的50年间就完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语言政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军事压力之下传授日文,对殖民地人民实行“国语”教育,试图将殖民地人民改造为日本人,通过军事强制性手段来推行的语言政策。
一
所谓的语言政策承载了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语言教育和日本的国体有紧密的关系,这是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的特征之一。
殖民地统治是宗主国政治、传统及文化的投影,通常是以该国的社会形态、政治思想、文化特征为基础而架构成形的。语言政策原本就是国家的行为,当然也就表现出不同国家的特征。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殖民地宗主国,其殖民地统治方针的形成经过、结构原理、特色皆异于欧美各国,因而,其殖民地语言政策也有其特异性。
(一)日本语言政策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因素
日本语言政策的意识形态表现为极其强调日本国体的神圣、日本文化的优秀。从脱亚论到大东亚共荣圈论,尽管内容有所不同,但这一核心内容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与日本民族的心理以及政治文化有着极大的关联。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不仅是殖民政府的政治方针的体现,也是其累积的文化理念和世界观的反映。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1.日本国家、民族主义因素:明治二十年前后,日本语中并没有民族这个名词。民族这两个字开始被一般人所普遍认识和接受,是在文化这个概念开始在日本普及的19世纪后期。18—19世纪欧洲流行着两种概念,一个是文明的概念,它象征着都市、未来、人类的进步,以及启蒙主义和普遍性,先是在法国、英国等当时较为先进的国家中盛行。文化的概念则兴起于德国、俄罗斯等当时较为后进的国家,代表着乡村、传统和过去以及人类的个别性、精神上的优越性和独自性。文化和文明之概念在形成之际都基于同一视角来批判当时的制度,日后为了维持各国自身的利益,这两个概念逐渐发展成为不同类型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对于德国、俄罗斯强调自己国家成立的根据是民族的古老、血统的纯正和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英国、法国等则标榜其国家形成的主轴在于人类进步、启蒙和普遍性的存在。分化的结果是两者形成文明—国民,文化——民族的两个不同的组合概念。这两个组合概念,不久便先后投射在日本这个新兴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轨迹上[1]。明治二十三年(1890),教育敕语诞生后,日本逐渐兴起德国浪漫主义式的民族观,将民族视为拥有共同血缘、语言、文化和精神的集团,即所谓单一民族思想观以及国体论,国粹主义也随之抬头。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中国台湾。此时,日本正在迈向国家的进程中;日本人对文化、文明的接受态度不但影响了国家的形成,并在日后强烈地反映在其殖民地统治的意识形态及发展上。
2.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的因素。民族的心理特征与其所居住和生活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文明的影响具有先天性和无从选择性,它是塑造一个民族性格的重要因素之一[2]。
从古代到近代,日本一直处于文化和文明的边缘,而自身却缺乏文化的原创性和文明的创造力,使其内心深处产生一种生存危机意识和强烈的自卑感。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日本人形成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3]。这种从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岛国封闭性,使人又容易从自卑演变为盲目的自负。这种自负是由自卑感引发的,是以自卑感为内部驱动力发展而来应对自卑的另类方式,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内心的平衡状态,从自负中获得暂时的满足感。日本民族容易从崇拜外国急转为民族主义的狂热,正好是这种心理机制的映像。在帝国主义国家之中身为后进国的日本,对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仍存有自卑感。它强调自己国体优越,而对欧美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潮、欧美的世界秩序的批判,其独特的心理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观、世界观和文化观的累积,使日本基本上无法接受西洋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而是需要创造出日本独有的思想观、世界观作为国家的指导理念,以显示其民族的优越性,满足其独特的心理需求。在这种条件下,日本的国体被构想出来了。
(二)日本语言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将语言作为同化殖民地人民的重要手段,不遗余力地推行“国语”(日语)。极力强调“国语”(日语)在塑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一体性中的重要性,用以维护其国体和满足殖民地扩张的需要,满足殖民者殖民统治需要。
1.日本的国体。国体本身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世界各国都拥有自己的国体,但日本人认为其国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优越无比的。台湾学者陈培丰将日本的国体定义为“以天皇制国家原理为中心,具有拟宗教式性质的近代日本政治文化”[4]29。国体强调天皇是人神,日本人都是天皇的子孙,天皇对于所有的子孙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种国体论将施政的平等建立于纯血性的前提上,强调纯血性,排除异民族在外,而这种构想也使得国体给人一种庄严、古老与神秘的印象。国体以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作为两大圣典。国体论在当时对日本建立强大的国家统治基础和抵抗外族的入侵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维护其天皇统治的根基。因而,日本民族对国体有着强烈的情感,在日本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但国体论意识形态与殖民地统治又正好是对立关系。因为血缘上、地缘上由汉民族和高山族所构成的台湾居民,明显地与天照大神的子孙和民族毫无关联,历史上二者也缺乏拥有共同的神话空间。如果以天皇制国家伦理、道德精神与一视同仁的政治体制来统治台湾,要将台湾人视为天皇的子民,要求他们尽子孙之责去崇拜日本的国体论,就会与国体的原理背道而驰,也必然会引起日本政治体制上的动荡。然而,对于日本而言,成为拥有海外领土的东亚帝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其政治、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极大的益处,因此,日本也不可能受制于国体而放弃占领台湾的权利。如果因台湾而放弃国体,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国体的狭隘性,这是日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需要日本政府思考一个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种矛盾冲突。
2.“国语”的作用
如果日本想在国体的束缚下为台湾统治找出路,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同化让国体和殖民统治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去除因为统治台湾造成的国体理论上的瑕疵。而要完成这些任务,语言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媒介。因为语言本身除具有文化价值外,还具有政治价值。当一个国家企图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覆盖或复制到另一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民族,控制其经济、政治等实权的时候,对殖民地人民进行语言教育是最直接的方式。
制定近代日本语言政策最重要的人物上田万年(1867—1937),在甲午战争前发表了日本近代史上重要的演说。上田万年把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定位在所谓一个国家、一个语言、一个民族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框架中,为即将拥有海外领土的单一民族国家原理预留下一个退路和空间,以维护其“优越”国体的完整性[4]39。这种逻辑的操纵把日本人、大和民族的血缘关系的定义从先天转向后天,并逐渐成为当时台湾统治的主流思想。语言则成为同化的主要手段,这种观念也被日本政府所采用。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如果透过语言这个后天的教化工具,让居住在台湾的人民都学习并使用的话,就可以通过语言这个包含强烈意识形态的工具来改变台湾人的原有思想观念,移植忠君爱国的思想,将他们改造成日本人。这样,在观念上就可以自圆其说地去维护基于拟血缘制国家原理而成立的国体之优越性。透过语言这一媒介,把台湾人同化于日本的大家族中,从而调和日本在支配异民族时所引起国体上的矛盾和冲突,满足了其殖民统治的需要。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国语”(日语)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语言的同化,使台湾人民建立对日本这个国家的内在认同。日本殖民政府将“国语”(日语)当作同化殖民地人民的最有效的手段,投入大量的财力对殖民地人民实行国语教育。1895年10月,伊泽修二在担任总督府学务部长后不久,就前往台南拜访英籍宣教师托马斯·巴克莱。巴克莱以自己在台湾从事近12年的宗教教育经验,介绍他用罗马字拼注台湾语(闽南语)教育台民的方法,认为采用以方言为形式的母语教育是成功的。若以英语或日语在台湾办学,将徒然无效[5]151。但伊泽认为台湾人的教育非用日语不能成功,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而是要把本岛人同化成日本人为目的的教育。因此在占领台湾初期,日本在财政紧迫的状况下,国语教育的创始者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不但实施了无偿式的入学制,甚至为了奖励台湾儿童入学,还付给学习者津贴。甲午战争后的40年间,台湾总督府花费了大量的教育费用,其目的仅仅为了培养二、三十万的国语使用者[4]12。这种“国语”同化的政策是非常不经济的。当时明治政府聘用的英国人顾问科克伍德曾警告过日本政府,与其让大多数台湾人去学习日本语,不如让一小部分日本官员去学习台湾话更节约成本、更经济。因为如果只是为了统治上的方便,对殖民地有实施殖民语言教育的必要,但是宗主国的国语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这种有悖于殖民统治目的“非经济性的语言教育政策”[5]151,居然得到日本国内近乎一致的支持。这在世界殖民史上具有明显的特异性,是从未有过的殖民教育现象。
将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是台湾殖民统治的最高目标,教育只不过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而已。殖民者认为,只有让台湾人“熟习”日语,才能进一步让台湾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等与日本人完全一致,才能实现殖民统治的根本目的。所以,台湾教育必须是日语教育。不但以日语为教育用语,初等教育也基本以日语为教育内容。相比其他殖民国家重视高等教育,日本将语言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初等教育上。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从1854年开始统治印度。英国的殖民教育方针是重视中、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抑制初等教育。日本在台湾的做法恰恰与英国相反。日本主要通过发展初等教育,使多数台湾人学习日语,试图把他们同化为日本人。而大学只有一所,专门学校也只有五所,并且这些大专学校大多为日籍学生所独占。
日本的殖民教育重视普及初等教育的结果是,日本统治台湾50年,初等教育普及率达到71.3%[6]。从上述分析及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知道,日本重视初等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利用儿童幼年期的可塑性,以“国语”来同化异民族,以大量养成拥护“国体”的臣民。换言之,是将台湾人导入大和民族之中。日本之所以重视初等教育,就是想把殖民地的人民改造成为“日本人”。
二
日本的殖民地语言政策是依靠军事力量来强制性来推行的,这是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的又一特征。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语言和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和语言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7]在殖民地时期,日本依靠其军事上的优势,保证了“国语”(日语)的绝对优势地位。这种强制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从政策制定的需求上看,就是要满足高度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求,推行日文是满足殖民地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满足不同民族间沟通、交流的需要,因此基于此的语言政策就充满了殖民宗主国的意味。首先,作为宗主国,内在的一面(和日本精神、日本文化的同一化)认为日文教育不仅要以全面普及日文为目的,而且也要灌输以皇国史式的建设及皇国为中心的新秩序建设的精神。从日本占领台湾之后,普及日文被强调为日本人化最重要的手段。推行普及日文意味着首先要教授人民的是日文,然后通过日文让其学会日本文化以及身为日本国民应该具有的意识。其次,有助于日本在世界秩序、“大东亚共荣圈”中的地位,这些因素也成为普及日文的原动力。宗主国家语的想法,从日本历经占领朝鲜、成立伪满州国、爆发卢沟桥事变之后的1938年前后成为主流。
(二)从政策制定的机构来看,台湾的语言政策是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台湾总督府制定的,伪满洲国的语言政策是由掌握实权的关东军制定的,这也意味着其政策是在军事力量的推动下执行的。
(三)从推行手段上来看,日本没有善用文化政策,只依赖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其他殖民地宗主国一般都利用传教来传播语言或文化,如统治台湾时的荷兰殖民者和统治北美及非洲的英国、法国殖民者,都利用基督教来传播宗主国的语言和文化。在传教的语言上大多采用了殖民国家的通用语言,并没有强迫殖民地人民学习宗主国的国家语言。但日本不具备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拥有的世界性宗教和具有奉献精神的传教士。虽然日本极力强调其国体的优越性,但因为国体只是一种概念,缺乏像基督教那样的教义、教化力、感化力,在殖民地实际上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日本本国也缺少自己的先进的文化,在古代学习的是中国文化,近代又学习欧洲文化。尽管有茶道、花道、日本舞蹈等独特的文化,但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殖民地统治上起不了作用。在国体观念的影响下,日本殖民者认为只有学习日语才能变成日本人,才能建立起所谓的“东亚共荣圈”,因此,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政府只能依靠军事的优势,强迫殖民地人民学习日语。
从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看,语言的地位常常随着权力的变化而变化。国家共同语言和官方语言以及各种地方方言只不过是权力角逐的产物。同时任何语言政策的形成,是政治角逐的结果,这种关系在日本殖民地表现得更为明显。同样是殖民地教学语言方面,其他殖民主义国家采取了与日本不同的教育政策。欧洲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法国,曾在其殖民地越南实施法语的普通教育,后来发觉效果不佳,才又改用地方语教学。同样是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荷兰殖民者1624年,即占据台湾南部的第三年,就派出牧师进入新港社,向居民学习当地土语,并以罗马字拼注土语,成了所谓“新港语”和“新港字”。此后,荷兰人在台湾各地兴办学校,其教学语言就是“新港语”。西班牙殖民者1626年占据台湾北部后,也派出神父学习当地土语,然后用拉丁语注释土语,进行传教和办学活动。德国对其殖民地的教育,也不强求以德语来进行教学,而是“专心于其殖民地土语的辞典及文法的编修”,以当地土语作为教学语言。
日本与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不同,它利用其政治、军事优势,强制推行宗主国的国家语言——日语。例如,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军队强占台湾之后,由台湾总督府制定和实施了国语教育政策,通过在当地建立国语学校来普及日语。其后,又通过公布台湾教育令等一系列行政手段加大学校在普及日语方面的作用。以台湾公学校的课程安排为例,早期的公学校开设的“国语”作文、读书、习字三种(以后合并为“国语”科)周学时数达21学时之多,占总学时数的三分之二强,几乎是把公学校变成日语学校了[8]196。鉴于殖民当局在公学校主要上日语课,而不设汉文课,引起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04年修正公学校规则,适当减少日语课的周时数,增设汉文课,每周2—5学时,但日语课的周学时仍然高达10—14学时。在殖民当局发展公学校教育的同时,对台湾原有的书房教育则百般限制、压制和刁难,使书房不断减少,至1922年,合台湾书房从1 500多所减至194所,学生数从20 000多人减至5 664人[8]246。此时,总督府为了推行日语、禁绝汉文,通过修改公学校规则将汉文课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汉文课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1937年,在“战时体制”的“皇民化运动”中,台湾殖民当局决定废除汉文课,从此,汉文教育在公开的教育场所消失了。其后,这种方法同样用于中国其他的殖民地地区。例如,1932年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其“国语”是满语和日语。但是公用语被定为日语,并在许多学校开设了日语课程。1937年通过的新教育令,从1938年1月1日新学期一开始就给予了日语第一“国语”的地位[9]。
除了利用学校教育强制学生学习日语外,日本殖民者还通过社会手段强制殖民地人民学习日语。在中国台湾,由于公学校长期以来入学率偏低,台湾人回家后所说的仍然是台湾话,台湾话仍然是台湾人所使用的语言。在此情形下,日本殖民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殖民政府规定在公共场所也必须使用日语,禁绝台湾人在任何公共场所使用台湾话交谈[10]。同样,这种强制使用日语的规定也在伪“满洲国”里出现。它涉及了当时的各个行政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而且在满洲国所有的地区内,日文是唯一必须要教授的语言,满语及蒙古语则只限定在某些地区,其地位也在日文之下。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伪满洲国,其“国语”竟然不是自己的母语,而是另一个国家的语言。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的强制性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结 语
正常的语言接触和学习,本来是为了满足双方的交际的需求,具有双向性质,但是日本殖民政府在中国推行的语言政策,是一种通过军事占领,强迫殖民地人民学习日语的强制性语言政策,它并不是为了满足民族之间沟通和交流的需求,而仅仅是为了满足日本殖民统治需求的一种单向性的语言政策。日本殖民者试图通过日语(国语)语言媒介,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殖民地人民,改变和控制被殖民者的思想,为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服务。在这种军事压迫下,被殖民者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语言政策剥夺了被殖民者的语言权利,使其面临着母语流失、文化贬值等诸多威胁。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与欧美的殖民地语言政策相比虽具有特异性,但其本质没有改变,仍是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与文化侵略。我们必须通过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来了解其“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
[1]陈培丰.同化的“同床异梦”[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42.
[2]刘利华.日本民族心理影响因素探究[J].全球视野理论月刊,2008(1):141.
[3]龚道贵.地理环境与日本民族精神[J].黑河学刊,2008(9):129.
[4]陈培丰.重新解析殖民地台湾的国语“同化”教育政策——以日本近代思想史为座标[J].台湾研究,7(2).
[5]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M].周宪文,译.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
[6]汪婉.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及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之认同”[J].抗日战争研究,2006(11):65.
[7]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文明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88.
[8]庄明水.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4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9]曲铁华,梁清.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1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08.
[10]庄明水,谢作栩,黄鸿鸿.台湾教育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