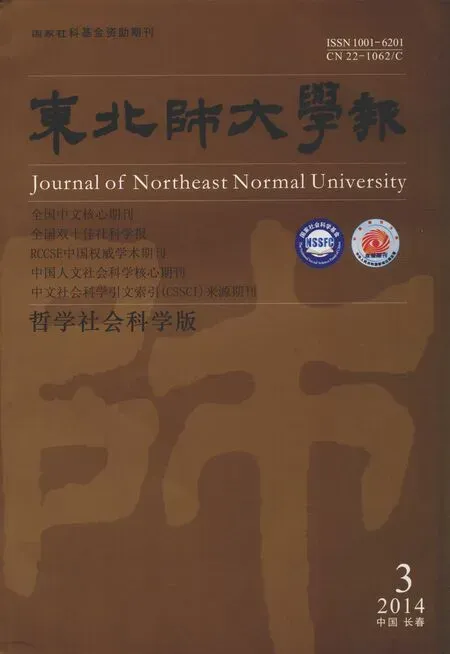古代埃及国王沙桑克一世巴勒斯坦战争考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130024)
近年来,关于公元前10世纪的巴勒斯坦考古地层的勘定是《圣经》考古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学者们对公元前926年沙桑克一世巴勒斯坦战争的讨论。由于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地层毁坏是勘定公元前10世纪巴勒斯坦考古地层的主要依据。于是,沙桑克一世巴勒斯坦战争的影响及其在巴勒斯坦考古地层勘定上的作用遂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沙桑克一世,古代埃及第二十二王朝,也即利比亚王朝的创建者,其在位时间大约为公元前945—924年,在《圣经》中沙桑克被称为示撒,他曾于公元前926年在巴勒斯坦地区作战。在《圣经》研究方面,许多学者都曾发表过关于沙桑克战争的专题论文[1]139-150,1-16。在埃及学方面,科琛在他的题名为《古代埃及第三中间期》的专著中对此次战争进行过专门的讨论[2]292-302。尽管这些学者在战争细节的描述上存在着差别,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却基本相同,即他们都是以《圣经》关于该战争的记述为主要依据。在《圣经》中,沙桑克一世的战争主要被记录于《列王纪上》第14章第25—28节和《历代志下》第12章第1—12节中。此外,他们还使用了古代埃及文献和考古资料。在古代埃及文献和考古资料方面,沙桑克一世卡尔纳克神庙中的浮雕是他们最为有力的证据[2]432-447。他们把浮雕中的地名表作为此次战役的行进路线图,以此来重建战争。
然而,在使用地名表重建沙桑克一世战争上,学者们却遗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圣经》仅仅提到犹太首都耶路撒冷是埃及人的主要进攻目标,而地名表则主要由以色列和奈格瓦地区的地名组成,犹太的地名少有提及。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死后分裂成仍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南部国家犹太和以撒玛利亚为首都的北部国家以色列。奈格瓦(Negev),以色列南部沙漠地区或半沙漠地区的总称,占以色列领土面积一半以上。为此,学者们认为,这是因为《圣经·列王纪上》记述的重点是犹太,而忽略了埃及战争部分。事实上,《列王纪上》用了大量的篇幅记录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统治,对犹太的记录却很少。第二,学者们在重建战争时没有对沙桑克一世进攻耶罗波安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读,一些学者认为沙桑克一世是为了惩罚耶罗波安的背叛而对其宣战的[1]147,[2]298。目前,我们的确有证据显示耶罗波安曾归顺过埃及,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曾反叛过。
在使用沙桑克一世的胜利浮雕作为重建沙桑克一世战争的时候,学者们也遇到了一些难题。第一,胜利浮雕由三部分组成:以杀戮敌人为主要场景的浮雕本身,铭文和地名表。然而大多数学者们只把目光投到了地名表上,他们往往忽略了铭文和浮雕本身在重建战争上的价值,这将直接导致他们对浮雕的理解不够全面。第二,学者们并没有注意到沙桑克的胜利浮雕只是许多同类浮雕中的一个。新王国时期,胜利浮雕大量出现,这就意味着沙桑克的胜利浮雕是这类浮雕的承续,甚至到第三十王朝时期胜利浮雕仍然存在①本文所提到的胜利浮雕包括以下三个要素:杀戮敌人的场景,铭文和地名表。而这三个要素并不是胜利浮雕所独有的。在古代埃及,从前王朝时期到罗马征服时代,以杀戮敌人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一直存在着,如从前王朝向第一王朝过渡时期的纳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第五王朝国王萨胡拉(Sahure)和尼乌塞拉(Nyuserre)的浮雕,第六王朝国王派匹一世(PepyⅠ)和派匹二世(PepyⅡ)的浮雕,第二十六王朝国王塔哈卡(Taharqa)的浮雕。参见,J.A.Wilson,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pp.48-9,p.55。此外,地名表也被发现于其他类型的考古和文献资料中,如阿蒙霍特普三世地名表被发现于其雕像底座上。。因此,只有把胜利浮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对其中的某一个浮雕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为此,我们收集了其他十一块胜利浮雕:三块属于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479年—前1425年);一块属于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约公元前1427年—前1400年);一块属于第十九王朝国王塞提一世(约公元前1294年—1279年);两块属于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79年—前1213年);两块属于第二十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84年—前1153年);一块属于第二十五王朝国王沙巴卡(约公元前716年—前702年),以及一块属于第三十王朝国王奈布塔奈布(约公元前380年—前362年)②十一块浮雕的详细资料如下:图特摩斯三世:卡尔纳克神庙第六座塔门的西墙,编号为K C 56和K C 152。图特摩斯三世:卡尔纳克第七座塔门南墙,编号为K G 88和K G 90。图特摩斯三世:卡尔纳克第七座塔门北墙,编号为K G 40和K G 43。阿蒙霍特普二世:卡尔纳克第八座塔门南墙,编号为K G 143(东)和K G 145(西)。塞提一世:卡尔纳克柱廊大厅北侧外墙,编号为K H 6(西)和K H 14(东)。拉美西斯二世:卢克索神庙庭院西侧外墙,编号为L G 44(北)和LG 49(南)。拉美西斯二世:卡尔纳克柱廊大厅南侧外墙,编号为K O 44(西)和K O 50(东)。拉美西斯三世:卡尔纳克神庙前厅北墙,编号为K K 10(东)和K K 1(西)。拉美西斯三世:迈迪奈特·哈布神庙第一塔门外墙,编号为MH A 39(南)和 MH A 31(北)。沙巴卡:麦迪纳特·哈布小型神庙埃塞俄比亚塔门西墙,编号为MH B 223(北)和 MH B 232(南)。奈克塔奈布:迈迪奈特· 哈布小型神庙柱廊东墙,编号为MH B 267(北)和MH B 270(南)。参见 H.H.Nelson,Key Plans Showing Locations of Theban Temple Decorations,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 56,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其中,拉美西斯二世的一块浮雕被发现于卢克索,拉美西斯三世的一块浮雕以及沙巴卡和奈布塔奈布的浮雕被发现于迈迪奈特·哈布,其他浮雕均被发现于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沙桑克一世的浮雕也被发现于此。
在对这些浮雕进行研究后,我们发现:第一,这些浮雕中的地名表并不是军队的行军路线图。在把这些地名表与以图特摩斯三世的行军路线为代表的埃及真正的军队行军路线对比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图特摩斯三世行军路线图出现在图特摩斯年鉴上,该年鉴被刻写在图特摩斯三世的卡尔纳克神庙外墙之上③图特摩斯三世年鉴的原始文献,参见K.Sethe,Urkunden desägyptischen Altertums,Abeiling IV:Urkunden des 18 Dynastie,Leipzig and Berlin,1906,pp.645-67;关于该文献的译文,参见J.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Ⅱ,Chicago,1906,§§406-540;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Ⅱ,Berkeley,Los Angeles & London,1975,pp.29-34;J.A.Wilson in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ed.by J.B.Pritchard,Princeton,1955,pp.234-243.。
年鉴以散文的形式对图特摩斯的第一次战役,也即米格都战役进行了细致的描述[3],同时,它也被卡尔纳克神庙中的另外三个被征服城市列表所证实。当我们把来自于年鉴的行军路线与另外三个地名表相比对后发现,后者不是以军队的行进顺序排列的。加沙——年鉴中提到的位于伽南的第一座城市,没有被列入地名表中。图特摩斯三世接下来经过的两座城市叶姆和阿如纳在地名表中有所记载④叶姆(Yehem)在地名表A和B中的序列号为68,阿如纳(Aruna)在地名表A和C的序列号为27。。但是它们的位置靠后,且出现的顺序与年鉴的记载正好相反。年鉴中的第四座城市米格都,在地名表中是第二座城市①在地名表C中米格都没有出现,但是该地名表的头三个地名没有被保存下来,或许米格都是这三个地名中的一个。。而卡代什,图特摩斯三世并没有到过这座城市,在地名表中却位列第一[4]125。此外,地名表中的其他主要城市,图特摩斯三世都没有到达过,但是在米格都战役中,它们却联合起来与埃及对抗。当我们把塞提一世浮雕中的地名表与业己勘定的塞提一世行军路线相对照后,我们同样能发现这样的结果。拉美西斯三世的浮雕地名表尤为如此,他的地名表包含了巴勒斯坦地区的125座城市,但却没有一个是他真正有过战事的城市②拉美西斯三世曾在以下地区进行过军事行动:阿矛(Amor),参见K.Kitchen,Ramesside Inscriptions,Vol.V(以下简称KRI V),Oxford:Blackwell,1969-1990,p.40:1,扎黑(Zahi),KRI V,30:5and 40:7,图尼普(Tunip),KRI V,78:15,伊莱特(Ereth),KRI V,79:12,和纳哈林(Naharain),KRI V,88:8。拉美西斯三世还曾与几支海上民族作战:派莱塞特(Peleset),KRI V,40:3,杰克(Tjeker),KRI V,40:3,晒克莱什(Sheklesh),KRI V,40:3,登延(Denyen),KRI V,40:3-4,和外晒什(Weshesh),KRI V,40:4。这些地名同样也没有出现在地名表中。。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浮雕中的地名表并不是军队的行军路线图。
第二,这些胜利浮雕并不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而创作的。如果我们把浮雕的三个部分,即铭文、场景描绘和地名表,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考察,我们将不难得出这个结论:铭文是以阿蒙神③阿蒙(Amon),新王国时期埃及的主神,他通常与太阳神拉合二为一,称阿蒙·拉神。的神谕形式来记述事件的,事实上,它没有提及任何战争。相反,它却提到了作为地理名词的亚洲和努比亚,以及亚洲人和游牧民族贝都因人。铭文中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语句是“所有的异邦”。浮雕展示了法老正在打击一群敌人的场景,敌人的身份很模糊,通常他们是亚洲人和努比亚人的混合体,因为亚洲人和努比亚人是埃及人心目中敌人的代名词[5]143-148。
现在,我们考察胜利浮雕三要素中的最后一个要素——地名表。我们发现,地名表与铭文和浮雕本身一样也是对埃及人心目中的所有异邦的展示,只是它们在展示异邦时使用了不同的方式:铭文记述了法老对整个世界的征服,地名表则为法老的这一行动作出了图解。换言之,铭文讲述了法老征服所有的异邦之地,与此同时,浮雕展示了法老正在杀戮所有的异邦俘虏,而地名表则开列出了法老的征服之地。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胜利浮雕并没有记录战争,它展示了法老的丰功伟业,在这里,法老被描绘成世界的征服者。
基于此,沙桑克的胜利浮雕不能用来作为战争确乎发生的证据。他的浮雕没有保存下来军队行军路线图,它也不是为纪念战争的胜利而作。于是,《圣经》就成了我们研究沙桑克战争的主要证据。此外,出土于米格都的沙桑克石碑对战争也有所提及[6]61,Fig.70。然而,该文献除了沙桑克的第四和第五王衔④古代埃及国王有五个王衔,它们是荷鲁斯王衔、两夫人王衔、金荷鲁斯王衔、上下埃及之王王衔和太阳神之子王衔,其中只有后两个王衔加有王名圈。以及一些颂扬国王的词句外,其他部分均因破损严重而无法释读。尽管如此,学者们仍将其作为沙桑克征服米格都的证据[1]141,[2]299,因为他们认为,埃及人将石碑竖立在某一个异邦城市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纪念埃及对该城的征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塞提一世的第二块本特山石碑是为纪念埃及击败阿皮如人⑤过去学者们通常认为阿皮如是一个种族,与希伯莱(Hebrews)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莱德弗德认为阿皮如一词的原始含义是“灰尘的制造者”,即那些策马飞奔的人。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550年/1500年—前1200年)他们居于巴勒斯坦社会的边缘,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他们居住在巴勒斯坦各城邦的农村,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参见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195。在《以色列历史》中,布瑞特认为阿皮如一词并不是指一个种族,而是指一种社会阶层。任何种族都可能有阿皮如这个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没有公民权,没有固定的住所,处于一种半游牧的状态,间或以抢劫为生。偶尔他们也定居在城镇。在动荡的年代,他们常常组成一支临时军队,掠夺他们所需物资。当他们被原来所居之地驱逐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把自己卖到埃及,在埃及的王室工程中充当苦力。由此他断定,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卖身为奴的阿皮如应该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见J.Bright,A History of Israel,Philadelphia:Westminster,1952,pp.82-84.对如哈马城的进攻而作[7]Vol.I,12-13,但是这块石碑却被竖立在本特山。本特山是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它不是阿皮如人的城市。拉美西斯二世的本特山石碑也是如此,这块石碑虽然被竖立在本特山,但却与战争无关[7]Vol.Ⅱ,27-29。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拉美西斯二世从未在本特山有过任何军事行动。由于该城一直被埃及牢牢控制着,因此,埃及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对其述诸武力。
根据米格都石碑,我们无法对埃及和米格都的关系进行准确的勘定。类似的石碑在其他城市也有所发现,而埃及对这些城市却有着不同程度的控制。例如,作为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在整个新王国时期,埃及在本特山都有着完全的统治权,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能够证明这一点,而埃及与卡代什的关系则有着另一番景象[7]Vol.Ⅱ,2-26。根据这座城市出土的塞提一世石碑记载,这位十九王朝的埃及法老曾征伐过该城。这座城市在被埃及征服后成为埃及的一个属国,但却不是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中心。这表明,埃及并没有像对本特山那样,对卡代什实行过直接有效的控制。与卡代什的情形相同,提尔也是埃及的属国,塞提一世在这座城市同样也竖立过一块石碑。然而,与卡代什不同的是,提尔从未被埃及进攻过,长期以来,该城一直与埃及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根据上述事实,我们认为,沙桑克的米格都石碑反映了居于米格都的以色列人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埃及对他们的统治,但是它却无法证明埃及对该城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在讨论了来自于埃及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后,我们发现,《圣经》是关于沙桑克战争的最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即使是《圣经》,也没有为我们提供太多的关于此次战争的记述。《列王纪上》第14章第25—28节只是提到在罗波安统治的第5年,沙桑克进攻耶路撒冷,并从王宫和神庙中掠夺了大量的珍宝。然而战争并不是这段话的中心议题,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所罗门的金盾牌没在神庙中。此外,《历代志下》第12章第1—12节讲述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对沙桑克战争的反映。
除了上述两章节外,《圣经》的其他段落也提到了有关沙桑克的信息。耶罗波安为了逃避所罗门以叛国罪对他的追杀,而躲藏在沙桑克的宫廷之中。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统治时期的高官,他曾谋划了反对所罗门的政变,结果被所罗门发现后处以死刑。为此,他逃到了埃及,并向当时的埃及法老沙桑克寻求政治保护。所罗门死后,他返回以色列,并在示剑参加了反对罗波安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国南北分裂,他成为北部以色列国国王,罗波安偏安于南部,成为犹太国国王。
根据埃及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圣经》的记载,关于沙桑克战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二十一王朝时期的埃及对外政策十分复杂,一方面,埃及法老与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的统一强大的以色列签订了同盟条约,《列王纪上》多次提到所罗门曾迎娶了埃及公主。与此同时,埃及却窝藏了来自以色列的政治逃亡者。比如以东家族的哈达德,他返回巴勒斯坦后,在大卫王之死上有所行动,并因此挑起了战争。据《圣经》记载,基色曾被埃及征服,后来在埃及公主嫁给所罗门王后,该城重归以色列。很有可能,埃及的对外政策具有两面性。当埃及国力衰弱的时候,埃及无法公开与以色列抗衡,因此它就通过政治联盟来确保两国的友好关系。然而对于埃及法老来说,军事力量强大的以色列始终是埃及东北部边境安全的最大隐患,为此,他们便在幕后不断地支持以色列的反对力量,以此达到消弱以色列国力的目的。
从第二十一王朝到第二十二王朝,埃及的对外政策始终如此,这就是沙桑克窝藏大卫王的主要对手之一耶罗波安的原因。但是伴随着所罗门王之死,沙桑克似乎看到了灭亡以色列的机会。当耶罗波安从埃及返回以色列,并参与了反对所罗门王的继任者罗波安的战事之时,他很有可能得到了沙桑克的支持。可以说,埃及的幕后操纵是以色列分裂的原因之一。
据《圣经》记载,以色列分裂后,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太之间冲突不断,埃及法老沙桑克也趁势参与其中,并支持他的盟友耶罗波安,反对犹太。为此,沙桑克进攻犹太首都耶路撒冷,并从这座城市的宫殿和神庙中掠获了大量物品。《列王纪上》第12章第21—24节记述耶罗波安曾计划重新统一以色列,但却在预言家示玛雅的建议下改变了这一想法。而事实上,正是沙桑克劝说他放弃了攻打犹太的想法。沙桑克返回埃及后,犹太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与耶罗波安抗衡了。
埃及在制定了对外政策后,便开始把其付诸行动。公元前10世纪早期,埃及的实力并不足以与以色列抗衡。于是,埃及便利用一切机会,从其内部削弱以色列。以色列和犹太的最终分立为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创造了很好的生存空间。在此之前,强大的以色列给埃及东北部边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此,他们不得不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色列分裂后,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埃及所惧怕的强大统一的以色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彼此纷争不断的小国。而且,其中的一些小国还不时地向埃及寻求保护。以色列分裂前,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地位十分被动,始终处于防御状态。通过支持耶罗波安的反叛,埃及变被动为主动,一跃而成进攻态势。
通过对近年来关于公元前10世纪的巴勒斯坦考古地层年代的勘定以及它与沙桑克巴勒斯坦战争的关系的阐述,沙桑克战争的影响并不广泛。相反,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本身也没有被完全摧毁。这就意味着在勘定公元前10世纪的巴勒斯坦考古地层上,考古学家们需要寻找其他依据。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对从前被勘定为沙桑克所毁坏的地层进行重新研究,进而找出真正的毁坏者。
事实上,这项工作并不困难,因为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早期,在巴勒斯坦曾发生过很多场战争,这些战争不仅发生于以色列和犹太之间,而且也发生于这两个国家和它们的邻国之间。在此期间,以色列的政权因军事政变而几易其手,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毁坏地层或许是以色列内部纷争造成的。不管怎样,在公元前10世纪的巴勒斯坦考古地层的毁坏上,沙桑克战争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1]B Mazar.S Aituv,B A Levine.The Early Biblical Period:Historical Studies[M].Jerusalem,1986;G W Ahlstrom.Pharaoh Shoshenq's Campaign to Palestine[A].A.Lemaire and B.Otzen.History and Traditions of Early Israel:Studies Presented to Eduard Nielsen[M].Lieden,1993.
[2]K A Kitchen.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1100-650B.C.)[M].Warminster,1986.
[3]郭丹彤.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的物品及其学术价值[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60-64.
[4]D B Redford.Pharaonic King-Lists,Annals,and Day-Books[M].Mississauga,1986.
[5]G Belova.The Egyptian Idea of Hostile Encirclement[A].C J Eyre.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gyptologists[M].Leuven,1998.
[6]R S Lamon,G M Shipton.Megiddo I,Seasons of1935-39,StrataⅠ—Ⅴ[M].Oriental Institute Publications,1939,42.
[7]K Kitchen.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Z].Oxford,Vol.I.1993;Vol.Ⅱ.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