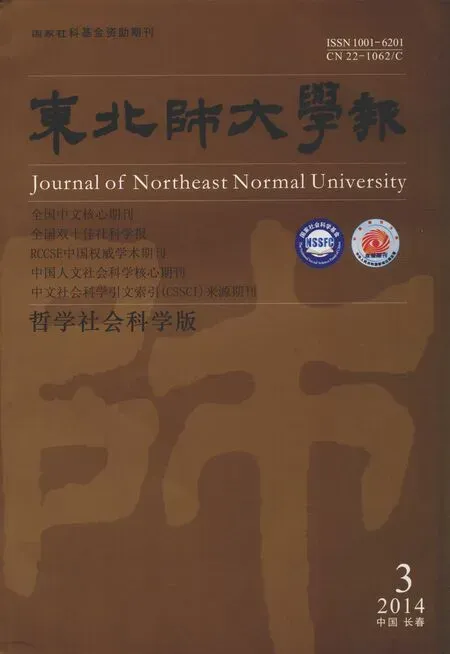古代埃及王权历史表述模式的起源
(吉林大学 文学院世界史系,吉林 长春130012)
古代埃及的君主集权政治是古代世界神权政治的典型代表。神权介入社会管理体制并渗入民众的思想观念的每一个角落,使王权体制成为一种“天盖”式的专制体制。伴随着国家的形成、统一和国家管理机构的强化,作为社会运转轴心的王权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固的“历史”表述模式。尤其在各种可视的历史证据中,以军事强权为支柱并辅之以宗教权威的王权符号体系的表述模式日益明显。这种关于王权的历史表述模式,不论是可视的实体符号还是王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文献叙事,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王权表述的很多要素在早王朝以至于早王朝之前的历史时期已经出现,其中包括王权历史表述的思想根基、基本形式和主体内容,它们分别是:王权的象征符号体系、可视的文字艺术以及编年形式的历史记录等。
在对古代埃及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文献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现代的严格意义上进行历史观念性质的界定和历史文献种类的区分,这样必定导致这一领域相关研究的局限。对于王权的历史信息基本的表述模式研究,国外学者在历史学、考古学、图像学、文字学,以及艺术学等领域的最近科研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对其起源进行推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考古队近年来在阿贝多斯王室墓群的重新考察和挖掘给我们提供很多这一领域的新证据。这些新的考古证据也印证了T·A·H·威尔金森在近期出版的《早王朝时期的埃及》一书中的一个基本结论:导致埃及国家形成的各种趋势在前王朝早期就已经出现了[1]37。
一、王权象征符号的起源
古代埃及关于王权观念的历史表达方式是以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为基础的。其中既包括王冠、服饰、连枷、权杖、王衔、王名框(serekh)和王名圈等可视符号,也包括内政外交、文治武功、神圣品质、宗教庆典和丧葬仪式等具体历史信息的表述[1]156-197。随着历史的沉积,这种象征性的符号体系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可视图案和模式化的叙述方式。古代埃及王权形成过程漫长而复杂,我们对文字产生之前的早期王权的历史考察中很难在纯粹的原始艺术符号与王权信息之间划一道清晰的界限。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艺术作品中融入王权与社会的信息已经不可避免。
到了涅伽达文化Ⅰ末期和涅伽达文化Ⅱ初期,原始的艺术形式里增添了最初的“王权”信息。在阿贝多斯U墓区239号墓出土的一个白十字线陶罐上,描绘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古埃及军事胜利的场景。这种胜利的场景不是通过暴力的战争场面而是采用打击战俘的情景来表示。头戴羽毛状冠饰、身后佩戴一条假尾而且身形高大的胜利者“控制”着形象较小、双手被缚在身后的被俘者。在不同的几组画面中,有的胜利者手握权杖,意味着对战俘的打击[2]75。描绘类似场景的陶器还有布鲁塞尔E3002、伦敦UC15339等几件陶器。这些陶器上描绘的场景极有可能是国王“打击仇敌”这一主题最早的例证。这种用权杖打击战俘的形象是整个埃及历史时期国王军事胜利的重要象征①这种“打击仇敌”的胜利象征,贯穿整个埃及的历史。登王象牙标签、斯尼夫鲁浮雕、图特摩斯三世的卡尔纳克神庙的塔门浮雕,以至于到希腊化时代托勒密七世的菲勒岛伊西斯神庙的第一塔门上的浮雕中都有类似形象。。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偏菱形的、动物型的和盾牌型的调色板,其中一块偏菱形的调色板(斯德哥尔摩EM 6000)上带有捕猎河马为内容的图案刻痕。国王捕猎河马在以后的历史时期通常被认为国王体质和个人能力的表现,也象征着秩序对混乱的胜利。还有的调色板上刻有两头相对而立、嘴部对接的羚羊形象,双头羚羊形象后来也成为王权标志的一部分。
另外,涅伽达文化Ⅰ末期和涅伽达文化Ⅱ初期1610号墓出土的黑顶陶上刻有最早的红冠图案。同样属于涅伽达文化Ⅰ末期的1443号墓还出土了迄今最早的圆盘型权标头。作为王权重要标志的荷鲁斯形象也出现在1546号墓出土的陶罐碎片上。总体来讲,这个时期关于王权的信息是微弱的,我们很难在这些相对孤立的证据中确定它们和早期强权人物的具体联系。但是头饰、王冠、假尾、权杖、鹰隼、打击战俘、猎取河马等后来王权的重要象征符号和场景在涅伽达文化Ⅰ末期和涅伽达文化Ⅱ初期已经初露端倪。
涅伽达Ⅱ时期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革。这一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以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传播和商业竞争使得埃及形成了一种近乎于“全国性”的文化融合,这是促使某些社会精英人物意图政治统一的潜在因素。社会管理和生产领域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涅伽达出现了使用高温窑生产陶瓷器皿的技术,导致了贸易市场的垄断,继而彰显了这一地区经济和政治地位。这样,这一地区的陶瓷器、调色板和权标头等器物上的图刻便具有了某种权利象征的含义,和此前一些纯粹的艺术象征截然不同了[3]。
商品生产的地区优势和特色促进了各地之间频繁的贸易接触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船只作为沟通南北的动态标志正好适应了这一整体氛围。从船只的实用性来讲,它是能够运载满足特权人物需求的来自北方和东方的铜、石材、黄金、象牙等重要原料的主要交通工具。这样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下,船只有发展成为统治标志的可能。这一时期涅伽达文化陶罐上的绘图最常见的就是镰刀形的大船。希拉康波里100号装饰墓中壁画的主体背景也是六艘船只,画面中还有众多狩猎和战争场景。画面中的打猎的场面已经不是简单地对生活场景的刻画,其中描绘的陷阱捕猎、大人物力分双狮等捕猎场面可能包含着诸多贵族特权的信息,包括先进武器的展示、更多食物种类的获取以及酋长间交流、协作的可能性的展示[2]77。描绘船只贸易、渔猎与征战的画面还出现在大约属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在戈伯伦出土的一块破损的纺织物上。
从涅伽达文化Ⅱ初期开始的政治权利的集中情况迅速而复杂。“王权”虽然已经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王权的具体信息和性质依然显得模糊,而且我们很难考量这一时期神话传说、宗教仪式和王权观念相互结合的具体过程。不过,埃及人此时已经开始编织出一套与众不同的意识形态将领导权和权威注入到各种复杂的象征和仪式当中去,这些意识形态成为强化王权权威、加速国家出现并推动政权统一的有利因素。
到涅伽达文化Ⅲ时期,关于王权的信息已经十分明朗,各个邦国之间的联盟和争霸乃至于政治上的统一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阿贝多斯U-j墓(约涅伽达文化ⅢA2时期)现已被确定为蝎王I的王墓[2]134。能够证明蝎王I存在的证据还有在格贝尔·塔乌提(Gebel Tjauty)发现的岩画。岩画右侧有蝎子和鹰隼的形象,左侧有一个大人物用绳索牵着一个双手被绑在身后的战俘。在战俘前面不远,刻画着类似于一只水鸟正在啄食一条蛇的图案,与之类似的图案在布鲁克林刀柄以及库斯图尔L墓区23号墓中的绘画陶器等文物上也出现过,这种图案可以代表一个地区或者诺姆的标志,抑或是一种胜利的象征性表达。据此基本可以推断这是蝎王I对邻近地区其他地方首领的一次军事胜利。
到了前王朝末期,在众多的调色板、权标头和刀柄的浮雕上,王权形象的象征性表达方式逐渐成熟起来①刻画较为精细的调色板包括:仪式调色板、猎狮调色板、利比亚调色板、战场调色板、公牛击敌调色板以及那尔迈调色板等。其中,战场调色板和那尔迈调色板表现政治和历史的题材。战场调色板定位于早王朝末期,约公元前3150年,其上浮雕的象征性元素明显较以前的历史时期强化:象征着王室权力的狮子扑倒并撕咬敌人,而形象大小、姿态不一的鹰隼正在帮助狮子啄击敌人。浮雕上方的鹰隼形象颇有新意,通过加上臂膀的方式拟人化,押走被捆绑的战俘。。尤其是保存完整、雕刻精细的那尔迈调色板,透露出一种王室规格的艺术标准。这块高63厘米的盾形调色板原本发现在希拉康波里一个早期神庙中。调色板中对那尔迈形象的刻绘已经展示了在后来历史时期里出现的埃及君王的主要的象征性标志,包括王名框、红冠、白冠、连枷、短裙、兽尾和带有母牛头图案的流苏等服饰,还有国王打击仇敌、国王化身为公牛攻击敌人城磊、荷鲁斯抓住敌酋,以及后来文献中所称“荷鲁斯的追随者”的最初图例[4]。另外,画面上人物的大小比例十分明确,尤其是正面上部一栏那尔迈巡视被斩首的敌人的画面中,那尔迈形象最为高大,和代表“荷鲁斯追随者”的旗帜一样高,其次是那尔迈身前和身后的两位侍者或者官员,大约是那尔迈身高的一半,再次是走在巡视队伍前面的四个掌旗者。这种用人物大小比例来表达社会等级划分的方式在后来的王室艺术中成为一种基本的规范。
那尔迈调色板形成了以后埃及艺术的一种标准范式,但是埃及王权的象征符号体系和历史表述模式的发展还远远没有结束。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历史问题的出现,用更为精细的神话传说、宗教仪式和铭文雕刻包裹起来的王权已成为必然。
二、可视文字艺术的起源
阿贝多斯U-j墓当中出土了象牙或者骨质的标签170余件,标签的一般大小是1.5厘米长,1.25厘米宽。这些标签上的符号,通常被认为是埃及象形文字起源的最早证据。在墓中还发现刻有蝎子符号的陶罐,在近年来对“0王朝”甚至“00王朝”国王世系的构建中,U-j墓的墓主通常被认定为蝎王Ⅰ②根据F·拉斐尔的研究,00王朝的“原国家”政权应该定位在涅伽达文化ⅡC-ⅢA2时期(大约公元前3500—3220),相关世系情况可参阅:http://xoomer.virgilio.it/francescoraf/hesyra/dynasty00.htm。。这种早王朝之前国王世系的构建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其重要原因在于直接文字证据的缺乏以及画面表意方式的原始。比如格贝尔·塔乌提岩画右侧的蝎子和鹰隼符号,因为其位置关系,我们很难确定这些符号指代的就是在画面最左侧的“王”。而在前王朝末期蝎王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等文物之上,标记在国王的面前蝎子符号和代表那尔迈的文字符号明确地表示了蝎王(通常被认定为蝎王Ⅱ)和那尔迈的身份。
在体系化的文字产生之前,文字符号在器物上的应用还非常稀少和初级。U-j墓当中出土的标签上的文字,内容涉及数字、物品名称,也可能还有地名和王室地产的名称。这些标签上的文字符号的一个巨大意义在于:它们极有可能已经具有表音功能,而不是简单的“画成其物”的象形符号[5]262。
到了前王朝末期,文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涉及那尔迈的文物上的文字信息比较丰富,尤其是那尔迈调色板。在更早的调色板中,文字符号的运用并不多见。在利比亚调色板上所雕刻的城防工事中刻有一个象形文字符号,在这块调色板的另一面,有一个被伽丁内尔释为“利比亚”的象形文字符号。而在那尔迈调色板上,不但有类似于利比亚调色板上刻写在防御工事里面的符号,而且更多的文字符号充斥在画面中间,这些符号主要是用来标记人物的姓名抑或身份等信息。代表那尔迈名字的形象文字字符在正反两面共出现三次,另外作为画面突出表现的那尔迈头戴白冠用权杖打击跪在地上的被俘敌酋的画面中,敌酋的头部后面有两个象形文字符号“鱼叉”和“湖”,读作“瓦什”,通常被认为是敌酋的名字。在他的头顶还刻有一组图画(也有观点认为是文字),即荷鲁斯抓住一个抽象化的俘虏形象(以头部和一个接在脖颈处的长方形表示),俘虏的背部长着呈扇形均匀散开的六根纸草,其基本意思是“荷鲁斯打败了沼泽之国的敌人”,也有学者认为六根纸草代表着被俘敌人的数目为6 000。在调色板正面上部一栏,那尔迈身后的执鞋侍者前面有一个花瓣型的符号和一个读作“海姆”的符号,“海姆”即“仆从”之意。那尔迈身前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引路人,他面前的文字符号发音为“查特”,这个词可能是维西尔的早期写法[5]199。在被割去首级的敌人上面,有四个符号抑或是画面,包括一扇门、一只鹰、一只拿着鱼叉的鹰还有一条首位都很高的船,其中含义至今没有定论。
文字的运用和有秩序感的画面安排使那尔迈调色板的叙事性明显增强。这块调色板上正反两面共五个画面,其中有四幅是表现历史事件的,所叙述的历史场景可以总结如下:头戴白冠的那尔迈俘获并准备杀戮可能名为“瓦什”的敌人首领;那尔迈头戴红冠在两名重要官员陪同下视察被斩首的敌人;那尔迈化身为公牛攻击另外一个敌人并摧毁其要塞和城市[6]。
早期文字的运用似乎还比较随意,其写法完全以整幅画面的内容和空间需求而安排。比如从各种文物来看,那尔迈名字存在多种写法[7]115。在那尔迈的圆柱形印章(阿什摩林博物馆E3915)上,代表那尔迈名字的一个符号,一条鲇鱼,居然长出了两只手臂握住武器打击利比亚人,名字上方还有展开双翼的鹰隼保护着。在一枚那尔迈标签上(阿贝多斯B16,2),作为那尔迈名字组成部分的鲶鱼符号也是长出两只手臂,而且仿效那尔迈调色板上的场景,一只手握住权杖举过头顶做打击姿态,另一只手抓住敌人的头发。这是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创作,这里面也透露着文字的某种神秘力量,尤其文字符号用在表达人名的时候。
那尔迈调色板以及那尔迈权标头等文物印证了早王朝末期文字体系进一步发展的进程。可能与文字的产生、运用以及书写材料变化相关的一种情况是:在那尔迈之后,涅伽达文化时期作为王室纪念物的调色板和权标头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种可视的文字本身却就此成为埃及王室艺术的一种主体形式。
就功能而论,和其他文明的早期文字一样,埃及象形文字体系也因为国家机构的形成而完备,并用之于行政管理、财产清查和商业记录。埃及文字系统的发展从开始到完备的阶段大致可以定位到从阿贝多斯U-j墓的蝎王Ⅰ时期到第一王朝登王时期,而第一王朝中期之后,埃及的文字体系也没有停止进一步完善的过程[7]124。在第一王朝时期纸草已经产生,商业和管理的文书写在价格低廉的纸草上更是一种趋势。但是由于王权的逐渐强化以及与王权相关主题展示的需求,可视的文字艺术一直是王室艺术的最基本形式。文字被用在各种纪念物上,尤其是各种具有纪念性质的建筑上,神庙、陵墓的墙壁和屋顶都存有大量的浮雕和壁画,这些浮雕和壁画常常配以象形文字使画面更加丰富。其中的文字不只是用来填补空白,文字和壁画上的形象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它们都具有自然力量。塔门、方尖碑等建筑物也是如此,尤其方尖碑上,上面都是埃及象形文字的阴刻图案。文字本身具有一种自然力量,具有神圣的属性,具有传统权威,具有王室意味,具有展示功能,这是其他的文字体系所不能比拟的。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我们通常所说的象形文字,即大约在第一王朝逐渐完备的“圣书体”文字,一直使用到希腊、罗马统治时代。
三、编年记录的起源
早王朝时期,文字的运用已经较前王朝时期大为进步,在王室和私人的墓碑上、墓中出土的标签上以及陶瓷器皿上,都附有一定的文字信息。其中,墓中出土的标签包含的王权的历史信息含量最多。前王朝早期作为随葬品的标签在早王朝时期发展成一种形制更大的标签。整体来讲,这些骨质、象牙或者木头标签一般为长方形,长度不超过9.45厘米,厚度在3-5毫米左右。这些标签上面记录的内容已经不是简单的随葬物品情况,而是一些重要的事件。这些标签当中,有一种年签最为重要。年签只记载某一年份的军政和宗教等要事,而且国王的名字要刻在其中。从国王杰特开始,才出现带有象形文字“年”(rnpt)符号的年签,以引导出具体的事件或者说能够为这一年份命名的重大事件。这种年签上有时也会陈列一些物品的清单,注明其出处、质量和数量等信息。还有些标签记述重要的庆祝活动,尤其是宗教节日和建造房屋,通常王名也要刻入其中。除了上述两种标签之外,还有一种标记一些中下层官吏的随葬品情况的私人标签。这些标签的解释难度很大,学者们对它们的用途、内容等问题争议很多。尤其是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上面所述事件和政府的行政职能有关,有人则侧重在政府的经济管理,而新的观点则认为以前学者的争论实则缺少对这些年签上所表述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物件之间关系的一种综合解释[8]。
从已经公布的这些标签来看,它们主要集中在第一王朝诸王统治时期。在从那尔迈到卡阿诸王的标签中,文字性质在逐步强化。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开始几位国王的标签中,图画叙事的性质还很明显。涅伽达王室马斯塔巴墓出土的一枚阿哈王的标签上(开罗博物馆CG 14142),在右侧中下部有两组人物画面,上侧中部有船只的刻画。同样,在萨卡拉出土的哲尔王的一枚标签(萨卡拉S3035)上似乎描绘着人殉的场景[9]22。在阿贝多斯还发现与上述标签风格类似的另一枚哲尔王的标签(乌姆埃尔卡伯t.O22),很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早期象形文字的难解。尤其是我们面临着文字符号和场景刻画的双重抽象化,有些符号很难断定是文字还是图画。从杰特开始,标签上的文字性质明显了。虽然在杰特之后的登王檀木年签(大英博物馆32.650)上依然刻有登王在界石间奔跑的场景,但是登王标签上的文字成分占据了主体。整体来讲,此时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完备阶段,词不达意之时,便辅之以绘画,所以这些标签上的文字还十分简古难解①据研究,早王朝时期最长的语句是关于第二王朝国王伯里布森的一段文字:金色的[神]把两地赐予了他的儿子——上下埃及之王伯里布森。参阅:K A Bard.ed.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Routledge,2005,p.966.。另外,标签上的所能容纳的文字信息量有限,书写刻画的空间要经过精心安排。
王权的观念在这些标签上体现出进一步成熟的趋势,很多标签都带有荷鲁斯站在王宫正门形象的“王名框”,荷鲁斯王衔已经根深蒂固,此时还出现另外两种王衔。卡阿王的多枚标签上都刻有“两地之主”(nbty)的王衔符号,即秃鹫和眼镜蛇分别站立在两个表示“主人”的象形字符之上。在出土于阿贝多斯乌姆埃尔卡伯U墓或者Q墓的一枚属于国王赛麦克赫特的一枚年签上,出现了上下埃及之王(nsw-bit)的王衔。在赛麦克赫特和卡阿的诸多标签中,都可以同时找到荷鲁斯、两地之主和上下埃及之王这三个王衔。这种王衔的出现,证明宗教、神话和仪式的进一步结合。在阿贝多斯乌姆埃尔卡伯Q墓区出土的卡阿王的一枚标签上,记录了塞德节庆典,后来帕勒莫石碑上也有许多对宗教庆典的记述,尤其是以塞德节和阿比斯巡跑为多。
最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标签,尤其是年签,和后来的编年记录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年签最右侧都有一个在中下部呈直线至上部以弧线向左方弯曲的象形文字“年”的符号,左侧所刻文字便是此年中发生的事件。这种“历史”记录形式还远远不是后来出现的比较完备的具有一定纪年方法的编年记录。古代埃及人在早王朝之前很漫长的时间里一直未能从事件的经历中分离出时间观念。一直到早王朝诸王的年签里,我们才看到了“事件”和“时间”结合,产生了一种以重大事件标记某一年份的名年方式。但是这种以事名年的记录很明显存在缺陷,当一年中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便没有相关记录,这样造成“历史”记录的中断乃至于年代次序的混乱。不过这一开端,意味着更为完备的编年记录出现的可能。从后来的帕勒莫石碑、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图灵王表和曼涅托的编年史残篇来看,只有这种“年事”结合的记录形式出现后,才有可能出现连续的编年记录。
虽然一直到第五王朝才出现了古埃及第一份完备的“王室编年记”,但是我们无法排除此前一种口耳相传的以记忆形式延续的王室编年史的存在。比如,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出的两枚新的印章,分别属于卡阿和登王时期的文物。此上分别连续性地列举了从那尔迈开始的第一王朝诸王,登王印章所列举的王名截止到登王,卡阿印章截止到卡阿[10]。虽则这种连续性地列举王名的方式意在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以及表达对先王的崇拜,但是这里面透露出的王权观念确实很难估量,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国王年签的积累加上王权连续性观念的逐渐强化,完全可以导致记录方式的变革。文字的经济统计和行政管理功能的实现方式之一便是各类图表的制定,在第三王朝开始的一些马斯塔巴墓上的供品清单都是以表格的形式刻画的②详见J·卡赫尔编订的《早期埃及语词典》(Frühägyptisches Wörterbuch)。。所以到了第五王朝以后出现了以帕勒莫石碑为代表的王室编年记上面的以“年”的象形字符巧妙地运用到表格形式的记录当中,应该是存在早期基础的。
尽管标签当中没有帕勒摩石碑上的关于尼罗河水位的记载,但是标签和后来帕勒莫石碑上的以“年”字的象形文字符号分割成的表格里面的文字安排有很多近似之处。二者在内容方面也有互相印证之处,比如登王的一个象牙标签上面展现了他手持权杖打击跪在地下的亚洲人的形象,右边的文字可以释读为:第一次击败东方人。而其中的信息和后来巴勒莫石碑上所载“打击穴居人”的记载相吻合[9]24。但是整体来讲,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标签和后来编年纪录上的内容之间的相互印证存有很大难度。
古代埃及的王权历史表述模式的成熟而典型的代表是卡尔纳克的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11],其中文字、图像和编年并行。其更为早期的表述形式可以视为以帕勒摩石碑为代表的古王国时期的“王室编年纪”。当然,王权历史表述的内容不应该局限于编年形式的记录,而我们面临的难处在于古代埃及人根本没有“历史”观念,所以几乎所有的文献都附带着王权信息。不过,前王朝末期和早王朝初期是王权历史表述模式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涉及那尔迈的文物既有调色板和权标头,也有标签和印章,这本身就说明那尔迈是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国王。但是王权的历史表述在此之前已经奠定,在此之后继续发展,因为埃及的文化体系能够不断地把新生的事物溶入到以“创世”为基准的传统权威观念当中。这样一种起源甚早又能不断“更新”的王权历史表述系统一直支撑着一种强大、神圣、复杂、私密而又难解的权利体系。
[1]T A H Wilkinson.Early Dynastic Egypt[M].London and New York,2005.
[2]S Hendrickx.Iconography of the 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Periods[A].E Teeter Edited.Before the Pyramids:The Origi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M].Chicago,2011.
[3]金寿福.古代埃及早期统一的国家形成过程[J].世界历史,2010(3):22.
[4]I Shaw,P Nicholson.British Museum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M].London,1996:133.
[5]I·肖.重构古代埃及[M].颜海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6]郭丹彤.那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统一[J].历史研究,2000(5):122-127.
[7]Jochem Kahl.Hieroglyphic Writing During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an Analysis of Systems[J].Archéo-Nil,2001(11).
[8]K E Piquette.Writing,“Art”and Society:A Contextual Archaeology of the Inscribed Labels of the Late Predynastic-Early Dynastic Egypt[EB/OL].http://www.bookfi.org/book/1031984:52-54.
[9]P A Clayton.Chronicle of the Pharaohs:The Reign-by-Reign Record of the Rulers and Dynasties of Ancient Egypt[M].Thames & Hudson,2001.
[10]J Baines.Visual and Written Culture in Ancient Egypt[M].London and New York,2007:127.
[11]郭丹彤.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的物品及其学术价值[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