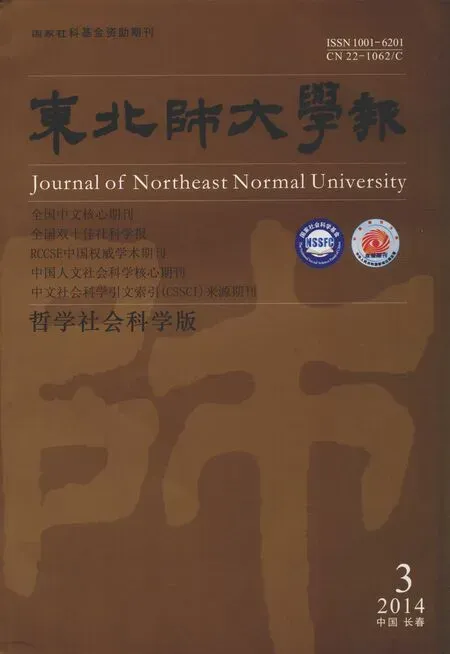象形文字与圣书文字
——兼谈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
王海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象形文字与圣书文字
——兼谈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
王海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象形文字”是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东汉学者许慎将其定义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我国学界对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在术语方面的刻意区分,理解上的含混模糊,以及把圣书文字(hieroglyph)视为象形文字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误将“hieroglyph”译为“象形文字”,从而与我国传统文字学术语“象形文字”相混同而导致的。象形文字只是人类文字的初级阶段,或者只是某文字体系的一种文字类型。因此,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图画文字;圣书文字;古埃及文字
当前国内学界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是由于对古埃及文字缺乏深入了解,而以貌取名、盲目套用中国传统文字学术语“象形”之说而导致的一个错误①参见王海利:《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译名问题》,《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52-57页。后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4期)转载。国内文字学界大多接受了笔者的建议,不再把古埃及文字称作古埃及象形文字,而是改称古埃及圣书文字。例如,陈永生:《甲骨文声符与圣书字音符的对比》,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罗晓静:《圣书字的宗教符号性》,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张晓雯:《甲骨文与古埃及圣书字象形字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田田:《甲骨文形声字形符和圣书字定符的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黄亚平、张晓雯:《圣书字的象形字及其文化意义》,《东方论坛》2010年第2期,第69-72页;陈永生:《汉字与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国内世界古代史学界对该问题持商榷态度,参见李长林:《关于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兼与王海利同志商榷》,《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116—119页;吴宇虹:《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90—98页。。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并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状况,有益于对该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文字的定义与人类最初的文字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什么是文字呢?在文字定义问题上,大体而言分广义和狭义两派。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称之为文字[1]。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只有用来系统记录语言的符号才是文字。我们通常使用的文字概念是狭义的文字概念。
关于文字的起源问题,不但是近代以来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古代所有有文字的民族共同关心的问题,几乎所有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都曾经试图对其文字的起源作出解释。18世纪以前并没有科学的文字起源论,因此所有关于文字起源的说法都不外是反映在民族神话中的文字神赐论和圣人造字论[2]。18世纪英国学者威廉·瓦尔博顿(William Warburton)通过研究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文字、古埃及文字、中国汉字,提出了文字是由“叙事图画”演变而来的理论②参见William Warburton,Divine Legation of Moses,London,1738.。由图画而文字的进化论就这样产生了。20世纪美国学者盖尔布(I.J.Gelb)在《文字研究》一书中也指出,文字“由模仿真实物体的形状而来。所有文字的基础都是图画(picture)。这不仅体现于所有现代原始文字在形体上是象形(pictorial)的,而且因为所有古代东方文字体系,如苏美尔、埃及、赫梯、中国等都起源于真正的图画文字(picture writing)”[3]。盖尔布的《文字研究》是文字学研究中的力作,影响巨大,几乎所有后来者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即文字起源于图画①最近几十年来,盖尔布的学说愈来愈受到挑战。美国学者Denise Schmandt-Besserat在Before Writing(2vols.,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92)书中提出新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陶筹(即呈各种几何形状,或者各种动物、器具等形状的小型的陶制物)演变而来。虽然她的观点一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但是后来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她认为楔形文字由陶筹演变而来,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字都是直接由陶筹演变而来的。因此,该学说并不是解开所有有关文字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仅就楔形文字而言,仍有诸多问题不能解决,如陶筹于何时何地首先演变为文字等问题,并没有因陶筹论的提出而得到解决。参见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60—66页。。
我国文字学者陈梦家认为“文字既不起于八卦结绳,而是起源于图画。”[4]18既然文字起源于图画,人类的初文是图画文字。那么,图画与文字是一回事吗?就二者的关系问题,陈梦家曾总结出5点区别[4]21-22:1.图画是物体的写象,它的目的在拟像,比较的求作成物体的正确的写照。文字也是物体的写象,它的目的在传意,所以只要达到“视而可识,察而可见意”的地步,不必个个字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2.图画是客观的、具体的、写实的,文字可以是主观的、抽象的、写意的;3.图画的篇幅是不受限制的,文字却有约束成以表现一事一物为单位的趋向;4.图画经约束成以表现一事一物的单位,它由个体变为共相了;5.文字不必太具体太像,它可以加以人意。文字与语言皆是社会性的,它一被社会所公认,约定俗成,个人只有服从它而应用它。因此陈梦家认为:“文字与图画是同源的,但文字不就是图画。……文字与图画同源而不是一件事。”[4]19,20高明也有过类似的阐释,他说“我们说文字起源于原始图画,但是,图画并不等于文字。”[5]
我国文字学界还曾经提出过“文字画”这一术语。该术语最早由沈兼士提出。他认为“在文明没有发明以前,用一种粗笨的图画来表示事物的状态、行动,并数量的观念,就叫做文字画。”[6]“文字之形式,直接与绘画成为一个系统,证之于埃及文字画,巴比伦亚叙利亚楔形文字,中国古代钟鼎款识中留存之图案化的文字画,及六书中之象形文字,莫不皆然。”[7]当然,沈兼士将埃及古文字称为文字画是错误的。周有光指出“文字画是超语言的,可以用任何语言去解说,但是事先要有默契,否则难于理解。”[8]他认为“原始的‘文字画’,严格说还不能算是文字,只是已经能够综合运用表形和表意两种表达方法。”[9]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看,文字画是具有文字性质的图画,而不是图画文字。反过来,将图画文字认为是文字画也是错误的。唐兰指出:“学者间更大的错误,是把图画文字说成文字画。我们说图画文字,是用图画方式写出来的文字,如照沈兼士先生等的说法,叫做文字画,还不能算是文字,两者间的区别是很大的。”[7]71
国外学界也曾提出过几个与“文字画”相关的概念,如“思想文字”(Gedankenschrift)、“表现文字”(Vorstellungsschrift)“内容文字”(Inhaltsschrift)[10][11]等,它们都属于描述性(或表现性)的、旨在助记和识别的“文字”[3]50。特里格尔(Bruce G.Trigger)主张将这类文字称为“会意文字”(semasiography),其基本特征是这类文字常常由多个符号组成,用来表达一定的观念、思想和内容。但是,这类文字中的一个符号可以包含多个意义,符号本身也没有固定的读法。因此严格意义上讲,“会意文字”(semasiography)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而只是“前文字阶段”②“前文字阶段”也是西方文字学者的一个共识。德文中将这个阶段称为“Vorstufe der Schrift”;英文中将这个阶段称为“forerunners of writing”。的产物,但是它们对真正意义上文字的产生却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很可能由此进化而来。不过,国内外学界目前尚不能精确地描绘这个进化过程。因为目前所知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如古代埃及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以及中国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资料”[1]2。
二、国人对象形文字的界定
象形文字是我国传统文字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首次对“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给出了定义并给出了例证。他对象形是这样定义的,“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也就是说,随着事物的轮廓,用弯曲的线条,画出物体的形状,创造出的文字就是象形文字。唐兰指出:“真正的初文,应当是象形文字”[7]69。陈梦家也指出:“文字取象于天、地、人、物、鸟兽、树木,所以文字乃是天地万物个别的图画;万物各异其类其形,所以造字必得‘依类象形’。万物各别的图象,就是象形文字。”[4]18唐兰解释说:“凡是象形文字:(一)一定是独体字;(二)一定是名字;(三)一定在本名意外,不含别的意义。例如,古‘人’字象侧面的人形,一望而知它所代表的就是语言里的‘人’,所以是象形字。”[7]66显然,古人造字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依物画形,以形表意,从而首先创造出一批象形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象形文字就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图画文字,它是人类文字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
象形文字就是图画文字吗?国内学界对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主张二者不同者
如东巴文学者傅懋勣指出:东巴文中包含着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两种类型,并提出了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别。他说:“过去所称的象形文字,实际上包含两种文字,其中一种类似于连环画的文字,我认为应该称为图画文字,绝大多数东巴文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是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绝大多数字形结构来源于象形表意的成分,应当仍称为象形文字。”[12]其实,傅懋勣所称的“连环画文字”并不是“图画文字”,而是上文中提及的“文字画”。相反,他所称的“象形文字”其实是“图画文字”。他之所以将象形文字与图画文字刻意相区分,很可能是因为把并不是文字的文字画误认为成了文字早期阶段的图画文字。汪宁生指出:“真正的文字从表音开始,具体说来即表音的象形文字才算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以前出现的任何符号或者图形,都只能算原始记事的范畴。”[13][14]认为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两个术语不同者国内学者还有聂鸿音。他指出“说到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分,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一个标准就是‘符号化’的程度。也就是说,一套字符如果对所表现的客观事物形象描绘得十分具体,很少甚至没有出现相对抽象的符号,那么人们就倾向于说它是一种‘符号化’程度很低的图画文字;反之,一套字符如果对所表现的客观事物形象描绘得十分抽象,并且使用了大量的非描绘性符号来表现语言中‘无形可像’的成分,那么人们就倾向于说它是一种‘符号化’程度很高的象形文字。”[15]58
显然,聂鸿音认为字符的抽象程度可作为区分象形文字和图画文字的标准,即字符抽象化程度低者是图画文字,抽象化程度高者是象形文字。抽象到多大程度才算象形文字呢?我们不妨来看许慎对“象形”的定义:“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既然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显然“对所表现的客观事物形象,描绘得十分具体”(引自聂鸿音语)。按照聂鸿音所说的,这样的字应该是图画文字,而不是象形文字了?显然这与许慎对象形的定义相违背。唐兰阐述说:“象形文字,即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惯用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例如,画出一只虎的形象,就是‘虎’字。”因此,他认为“凡是象形文字,名和实一定符合。”[7]66不过,比较文字学的研究表明,象形文字“并不是不折不扣的画成其物,而是对某一具体物象进行的一种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的高度概括。”[2]280因为这种概括受地域特点、自然环境、文化传统、民族认知、心理因素等影响。显然,聂鸿音也意识到了自己论述中存在的问题。他解释说:“应该承认,这个区分标准虽然本身没有错误,但毕竟显得过于理想化了,若把它用于课堂教学自然无可非议,但若用于具体的文字研究实践,则难免遇到重重困难。”[15]58因此他最终这样坦言:“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两个术语,一直没有赋予它们最为理想的定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似无必要在几个术语的译法上咬文嚼字,把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等同起来也未尝不可。”[16]57-58
(二)主张二者相同者
如罗邦柱主编的《古汉语知识辞典》中认为“在文字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具有浓厚图画色彩的文字。早期的象形文字都属于图画文字,每个字都酷肖物体的自然形状,有的完全像实物之形。”[16]
20世纪以来,陆续有中国学者使用“六书”理论阐释分析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字。最早的比较研究是在中国古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二者之间进行的。1941年,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前中山大学教授黎东方,为法国埃及学家摩赖(Alexandre Moret)《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①参见[法]摩赖:《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刘麟生译,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年(1941年)。一书写了中文版序言。他在序言中将古埃及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作了比较。1942年,黄尊生开始尝试将埃及文字与中国“六书”进行比较,他在阐述古埃及文字演变过程及其结构特点的基础之上,比较了古埃及文字的组织原理与中国的“六书”说。他指出“依文字进化之公例,最初文字大都起于象形,古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初见者均为象形文,其绘物成文起于一种表意之需要,此两民族相距万里,然其表意方法则不约而同。”①参见黄尊生:《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2年第2期。50年代以降,周有光从比较文字学的角度,对古埃及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字、玛雅文字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六书”不仅能说明汉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同样能说明其他类型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即“六书”具有普遍适用性②参见周有光:《圣书字和汉字的“六书”比较——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例证之一》,《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1期,第82—85页;《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153—167页;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第166—186页。。近年来学者们又将“六书”理论应用到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的分析。这些比较分析和研究都表明,人类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在诸多人类早期文字体系中,象形文字都占有相当的数量,“象形不但是汉字的主要类型,也是原始楔文和古埃及文字的主要类型。”[3]280
由此看来,正如黄亚平所指出的那样,“象形字的问题是一个看似简单明了,而实则复杂多变、内涵丰富的基本问题。”[17]邓章应也指出,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两个术语“都是从文字的符号外观角度命名,过去在指称外延上有重叠之处,内涵也有混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即使是在理论上将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分得很清楚,在实践上仍然存在很多困难。”[18]
三、古埃及文字被误认为象形文字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统治埃及之后,发现古埃及文字多半出现在神庙中,刻写在石头上,因此给它取了一个希腊语名字“ερογλφος”③该词最早见于公元前1世纪狄奥多罗斯的著作。参见Diodoros Sikeliotes,Bibliotheke Historike,3.4.1。(为了行文的方便,不妨将之音译为“海若格里弗”)。“海若格里弗”本身是一个合成词,“ερς”意为“神圣的”;“γλφω”意为“雕刻、刻写”,故二者合起来意为“神圣的书写”。英文中使用的“hieroglyph”,德文中使用的“Hieroglyphe”,法文中使用的“hiéroglyphe”,皆由该古希腊文直译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对该词并没有直译为“圣书文字”,而将该词译为“象形文字”,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④国人最早将古埃及文字称为“象形文字”的极可能是黄遵宪。他在光绪二十五年(1879年)写的一首诗中吟诵道:“上烛光芒曜日星,东西并峙两天擎。象形文字鸿荒祖,石鼓文同石柱铭。”他作注解释说:“埃及国石柱为(中国)周以前物,字多象形。”据此,他所称的象形文字当为古埃及文字。但黄遵宪虽到过海外,但估计他并未接触过“hieroglyphic”一词,因此还不能说他是把该词译为“象形文字”的始作俑者。他只是把汉语中已有的“象形”与“文字”组成一个新词。在中国,推想大概从此以后,象形文字就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用以称呼古埃及的文字。参见李长林:《关于古埃及文字的中文名称问题——兼与王海利同志商榷》,《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第118页。。鉴于笔者对该译名错误的原因已进行过详细的论述,故不再赘言。在此,笔者从两个方面再做一些补充说明。
将古埃及文字视为“象形文字”的错误并非我们国人所独犯,西方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几乎很少有人考虑过解读这些外形很熟悉的古埃及文字的可能性。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受到偏见的束缚,即“认为埃及文字不跟其他任何一种文字一样,文字中无疑地隐含着空谈哲理的祭司们的神秘智慧,而只有洞悉妖术魔法之奥秘的人才能理解这些文字。”[19]35公元5世纪的一个名叫荷拉波隆(Horapollo)的埃及人,使用希腊文撰写了一部关于“海若格里弗”的书。应该说他是具备一定的古埃及文字知识的,对一些古埃及文字的意思多少有些了解,但是他的解释却是纯粹寓言和象征式的,即把每个古埃及文字符号都分析成一个寓言或象征。如将“兔子”(古埃及文字“打开”一词)解释为,因为兔子的眼睛总是睁开的,即使睡觉时也是睁着的,故古埃及人用“兔子”表示“打开”这个动词;古埃及人用“秃鹫”(古埃及文字“母亲”一词)表示“母亲”这个词,因为秃鹫这种动物全都是雌性的,没有雄性的⑤参见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translated by George Boas,Princeton,1993.。我们今天看来,荷拉波隆的解释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但是他对古埃及文字的解释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以后1 400多年里人们解读古埃及文字的圭臬,几乎无人敢越雷池半步。17、18世纪的人们仍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对布满在纪念碑上的那些神秘文字同样感到惊讶,也未曾想到设法解读这些文字,并理解其内容[19]16。因此,千多年来古埃及文字之所以无法被成功破译,是因为学者们走入了“象形”的误区。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Champollion)在释读古埃及文字的早期,仍然受到古埃及文字含有象征性的这种概念的束缚。他将英国学者托马斯·杨(Thomas Young)那个时代就已经知道的托勒密(Ptolemy)名字中的狮子符号,当作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战争(希腊语Ptolemos)的象征[19]40。后来,商博良逐渐认识到古埃及文字所采用的并不是神秘的象征符号,而是一些语音符号。因此,商博良之所以能把古埃及文字成功破译,是因为他抛开了“象形”的误区,发现了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是拼音。
2011年,国际著名埃及学家申克尔(Wolfgang Schenkel)教授发表了文章《古埃及文字在多大程度上象形》。他指出,认为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量的古埃及文献被转写成“海若格里弗”导致的。事实上,古埃及保存下来的“海若格里弗”文献在数量并不占优势。相反,数量更多的是祭司体、世俗体文献。不过,现代学者为了研究的方便,往往将祭司体、世俗体文献转写成规范的“海若格里弗”。如此一来导致人们感觉大量古埃及文献都具有图画丰富、形象逼真的特点,即“象形文字”的特点。申克尔还指出,随着一些电脑软件(如JSesh,i-Glyph,WinGlyph,MacScribe)的出现,使得古埃及“海若格里弗”可以十分方便地在电脑上打出来,从而使得古埃及文字大量进入人们的视野,也是导致人们误认为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的一个原因。申克尔最后指出,“古埃及文字中的绝大多数符号具有表音的功能,与符号本身所表示的意思没有联系”……“古埃及文字并不是象形文字”[20]。
四、结 语
笔者建议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圣书文字,因为这样既符合“海若格里弗”的希腊语本意(“神圣的刻写”),又恰和古埃及人对文字的称呼(mdwntr,“神圣的书写”)。不过,考虑到人类认知的特点,一个新术语的接受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忽然改变原有的称呼难免会一时不太习惯。因此,笔者在此建议不妨这样处理:在泛指古埃及文字(只是一般称呼时),直接称之为古埃及文字即可,不可画蛇添足称之为“古埃及象形文字”;如果在对古埃及文字的几种不同的形体进行具体称呼时,可分别称之为古埃及圣书体文字、祭司体文字、世俗体文字。
另外,我国文字学界对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在术语方面的刻意区分,在理解方面的含混模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误将“海若格里弗”译为“象形文字”,从而与我国传统文字学术语“象形文字”相混同而导致的。如果我们大大方方地将英文中的“hieroglyph”,德文中的“Hieroglyphe”,法文中的“hiéroglyphe”,按其本意译为“圣书文字”。另一方面,我们把英文中的“pictography”(或pictogram,或picture writing),德文中的“Piktografie”(或Bilderschrift①“Bilderschrift”一词,最早由德国学者Arthur Ungnad提出,参见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BandⅡ,Berlin 1938,p.91.)、法文中的“pictographie”,译为“图画文字”或者“象形文字”(即接受图画文字这个概念就是我国传统文字学中所说的象形文字,而不是再将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刻意区分开来)②笔者注意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并没有收录“图画文字”这一词条。我国文字学者显然将“图画文字”等同于“象形文字”。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如此一来,一切问题似乎可迎刃而解。
综上所述,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类文字很可能起源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物体的图画,即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象形,即我国传统文字学意义上的“象形文字”。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是人类文字的第一个阶段,是文字和语言相结合的初级阶段,然后以这个阶段为起点向假借(以形表音)阶段发展,最终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或兼表形音的形声文字)。显然,象形文字是人类文字发展史中的某个阶段的产物,或者只是某个文字体系中的一种文字类型,正如我国文字学者刘又辛指出的那样:“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哪种古文字属于纯粹的象形文字。”[21]因此,我们使用“象形文字”这一术语,作为世界上某国家(或地区)的文字的统称是不科学的。换言之,我们既不可以简单地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③笔者对古埃及语词典中收录的古埃及字进行了随机统计,在323个字中属于“象形文字”的只有3个,约占0.9%。参见R.O.Faulkner,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Oxford 1981,pp.52-76.;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中国汉字称为象形文字④据统计,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象形字只有364个,约占总数(9475)的3.8%,形声字7 697个,约占总数的80%。到了宋代,汉字中的形声字已高达90%。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占90%以上。因此,形声字才是汉字的主要类型。。总之,把古埃及文字称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同时也是国际上曾普遍犯下的一个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该错误进行彻底澄清和及时修正。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J].世界历史,1997(4):61.
[3]I J Gelb.A Study of Writing[M].the revised edition,Chicago,1963:27.
[4]陈梦家.中国文字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高明.中国文字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3.
[6]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69.
[7]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11.
[9]周有光.字母的故事[M].修订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3.
[10]Karl Weule.Vom Kerbstock zum Alphabet[M].Stuttgart,1926:13.
[11]Alfred Schmitt.Die Erfindung der Schrift[M].Erlangen,1938.
[12]傅懋勣.纳西族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别[J].民族语文,1982(1):1-9.
[13]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1):42.
[14]汪宁生.汪宁生论著萃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75-76.
[15]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16]罗邦柱.古汉语知识辞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33.
[17]黄亚平.象形字的几个问题[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77.
[18]邓章应,李俊娜.对象形文字和图画文字的认识历程[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3.
[19][德]弗里德里希.古语文的释读[M].高慧敏,译.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6.
[20]Wolfgang Schenkel.Wie ikonisch ist die altägyptische Schrift?[J].Lingua Aegyptia:Journal of Egyptian Language Studies,2011(19):125-153.
[21]刘又辛.从文字的分类模式看汉字的历史地位[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104.
Xiangxing Wenzi and Hieroglyph:On the Chinese Nam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
WANG Hai-li
(College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95,China)
Generally speaking,the earliest writing is picture-writing.The term Xiangxing Wenzi is a Chinese traditional term for writing studies.Xu Shen(a scholar of Han Dynasty)defined it as“the Xiangxing,those simple pictographs that primarily represent the objects they depict,such as the characters of the Sun and the Moon”.In China,the deliberat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ictograph and the Xiangxing Wenzi,and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 Xiangxing Wenzi and Hieroglyphs results from the mistranslation of Hieroglyphs into Xiangxing Wenzi.This mistake is due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Egyptian hieroglyphs for Xiangxing Wenzi,and coincid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erm Xiangxing.In fact,the Egyptian hieroglyph is not Xiangxing Wenzi,but actually an alphabetical writing.However,its“alphabets”were written in the form of pictures.Chinese people generally misunderstand Egyptian hieroglyphs for pictographs.This mistake should be corrected as soon as possible.
Xiangxing Wenzi;Pictograph;Egyptian Hieroglyph
K411.1
A
1001-6201(2014)03-0012-06
[责任编辑:赵 红]
2014-02-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SS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740005)。
王海利(1972-),男,山东泰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