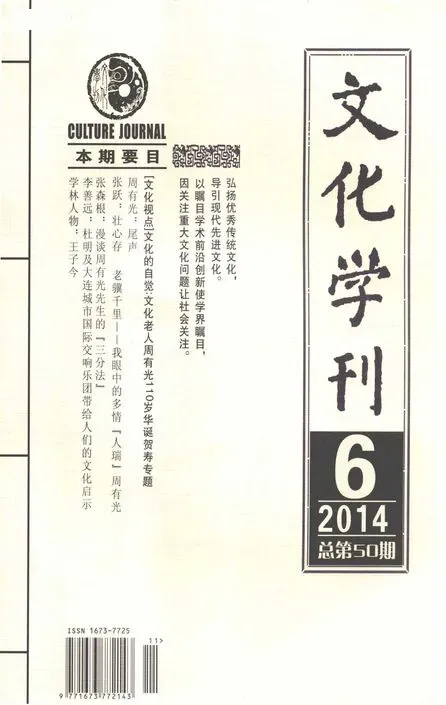中国传统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崔树芝 林 坚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书院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是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1]书院是我国古代从事教学活动的场所,还有研究机构性质。自唐至清末存在了一千多年,成为士子读书治学活动集中的地方。
书院创办的目的在于培育士子,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敦睦社会,具有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
一、书院的界定
中国传统书院历史久远、分布广泛。学界对书院已有很多研究,但关于书院的起源、性质等都还存在争论。要研究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需要先对书院进行界定。
据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玉海》解释:“院者,取名于周垣也。”是指有围墙的房屋。顾名思义,“书院”本意是藏书之所。
一般认为,“书院之名起于唐代,以唐玄宗开元间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为最早。”[2]它们是皇家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对此邓洪波提出质疑,主张书院是起源于唐玄宗前的民间书院。[3]李才栋却提出邓使用的史料并非可信。[4]
而具有讲学性质的书院起于何时也众说纷纭。有史料表明,唐代漳州首任刺史陈元光在垂拱二年(公元686 年)平定闽粤之间的“蛮苗”暴动之后请求设立漳州府,他认为“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设置州府和兴办学校是化民成俗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所谓“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盖伦理讲则风俗自尔渐孚,法律彰则民心自知感激”[5]。陈元光之子陈珦以漳州文学教官身份“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松洲书院的创建当在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09 年),有人称之为我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
对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李才栋先生有所怀疑,所以松洲书院的地位姑且存疑。后来,李才栋发现了定制于唐大顺元年(890 年)的江州陈氏家法,找到了陈氏东佳书堂教学的确切资料,推断“唐末至晚在大顺元年以前已有教学性质的书堂、书院”[6]。
书院到底起源于何时,其实对于书院的界定并无太大影响。因为书院成为一种教育制度成型于宋代,后代的书院意象也基于此,因而对于书院性质的争论以及书院在历史中存在的多种形态,却着实给书院的整体性研究带来了麻烦。
李才栋先生力挺书院基本上是私学(他认为的“私学”不是从公私相对来讲,而是指和“官府之学”相对的“民间之学”),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却有朝廷设官,奉文改制,变为官学性质的书院。”[7]邓洪波、陈谷嘉等人考察了书院在历史发展中具体的各种类型以及等级差异,他们在《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书院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了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质而言之,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书院与官学、私学,三足鼎立。[8]台湾学者陈雯怡认为宋初书院是乡党之学,但南宋出现了“书院复兴运动”,形成了集合官学制度与私学精神的新模式,“这些闻名遐迩的旧书院的兴复,也使其所被赋予的新精神随之流传,成为影响南宋书院的新典范。”[9]陈雯怡女士也反对笼统地界定书院的做法,而是想在历史中还原真实的书院。她在《由官学到书院》一书中有专节检讨书院界定问题,认为“诸种形式的书院,粗略归纳起来,私人所创办者,可以区分为家塾式、大型私家式及私塾式三种;官方所兴办者,也可分为官学延伸式及对象特殊式。”[10]想通过对书院下一个定义来统括书院现象,并对书院进行数据的统计,“其解释性是相当有限的”。[11]正确的方法是在对书院通盘认识的基础上,探索现象背后的共同特质。“即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透析其特性,并将这些特性放在各个不同的社会、思想脉络下来理解……必须换个方向,回到历史中来观察。”[12]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虽然书院起源于唐朝,但是书院制度的成型却在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以后,然而,同在“书院”的名号下,现实中的书院却有各种表现形式,很难给书院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也必须在此多样性中得以认识。
二、书院理想中的社会教化功能
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之前,书院都不成规模,也难以持久维持,往往伴随书院主持者个人因素而沉浮兴衰。拿北宋享有盛名的白鹿洞书院来说,朱熹出任南康军时,白鹿洞书院差不多只剩下遗址,要当地人带路才找得到。[13]书院的发展客观上也需要制度化的保障。陈雯怡指出:“在旧传统中蕴含新典范,在官方制度中注入私学精神,正是书院兴复的性质,也是书院复兴运动初期所立下的‘新’书院制度的模范。”[14]这类书院她称作“讲学式书院”“它保留了书院理想强烈的私学意象,尽管现实中书院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在理念上,书院却一直被视为私学理想的象征。”[15]
传统书院为何在此时复兴?它传达何种书院理想和教育理念?这首先必须放到宋代社会中才能看得明白。
经过五季战乱,新建立的政权急需人才,放宽科举取士范围,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三月二十一日,朝廷明确规定:“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圣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16]只是朝廷财力以及精力有限,无法满足士子求学需求,于是默许或支持书院发展。这是北宋初年的情况,因应科举制度的成熟,社会各阶层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出身,刺激了教育需求,而现实的教育需求又无法得到满足,于是书院以乡党之学的身份兴起。但是经过北宋三次兴学,书院即开始衰落,而官学的兴盛,却越来越无法承载教育的理想,沦为科举的附庸,成为追求功名利禄之地。
书院的设立一开始即与科举进仕的官学异趣,显示出求道特征。道学宗主周敦颐开办濂溪书堂,程颢回忆在那里求学的经历时说:“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程颢自称自十五六岁听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心。”[17]
对科举的弊端,两宋士人皆有清晰的认识。北宋陈襄(1017-1080)为闽中理学第一家,他创办古灵书院,认为:“学校之设,非所以教人为辞章取禄利而已,必将风之以德行道艺之术,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兴治美俗也。”[18]陈襄反对以科举进仕为目的的教育,而把德行道艺、兴治美俗作为书院的教育目标。
朱熹也对官学和科举有贬遣之辞:“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认为当时的官学有舍本逐末的危险,强调教学要注重“德性道艺之实”。[19]“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20]官学教育流为科举附庸,出现严重弊病,教者为科举而教,学者为科举而学,结果是“风俗日敝,人才日衰。”[21]需要书院补其不足。
张栻在主持岳麓书院时,写下《岳麓书院记》作为培养人才的大纲,可以看出其书院教育的理念。文中说:“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利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22]
这种兴治美俗、传道济民的教育理念集中表现在书院学规里,最著名的要数朱熹拟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该揭示有五项内容,分别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2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修己治人的用世内涵。陈雯怡指出:“白鹿洞学规不同于一般的学规,对宋代教育的发展,具有带领行作用,因此成为学风的转折点。”[24]邓洪波先生也说:“《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淳佑元年(1241),宋理宗皇帝视察太学,手书《包鹿洞书院学规》赐示诸生。其后,或摹写,或刻石,或模仿,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25]它俨然成为国家教育纲领了。
如果联想到书院复兴运动与儒学复兴运动几乎同时,那么我们不难理解复兴的讲学式书院天然成为新儒学的道场,通过社会教化整顿人间秩序。新儒家虽重内圣的修养工夫,但是他们的终极关怀却在外王,在整顿人间秩序。正如刘子健先生在对两宋之际文化转向的研究中指出的:“新儒家致力于教育和社会重建,坚信道德的方法是唯一出路,主张国家和社会都必须遵守道德。”[26]这种新的儒学传统转向内在,意欲由内而外地培育人的精神境界,移风易俗,实现整个社会的善治。
三、中心与边缘的配合
中国传统书院在现实中的社会教化功能得力于中心与边缘书院的配合。
学规可谓是书院教育理念“制度化”的代表,加之书院复兴运动中形成的结合官学制度与私学精神的新模式,书院得到社会认同并加以推广,名声大躁。除复兴中的讲学式书院以及原初的书院类型继续存在外,地方社学、乡校,家族私塾以及官学延展组织等,或模仿新建立的书院模式,或只是简单地以“书院”冠名,使得现实中的书院呈现多种色彩,也显现出相对官学而言较大的灵活性。各种类型的书院与讲学式的书院仿佛形成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讲学式书院处于书院组织的精神中心,把它的光芒发散延伸到边缘。中心保持书院的教育理想,边缘实现教育的普及,中心与边缘相互配合,弥补官学理想与现实的不足,达成社会教化之功能。
承载书院理想的讲学式书院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的,即使在南宋末期开始出现书院官学化趋势,元明清政府逐步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书院仍然具有相对的宽松空间。姑且不论蒙元满清遗族统治前期宋、明遗民为保士风名节,不仕异族,谨防华夷之辨而投身书院讲学事业,元朝初年,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朝廷实际上是接受遗民办书院的选择,对民间书院持宽松政策。即使政治后来趋于稳定,“在元至元(公元1271-1294)末期,元朝政府修改、改变了对书院放任、宽松的政策……采取措施以加强对书院的控制。”[27]根据邓洪波的统计,元代的官办书院仅占17.23%,认为民力是元代书院的主要力量。[28]而元代建立的第一所官办书院——太极书院,显示出明显的道学取向。元代郝经有《太极书院记》,文中记载:“庚子、辛丑间(太宗十二三年,1240-1241)。中令杨公当国,议所以传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相与讲明,庶几其可……今建书院以明道,又伊洛之学传诸北方之始也……使不传之绪,不独续于江淮,又继于河朔者,岂不在于是乎!”[29]
清朝书院政策先是抑制,顺治九年(1652)颁布训文卧碑,控制言论,成为书院教条。康熙开始适当恢复和鼓励,到雍正、乾隆时期又大力支持、提倡书院的建设,使得满清一朝的书院多达四千三百多所。[30]朝廷主导下的书院建设,无疑加重了政府对书院的控制,如肖永明先生所指出的:“清代书院的发展,是以其自主性、独立性的丧失、自由讲学精神的被阉割为代价的。”[31]但是清朝四千三百多所书院中,官办书院也仅占56. 67%,虽占大多数,也并不能一手遮天。而且正如陈雯怡所说:“官办与否并非关键所在,兴办时的理念以及接下来的支持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更确切地说,为了使其教育理念能维持久远,官办本来就是这些书院的目标。”[32]创建于雍正二年(1724)的钟山书院《延师养士则例》载:“采访有文望品望、年高而精明强固,足以诲人者‘掌教’,不拘爵秩、不拘本省外省。”[33]这说明清朝对书院的控制并没有面面俱到,书院仍然有一定的择师自主权,而不是靠朝廷的委派。这一点对于书院能否保持私学精神至关重要。而从反映办学理念的学规来看,清朝很多官办书院也还是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典范,如道光三年(1823)江苏宿迁兴建的钟吾书院,在《钟吾书院议立规条详请奏定原册》中说:“书院之设原为端士习,正人心,必主讲得人,方足以养育贤才,昌明正学。今书院初建,令遵鹅湖、鹿洞之规以端其始,首在讲明正理,研明经义……”[34]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主讲得人的办学理念。
从朝廷对书院的控制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书院教育中存在着较独立的价值诉求,这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有明一代四次禁毁书院,可见书院与皇权的冲突。比如明末的东林书院,就因议论朝政而遭迫害,牵连甚广。
由上述可知,在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中形成的书院意象,作为私学理想并没有在后来消失,它成为各种书院的精神中心,承载着书院教育理想。
余英时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讨论了明清儒学的转向问题,指出在宋朝士大夫相信“得君行道”,而明代政治环境苛刻,“行道”以“得君”为先决条件,而这个条件便根本不存在。但是儒家的淑世精神不允许士人对社会坐视不管,于是明儒找到了另一条行道之路,即“觉民行道”,王阳明“良知”学说实开其端绪。[35]“觉民行道”之载体便是书院讲学,使得书院走向民众[36],明代至阳明先生而书院大兴,并影响到后来的书院品格。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至此已相当明晰,陈谷嘉、邓洪波等人认为书院有“开发民智,使人摆脱落后与愚昧,提高国民的素质”的使命[37],在此有更直观的材料。
上文说的边缘书院是相对于饱含书院理想的讲学式书院而言,各色各样的书院或因应“书院复兴运动”形成的书院模式,或受到书院复兴的影响而冠以“书院”之名,他们以其灵活性优势存在于教育的各个层面,乃至于成为凌驾官学之上的高等学府。书院复兴很重要的原因是正官学之失。讲学式书院更多的是在书院理想引领士风上补官学之不足,而各式各样的书院则更多地补官学不能满足众多的教育需求之不足。南宋书院只到县一级别,而一县管辖内的很多地方的教育需求就无法满足,元以后虽然官学也到了乡社一级,但是偏远的地区还是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官学的普及困难很大,而书院以其灵活性,如官民合办、家族以及个人都可以成为书院建设的主体。而且官学只容纳当地的士子求学,至于四方游学之失,皆设书院以容纳,因而书院成为学术交流的中心。凡是官学不到的地方,皆有书院的身影。在教育的普及上,书院功莫大焉。
四、书院社会教化功能的实现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的实现,我们可以从书院参与者(动力系统)、现实的书院活动(功能系统),以及书院规模的扩张(影响力系统)三方面来理解。
自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以后,书院被社会普遍接受。肖永明先生在《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视野中的书院》一书中,辟专章研究书院发展的社会动力,从君王、各级官员、家族力量、士人以及商人等社会角色的动机中,探究书院发展的动力系统。君王支持书院意欲对书院进行有效控制;官员是出于儒生本色与情感趋向、经世追求和救世情怀以及教化民众的官员职责;家族力量是出于和睦亲族提高家族地位和社会影响;士人是出于文化理想、现实关切以及身份认同;商人则想通过书院活动,改变社会地位。[38]上述动力系统,我们可以发现书院参与者的广泛,书院精神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正反映了儒家的社会理想,用儒学精神整顿人间秩序。与官学相比,书院承载了更多的价值理想。
从现实的书院活动方面,书院历来有“三大事业”的说法,即藏书、讲学和祭祀。
“书院”的原意即为藏书之所,因而藏书是书院的首要事业,它是教学、研究的基础,藏书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书院地位的标志。图书在古代是相当重要的文化资源,因印刷水平有限,图书资源弥足珍贵。肖永明先生说:“一个地区书院藏书、刻书事业的发展,可以增加该地区文化积累总量,是当地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39]有的书院藏书多得惊人,如南宋魏了翁创办的鹤山书院,他把自家藏书划归书院,又购置一些,共十万卷之多,比当时国家藏书还多。宋理宗为其亲题匾额“幸有鹤山房,图书绕梦香”[40]。书院的藏书相较于官府藏书和寺院藏书,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和公共服务性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书院的社会教化。
藏书只是教育活动的基础,讲学才是书院的本职,主讲得人与否是书院兴衰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书院教育以学规为其纲领和精神,学规一般规定进德修业的条目,有的还有读书法之类的为学之方,学生跟随老师陶养其间,对其人格理想的形成和学业的增进,大有裨益。书院有讲会活动,每逢讲会,民众也都纷纷来观看,传说朱熹到岳麓书院讲学时,来听讲的多达千人,学生们所乘的马匹将书院前池塘的水都饮干了。明朝书院走向民众,书院讲会蔚然成风。王阳明弟子、泰州学派王艮在书院讲学,农工商贾各界人士前来听者多达千余。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也是“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41]。这说明书院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书院讲会俨然成为一种地方习俗。书院不仅是读书的场所,而且向社会开放,文人墨客在一起讲学论道、讨论时局,成为公众文化活动的场所,承担着传播、改造、更新文化和社会风尚的重任。
书院最能发人激越肃穆的是祭祀。书院的祭祀与其他祭祀不同在于,祭祀的对象是被学派宗奉的先师先贤,以及与书院学术传统相关的历代儒学大师。另外,书院还祭祀有功于书院创建、发展的官员,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在受到科举影响以及官学化以后,书院也祭祀魁星和文昌帝。通过隆重的祭祀活动,整齐肃穆的外在仪式,参与祭祀的人在志虑思慕中增强了对儒家价值理念的认同,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书院的祭祀具有公共性,对外是开放的,民众都可以过来参观,这样就使书院秉承的价值理念渗透到民间,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尤其是祭祀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使得祭祀更贴近现实,并更具有鼓舞、激励作用,被祭祀的对象身上的精神会成为无形力量,改造当地的民风民俗。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随着书院数量以及范围的扩展愈益彰显。从数量上来看,在唐五代时期,全国只有三十余所书院。北宋有七十余所,到南宋,书院总数达到五百所以上,说明书院已经成熟。元代书院也有四百多所。明代书院近两千所,到清代更增加至四千三百多所。[42]如果姑且不论书院的性质问题,就数量上看,书院随着历史的演进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在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接受它的社会。而从地域分布来看,在其萌芽之初,书院只在个别地区零星出现,经过长期发展,书院逐渐遍布全国。明代扩大到19 个省区,清朝从雍正年间即开始大量创建省会书院,使书院的分布空间进一步拓展。全国除了西藏以外,都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书院。这些书院通过中心与边缘的配合使社会教化功能尽可能广地扩展出去。
由上述可知,书院发展动力充足,功能完备,影响深远,为实现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五、结语
书院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在古代中国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教化功能。“书院复兴运动”中兴复的讲学式书院以兴治美俗、传道济民为宗旨,渗透着儒家整顿人间秩序的理想。这类书院成为私学理想的象征,而且一直没有中断,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风雨兼程,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和价值维系之地,甚至在清末改制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一代儒宗马一浮为了培养读书种子,保存圣贤血脉,1939 年创办复性书院。有“最后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于同年创办勉仁书院,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想搞中国文化研究院,却一直没有机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发起了中国文化书院。钱穆于1949 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致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新亚书院”办得相当成功,1963 年与崇基、联合三所私立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连胡适这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对书院的命运唏嘘不已,他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43]
大致概括书院的特点,主要有:第一,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不但教知识,而且注重人格培养。第二,实行“全科教育”,不但研读经史子集,而且学习棋琴书画。第三,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书院的山长、主讲一般是博学多才之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第四,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倡导学术交流。第五,书院的教学,有教无类,不受门派、地域限制。第六,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第七,书院学习以求知为宗旨,注重真才实学,不以功利为目标,不以虚名为诱导。第八,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识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这些都有助于实现社会教化功能。
我们对书院进行全方位研究以及探究传统书院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极为必要。
[1][3][25][28][30][3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2.1-2.163.197.410.305.
[2][4][6][7]李才栋. 直面书院研究中的分歧与辨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2006,(4) .
[5][唐]陈元光.请建州县表[A].全唐文( 卷五四四) [C].北京:中华书局,1985.
[8][37]陈谷嘉,邓洪波.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464.
[9][10][11][12][14][15][24][32]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M].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2004.38-42.266.276.280.54.399.65.65.
[13]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43.
[16][17]苗春德.宋代教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61.165.
[18]左靖.碧山东亚的书院[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64.
[19]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20.
[20][23][宋]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跋) [A].王涵.中国历代书院学记[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21][41]朱汉民:中国书院文化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2.102-103.
[22][宋]张栻.岳麓书院记[A].王涵.中国历代书院学记[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6.
[26][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7.
[27][31][38][39][42]肖永明. 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15. 328. 51- 153.443.51.
[29][元]郝经. 太极书院记[A].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71-172.
[33]王涵.中国历代书院学记[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0.
[34]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M].中西书局,2011.299.
[35][美]余英时.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175-211.
[40]顾沿泊.古代书院藏书对现代图书馆的启示[J].河北学刊,2010,(4) .
[43]胡适. 书院制史略[A]. 卞孝萱,徐雁平. 书院与 文 化 传 承[M]. 北 京: 中 华 书 局,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