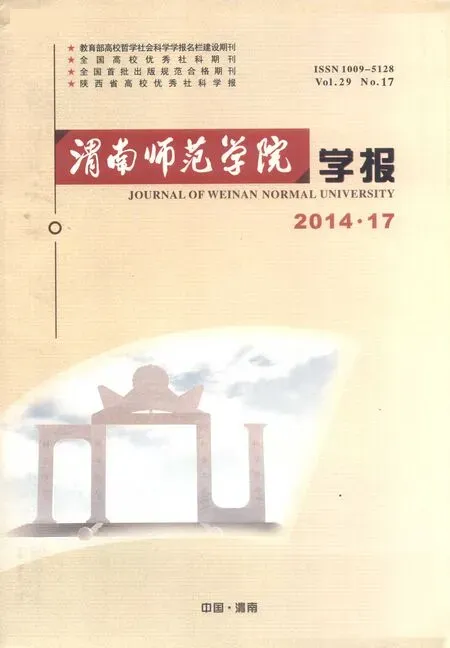论抗战时期国家权力对文学生产的“规训”
罗 建 周
(1.商洛学院 语言文化传播学院,陕西商洛726000;2.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710119)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中国领土,对于中国而言,不仅造成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领土被侵占,而且还造成了国家权力层面的中国主权被侵犯。当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遭受外来威胁时,国民党作为抗战时期中华民国的统治者,势必会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地维护国家权力的唯一性、合法性。在特殊历史境遇中,强化的国家权力施用于自己的国民无疑也是一种途径,这种放大、强化后的权力对其所统治、管辖区域的一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活动必然会产生不少负面影响。文学艺术生产作为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从未幸免于这场历史浩劫,其经受着或敞开或隐蔽的审查与监管。抗战时期文学生产所遭受的一系列来自文化政策、出版法规等的“规定”“训诫”,用福柯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国家权力对文学生产的一种潜在的“规训”。
一、文化政策对文学生产的“规定”
在文学生产过程中,文化政策对作家创作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是文学产生的风向标。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以抗战为由,竭力推行本党主义专制文化,故前后几次出台服务于专权的文化政策,仅就抗战初期、中期前后两次的文化政策纲领,足可揭穿其对“五四”以降文学生产秩序的强力干涉。
1938年3月底,国民党在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抗战时期的文化纲领:
建国之文化政策,即所以策进抗战之力量……[1]1
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所谓民族国家本位之文化,有三方面之意义,一为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一为抵御不适合国情之文化侵略。[1]3
诚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家受战争牵制,战争就像加速器一样推动国家机器急速运转,同样文化政策也受国家机器的牵引,也随之疯狂运作。研读上述“文化纲领”要义,我们不难看出,为适应抗战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国民党当局及时调整文化政策,欲使一切文化服务于政治权力。在调适后的文化纲领中明文规定“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言外之意就是欲限制非民族国家本位文化的发展,进而否定“五四”以降的追求独立、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重新“规定”文化政策的方向,即以倡扬民族国家文化服务于抗战为幌子,实为暗自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1940年1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筹组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随后成立了“文化委员会”,下设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宗教等小组。“文化委员会”在《告文化界书》中强调,虽然文化界“为抗战建国尽最大的努力”,“不惜牺牲最大的代价”,“忍饥受冻,流血流汗”,但是“目前抗战形势已和从前不同”,所以更需要为“民族道德的激励,社会风气的转移,民族伦理观念的革新”尽力,“今后无论团体或个人”,都要“切实服从军令政令”[2]。1942年9月,张道藩代表国民党当局就文化政策问题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3]
显然,从抗战初期确立的“文化纲领”到抗战中后期张道藩代表国家文艺政策机关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代表着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的张道藩提出的文艺、文化政策等就是国民党当局对文艺、文化的“官方姿态”,。在竭力维护抗战文化专权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倡扬的文化政策对文学生产起到了舆论引导与监管的作用。
二、出版法规对文学生产的“训诫”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加速了全中国进入极端的战争状态,随之,极端、高度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战时应时而生。文学艺术作为战火硝烟中宣扬国家意识形态的有生力量,其社会功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也遭受了国家权力对文学生产各个环节的“训诫”。
就文学生产过程中图书杂志的出版发行来看,国民党以抗战为由,设立两级图书杂志审查机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地方图书杂志审查机构,对图书杂志的出版发行实施严密的审查制度。仔细研读并梳理当时紧锣密鼓制定并出台的相关出版法规,不难发现:国民党当局颁布的出版法规大多是在出版发行环节上设障“拦截”的,主要是在“原稿审查”、印刷、发行等环节上实施“监控”。[4]
一是“原稿审查”制度的颁布。有关“原稿审查”方面的法规有: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会第86次常务会议通过《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106次会议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六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等[5]249-253。国民党当局设立“原稿审查”,是沿袭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原稿审查制度。全面抗战爆发,虽然仍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担心进步文化的发展会消解自己的文化专制,所以再度启用“原稿审查”,以求铲除异己文化力量。从书刊的传播层面来看,国民党当局欲在编辑采稿环节拦截进步文艺书刊进入公共视野,真正的企图是确保自己的文化领导权。
二是印刷、发行制度的颁布。如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内政部颁布的《印刷所承印未送审图书杂志原稿取缔办法》,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行政院公布的《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民国三十二年颁发的《修正书店印制店管理规则第15条条文》,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行政院公布的《修正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第 25条、第 26条条文》等等,[5]412-421规定如有书店(局)、印刷所承印未经原稿审查通过的书刊,将没收印刷费并再处罚款,情节严重强制停业整顿等。这些法规对部分进步书店受到了致命打击,被迫停业或关闭了不少。除了对承办印刷的书店(局)、印刷所等的严密“监控”之外,国民党当局还在图书杂志的发行传播渠道上设立“关卡”,如在邮局、文化站代购运输环节上设立相关的法规遏制进步出版物的流通。如《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各机关书店交运书刊须知》(颁布年月不详),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一日颁布的《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文化特约车代运各机关书店出版社书刊办法》等等[5]432-438。这些法规对书刊的发行产生强力约束作用,导致书刊无故滞留、遗失,严重阻碍了图书杂志的传播与接受。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地方两级审查机构分布范围较广,几乎遍布全国大中城市,所有图书杂志须无条件就近接受原稿审查、印刷制作检查、发行传播审查等,如违反规定均将接受严肃处罚,具体由审查机构遵照出版法规强制执行。很显然,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从文化政策出发,先后颁布了不少出版法规,这为其干涉文学生产寻求了制度层面的“合法性”。这一时期图书杂志的出版发行均遭受了来自国家权力的“规训”,尤其是类似于红色书刊的进步出版物均遭受过严酷的“训诫”。在今天看来,这些文化政策、出版法规从拟定到出台,背后无不隐藏着强大的政治诉求,这种不择手段的文化领导权争夺战,必然会扰乱正常的文学生产秩序,导致文学生产背离艺术生产的精神属性。
三、文学流弊的反思——以抗日小说为中心
抗战时期,国家权力主要通过文化政策、出版法规两种途径对文学生产实施“规定”与“训诫”。文化政策的出台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委员会”支配,出版法规的执行有效巩固了相应的文化政策。但在今天看来,由于国家文化政策、出版法规等强制干涉文学生产,故而大大消解了文学生产的本质属性,迫使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艺术逐步走上了唯民族国家文学意识的独木桥,损伤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就抗战文学中的抗日小说而言,这些小说带有明显的“战争化”特征,大多小说陷入“敌我二元对立”的 三种“叙事圈套”,即“歌颂英雄”“汉奸必除”和“鬼子必败”[6]。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般是三大类:英雄、鬼子和汉奸。英雄多为高大、勇猛、魁梧之人,鬼子长相丑陋、行为凶残,汉奸一般是奸佞小人、猥亵之相。在形象塑造方面过分放大英雄的英勇才智,故意贬低或丑化鬼子,对待汉奸的恨超乎鬼子。这三类形象的塑造流于粗糙、平面,罕有人物心理的描写,人物塑造急缺生命的质感。就英雄形象的塑造来看,形象过于单一,缺少对平民英雄或百姓英雄的精心塑造,同时缺乏细腻、立体的英雄性格、心理的挖掘等等。另外,极度缺乏对战争的反思,抗日小说人物多是被抽空了“人性”与“本真”的空壳。
如上论及的种种文学弊病并没有伴随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终止,也没有因为文学的“进化”而不治自愈,反而是这种文学的流弊至今仍在蔓延。今天荧屏上泛滥着良莠不齐的抗日影视剧,雷人的抗日“神剧”在娱乐化、商业化的操作下,不断地亵渎和歪曲这段民族的血泪史。其实,这些过度传奇化的抗日影视剧,如此“火爆”的场面至少可以投射出国民身上的劣根性,如以过分放大“抗日奇侠”的战斗能力,以求满足妄自尊大的虚荣心理;随意篡改历史,用矮化敌军实力来自娱自乐,以求“精神胜利”,是极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面对抗战时期那段特殊的历史,我们可以用“同情之了解”的眼光去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然而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到今天,反观当下抗日影视剧艺术上的种种流弊,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今天影视剧的诸多弊病与80多年前的抗日小说弊病如出一辙。这绝不是历史重演,而是亟需我们深思的问题。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文化运动委员会告文化界书[N].大公报,1942-02-07.
[3]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J].文艺先锋,1942,(1):5-10.
[4]罗建周.论国家权力对《文艺阵地》的“规训”[J].商洛学院学报,2013,(3):54 -57.
[5]刘哲民.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6]罗建周.战时“暴露与讽刺”抗日小说的叙事特点——以《文艺阵地》为中心[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15 -118.
——从学科规训视角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