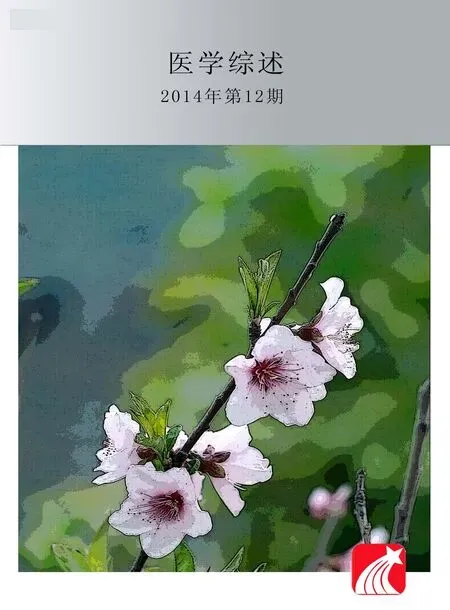“治未病”理念对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防治的意义
徐立华(综述),谭善忠(审校)
(1.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南京 210046; 2.南京市第二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南京 210003)
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将慢性无症状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chronic asymptomatic hepatitis B virus carriers,AsC)分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和非活动性HBsAg携带者。我国是病毒性肝炎的高发区,全世界HBsAg携带者约3.5亿,其中我国约1.2亿[1]。AsC平素无症状,血清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在正常范围内,但有的患者出现某些症状之后往往会被检查出肝炎、肝硬化或是肝癌[2],因而祖国医学“治未病”理念防止这些疾病的发生显得十分重要。
1 “治未病”的源流及概念
中医“治未病”首在《黄帝内经》提及[3],而对此影响较大的书籍有《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淮南子》等。先秦汉初有关文献中“防患于未然”和“不药而愈”等避祸防患观念,影响到中医界,《黄帝内经》恰当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某些哲学理论,并密切结合临床实践获取的医疗经验,使之升华为中医独特的“治未病”思想。
《黄帝内经》中共有三处提及:①《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②《灵枢·逆顺》“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③《素问·刺热》“肝热病者左颊先刺…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此外,另有一些隐含“治未病”的篇章。其后《难经》中《难经·七十七难》有“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何谓也…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对《内经》作了补充。
历代医家以此为据,将此思想不断发展,以东汉张仲景最为突出,他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提出预防疾病思想,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在《金匮要略》[4]中进一步论述疾病传变的规律和防止传变的治疗方法。如:其首篇就记载“上工治未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未病先防有“禽兽灾伤,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并且进一步提到“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既病防变即有病早治,防止病邪深入于里,以致“九窍闭塞”,甚至“流传脏腑”,使病情进一步加重或恶化。
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发挥[5],东汉华佗创五禽戏健身法,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晋代葛洪强调气功摄生等也是“治未病”思想的体现。至清叶天士在《温热论》[6]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强调了发病之后要防止疾病的传变,防变于先,先强壮易受邪的脏腑。吴鞠通在《温病条辨》[7]中阐述三焦论治法则及其传变规律,认为温病始上焦,终下焦,“治未病”当“存阴护正”等治疗思想,对既病防变作了进一步发展。现代各医家结合西方医学将它的内容又加以丰富[8],将预防疾病发生、防止疾病进一步加重、出现并发症或预后复发而采用的所有的养生的方法均称之为“治未病”,其最终目的为未病养生,预防为主,防微杜渐,适时救治,已病早治,防其复发。
“治未病”的概念[9]就是从上述理论中不断提炼发展而来,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未病先防,即在未发病之前,通过各种养生之法,达到增强体质,颐养正气,提高机体抗邪能力,免受致病因素侵害,以防止疾病的发生,维护健康;既病防变,即在疾病初期,趁其病位较浅,病情尚轻,正气损害不甚时,予以早期治疗,防止疾病的深入传变,波及其他脏腑;病后防复,即在疾病临床治愈后,调节阴阳,增强正气,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防止疾病的再发生。
2 AsC防治的重要性
AsC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持续存在6个月以上、无肝病相关的症状和体征、血清丙氨酸转氨酶基本正常的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1]。许多学者认为,AsC处于免疫耐受期,无临床症状,丙氨酸转氨酶正常,并不主张治疗,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手不管[2]。多项研究发现,绝大部分AsC存在不同程度肝脏炎症和纤维化,其中约50%为轻度改变,8.6%炎症和(或)纤维化程度在3级(期)或以上。随着病程的延长,乙型肝炎病毒携带可发展成为肝硬化、肝癌[10-12]。
AsC若转为肝炎反复发作,则需抗病毒治疗,抗病毒药物包括干扰素及核苷两大类。使用干扰素可出现发热、皮疹、脱发、白细胞下降等诸多不良反应,有些患者不可耐受。而核苷类药物的不断出现[13],虽然为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选择,但是长期应用容易引起病毒耐药的发生。
肝炎进一步发展到肝硬化则难以逆转,至肝癌时其存活率更是低下。处于乙型肝炎病毒携带状态时期,由于此时患者机体脏腑基本生理功能尚稳定,治疗相对容易,因而显得至关重要。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认识到乙型肝炎病毒携带在治疗乙型肝炎中的重要性[14],提出于乙型肝炎病毒携带期治疗疾病,纠正患者体质偏差,平衡阴阳,五脏安和,则可减少、延缓、阻断肝炎的发生和病情的发展。
3 “治未病”思想在乙型肝炎病毒携带防治中的意义
就中医学正邪关系的角度来说,AsC机体处于正邪僵持时期,暂时维持机体功能的稳定。随着病毒携带时间延长[15],机体的免疫功能愈低,在一些过度劳累、烟酒刺激、肝损性药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会导致疾病的进展甚而恶化。虽然病毒复制,又不断被清除,患者处于病情稳定期,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此时只能说明邪气尚浅,但仍需要治疗,如《金匮要略》中提及“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有病早治,“既病防变”。
目前对于乙型肝炎病毒携带的治疗,西医主张高复制期AsC并无明显的肝脏损害,间断服用一些护肝药物即可。非复制期AsC一般病情不活动,无需处理。只有AsC出现明确的丙氨酸转氨酶增高,不论其增高幅度,亦不论其有无症状,均应积极治疗。其中较轻的可在门诊治疗观察,难以控制其活动者则住院治疗。由于西医对于乙型肝炎病毒携带的治疗无积极性[16],需等待其出现相应的症状或实验室结果异常方给予治疗。因此利用中医辨证理论对AsC进行辨证论治,调整其阴阳平衡,阻止或延缓疾病的发展,若放任不管等其出现异常再进行治疗则正应了《黄帝内经》中“治五脏者,半生半死”的说法。
4 “治未病”理念在AsC防治中的应用
治疗疾病应注重于:病未发,防微以杜渐;病已成,则把握进退;病痊愈,需慎防劳复;莫等亡羊补牢,力求事半功倍之效[17]。在祖国医学“治未病”思想的指导下,防治AsC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4.1调养情志 情志变化是脏腑机能活动的表现形式之一[18],可以自我调节,防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使机体保持生理上的协调,所以防止肝炎的发作可以通过调节情志来治疗。“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因而要放松心境,调畅气血,怡情放怀,调节脏腑功能,防止肝炎的发作。
4.2劳逸适度 古语有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19]。说明了运动的益处,并且指出了不运动的危害。虽然是乙型肝炎病毒携带,但不可久卧,久卧则伤气,且通过锻炼,调节气息,静心宁神,既可以达到畅达经络强健体质的目的,又可预防肝炎的发生。
4.3饮食有节 饮食应合理,既不可暴饮暴食、饥饱失常、饮食不洁,又不可偏嗜过度;暴饮暴食、饥饱失常则脾胃受损,脾运失健则水谷不化,水湿内生,诱发肝炎的发生[20]。过食酒热肥甘、嗜食厚味则可助热生湿,影响脾胃运化、肝之疏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即指出饮食要有节制,否则易生疾病。因而应控制脂肪摄入,保持低盐饮食,增加豆制品、奶制品、蔬菜、水果等食物的摄入。
4.4药物调理 据患者体质服用中药以调其阴阳,安其未受邪之地[21],防止疾病的传变,《素问·玉机真藏论篇》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且“肝为五脏之贼”,因乙型肝炎病毒携带期病变在肝,尚未影响他脏,但再临床治疗中,一定要考虑且兼顾与肝脏相关的脏腑,防止疾病的传变。
此外,尚有使用针灸、药物敷贴肝胆病变部位等外治法治疗本病,均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且又有简便、快捷、不良反应少的特点[22]。
5 结 语
中医“治未病”思想源远流长,在提倡预防为先的现代医学理念里,中医治未病说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机。作为中医学重要的防治思想,它对于临床疾患皆具有指导作用。针对AsC易出现的情志失调、饮食不节、劳逸失度等原因,以“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作为指导思想,根据“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将“精神调养,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等中医“治未病”防治理论运用到临床治疗中去,防止、延缓和减少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1] 肖丽娜.慢性无症状HBV携带者的中西医研究进展[J].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21(4):288-290.
[2]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病学分会.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1,27(1):1-16.
[3] 张家礼,陈国权.金匮要略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2009:51.
[4] 郑亮,王媛媛.《金匮要略》“治未病”思想体会[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1,9(2):17-18.
[5] 赵盛云.“治未病”研究现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8(6):1306-1308.
[6] 杨进.温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68.
[7] 张志斌.吴瑭及其《温病条辨》的学术思想研究[J].浙江中医杂志,2008,43(1):1-4.
[8] 张曾亮.中医“治未病”理论的研究[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3,11(1):84-85.
[9] 张文斌,王永炎.试论中医“治未病”之概况及其科学内容[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0(7):440-444.
[10] 陆忠华,陈卫,王娟华,等.220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病理特点及5年随访[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9,29(4):530-533.
[11] 朱陇东,袁宏,陈琳.慢性无症状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组织病理及临床分析[J].临床肝胆病杂志,2010,26(6):633-637.
[12] 张惠勇,陈碧芬,郑瑞丹,等.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肝组织病理与临床分析[J].现代医药卫生,2011,27(20):3054-3055.
[13] 杨丽.核苷类药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研究进展[J].实用临床医学,2009,10(12):129-131.
[14] 刘士敬,刘歆颖.中医肝病“治未病”的意义和设想[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1,9(15):1-3.
[15] 刘苏.浅谈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辨体施治”[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1,9(15):103-104.
[16] 柯晶,谢琴秀,张亚飞,等.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129例患者肝组织学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传染病杂志,2012,30(8):490-492.
[17] 荀运浩,过建春,施军平.从“治未病”理论入手论治慢性肝病[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27(1):131-132.
[18] 莫芳芳,叶海丰,张国霞.《黄帝内经》七情学说研究与思考[J].吉林中医药,2008,28(8):614-616.
[19] 田明,张国霞.中医“治未病”与当代亚健康[J].吉林中医药,2011,31(10):925-926.
[20] 郭季春,杜强.中医“治未病”思想在脂肪肝健康教育中的意义[J].医药论坛杂志,2011,32(9):175-176.
[21] 陈兰羽,吕文良.以“治未病”理论论治慢性乙型肝炎[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29(1):210-211.
[22] 毛德文,薛发鏐,宾容,等.乙型肝炎携带者中医认知与治疗概述[J].山西中医,2012,28(1):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