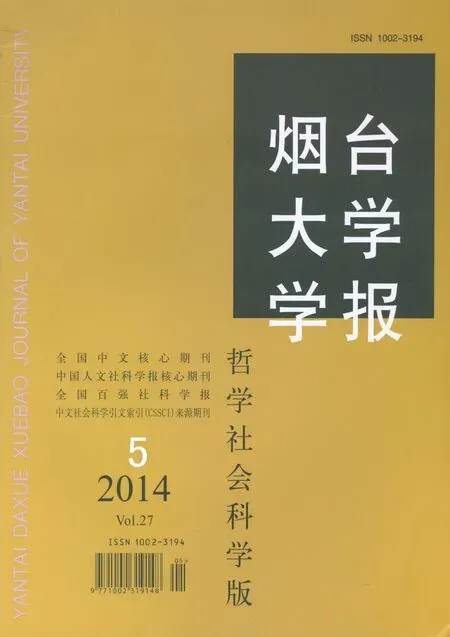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刘 军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北魏宗室阶层,即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是北魏王朝统治核心代人军功贵族集团的基石和骨干,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全面处于强势状态。为巩固宗室群体的领导地位,使之真正成为皇权的藩屏与支撑,北魏又采用魏晋五等贵族爵(王、公、侯、伯、子、男)将其打造为官僚体系之外的封君序列。关于北魏宗室阶层的受爵问题,学界业已取得丰硕成果。①通论性成果有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专题性成果如张鹤泉先生关于北魏宗王爵位封授的系列论文《北魏孝文帝改革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考》(《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北魏后期诸王爵位封授制度试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笔者亦曾系统梳理北魏宗室授爵基本特征,写有《北魏宗室阶层授爵略论》,载《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4期;着重考察北魏开国伊始王爵人事格局,写有《北魏“天赐十王”考辨》,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然而,已有论著大多从宏观视角把握宗室受爵的特性,却忽略了具体的技术操作环节。故本文拟从宗室封君的食邑分布、礼仪待遇、仕宦标准和爵位封授管理四个方面展开,为北魏爵制的总体研究提供必要的参照,找寻贯穿其间的制度主线。
一、北魏宗室封君食邑的地理分布
魏晋授爵比拟上古封建诸侯,通常伴随举行食邑的封授。但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改革爵制之前实行虚封,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七四对此阐释甚详。不过,北魏前期爵称中的地名绝非毫无意义的名称,该地名的空间方位和建制级别是衡量、调节封君地位的标尺。*张鹤泉:《北魏前期诸王虚封地改封考》,《古代文明》2011年第1期。也可以说,这时爵位连带的是并未落实的虚拟食邑,抑或一俟时机成熟便能兑现的承诺。故《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存录道武帝天赐元年(404)九月诏书云:“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这给人的感觉像是有期可待的信用支票。换言之,这些所谓的“封邑”在北魏统治者的观念中是确实存在的,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对汉人大族爵号与郡望关系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民族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第252页。那么,分析北魏宗室封君虚拟食邑的地理位置也就有了研究价值。
遍检史料,北魏前期有据可查的宗室“国邑”分布情况如下:(一)河北地域共34处:相州、定州各8处,冀州7处,瀛洲5处,安州、营州各2处,平州、燕州各1处;(二)山西地域共6处:肆州4处,并州、汾州各1处;(三)关陇地域共12处:雍州6处,秦州3处,泾州2处,梁州1处;(四)青齐徐兖地域共19处:徐州6处,青州、扬州各4处,兖州3处,齐州2处;(五)河南地域共24处:豫州14处,郢州6处,荆州3处,洛州1处;(六)江南地域共8处。*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9年。下文所用数据亦引自该文,恕不再一一注出。由此可知,北魏在规划未来政治版图时,将宗室爵邑集中部署于河北平原(约占总数的33%)及江淮至荆洛一线(约占总数的42%)。前者力图巩固统治重心,后者旨在激励宗室锐意进取、攻城略地,以求继续在南进征程上建功立业。山西和关陇地域食邑较少,所占比例仅6%和12%。这是因为山西临近京畿,而关陇为新占之战略要地,遵照华夏传统信条均不宜实施分封。
另外,宗室虚拟封邑与平城京畿的地理关系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畿内无分封是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这个信条是否得到北魏王朝切实贯彻了呢?道武帝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际便划定千里邦畿。《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河东道三》“云州”条载:“东至上谷军都关(北京延庆),西至河(内蒙古托克托喇嘛湾向南延伸至河曲),南至中山隘门塞(山西灵丘东南,当时中山与灵丘两郡交界处),北至五原(内蒙古九原),地方千里,以为甸服。孝文帝改为司州牧,置代尹。”*北魏平城京畿四至今日所在位置,参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1-52页。京畿界限明确固定,时人畿内概念十分强烈。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曾专门征发十万民夫,“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魏书》卷四《太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册,第101页。作为地标。若结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卷进行标图作业,将前述宗室封邑与之相比对,不难发现,即便是虚拟分封,宗室食邑也绝不侵犯京畿地区,拓跋统治者对华夏古礼的尊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至十八年(494),推行“五等开建”,在早先虚封爵(后改称散爵)基础上另设开国爵序列,探讨宗室开国爵食邑分布之特点便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笔者统计结果是:(一)河北地域共45处:相州12处,定州10处,冀州8处,瀛州7处,幽州、燕州、安州各2处,营州、平州各1处;(二)山西地域共18处:并州12处,肆州4处,建州、汾州各1处;(三)关陇地域共18处:雍州9处,泾州4处,河州、秦州、岐州、梁州、华州各1处;(四)青齐徐扬地域共43处:兖州11处,青州10处,徐州9处,济州、齐州各4处,扬州3处,光州2处。河南地域因迁都洛阳改设京畿,而将原有封邑全部搬迁。这表明,北魏后期宗室封君食邑仍密布河北(约占总数的36%)和青齐徐扬(约占总数的34%),这与前期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由于都城南迁,荆豫河洛不再划地开国,山西、关中地区食邑数量则相应增长,比例皆提升至15%。以上仅是宗室分封之个案,并不足以说明北魏整个食邑体系的分布特征。但是,换个角度说,亲尊莫二的宗室尚且如此安置,一般的庶姓官贵恐怕也不能例外。
总而言之,北魏宗室封君的食邑安排严格遵循地域避让原则,行政级别为司州的京畿地区绝不分封,战略要地审慎封授,内地的一般区域则酌情安排。这既体现了对华夏政治传统的恪守,亦符合王朝现实统治的需要。
二、北魏宗室封君的礼仪待遇
礼仪是等级社会区分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北魏宗室封君的实际身份地位便集中体现到相应的礼仪待遇上,其具体内容需要辨明。《魏书》卷九《孝明帝纪》载,正光元年(520),柔然国主阿那瓌来降,十一月己亥诏曰:“可封朔方郡开国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户,锡以衣冕,加以轺车,禄恤仪卫,同乎戚蕃。”诏书中的“戚蕃”实指皇魏宗王。*关于“戚蕃”的特定含义,见《魏书》卷四○《陆俟传附陆睿传》,太和十九年(495),定州刺史陆睿谋反,欲推举南安王元桢、阳平王元颐和乐陵王元思誉,李冲、于烈上表曰:“睿结衅在心,阴构不息,间说戚蕃,拟窥乾象。”可知,“戚蕃”专指南安、阳平和乐陵诸宗室王。阿那瓌既等同于宗王,那么反过来说,北魏宗室封君所享受的基本礼遇就应有冠冕、乘舆和仪卫三项。
北魏冠冕实现正规化和序列化走过漫长的道路,直至孝文帝太和改制,尚有守旧元老东阳王拓跋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武卫将军谓传附丕传》,第2册,第360页。到了孝明帝熙平二年(517),才由清河王元怿和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册,第238页。宗室封君由是穿着制式朝服体现身份等级。其样式可参考沿袭元魏的北齐河清服制。《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明载:“远游三梁,诸王所服。其未冠,则空顶黑介帻。开国公、侯、伯、子、男及五等散爵未冠者,通如之。……诸王纁朱绶,四采,赤黄缥绀,纯朱质,纁文织,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广九寸。开国郡县公、散郡县公,玄朱绶,四采,玄赤缥绀,朱质,玄文织,长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广八寸。……”宗室五等封君的级别位差藉此得以鲜明呈现。
北魏对宗室封君的乘舆也有严格的规定。早在道武帝开国之初,令封君得乘“右騑”的金根车;诸皇子亲王驾驷,“鸾辂立乘,画輈龙首,朱轮绣毂,彩盖朱里,龙旂九斿,画云楱”;公乘安车,“缁漆,紫盖朱里,画輈,朱雀、青龙、白虎,龙旂八斿,驾三马”;等等。*《魏书》卷一○八《礼志四》,第8册,第2812-2813页。这套制度草创粗糙,需留待日后完善。《隋书》卷一○《礼仪志五》:“至熙平九年(笔者按:疑为元年之讹误),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宗室封君座驾的等级标志才愈发明显。
宗室封君的仪仗气派非常,按照级别配备数量不等的仪卫侍从人员,如皇子亲王设典卫令、斋帅、防阁等。*《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第2册,第538页。突出的典型是高阳王元雍,“给舆、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杨衒之、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四《城西·追光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6-177页。这或许是宗王一级的特别礼遇,宗室五等爵也有各自的仪卫等级,只是囿于资料,实难知晓。不过,北魏宗室封君的等级差别可在皇帝卤簿中得到曲折的反映。《魏书》卷一○八《礼志四》:“(道武帝)天赐二年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陈卤簿。列步骑,内外为四重,列标建旌,通门四达,五色车旗各处其方。诸王导从在钾骑内,公在幢内,侯在步矟内,子在刀盾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宫卑者先引。”可见,宗室封君依爵位高低被排摆在皇帝法驾由近及远的不同位置上,其身份尊卑便一目了然;而宗室封君凌驾异姓勋贵的身份也初露端倪。总之,脱胎“生蕃”的拓跋族入主中原后,积极吸纳华夏礼仪文化,在皇族内部利用礼制构建等级序列,灌输尊卑有别的纲常名教,并使之与爵位制度相配合,昭示着他们疾速迈向文明阶段。
三、爵位对北魏宗室仕宦的影响
北魏社会究竟是“官本位”还是“爵本位”乃时下学界热议的话题。一般认为,官职在决定身份、配置资源方面发挥的作用似乎更大,“官本位”论于是占据上风,爵必须向官靠拢,转换为官资,方能实现自身价值。北魏从道武帝天赐定制到孝文帝后《职员令》的颁行,都在尝试官爵一体化,即把官和爵纳入同一品阶序列参照比较,目的就在于此。如果套用阎步克先生“品位”与“职位”的理论,爵位构成了跟人走,而不是附丽于职位的“本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页。为维护封君的政治权利,爵位可依据自身的秩级获得相应的官职。北魏封君仕宦资格的兑现方式前后期迥然有异,暂以孝文帝太和改制为界,前期是以将军军号为媒介搭建官爵连通的纽带。具体而言,朝廷在册封的同时自动授予级别相当的将军军号,封君便可据此军号起家。这样看来,封君的起家官品与爵位秩级是等同的,其利益得到很好的照顾。宗室作为受爵主体无疑是这套运作程序的启动者和最大受益者。
学者研究发现,爵位与将军军号的固定搭配始于明元帝册封诸皇子。*张鹤泉:《北魏前期封授诸王爵位加拜将军号制度试探》,《史学月刊》2012年第11期。《魏书》卷三《明元帝纪》:“(泰常七年四月)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厘,拜相国,加大将军;丕为乐平王,加车骑大将军;……俊为新兴王,加镇军大将军。”必须说明的是,宗室封君的将军军号不仅惠及己身,还可随爵位传袭,后世蕃代者仍以此释褐。如乐安王拓跋范嗣子拓跋良袭爵,加卫大将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第12期。太武皇子“东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军大将军。……子道符,袭爵,中军大将军”。*《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东平王翰传》,第2册,第418页。以上是身份尊显的宗王,我们相信,宗室五等封君都有类似的待遇,只是欠缺资料证明。通过爵位与将军军号的组合,宗室封君得以高阶起家。但好景不长,《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旧制,诸以勋赐官爵者子孙世袭军号。(太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意即将爵位和将军军号彻底脱钩,封君就此失去了军号起家的特权。究其原因,王朝日久,爵位不断累积,军号愈发轻率泛滥,由此造成的职位、薪俸成为亟待卸掉的包袱。
北魏太和中叶,孝文帝在南朝降臣刘昶、王肃的辅佐下改革官制,系统吸收南朝发达的贵族制,贯彻“流品”思想成为宗室实现贵族化的首要举措。*宫崎市定:《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5页。按照贵族主义的原则,拓跋氏原本相对平等的氏族“直勤”体制让位给基于父祖官爵权势的家格门第。宗室封君凭借爵位优势在仕进方面又可独占鳌头。《魏书》卷八《宣武帝纪》载永平二年(509)十二月诏曰:“五等诸侯,比无选式。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从六上,伯从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异族出身:公从七上,侯从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从八上。清修出身:公从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从九上,男从九下。可依此叙之。”所谓“同姓”,即是皇室宗亲,此诏规定了宗室五等封君的起家标准。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讲法,这里采用的官品是太和廿三年颁行的后《职员令》,其最大特点是唯“流品”是从,以魏晋旧官制六品贵族线为界,其上重划流内正从九品,其下单列流外勋品,以示士庶天隔,使得各居其所,互不干扰。*宫崎市定:《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6页。那么,回归魏晋旧制换算宗室封君起家官品分别为公、侯、伯皆四品,子、男五品,该标准在理论上对应中正乡品一品,是异姓名望士族(门第二品)根本无法企及的。北魏王朝混同胡汉,倾力包装宗室为天下头等冠族的意图暴露无遗。宫崎市定所谓内徙拓跋族“有尊严的汉化”意即如此。
宣武帝永平诏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规定宗王的起家标准,需要梳理史料予以补充。北魏后期把宗王分为皇子亲王和后嗣藩王区别对待,皇子册封亲王,不再例加诸大将军衔,而是授予内外要职。据《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列传》记载,孝文皇子京兆王元愉“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后《职员令》定其为正三品;清河王元怿“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此职亦为正三品。据考证,广平王元怀的起家官同是正三品侍中,*刘军:《〈魏书·广平王元怀传〉补疑》,《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汝南王元悦则出身正二品的高级文散特进。*《魏书》卷九《孝明帝纪》,第1册,第225页。由此可知,皇子亲王起家的区间是正二品至正三品。至于嗣王,解褐范围应在从三品之下,以便与皇子亲王相互衔接。如广平王元悌,陈留王元宽起家从三品散骑常侍;乐浪王元忠,彭城王元劭起家正四品上阶少卿;广川王元焕,南平王元暐,武昌王元和,淮南王元敬先、元宣洪起家从四品下阶谏议大夫。*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研究》,第115-118页。总括而言,正从四品是宗王起家的底限,也是其独享的权利领地,绝不容忍其他势力染指。宣武帝时,帝党人物甄琛勾结恩幸,飞扬跋扈,“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 便遭痛斥“亏先皇之选典,尘圣明之官人”。*《魏书》卷六八《甄琛传》,第4册,第1513页。是为明证。
在官爵一体化的后《职员令》中,王、开国郡公为正一品,开国县公、散公为从一品,开国县侯正二品,散侯从二品,开国县伯正三品,散伯从三品,开国县子正四品,散子从四品,开国县男正五品,散男从五品。宗室五等封君的起家官品俱低于爵品,这与北魏前期二者保持一致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样,宗室封君就需要经历一段晋升途径方可实现官爵齐平,这段距离远近不一,大致王差一至三品,公差五品,侯差四品,伯差三品,子差三品,男差二品,平均值约为四品,这与魏晋乡品与起家官品相差四品的惯例异曲同工。那么是否可以推测,对于北魏宗室而言,爵位是其乡品评定的重要指数,通过爵与官的协调配合最终达成宗室阶层有序的官僚化。此外,宗室的爵位还可恩荫亲族、保举子弟入仕,带有任子的残痕,笔者将另著专文对此论证,兹不赘述。北魏无论胡汉,士子仕进仍然延续魏晋九品官人法,“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8册,第2974页。上述研究进而揭示,爵位在形成宗室官资,决定其仕途升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爵位的这种政治功效是毋庸置疑的。
四、北魏宗室爵位事务的管理
爵位关乎宗室地位的升降、权益的多寡,乃至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朝廷对宗室受爵事宜格外关注,除制定完善的规章细则外,还明令相关衙署从严管理。杨光辉先生指出,汉唐的爵位由皇帝、尚书省和鸿胪寺统一处置。*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03-106页。北魏照搬汉晋旧制,自然不会例外。现搜罗史料,予以验证。
首先,君临天下的皇帝对宗室受爵拥有最高决断权。宗室只有经过皇帝下诏册命才能正式获得爵位。《元顺墓志》:“孝昌二年中,有诏以文宣王于高祖孝文皇帝晏驾之始,跪玉几,受遗托,辅宣帝之功,追加嗣子任城王彝邑千室。析户五百,分封公为东阿县开国公。”*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皇帝的诏册作为授爵凭证,必须永久保存。《元昭墓志》:“爰发明诏,析土瀛墟,胙以山河。乐城县公食邑千五百户,丹书铁券,藏之宗庙。”*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45页。若宗室封君绝嗣,皇帝可为其指定继承人。《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附大曹传》:“(太原郡公元大曹)卒,无子,国除。世宗又以大曹从兄子洪威绍。”同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河间王脩传》:“(河间王拓跋脩)薨,无子。世祖继绝世,诏河南王曜之子羯儿袭脩爵。”宗室爵位传袭发生纠纷,皇帝予以终审裁决。武昌王元鉴死后,先前主动让爵的兄长元和与侄子元伯宗竞求承袭,世宗诏曰:“和初以让鉴,而鉴还让其子,交让之道,于是乎著。其子早终,可听和袭。”*《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河南王曜传附和传》,第2册,第398页。又济阴王元郁赐死,子侄元弼与元诞争袭,“诏以(元)偃正元妃息昙首(诞),济阴王嫡孙,可听绍封,以纂先绪。”*《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上·济阴王小新成传附诞传》,第2册,第448页。宗室如悖逆礼法、袭爵失序,皇帝必须及时纠正。如文成皇子河间王拓跋若去世,“诏京兆康王子太安为后。太安于若为从弟,非相后之义,废之,以齐郡王子琛继。”*《魏书》卷二○《文成五王·河间王若传》,第2册,第529页。又赵郡王元干之子元谌,“本年长,应袭王封,其父灵王宠爱其弟谧,以为世子。庄帝诏复谌封赵郡王。”*《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赵郡王干传附谌传》,第2册,第544页。可知,北魏皇帝在宗室受爵问题上的权威神圣不可动摇,充分说明爵位是人王帝主驾驭臣工的利器。
其次,尚书省对宗室受爵享有建议权。尚书省通常秉承皇帝意旨,酌情拟定宗室受爵议案,再呈献皇帝御览核准。典型事例见《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上·广平王洛侯传附匡传》,宣武帝时,过继至广平王元洛侯门下的元匡“表引乐陵、章武之例,求绍洛侯封,诏付尚书议。尚书奏听袭封,以明兴绝之义”。当时,以外戚高肇为首的尚书省频频处置宗室爵位事宜。如前引元和、元伯宗叔侄竞夺武昌王,尚书令高肇述说奏报事件原委,提议“(元)和先让后求,有乖道素,请令伯宗承袭”。*《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河南王曜传附和传》,第2册,第398页。高肇又遵皇帝指示,调整宗王的食邑户数。朝臣张普惠事后指出:“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第5册,第1742页。足见,北魏尚书省在宗室爵位事务上是有充分发言权的。进而表明宗室受爵不是皇家的“私”事,而是关系国运的“公”事,所以要同其他政务一样,统归行政中枢尚书省办理。
再次,宗室爵位的封授和削夺由鸿胪寺具体执行。鸿胪位列九卿之一,本是掌管爵位的最高官署。《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不过,魏晋以降,九卿式微,权力渐被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攫夺。北魏鸿胪作为宗室爵位授拜或罢黜仪式的主持者,仅具礼节象征的职能,毫无处分权可言。举例来说,元英攻略义阳,“世宗大悦,乃复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户,遣大使、鸿胪少卿睦延吉持节就拜。”*《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附英传》,第2册,第499页。这是授爵,夺爵亦如此。宣武帝时,御史中尉崔亮弹劾北海王元详贪贿淫乱,“请以见事,免所居官爵,付鸿胪削夺,辄下禁止,付廷尉治罪。”*《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上·北海王详传》,第2册,第562页。即在将案犯引入司法审判之前,由鸿胪先行夺爵程序。总之,鸿胪在宗室爵位事务中的象征意味大于实际作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拓跋族长宗师召集的皇家议事会——宗议对宗室爵位的传授产生极强的影响力。《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附熙传》:“(中山王元英世子元熙)轻躁浮动。英深虑非保家之主,常欲废之,立第四子略为世子,宗议不听,略又固请,乃止。”可见,宗室封君违背法度、擅行废立必遭宗议阻挠。我们知道,北魏宗议是拓跋氏“私”的家族组织,主要依靠“家规”而非“国法”约束宗室。*刘军:《拓跋宗师考述》,《唐都学刊》2012年第1期。宗议及尚书省、鸿胪寺是分别从“私家”和“国家”两个层面管理宗室爵位的,二者皆隶属于皇帝,唯皇权马首是瞻。从这个意义上说,宗室受爵运作不能简单地视为诸衙署间的权力制衡,还要看到皇帝协调公私、家国场域的平衡效用。
综上所述,关于北魏爵制的总体研究及宗室阶层在封爵体系中的地位,学界已经取得相当进展,我们只能就宗室受爵的操作管理和爵位的某些功用寻找突破点。前文所论再次证明北魏爵位不是空洞的荣誉称号或身份象征,而是与实际的统治权益紧密相关的。除了耳熟能详的衣食租税和亲恤外,还有礼仪优待和政治效用,这两项乃前人未曾措意之处。进而言之,爵位蕴含的等级秩序需要外在物化的仪式程序予以表现,还要附着于官僚机器的运行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北魏在内的历代封建王朝的爵制都不具有独立性,“官本位”而非“爵本位”才是中华帝国现象的本质属性。我们还看到,北魏朝廷对宗室受爵的管控异常严格,无论是虚封爵还是开国爵,食邑的地理分布都是经过认真考量和细致斟酌的,恪守儒家传统地缘政治理念为依据。而在宗室爵位事宜的处理上,专制皇权也要综合“公”与“私”两方面的意见,折射出中古胡人家国语境的现实转换。总而言之,北魏封爵在宗室阶层趋向官僚贵族化的进程中起到助推作用,它绝非后世史家评价那样空泛虚滥、流于形式,而是充分发挥了治国利器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