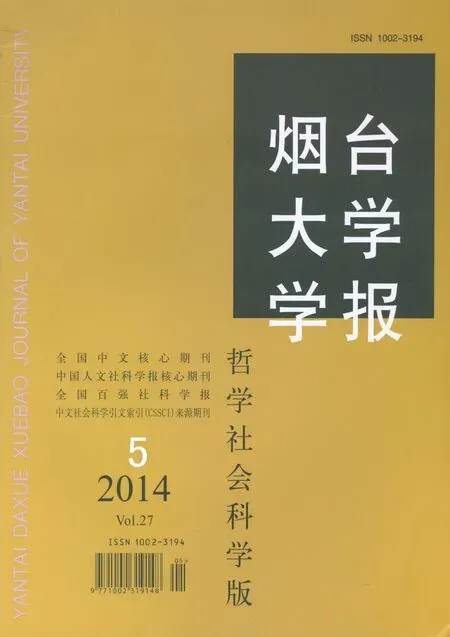论《阿Q正传》对儒家良莠混合学说的否定与“反讽”修辞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儒家学说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不可否认,儒家学说中有一些迄今仍然是合理,甚至是十分精辟的学说,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同时,也存在一些良莠混合的学说,其中,儒家关于“名”与“实”的学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斯亦不足畏也已”等学说,就是典型的良莠混合的学说,对此,鲁迅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小说中以鲜明的反讽修辞,对其展开了批判。不过,鲁迅的批判是有选择的,正是这种选择,不仅使鲁迅对儒家此类学说的批判具有了鲜明的针对性及相应的科学性,而且,也为小说中反讽修辞的大行其道,提供了顺畅的渠道。其中,《阿Q正传》中的例子不仅最典型,而且最集中。
一、鲁迅对儒家名实之辨学说的否定与小说的反讽修辞
名与实,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儒、道、墨、名、法等诸家学说,均对‘名’与‘实’的关系进行过深入论述,而其中孔子的论述对后世影响至深且巨。”①张全之:《〈阿Q正传〉:“文不对题”与“名实之辨”》,田建民,赵京华,黄乔生主编:《“鲁迅精神价值与作品重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的开头就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关于“名”与“言”的观点。“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才下笔,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②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不过,尽管鲁迅在引用了孔子的这一学说后,很诚恳地写道“这原是应该极注意的”,在小说实际创作的过程中也的确“极注意”了“正名”,不仅“极注意”了为自己小说的题名“正名”,也“极注意”了为自己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正名”,但是,所谓“正名”的展开,不仅没有达到“名”与“实”的相统一,反而分道扬镳越来越远;不仅名、实最终没有统一,而且名、实之间还构成了尖锐的“反讽”,并通过这种尖锐的“反讽”修辞,综合体现了鲁迅在本质层面的反儒家学说的思想和在具体层面的反儒家学说思想的修辞手法。《阿Q正传》这篇小说,也就成为了最集中地体现鲁迅小说反讽修辞的神采及鲁迅小说通过反讽修辞表达反儒家名实之辨学说思想的代表。
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就是“用反语”,这是古已有之的一种修辞手段,作为一个中文概念,反讽是从英语Irony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而英语的Irony这个词直到1502年才在英语中出现,直到18世纪初叶才被欧洲学术界较为广泛地使用*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年,第22页。。尽管古今中外的理论家们关于反讽的性质、功能及构成要素的论述众说纷纭,甚至基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反讽存在的基本条件、构成方式的论述也多种多样,但反讽的基本规范如果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名”与“实”的关系上讲,那就是“名”与“实”不符。也就是布鲁克斯与沃伦在《现代修辞学》中所明了地指出的:“反讽总是涉及字面所讲与陈述的实际意思之间的不一致。表面上看,反讽性陈述讲的是一件事,但实际的意思则大为不同。”*转引自李建军:《小说修辞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但在鲁迅的小说中,反讽这种修辞手段的使用由于是直接与其思想上的反传统,尤其是与反儒家学说直接联系着的,因此,鲁迅小说中的反讽就不仅仅具有丰富的审美内容,而且也直接地彰显了鲁迅的思想特点。
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最直接体现鲁迅反儒家名实之辨的思想与其反讽修辞关系的内容,是小说的题名及小说各章的章名与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及书写的人物“行状”的不协调。小说的题名,不仅是一部小说展示自己所要书写的内容的重要引线,而且也是展示自己风格甚至是创作意图的重要依凭,因此,在小说中,题名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小说的题名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彰显作者思想倾向的功能,如《战争与和平》、《复活》,如《围城》等。
对于鲁迅《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反讽性特征,早在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不久即受到了人们的关注。1922年3月,周作人在论《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艺术特征时就曾经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他多为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周作人:《阿Q正传》,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页。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关注到了这篇小说题名及章名的反讽性,张全之的论文《〈阿Q正传〉:‘文不对题’与‘名实之辨’》不仅对小说题名及章名的反讽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而且,对题名及章名的这种反讽性与鲁迅反儒家的名实之辨的关系也给予相当精彩的分析:“鲁迅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的唯美主义者,而是一位思想家,他的任何艺术上的创新尝试,都有着深刻的思想动因和丰厚的思想底蕴。就《阿Q正传》来说,鲁迅有意布置的‘文不对题’的叙事方式,有着多方面的用心。一方面,是为了颠覆中国传统陈陈相因的艺术俗套,如史传文学中人物传记的模式化、叙事类文学中毫无新意的风月故事以及‘大团圆’的结局。鲁迅在其杂文中,将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斥之为‘瞒和骗’的文艺,就充分表达了这一想法;另一方面,无论鲁迅是否有意,小说极为瞩目的‘文不对题’现象,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名实之辨’也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反省。”*张全之:《〈阿Q正传〉:“文不对题”与“名实之辨”》,田建民,赵京华,黄乔生主编:《“鲁迅精神价值与作品重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72页。这段论述可以说是既揭示了鲁迅小说“文不对题”的思想根源,也论述了这种“文不对题”所表现出的鲁迅在艺术创造方面的杰出性以及鲁迅小说的艺术创造与反儒家学说的内在联系。
当然,这篇论文虽然不乏精彩,但也有缺憾,这就是,作者没有辨析鲁迅对儒家“名”与“言”关系批判和否定的具体针对性,因此,作者也就没有论述为什么鲁迅反对“正名”却还是在小说中为自己小说的“题名”正了名,而且是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正了名”?由此,也就直接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即:如果说这篇小说“文不对题”的状况显示的是一种反讽,那么,这种反讽是怎么形成的,鲁迅这种对儒家名、实之辨的颠覆,为什么就必然地会使小说形成鲜明的反讽修辞特征呢?
事实上,鲁迅固然反传统,对儒家学说的批判尤为深刻,但是,鲁迅对儒家学说中的好的东西终其一生也没有提出过否定的主张,对儒家关于“名”与“言”的学说也是如此。如果说,鲁迅反对儒家的“正名”学说,那么鲁迅在小说中又的确进行了“正名”,这岂不是“言行不一”的自相矛盾?由此可见,鲁迅对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他虽然从来没有公开地肯定过,但却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还是很好地遵循了,他对自己小说的“正名”,对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的“正名”,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此一来,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说鲁迅对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学说没有否定,不仅没有否定,而且还按照其学说进行了相应的实践,那么,整篇小说的反讽,包括整篇小说的题名、章名与小说内容所构成的反讽,也就失去了创作主体的思想依托,因为,反讽修辞构成的先决条件和“主体性”依据就是作者对对象的否定性思想,而反讽这种修辞,本身也是一种表达作者“否定”性思想倾向的修辞手段。有学者就曾十分肯定地指出:“它(即反讽——引者注)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李建军:《小说修辞学》,第217页。如果说在小说中,鲁迅对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学说并没有否定,那么,小说的反讽修辞,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其思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可见,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即:鲁迅在反对儒家关于“名”与“言”的学说时他反对的究竟是什么?而他用实际的行为认可“名”与“言”的关系,又是在什么层面上的认可?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就应该对孔子“名”与“言”学说本身进行一些必要的辨析。
孔子发表这一学说的具体状况及表达这一学说的具体话语在《论语》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我们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最可靠的方法是回到原文的现场,通过原文的记载来看孔子这一学说的原意。《论语》中是如此记载的:“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第十三》,《四书五经》,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53页。很明显,孔子关于“名”与“言”的学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为政”必须首先确立“名分”,如果名分没有确立,那么说话就不顺畅,事情也就办不成;另一层意思是从“立言”的角度谈的“名”与“言”的关系,在孔子看来,要使发表的意见行得通,首先就要让意见与名分一致。第一层意思,有着很明显的“等级”意识,是孔子的等级伦理观念在孔子“名”与“言”学说中的具体化;第二层意思,谈的是“立言”的内在规律,即“名”与“言”必须统一的规律。如果说,孔子这里所表达的第一层意思由于等级意识的渗入而显示了其腐朽性的话,那么,孔子关于立言先必正名,即“名”与“言”、“名”与“实”的逻辑关系,则是合理的,也是能被经验和实践所证明的。辨析了孔子《论语》中所提出的“名”与“实”的关系,我们再来看鲁迅在小说中的作为就会发现,鲁迅之所以认为孔子所说的“名不正言不顺”是十分重要的,很显然不是针对孔子“为政”的观点而说的,因为,作为一个反儒家学说的先驱,鲁迅不可能认可孔子立言首先必须确立人的身份的观点,而是针对立言,必须首先将“题名”弄清楚而言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惜花费篇幅为自己的小说的题名“正名”了,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鲁迅要为自己所要塑造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正名”了,因为,这些“正名”的话语,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后面言说的“顺利”展开。同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正名”的结果是“文不对题”了,因为这正是鲁迅反正统的儒家学说,尤其是等级学说思想制约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的反讽修辞得以形成的思想依据,表面看是鲁迅反儒家“名实之辨”思想制导的结果,其实质仍然是鲁迅反儒家陈腐的等级学说的结果。也正是因为鲁迅反对的是儒家学说中的腐朽的东西,这也就直接地保证了小说反讽修辞的实现。《阿Q正传》这篇小说的反讽修辞,与鲁迅反儒家“名实之辨”的思想逻辑就是如此。
二、鲁迅对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学说的批判与小说的反讽修辞
在《阿Q正传》中,鲁迅也有意识地对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学说进行了反讽性的批判。不过,鲁迅的批判不仅具有思想的针对性,而且更具有艺术的合理性,正是这种思想的针对性与艺术的合理性的有机统一,既为小说的反讽修辞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又使小说的反讽修辞具有了厚重的魅力。
儒家的这一观点是儒家的“亚圣”孟子提出的。《孟子》中的原文是:“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四书五经》,第112页。这一观点应该说也是儒家学说中的又一个良莠混合的观点,它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内容,又包含了显然不合理的内容。正是这种合理与不合理内容的混合,构成了儒家这一学说的复杂性。
儒家这一学说的合理性表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儒家这一学说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对生命发展规律的一种“无意识”的肯定。因为,从人的生命本身发展的角度看,“后”所意指的“后代”,是人生命发展的承续者,人发展到今天,就是一个“后代”接续一个“后代”不间断出现的结果,而人的发展历史,也就是一个又一个“后代”发展的历史。而如果出现了“无后”的情况,对人自己的发展来说,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讲,都肯定是灾难,是巨大的威胁。儒家特意强调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无后”的危害性,虽然不是自觉地从生命的基本意义出发提出的,更不是在鲁迅所认可的,“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的生命本体意义的层面提出的,但是,儒家这一学说中对“无后”危害性的强调,还是切合了人的基本生命意义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儒家的这一观点中是包含了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合理因素的。
儒家这一学说的不合理性表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这一观点提出的基本立场及伦理意识方面。从基本立场来看,儒家提出这一观点,主要是从家族伦理,即“孝道”的立场提出的,其基本的意识是将现实中生活的人的“无后”当作了一种严重违反伦理规范的行为,而将“有后”当作了人存在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并且无限的夸大了这种意义,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是,只要是为了“有后”,人的一切行为以及所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孟子在论述中专门列举的“舜的例子”,就说明了儒家的这一基本理论逻辑。“舜”在娶妻的时候是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但由于他娶妻的目的是“为无后”(即怕没有后代),因此,“君子以为犹告也”。很显然,这样的理论及其逻辑不仅完全颠倒了人存在的基本意义,而且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家族伦理观念及其理论逻辑的作用下,人类为繁衍后代的基本行为,特别是中国人繁衍后代的行为——“结婚”,也完全成为了一种与结婚当事人无关,而只与家族有关的家族行为,两性结合的基础“爱情”也完全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替代了,由此也就在中国人的生命繁衍行为中制造了众多的悲剧,如中国文学中所描写的那些男女之间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就是代表。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学说和理论逻辑的制导下,男性在两性结合中的权力得到了绝对的强化,男权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大行其道的理由,男子的“三妻四妾”这种本是摧残女性人格的不合理行为,不仅在道德的层面受到了社会及大众的普遍认可,而且在法律的层面还得到了历来统治者的坚定维护,而统治者自己更是“三妻四妾”的带头人,中国皇帝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现象最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而这些行为之所以会得到社会及最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可,而统治者更是身体力行,固然有多种理由,但其中一种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这些行为包括“三妻四妾”,都是为了家族(统治者当然更冠冕堂皇,是为了“天下”、为了“国家”)“有后”,都是为了避免作为人,尤其是男人对祖宗和长辈的最大不孝——无后。
正是因为儒家的这一学说具有如此的不合理性内容,其所产生的影响又如此恶劣,所以,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初即对儒家的这一学说及其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灭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44-145页。鲁迅不仅在杂文中借助先进的进化论的学说对儒家的这一学说及其恶劣影响展开了批判,而且在小说《阿Q正传》中也有意识的引用了儒家的这一学说,并用反讽修辞的手法在塑造阿Q这个人物形象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学说的批判思想。
对于鲁迅引用儒家的这一学说来表达自己反儒家学说的思想及塑造小说中的人物阿Q这一形象,曾有人认为,鲁迅如此引用不仅与小说中的人物不吻合,而且还使小说呈现了不应该呈现的“丑角的色彩”与“杂耍的成分”,并将这一些都当作了小说的“缺憾”。“我感觉阿Q、孔乙己、木叔和爱姑等等都似乎是旧戏里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浓厚。鲁迅的讽刺作品(这里只限于他的短篇小说)还有一点缺憾,就是,杂耍的成分太多,如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和阿Q的‘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叶公超:《鲁迅》,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这样的批评即使不是有意的攻击或刻意的否定,但也很显然是没有能洞察鲁迅的思想与艺术匠心所得出的结论。当这种观点发表后,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当时就撰文反驳说:“‘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也是为证明阿Q‘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才引用的,有什么‘杂耍的成分’可言呢!”*李何林:《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9页。李何林先生的反驳,主要是从小说前后文的关系展开的,其反驳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然,无论是对鲁迅在小说中引用儒家这一学说做法的否定还是肯定,他们都忽视了将鲁迅反儒家学说的思想作为立论的依据,也忽视了鲁迅引用儒家这一学说与小说反讽性修辞的关系。
对于孟子的这一观点,鲁迅虽然在小说《阿Q正传》中和在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都进行了引用,其基本的倾向也都是批判与否定,但其批判与否定是有很明显区别的,其区别既表现在批判的内容方面,也表现在所采用的修辞手法方面。鲁迅在杂文中引用儒家的这一观点虽是批判,但重心主要不是批判这个观点本身,而是批判借这个观点而重提“三妻四妾”和“多妻主义”的谬论及违背现代道德的行为,也就是说,主要是批判儒家的这种学说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即为了“有后”而不择手段的“三妻四妾”及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即“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灭到他人。”至于修辞,很显然不是反讽修辞。而在小说中则完全不同,不仅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且,还采用生动的反讽修辞,揭示了这种思想对人物的残害以及所导致的喜剧性与悲剧性后果。也就是说,在小说中鲁迅之所以采用反讽的手法来描写这种观点的后果,是因为鲁迅对这种观点持否定的态度,而很明显,鲁迅所否定的并不是这种观点中所包含的与人的生命发展相关的内容,而是这个观点中所包含的“孝道”内容以及这些内容所带来的喜剧效果。小说中阿Q所闹出的震动整个未庄的“恋爱风波”的喜剧性,正是鲁迅表达自己否定性思想倾向的直接载体,因为阿Q闹出“恋爱风波”的直接起源虽然是小尼姑的一句“断子绝孙的阿Q”,但这场风波的根源却不在别处,就在阿Q所信奉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儒家的学说,而阿Q所闹出的这场“恋爱风波”,不仅没有任何正向、积极的价值,与传统社会及现代社会那些为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包括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或两性结合规范的男男女女,如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杜十娘、卓文君,鲁迅自己后来创作的小说《伤逝》中的子君等所闹出的“恋爱风波”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本身就是一场闹剧,一场仅仅出于“我和你困觉”目的的闹剧,一场仅仅只是为了想使自己避免“无后”的闹剧,这场闹剧最根本的性质不是别的,正是喜剧性,而按照鲁迅的观点,喜剧是将人生没有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的,阿Q所闹出的这场“恋爱风波”正是“无价值”的,因为他向吴妈求爱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实现自己“要一个女人”的价值追求,而且还让他自己因此遭遇了来自秀才的一顿“暴打”,还因此失去了自己仅有的一点“财物”并由此而产生了直接的“生计问题”。鲁迅“撕开”了阿Q所闹出来的这场“恋爱风波”的“无价值”性并对这场“恋爱风波”的合理性及其价值给予了相应的否定,从小说所描写的内在及外在的逻辑来看,也就当然等于否定了导致和支撑这场无价值风波的儒家学说。而小说的反讽修辞,也正是从鲁迅反儒家这一学说的这一方面“反弹”出来的,并且,“反弹”得十分巧妙,完全是“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小说没有使用任何表示否定的词语及话语,也没有对阿Q的恋爱风波作任何否定的暗示,更没有对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学说进行任何的指斥,反而模仿文言文的笔法写道:“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不仅极力书写了儒家的这一学说对阿Q这个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的人的“巨大”影响,以至于使阿Q这个对“男女之大防”、对女人十分严格的“正人”也不禁“飘飘然”了,而且还藐似认可了这一学说所揭示的“无后”的确是人生的一件不应该忽视的“大事”。而小说的反讽,包括对儒家这一学说的反讽,也就恰恰在这种“表里不一”,字面意义与小说内容意义的不相符合中反弹出来了。
三、鲁迅对儒家“斯亦不足畏也矣”学说的批判与小说的反讽修辞
“斯亦不足畏也矣”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不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儒家的这个学说,也是一个良莠混合的学说,不过这一学说的良莠混合状态与前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学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良”性内容和“莠”性内容都直接包含在这句话中,而“斯亦不足畏也已”的“良”性的内容,则不是包含在鲁迅所引用的这句话中,而是包含在这个学说前面所表达的“后生可畏”的观点中;而其不合理的内容,就是鲁迅这里所引用的这句话。之所以说“后生可畏”的观点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其中不仅包含了“厚今”不“唯今”的合理意识,而且包含了很强烈的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的意识,即“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而这种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的意识,不仅意识本身具有合理性,其思想方法则更具有合理性;而这个观点后面所表达的“四十五十而不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虽然表明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十分沉重的“杂质”,这个杂质就是,这一观点所反映的正是儒家“礼不下庶人”的等级观念。
为什么如此说呢?这是因为,“斯亦不足畏也已”所针对的很显然不是有身份的上层人或“士大夫”阶层的“不足畏”,而是指一般的平民,即没有什么地位的人的“不足畏”。如果将这段话的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一个人如果到了四十、五十岁还默默无闻,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值得敬畏的。而一个人到了“不惑”(四十岁)或者“知天命”(五十岁)的年龄还默默无闻,这个人只能是一个“庶人”,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位“士大夫”或其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正因为这样的人不属于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阶层,那么对于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关注的必要,更不必对其表示敬畏。儒家的经典之一《礼记》中曾说:“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礼记》,《四书五经》,第206页。这里所说的“礼不下庶人”的观点,虽然是在国君、士人、大夫、庶人这四者的关系中阐述的,而《论语》中所说的“斯亦不足畏也已”的观点,是在泛指的意义上阐述的,但是,两种观点中所包含的等级意识,却是完全一致的,都强调的是“礼”或“敬畏”与一般人,特别是下层人无关。鲁迅在杂文《礼》中曾经针对现实中有人抱怨民众对“国耻”等纪念日淡漠的情况,以讽刺性的笔调指出:“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鲁迅:《礼》,《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3页。可见,在鲁迅看来,并非是民众对国耻等纪念日淡漠,而是因为统治者本来就以儒家“礼不下庶人”的学说为依据,将民众排斥在“礼”的规范之外了,而现在又正是“以礼治天下的时期”,所谓纪念日也不过是一种礼仪的形式,既然民众早就被排斥在“礼”之外了,那么,他们对于与“礼”相关的事情,包括纪念日这种直接地表示“礼”的形式的淡漠,也就错不在他们,而在统治者所坚守的儒家的“礼不下庶人”的学说。
也正是因为孔子的“斯亦不足畏也已”这句话包含了这样的等级意识,所以,它也就与“礼不下庶人”的观点一样,自然地受到了鲁迅的否定与批判。鲁迅在小说中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其批判也主要是针对儒家这种学说中所包含的等级意识展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从鲁迅引用儒家这一学说的具体语境及所要表达的意思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鲁迅用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主要就是未庄的民众,包括赵太爷等“上层人”在弄清楚了阿Q的“底细”后对阿Q“前恭后倨”的态度,其具体语境是:“村人对于阿Q的‘敬而远之’者,本因为怕结怨,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如果再结合鲁迅引用这句话之前未庄人对阿Q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未庄人无论对阿Q是“前倨后恭”还是“前恭后倨”,其思想行为都是符合“圣经贤传”的,或者说,未庄人对阿Q的态度,本身就是按照“圣贤之道”行事的结果。未庄人之所以在阿Q从城里回来后对阿Q很“恭敬”(不仅那些下层人对阿Q很恭敬,甚至连未庄的上层人赵太爷也对阿Q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在意”,以至于在等阿Q送东西来家看看的时候,还破例地“点了灯”),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阿Q有了几个钱,有了一点“财物”,更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阿Q已经达到了儒家学说所认为的“有闻”的地步,而不是“默默无闻”,不仅“有闻”,而且这种“闻”还从“浅闺”传入了“深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阿Q已经突破了“默默无闻”的境界,其身份在未庄人看来也已经不是一个庶人了,而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了,正如鲁迅在小说中用调侃的笔调所描写的一样:“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了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之后,未庄人之所以对阿Q又不恭敬了,也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阿Q已经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财物”了,更是因为,他们发现阿Q仍然不过是一个“庶人”,不仅是一个“庶人”,而且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一个较之儒家认为的“无闻”的人还差劲的人。既然阿Q不过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么,按照儒家的“礼不下庶人”的观点,阿Q也就当然“斯亦不足畏也矣”了。小说的反讽修辞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使用的,小说中引用的这句圣经贤传的语录的反讽意味,也正是从这里直接透射出来的,其透射的基本路径是:小说引用儒家的“斯亦不足畏也矣”来形容此时的阿Q在未庄人心目中的地位,从阿Q自身的状况来看,似乎的确是很恰当的,因为这个时候的阿Q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不仅与他上城之前一样无足轻重,而且更由于人们知道了他的“底细”后,使他的地位更不值一提了,但就是这种看似恰当的形容,却十分深刻地揭示了未庄人势利的心理,而“势利”的心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不管是从传统的意义上,还是从现代的意义上讲,都是“损人利己”的不良心理,都是应该否定的心理,而未庄人这种应该否定的势利心理及其价值意识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被统治者用儒家的学说“治”成的,可见,儒家的学说虽然“恰当”,但却没有产生积极的价值,相反却带来了消解的影响。小说引用儒家学说的反讽意味就这样透射出来了。
很显然,这里的反讽修辞,虽然针对的主要是“村人”,也就是一般大众,当然也包括未庄的上层人,但是,由于这种反讽修辞是通过引用孔子的话所构成的,因此,这也就使这种反讽修辞的功能具有了双重性,一重是指向孔子的这一学说本身,对这一学说本身构成了讽刺;一重则指向了大众,表明大众已经在思想观念上深受了孔孟之道的影响。由此,也就使得这种反讽既具有历史的深度,更具有了现实的意义。这也正是鲁迅对儒家这种良莠混合学说批判的特点及意义之所在,也是鲁迅小说反讽修辞的双重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