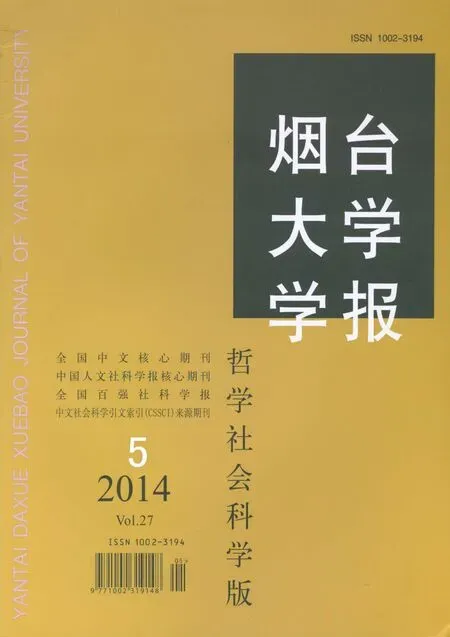北魏均田制颁行时间再议
张金龙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载太和九年(485)十月丁未诏颁均田制,卷一一○《食货志》亦载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其后,《北史》卷三《魏本纪三·高祖孝文帝纪》、《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上》、《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纪二》武帝永明三年九·十月条、《通志》卷六一《食货略一·田制》、《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历代均田之制》皆无异词。这表明,从文献记载角度来看太和九年颁布均田制并无歧义。然而,还有两条记载引起当代学者的疑问。《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其上均田疏中有“三长既立,始返旧墟”之语,说明当时已经设立三长制。而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年“二月甲戌(十三,4.2),初立党、里、邻三长”。但《李安世传》在记载均田疏之后即谓“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则均田疏必定上于均田制颁布之前。这样,均田制颁布时间和立三长的时间便发生了冲突。此其一。其二是关于《魏书》卷六○《韩麒麟传》相关记载的理解问题。“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齐州刺史韩“麒麟表陈时务”云: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农夫餔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
韩麒麟上表的精神与孝文帝均田诏并无二致,反映了共同的时代要求。韩麒麟建议:“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赐。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魏书》卷六○《韩麒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3页。其所言“计口受田”,学界一般认为即是均田制的另一种表述。从其上表来看,当时均田制尚未在全国普遍推行。有学者据此对均田制的颁布或施行时间提出了疑问,认为均田制的颁布不仅有可能晚于三长制,而且也有可能晚于韩麒麟上表的时间。
一、学界主要观点及其依据
《魏书·李安世传》载其上疏中“三长既立,始返旧墟”云云,与有关均田制和三长制颁布时间的记载存在矛盾,成为均田制和三长制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许多学者对此曾发表看法或进行专题研究。最初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均田和三长涵义的解释以调和两者的矛盾,后来者则怀疑两制,尤其是《魏书·高祖纪上》关于均田制颁布时间的记载有误。日本学者岡崎文夫最早注意到相关记载的矛盾,并认为均田制的施行是在三长制之后。*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东京:弘文堂書房,1932年,第667-668页。志田不动麿据《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认为,北魏于太和九年某月制定三长制,数月之后即同年十月实行均田法,按法令规定,从太和十年正月起,为了还受田而开始户籍调查,至次年二月完成。*志田不动麿:《北魏三长制制定年代攷略》,《歴史学研究》第3卷6号(1935)。陈登原云:“是故立三长者,所以括隐籍之户口也;颁均田者,所以赋诸荫附之人,于荒废之田也。然则太和九年之均田,太和十年之立三长,事乃一行而二歧。昔人何以先有均田,而后有整理户籍,知乎均田制之为括丁以垦荒,而三长制之为析户以定税,则九年而虚立田制,十年而立清查户口之税制,亦非于事不可能也。”*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83页。按是书1938年商务印书馆初版。这大概是中国现代学者最早就均田制和三长制相关记载的矛盾提出明确解释。*其后,蒙思明在中国学界最早就均田制与三长制实施的时间问题做了专题研究,参见蒙思明:《北魏实施均田制与三长制的年代问题》,《华北月刊》第1卷2期(1942)。钱穆认为:“李疏云‘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则应在十年立三长后,而均田诏尚在九年。据《魏书》,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附而行,则九年有均田诏,信矣。盖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上引则似确在立三长后也。”注且谓李疏“则明在推行均田以后”。*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上册,第333页。按是书完稿于1939年,1940年初版。吕思勉云:“案均田之制,在太和九年,三长之立,在其十年二月,《疏》云三长既立,而《传》云均田之制起此,似乎有误。窃疑此传所云均田,非指九年定制,乃三长既立,民返旧墟,豪强不便而扞格之,犹欲肆其侵陵劫假之旧,安世乃复以为言,魏朝从之,立为年断,使事久难明者,悉属今主,俾贫民亦有田可耕,以是谓之均田也。”*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下册,第1059页。
缪钺对于钱穆和吕思勉之说,颇不以为然,提出了如下看法:
钱、吕两氏之所解释,如细思之,仍有可疑者。均田固非一年可成,然下诏均田确在太和九年十月。观李安世疏详陈当时豪右占田甚广,细民无地可耕,援引井田古制,请政府抑豪强,恤贫弱,“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确是太和九年十月下诏均田以前之言,如在太和九年十月之后,朝廷已明令均田,纵使各地施行均田制,未尽完善,亦不应再作如是之语;盖均田诏下之后,理应人人有田,苟有弊病,应在郡县官吏授田之不公允,而不在豪右之冒认田地。至于谓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则臆测之言,毫无佐证,更不足以解此疑问。*缪钺:《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49页。
按钱、吕之解释因无佐证,自然不足以释李安世疏与均田制颁布时间之疑,然缪氏所言均田诏下达后之情形,如“理应人人有田”,即使有弊端也“不在豪右之冒认田地”,恐怕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当时豪右势力强大的社会情势下恐难臻此境界。不过缪氏提出的证据的确值得关注。《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永明)三年(485),初令邻、里、党各置一长,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四年,造户籍。”据此,则三长制的设立是在太和九年,而不是在太和十年(486),也就是说其设立完全有可能早于是年十月均田制的颁布。缪氏云:“太和九年夏间立三长,民返旧墟,因田地多为豪强冒认,细民无地可耕,故李安世上疏请朝廷均量田地,分给贫民,孝文纳其言,是年十月下诏行均田,而计口授田必须根据精密之户籍。如此,则当时情事,厘然可明。”“今既考定北魏立三长制在太和九年夏间,则《李安世传》中之疑义可以冰释矣。”*缪钺:《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读史存稿》,第50页。很显然,缪氏对其发现颇为自信。然而此说并未被学界所接受,唐长孺便认为《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得之传闻”,*唐长孺:《北魏均田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比较:三联书店,1959年,第18-20页。自然未必可信。日本学者松本善海在对《南齐书·魏虏传》与《魏书》有关记载详细考察的基础上,发现《魏虏传》有关北魏内部事务的记载存在少量纪年错误,其中大部分为提前一年,而关于北魏设立三长制时间的记载,不足以否定《魏书·高祖纪》太和九年的记载。*松本善海:《北魏における均田·三长両制の制定をめぐる諸問題》,《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东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260-281页。
李安世均田疏中的“三长既立”,《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一三·田制》作“子孙既立”,而“子孙既立”比“三长既立”似更符合上下文义。若此,则均田疏不上于三长制设立之后,均田制的颁布亦不必晚于三长制的设立。*按武仙卿最早发现这一异文(《北魏均田制度之一考察》,《食货》第3卷3期〔1936〕),李剑农亦认为“三长既立”应据《册府元龟》改为“子孙既立”(《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按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十二月甲申(初一,436.1.5)诏云:“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虽然北魏朝廷的诏令要求流民必须归还旧居,但恐怕并无多少人愿意重回旧土。此诏发布于均田制颁布前半个世纪,到李安世上均田疏时,这些流民无疑已是“子孙既立”。事实上,不用这么长时间,因为当时十五岁成丁(北魏前期小于十五岁),则流民离乡后用不了二十年即可“子孙既立”,若其离乡时子女接近成年,则“子孙既立”所需时间更短。甚至在冯太后第二次临朝听政之初因饥荒逃亡,到均田制颁布时便可“子孙既立”。然而,正如唐长孺所指出:“《册府元龟》由于转引或传刻之讹也常有错误,譬如均田令的颁布误列于太平真君九年,李安世上疏列于文成帝时,我们难以保证《册府元龟》引文一定正确”。*唐长孺:《北魏均田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7-20页。假使《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可信,或《册府元龟》所引为李安世上疏的正确文本,不管是哪种情况,矛盾皆可迎刃而解。那么,《魏书·高祖纪》和《食货志》所载均田制和三长制颁(班)行时间必有一误,但问题是此说并没有任何版本依据或本证予以支持,而且对于太和十一年韩麒麟上表所显示的情况也不能给出恰当的解释。唐长孺认为:“如韩麒麟之说京师有那么多的‘游食’,不象才‘均给民田’的样子。”结合《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所载太和十一年八月“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人”,“可见代京一带在十一年还没有实行均田。特别是韩麒麟建议‘制天下男女,计口授田’是对整个北魏统治区域而言的”。“不但韩麒麟仿佛完全不知道九年有均田令之颁布,为了灾荒问题而提出屯田建议的李彪也仿佛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按李彪建议载《魏书》卷六二《李彪传》,据同书卷一一○《食货志》可知,李彪封事上于太和十二年。“李安世疏中既然有矛盾的记载,加上上述疑点,我们对于均田令之颁布年月就很难确定为九年(四八五年)。”《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四年“十有二月壬午(十九,490.1.14),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朋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唐氏对此有如下解释:
诏书说明太和十四年,有了一种“丘井之式”可以依准,又有“条制”可以宣行,按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井是以九夫所受之田的土地来计算的单位,“丘井之式”和所宣行的“条制”显然是与均田和三长制相关。
由此他认为,“均田令是否在太和九年(四八五年)颁布是可疑的,但至迟太和十四年(四九○年)十二月前已有此制”。*唐长孺:《北魏均田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8-20页。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虽对均田制施行时间无明确看法,但他认为“韩麒麟使用‘计口受田’的表达,希望给田‘天下男女’”,“与均田制形成关系密切”(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8页注〔14〕)。换言之,其观点是均田制出现于太和十一年之后。
表面看来,唐长孺的看法的确颇有理据,然而其说却无法解释《魏书·高祖纪上》和《食货志》所载均田制颁布的时间问题。正因如此,此说同样未被学界所接受,唐氏晚年似亦不再坚持旧说*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大师讲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中册,第146页。。肯定太和九年颁布均田制的学者中,郑欣和高敏的相关论述值得关注。韩麒麟上表中有“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之语,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他提出的解决饥荒的方案之一,也被认为是太和十一年尚未实行均田制的主要证据。郑欣认为这种理解有误,谓“韩麒麟表中‘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乃是已经推行的制度,并不是他提出的建议”,亦即“太和十一年已经推行了均田制度”,因此韩麒麟的上表不仅不能证明太和十一年尚未实行均田制,反而还是均田制已经推行的力证。*万绳楠认为:“制天下男女,计口授田”,“只能说明:因为一次旱灾,很多受田农民又被抛离了土地,韩麒麟要求计口授田,是重新均田;不能说明太和九年均田未曾实行”。(《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71页。)尽管如此,从韩麒麟上表所述现状中的确看不到均田制已经推行的迹象,对此郑氏提出了三条理由:(1)“即使推行均田制,也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分到土地;即使大多数人都能均到土地,也不能保证他们不离开土地”;(2)“三长制、新租调制是和均田制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两个制度”,“到太和十一年韩麒麟上表时,三长制和新租调制的成立不过一年左右,而定户籍、租调到均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均田的推行不会太普遍”;(3)“太和十年、十一年,代京一带发生了大旱灾”,“即使均田制推行得十分彻底,大量人民变成‘游食之口’,也是在所难免的”。*郑欣:《北朝均田制度散论》,《魏晋南北朝史探索》,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8-159页。与郑欣的观点相同,高敏也不同意唐长孺对均田制施行时间的看法,他认为“应当承认太和九年均田令颁布之日,就是均田制开始实行之时”。*高敏:《北魏均田法令校释》,《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9页。但他并不同意郑氏对韩麒麟表中“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之语的理解,认为这“确是他的建议之一”。要解释其中的矛盾,“关键在于要把均田制的实行看作一个过程,也要把三长制、创新的租调制以及均田制当作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去看待”。*高敏:《北魏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实行年代辨析》,《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9页。尽管具体的理解有歧异,但郑、高两人对均田制实行问题的认识在整体上是一致的。
太和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封事,其中有云:“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困境,李彪建议实行和籴制度与屯田制度:
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
李彪认为,“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魏书》卷六二《李彪传》,第1386页。万绳楠认为李彪提出的和籴“这个办法在于维持均田制度”。*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271页。郑欣认为从李彪封事中“可看出均田制度已经推行的影子”,“李彪说的‘一夫之田’,就是魏孝文帝在太和元年三月丙午诏书中说的‘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也就是后来在均田令中规定的一夫‘受露田四十亩’。由于均田制的推行,使一夫田、半夫田这类术语流行开来;李彪用‘一夫之田’这句话,可说是当时均田制已经推行的反映。”*郑欣:《北朝均田制度散论》,《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第160页。高敏认为郑氏提出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魏书·李彪传》所云,不仅不能证明当时未颁行均田令,而且证明当时已颁均田令并正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高敏:《北魏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实行年代辨析》,《魏晋南北朝史发微》,第171页。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可以确证李彪上封事时均田制已经颁布。李彪所言“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同时反映了均田制和三长制颁布以后民众的权利和义务,也表明均田、三长两制颁(班)行之初,并未马上收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实效。不但未能使北魏朝廷所希望的改善社会经济窘境特别是严重的饥荒问题的目标立即实现,甚至还可能因为新制的实行引起暂时的混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形势更为严峻。
二、均田制颁于太和九年的证据
《魏书》卷五四《高闾传》载太和“十四年秋,闾上表”,谓“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虑狱讼之未息,定刑书以理之;惧蒸民之奸宄,置邻党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禄以优之;知劳逸之难均,分民土以齐之”云云。按“定刑书”指太和十一年的法律修订,*参见《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同书卷七上《高祖纪上》载太和八年八月甲辰诏谓“故变时法,远遵古典,班制俸禄,改更刑书”,九年二月乙巳诏谓“朕班禄删刑”云云,日本学者松本善海认为高闾所言“定刑书”当指此,即在施行俸制的同时公布刑书(《北魏における均田·三长両制の制定をめぐる諸問題》,《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316-317页)。按甲辰诏书与乙巳诏书所言“改更刑书”或“删刑”当为太和八年六月丁卯班禄诏所言“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而不是指对刑书的全面修订。因此,高闾所言“定刑书”应该是指《刑罚志》所载太和十一年的法律修订。因此,高闾所言“定刑书”应该是指《刑罚志》所载太和十一年的法律修订。“置邻党”“班俸禄”“分民土”分别指三长制、俸禄制、均田制*按“置邻党”“班俸禄”非常明确,而“分民土”虽稍模糊,但指均田制当无疑义。参见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页;郑欣:《北朝均田制度散论》,《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第160-161页。。也就是说,在太和十四年秋之前俸禄、均田、三长制这三项改革新政都已实行。高闾上表的具体时间应该早于太和十四年秋,表文开篇云:“奉癸未诏书,以春夏少雨,忧饥馑之方臻,愍黎元之伤瘁,同禹汤罪己之诚,齐尧舜引咎之德。虞灾致惧,询及卿士,令各上书,极陈损益。”《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一年(487)六月条:
癸未(廿九,8.4),诏曰:“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
按高闾表中所言“癸未诏书”即指此条,远在东南边地的齐州刺史韩麒麟在当年即上表言安民之术,而高闾身为朝廷大臣(尚书、中书监),绝不可能在三年多之后才对孝文帝就解决旱灾引起的饥荒问题而号召臣下出谋划策的“癸未诏书”进行答复,因而可推断其上表最可能是在太和十一年秋。*参见松本善海:《北魏における均田·三长両制の制定をめぐる諸問題》,《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317页。秘书丞李彪于太和十二年所上封事七条,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很可能也是响应“癸未诏书”号召的结果,因而也可印证高闾的上表不得晚至太和十四年秋方才提出。根据高闾的上表,可以断言太和十一年秋之前均田制和俸禄制、三长制都已颁(班)行,亦即均田制的确是在太和九年十月颁布的。*参见松本善海:《北魏における均田·三长両制の制定をめぐる諸問題》,《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317-318页。持相同观点的日本学者文献还有:西村元佑:《北朝均田攷》,《竜谷史壇》第32号(1949);佐佐木栄一:《李安世の上奏と均田制の成立——上奏年次の追求を通して》,《東北学院大学論集歴史学·地理学》第2号(1971)。
与俸禄制相比,均田制与三长制的实施难度较大,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即便没有阻力,也并非一蹴而就,何况一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三长制相对容易实施,而均田制则要复杂得多。太和十年二月设立三长制的同时,规定“定民户籍”。次年七月己丑(三十,9.3)诏曰:“今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九月庚戌(廿八,10.30)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赈贷平均。然乃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朕猥居民上,闻用慨然。可重遣精检,勿令遗漏。”*《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2页。由此可见,三长制设立一年半后“定民户籍”的任务也没有完全得到落实。若户籍不清,则“均给民田”便是一纸空文,*万国鼎:“均田必须周知户籍,方可按口授田,故立三长以定民籍。”(《中国田制史》,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第166页。)按新税制征收赋税更是纸上谈兵。同年八月“辛巳(廿八,10.1),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2页。很显然,京师地区可用于均田的土地十分有限,甚或根本没有,也就难以真正实施均田制。太和十四年“秋七月甲辰(初八,8.9),诏罢都牧杂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6页。此举意味着有不少国有牧地被转为农田,应该也是为了实施均田制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均田制实施的前提是要有地可授,李安世的意见是要从豪右手中分割土地和依附人口,但实际上“造籍”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很可能遇到豪强的极力阻挠,在无地可授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划出国有土地以供均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连年大范围的旱灾,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和剧烈的人口流动,使得均田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受到严重影响。均田制颁布后几年内,发生的灾荒见于记载者有:太和十年十二月“乙酉(廿九,486.2.7),诏以汝南、颍川大饥,丐民田租,开仓赈恤”。十一年“二月甲子(初八,3.18),诏以肆州之雁门及代郡民饥,开仓赈恤”。“六月辛巳(廿七,8.2),秦州民饥,开仓赈恤”。本月癸未(廿九,8.4)诏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要求“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旱灾之严重可见一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下诏“听民出关就食”,民户为了生计而离开本土,自然不可能实行均田制,即便已经实行也不得不废弃。十一月戊申诏谓“岁既不登,民多饥窘”,足见当年的饥荒并不仅仅局限于京师及雁门、代郡和秦州,而是波及到全国不少地方。事实的确如此,史称“是岁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太和十二年仅见“十有一月,诏以二雍、豫三州民饥,开仓赈恤”的记载,看来这一年饥荒范围较小,但在前一年流亡他乡的大量饥民并不一定能够马上返回故土,因而未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均田制。太和十三年四月,“州镇十五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以上所引具见《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饥荒波及的范围依然十分广泛,表明前一年的收成很不理想。在遇上灾荒时,北魏朝廷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开仓赈恤”,偶尔还有“丐民田租”的举措,本地无法救助时则会“听民出关就食”。这些措施在北魏以往各朝代都曾不断实施,并无新意。“开仓赈恤”的前提是当地政府的官仓中要有足够的存粮,否则便是一纸空文,太和十二年李彪所上封事中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和籴与屯田制度,即是由此而发。“丐民田租”的目的是为了缓和矛盾,事实上在灾荒年份饥民食不果腹,性命难保,不论是否减免田租,都不可能真正完成收缴任务,故此只是北魏朝廷的姿态,并无多大实际效用。“听民出关就食”是不得已而为之,前提是邻近地区获得丰收,有余粮可救济外地饥民。如果在广大区域同时发生灾荒,此法便不可行。
此外,孝文帝还采取了新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举措:太和十二年“五月丁酉(十八,6.13),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十三年八月“戊子(十七,9.27),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5页。由国家号召的兴修水利的行动,在北魏历史上所仅见,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先是在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试验,次年即推广到全国,可谓雷厉风行。此前发生的饥荒大多由旱灾引起,北魏朝廷认识到通过兴修水利以增加农田灌溉应该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孝文帝为应对饥荒号召臣下出谋划策,专门发布了“癸未诏书”,其后又于太和十三年二月“庚子(廿六,4.12),引群臣访政道得失损益之宜”;十四年二月“己卯(十一,3.17),诏遣侍臣循行州郡,问民疾苦”。*《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4、165页。通过这两次举措,孝文帝大概对地方基层的社情民意尤其均田制的实施状况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同时又得到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其结果在太和十四年七月甲辰“罢都牧杂制”以及十二月壬午“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两项举措中得到体现。甲辰诏是为了解决受田土地不足的问题,壬午诏则是为了解决豪强荫户的问题。这就表明,直到冯太后去世之时,均田制也没有在全国普遍推行,当然均田诏所希望的“兴富民之本”的目的也就不可能立即显现出来。正因如此,韩麒麟上表和李彪封事中均未明确提到均田制,均田制已经实施的迹象也不太明确。
总之,均田制是在孝文帝太和九年十月颁布应无疑问,但其完全落实则经过了数年时间,太和十四年十二月壬午诏可以看作是均田制和三长制完全落实的一个标志。因此也可以说,均田制和三长制虽然颁布于冯太后在世之时,但其完全落实则到了冯太后去世之后。冯太后死于太和十四年九月,孝文帝于次年正月“始听政于皇信东室”。*《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7页。则太和十四年十二月壬午诏颁布时,孝文帝仍在为冯太后服丧,由此足见他对落实均田制和三长制的重视程度和急迫心理。冯太后在世时,遇上旱灾往往要举行祈雨仪式,孝文帝一改此法,显示了他与冯太后完全不同的自然观念和行事作风。太和十五年(491)四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十一,5.5),有司奏祈百神”。孝文帝诏曰:“昔成汤遇旱,齐景逢灾,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诚发中,澍润千里。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唯当考躬责己,以待天谴。”*《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7页。不仅如此,此后也未见到祈雨的记载。孝文帝对自然规律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祈山川并不能致雨,灾荒问题只有通过改善治道才能缓解。*史称“鲁僖遇旱,而自责祈雨”(《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鲁僖遭旱,修政自敕”,“而时雨自降”(同上,卷三〇下《郎顗传》)。具体情形见《郎顗传》注引《春秋考异邮》:“僖公三年春夏不雨,于是僖公忧闵,玄服避舍,释更徭之逋,罢军寇之诛,去苛刻峻文惨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谤(罪)?不敢烦人请命,愿抚万人害,以身塞无状。’祷已,舍齐(斋)南郊,雨大澍也。”孝文帝的主张与鲁僖公颇为相似,而且从孝文帝对“日月蚀”的科学认识(《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二年九月甲午诏云:“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推测,他大概已经认识到水旱灾害的发生与所谓山川之神无关,而是自然法则的作用。透过孝文帝此诏,似可感觉到其时均田制已经完全得到实施的现状,而这无疑与去年年底“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有关。
三、补充论证
日本学者堀敏一认为:“均田制尽管在四八五年十月的诏令中颁布”,但“它并没有立即实行,而且确认土地所有者和制定户籍颇费时日”。“在四八八年到四九○年之间,在畿内、京城实行了土地的分割。”“在四八五年这个阶段,还不存在象现存均田法规这样详细的令文,而太和十六年令的编纂,表明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统治体制已经大体固定下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韩国磐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3、134页。虽然其观点并不十分清晰,但他的基本看法是可以感觉到的,即他认为均田制的实施是一个过程,485年均田诏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均田制的立即实施,甚至现存十五条均田令也不完全是485年颁布的,而应是太和十六年令文。*日本学者中持这一观点者大有人在,如佐川英治认为:“《魏书·食货志》记载的均田法是太和十六年的‘地令’,不是太和九年的。”(《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所见乡义与国家的关系》,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六年(492)“四月丁亥朔(初一,5.13),班新律令,大赦天下。”堀氏所言太和十六年令即指此次所颁(班)新律令的一部分。按太和十六年四月丁亥所颁(班)新律令,是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初八,5.31),议改律令”的结果,应该是对北魏现行法律的一次大规模修订,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对均田令条文进行修订,但绝不会大动干戈。在太和十六年四月丁亥所颁(班)新律令中,均田令亦当包括其中,其正规的法律名称应即《地令》。源怀在宣武帝时期考察北镇后所上表文中建议,“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魏书》卷四一《源怀传》,第926页。按“先贫后富”正是均田制受田的原则,见均田令第13条。*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曰:“《魏令》:职分公田,不问贵贱,一人一顷,以供刍秣。”(《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北齐”条引)按此《魏令》亦当为北魏《地令》,不见于《魏书·食货志》所载均田令,可能是均田制颁布以后增加的补充条款。而据下文,此条《魏令》在宣武帝初年就已存在。孝明帝时,司空、侍中、尚书令任城王澄“奏《垦田授受之制》八条,甚有纲贯,大便于时”。(《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澄传》)崔孝芬为司徒记室参军、司空属、定州大中正,“长于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516-517)中,澄奏《地制》八条,孝芬所参定也”。(同上,卷五七《崔孝芬传》)按“《地制》八条”即“《垦田授受之制》八条”,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应该是关于垦田授受的具体规程方面的改革,《魏书·食货志》所载十五条均田令文中是否包含了此八条的内容亦无从查考。从“大便于时”的记载来看,这八条《地制》在孝明帝时期曾加以实施。北齐均田令应该就是在经过改革以后的北魏后期均田令基础上进行修订的。从太和十四年“十有二月壬午(十九,490.1.14),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来看,当时应该已有《魏书·食货志》所载十五条均田令文的存在。也就是说,完整的均田令条文即便不是在太和九年十月均田诏颁布之时就已制定出来,也应该是在太和十四年十二月之前就已改定,所谓“丘井之式”“条制”主要当指均田令条文而言。若与三长制相联系,“丘井之式”的内涵便可一目了然。立三长诏开宗明义即云:“夫任土错贡,所以通有无;井乘定赋,所以均劳逸。”*《魏书》卷一一○《食货志》,第2855页。可见“丘井之式”就是“任土错贡”“井乘定赋”,即均田制和三长制及新租调制。*参见郑欣:《北朝均田制度散论》,《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第162页。也就是说,先实行受田,而后征收贡赋。据此,均田制与三长制孰先孰后的问题可谓不言自明。故可确切地说,太和九年(485)十月丁未(十三,11.6)诏意味着均田制正式颁布,而太和十四年十二月壬午(十九,491.1.14)诏则是均田制得以全面落实的重要标志。
齐郡公崔衡(435-488)约在均田制颁布之际出任泰州刺史,《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附崔宽传》:“先是,河东年饥,劫盗大起。衡至,修龚遂之法,劝课农桑,周年之间,寇盗止息。(太和)十二年卒,年五十四。”按“龚遂之法”是指汉宣帝时期渤海太守龚遂治理渤海郡的经验,他以良政治郡,使得盗贼横行的渤海郡迅速实现太平。其时,“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汉书》卷八九《循吏·龚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39页。经过汉宣帝亲自选用,老臣龚遂受命出守渤海。《汉书》卷八九《循吏·龚遂传》:
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渤海又多劫略相随,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一言以蔽之,“龚遂之法”即“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孝文帝均田诏的思想主张可以说与此完全相同。崔衡“涉猎书史”,应该非常熟悉前代有益的治国方略和为吏之道,在出刺泰州之前他曾向朝廷“陈备御之方、便国利民之策凡五十余条”,其中很可能就有体现“龚遂之法”的内容,因此其所陈五十余条“备御之方、便国利民之策”,必定与均田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太和十二年前在州刺史任上“修龚遂之法,劝课农桑”,无疑可以看作是地方官实施均田制的典范,也是均田制颁布于太和九年十月的确证。
前引《南齐书·魏虏传》谓齐武帝永明三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初令邻、里、党各置一长,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永明四年即太和十年“造户籍”。《魏书·高祖纪下》载太和十年“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先立三长再造户籍,乃必然之理,《南齐书》与《魏书》的记载并无矛盾。关于三长制,两书的表述有别,《南齐书》作“初令邻、里、党各置一长”,《魏书》作“初立党、里、邻三长”。“初令”是指颁布设立三长制的诏令,是未行之前,“初立”则是指三长制的确立,是已行之后。由此来看,缪钺推断“太和九年夏间立三长”,其后李安世上疏请行均田,孝文帝遂于“是年十月下诏行均田”,自有其道理,不过他“考定北魏立三长制在太和九年夏间”则未必尽然。事实很可能是,北魏孝文帝接受李冲建议下诏实行三长制是在太和九年春夏,同年十月颁布均田制,经过近一年的推行,次年二月十三日朝廷确认三长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确立。《魏书》卷一一○《食货志》:“(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这是太和十一年前三长制就已经完全确立的明证。由此可见,《魏书·高祖纪下》关于三长制“初立”时间的记载准确无误,则北魏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三长制应在太和十年二月之前一段时间,似不得晚于太和九年秋冬,应以春夏时节为宜。这样,《李安世传》所载均田疏中“三长既立”及史家之言“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便不再成为矛盾,反而成为理解均田制和三长制关系的关键记载。这样看来,在现代学界的相关解释中,日本学者志田不动麿的观点应该是最接近真相的了。
分析当时形势,可以推断李安世均田疏、李冲三长疏就是为响应太和八年八月甲辰诏书而上,均田制和三长制也就随之应运而生。具体而言,均田疏和三长疏上奏的时间以太和九年春夏时节的可能性最大。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制定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行动,而应该是放在一起共同考虑的结果。李安世上疏时或许就已清楚即将实施三长制,因而在其疏中提到“三长既立”云云,从疏文内容来看,主要是对三长制设立后将要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否则,就只能解释为是在三长制已立之后所上,目的是为了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当然其上疏也就不能看作是均田制的起因了。由于长期的战乱和饥荒的影响,北魏境内不少地区人口并不稠密,有较多的荒地可供分配,这无疑为均田制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如何使土地和民众有效地结合起来,以加强土地的利用,提高生产效率,使民众在完成国家赋税和徭役征发的同时有较多的蓄积,从而有能力渡过饥荒,是摆在当时北魏统治集团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均田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面对“民有余力”“地有遗利”的局面,实施均田制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