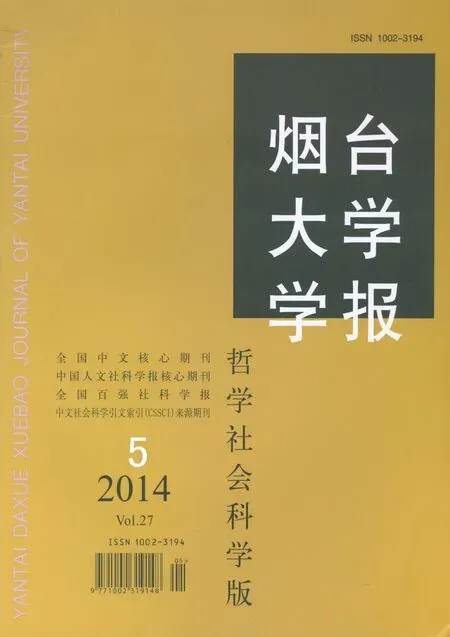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罗贤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在1988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著名史学家也是学会的第二任会长白寿彝先生就说过:“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召开不易,我们学会可以多开一些地方性的专题讨论会,人数可以少些,形式可以灵活些,论题一旦集中,研究就容易深入”。笔者认为,中国民族史学会这次在烟台大学召开的研讨会就体现了白老的讲话精神,会议规模不大而主题明确。今后还要争取多开这样一些地方性的专题讨论。
这次研讨会,将着重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族际互动与文化认同”问题。根据这一主题,我想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意在抛砖引玉,引发大家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一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的讲话中还说:“在中国民族史里,有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于深入地发掘。我们对一些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已经习以为常的看法,还是可以重新提出来进行再认识的。比如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意见。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这句话还有待于具体分析,说得太笼统,就缺乏说服力。我们需要从历史上研究,阐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时至今日,围绕白老所强调的问题,已然取得相当多的学术成果,但是还有比较广大的探索空间。
虽然历史上民族有分合,领土有盈缩,政权屡更迭,形势常变化,但是中国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这与世界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中途夭折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文明没有中断的很大原因就在于不断融入新鲜血液,不断地吸纳和辐射,文化的更新和民族的融合过程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还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在发展中长期保持着统一的趋势。美籍学者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就指出:“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此后以统一为常情为正轨,分裂为变态为异道,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尽管经历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大一统的王朝却是最基本的、主流的政治形式,具有很大的稳定性。相比之下,南北分裂、东西对峙,地方割据、政权鼎立等乱局所占的时间则要短的多,它们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大一统的王朝版图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其发展不均衡、形态有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和因素把这么多民族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相关的。纵观历史,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几千年来可以说没有中断,始终进行着。从现有文化遗物来看,中华大地上的多元文化群落间的渗透和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自发地开始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方面的内容更是史不绝书。在先秦时期的《礼记》等古籍中就最早记录了这种多民族的互动关系。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华大地就是华夏、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等“五方之民”的互动场域。周边民族对中原“诸夏”的渗透和交融,而中原“诸夏”对周边民族的辐射与吸纳,这两种影响一直在发生着作用,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基本的动力,并最终造成统一国家的基本格局。
我国学术界,已经大体上取得这样一个共识,即: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史,从民族的角度来说,就是一部民族关系史,一部民族之间的互动历史。贯穿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的中华各族由分散、接触、冲撞,走向交流、混杂、融合,最终形成一体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概念,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多样性构成多元,统一性构成一体,这是对中国历史中民族互动、文化交融、国家统一的一个高度总结,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基本特点提供了一个把握全局的总思路。所以说,“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基础。
二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互动过程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其中有和平交往的一面,如文化经济的交流、迁徙、移民、屯垦、贸易、通婚、和亲、设置郡县、羁縻安抚、杂居、融合,等等;又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如掠夺、战争、征服、奴役、分化、割据、压制、歧视、强迫同化,等等。在这当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也往往是混杂在一起,此外又有动机和效果的矛盾与统一,总之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关于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主要是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是主流;另一种认为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是主流。这两种观点的争论,各自都举出若干史实作为依据,长期以来见仁见智,论辩不休。随着争论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都没有能够准确地表达出主流的内涵。既然是主流,就应该是本质的反映。这个问题最深刻的内涵实质是中国这么广袤的地域,这么众多的民族,这么差异明显的生存环境,为何终于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像与其地理范围相似的欧洲那样形成为许多单一的民族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有关研讨会上,老一辈的民族史学家以明快的语言对此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证。如翁独健先生指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与互动,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白寿彝先生认为:“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以上观点堪称高屋建瓴,透彻、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各民族之间虽然时和时战,时战时和,但总是越来越趋向于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越来越趋向于统一,成为一种历史潮流,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民族史学研究的更加成熟。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觉得以上观点仍对我们探讨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为什么各族之间存在着这种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历史上民族关系尽管表现在许多方面,而经济关系是最本质、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随着各自经济生活的不断扩大,必然逐步形成互相需要、产品交换的依赖关系和带有地区分工性质的供求关系。民族关系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是各族之间经济利益的存在和发展。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市、通贡,甚至强行掠夺,连成一个互相补充的经济整体,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成为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和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边疆地区的畜牧业经济也成为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各自都需要,不可或缺。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的和与战,一般都是为了达到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经历了数千年的各种考验而持续存在,成为民族关系的牢固纽带和坚实基础。
对于这一点,我在自己所从事的北方民族史研究中也有所体会。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就宏观而言,涵盖着一个十分广阔而久远的时空范围。回溯中国历史,展现在你面前最多的画面,可能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对垒和碰撞。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最突出甚至是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可以这样说,这种矛盾从中华民族国家形成开始,几乎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结束。农耕和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形式,具有明显的差异。经济上的区别往往导致政治上的较量和军事上的搏斗。南北双方为争夺生存空间时常引发出剧烈的冲突、碰撞乃至战争。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同样存在着以暴力书写的历史。但历史又是充满辩证法的。与碰撞与冲突相携而来的,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强以及农耕游牧两大民族群体的交往、融合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由多元逐渐趋于一体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碰撞和互动来完成的,这一过程虽然充满了战争和暴力,或者说是用血和火书写了那段历史,但这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和渠道,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伴随着血的飞溅和火的闪亮,还有更经常的双方民众的迁移、官方使队的来往和边市贸易的繁荣,正是多种因素的交合作用,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最终统一起来。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用“民族重新组合”这一具有科学含义的术语,来处理胡汉之间民族的交融混化及历史变迁。着重指出民族的重新组合乃至融合,并非平面式、静态的配列,而是经由激烈的历史震荡来完成的。历史的负号性中蕴育着正号性,恰是“民族矛盾的机会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条件也增多了”。这样来观察分析问题,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民族互动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融与认同。文化乃是人类各种劳动创造成果的总和,有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有文化的生成和延续。正如费尔巴哈所讲的,人类就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完全不受外在文化的渗透,纯粹依靠内部的新陈代谢,实现封闭式的自我更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来说,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或文化冲突是整个人类进化史上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们中国的情况概莫能外,甚至更为突出。在中国多民族源流交错、杂居相处、频繁互动的历史大环境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会是单线、孤立发展的。南北方也好,东西方也罢,各个民族之间总要产生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渗透以至相互融通。除了强制性同化之外,这种互通现象,是一个自然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促进作用。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认同性,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生活,彼此吸收对方的文化成果,文化的融合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基础,各民族之间发展起持久而巨大的亲和力、凝聚力。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化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构成的,中原定居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两个基本类型。尽管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形成了众多文化区域,但这些区域均可以用农耕和游牧来加以划分。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史,其实就是以“耕”为核心的文化和以“牧”为核心的文化碰撞、交流、演进乃至认同的历史过程。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农耕和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他们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汇成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这一段话,我认为和费孝通先生所说“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的论断可说是异曲同工,都是认为只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中国文化。自中国文化形成以后,就以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结合为基本结构,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胡风汉制、夷夏并用、二元一体等等,不但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且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和深层根源。
“文化认同”是个包含许多内容的大题目。在这方面,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例如,何谓“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与“汉族文化”具有何种关系?能否等同?再比如,宗教在民族整合、文化认同中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文化认同?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认同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我个人在思考这一论题时产生的若干疑问,提出来就教于大家。希望能看到一些新的有建树性的理论观点。
三
理论和学术的发展,总是在它的内部不断地产生着矛盾和问题,从而也会不断地出现治学研究中的生长点和空白点,发现并解决这些新的问题,或者寻求新的视角、新的层面提出问题,列为选题,深入研究,就能把原来的理论和学术推向前进。在这方面,翁独健、白寿彝、费孝通等学界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生前曾反复强调的“在学术领域里是没有止境的”,“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等话语,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只要真正地继承和发扬这种不尽的探索精神、科学创新的精神,就会推动中国民族史学的进步,富有创见的科学成果就会不断地涌现。
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灵魂。相对于历史学科或民族学科整体来讲,民族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有着它独特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点,需要进行理论的概括来加以说明。毋庸讳言,民族史学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建设方面相对来说还显得薄弱。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民族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宁夏大学的陈育宁教授在这方面曾做过重要的开拓性工作,他的《民族史学概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探索》等书都很有影响力。烟台大学崔明德教授的《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隋唐民族关系初探》等专著,也都是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研究的力作。这些著作的问世,可以说是填补了当时的学术空白,具有拓荒性质,为我们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史学的理论研究建立了范式。此外还有一些学术论著也涉及到民族史的理论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是在民族史研究总的成果中,具有理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所占数量还是比较稀少。随着民族史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被提了出来。探讨和回答这些问题,成了民族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我们这次的“历史上民族互动和文化认同”就是一个具有较强理论色彩的主题。相信通过大家的认真研讨,一定会对民族史研究的深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会更加彰显出理论的概括、总结和指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