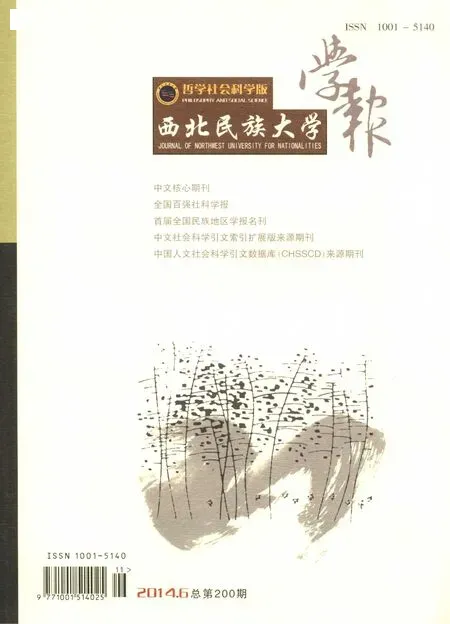试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的发展
张虽旺,王启龙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1)
宋代(960年-1276年)是我国历史上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各教派逐渐产生发展,并且竭力传播扩大各自教派在藏区的影响。藏传佛教各教派发展的状况在藏传佛教史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然而,对于处在“汉藏黄金桥”的河湟流域,佛教的发展不仅汉文史籍缺载,而且藏传佛教史上也鲜有记载,即使专门记述安多地区佛教发展的《安多政教史》[1]也只是对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关键人物拉钦贡巴饶赛和其他藏传佛教书籍一样做了简单的交代。那么,处在“汉藏黄金桥”交通要道的河湟流域,佛教的发展在宋代状况如何,宋代河湟流域又是在藏族唃厮啰政权和北宋、西夏、金轮流控制下的藏、汉等多民族杂居地区,这里佛教的归属是否应属于藏传佛教?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史料、资料的梳理,分析了宋代河湟流域的佛教发展历程。此一时期,河湟流域的佛教发展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着,一是汉传佛教继续传播;另一传播途径是在藏族中用藏语传播的深受汉传佛教禅宗影响却不同于藏传佛教的佛教发展道路,可将其归为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①任道斌主编《佛教文化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页。陈兵主编《新编佛教辞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第2-7页。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42-2348页。此处的藏语系佛教在实际意义上不同于辞典上对藏语系佛教的解释,是指藏传佛教各教派传入河湟流域以前在河湟流域藏族中使用藏语传播的佛教。辞典上对藏语系佛教的解释一般又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教。西藏佛教或藏地佛教属藏语系佛教。而宋代河湟流域藏族中使用藏语传播的佛教无法归入藏传佛教体系之内。
一、吐蕃佛教(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对河湟流域的影响
吐蕃时期的佛教发展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被称为藏传佛教“前弘期”。在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的传播还处于启蒙阶段[2]。即使如此,佛教在吐蕃的发展还是经历了一个传入、弘传和灭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在吐蕃社会的影响程度如何,对河湟流域的佛教发展又有何影响?
佛教在吐蕃的发展过程是与汉传佛教紧密相关的。“吐蕃佛教伊始就与汉地佛教紧密相关”,“唐朝佛教同吐蕃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吐蕃佛教的初传、创立和发展均与唐朝佛教有关”[3]。即使在“顿渐之诤”中,汉传佛教输于印度佛教,吐蕃佛教仍然深受唐代佛教的影响[4]。吐蕃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还始终存在着佛教和苯教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表面上看是佛教和苯教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吐蕃社会从奴隶制到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王室和贵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佛教就是在这种权力斗争中被王室通过联姻的方式引进的。松赞干布时期通过联姻的方式从唐朝和尼泊尔引进了佛像和佛经,并且还修建寺庙,不过这些寺庙里既没有僧人,更没有僧团,只有一尊佛像来供人们祭祀。王统记和教法史也没有寺庙里有僧人的记载。佛法僧三宝具足是在赤松德赞时期形成的。《拔协》是一本专门记载赤松德赞时期发展佛教的书籍,这本藏传佛教史籍本身就是一个佛教在赤松德赞时期发展的证据。赤松德赞为发展佛教迎请寂护和莲花生进藏传法兴建了吐蕃时期第一座拥有僧人和僧团组织的寺院桑耶寺(779年)还剃度了“七觉士”(或译为七试人),并且颁布了兴佛法典。《拔协》和《贤者喜宴》记载当时桑耶寺有出家僧人300人。此后,在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时都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兴佛措施。但是,佛教在吐蕃的发展程度如何,藏传佛教史籍并没有像记载后弘期佛教发展那样详细的记载,说明了当时的佛教发展也是有限的。佛教经过赤松德赞、赤德松赞、赤祖德赞这祖孙三代赞普的努力,在吐蕃社会产生了一定范围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也只是在王室直接控制的伍茹和约茹,也就是今拉萨和山南地区。这一点可以从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和苯教之间辩论后赞普放逐苯教教徒到边远地区而得到佐证,也可以从赤得松赞时期留下的石刻碑铭中找到答案[5]。朗达玛灭佛事件说明了佛教在与苯教的斗争中暂时失败了,也说明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影响还是有限的。
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有限的,那么河湟流域是否受吐蕃佛教的影响?唐“安史之乱”以前河湟流域一直处于唐蕃之间的反复争夺之中[6]。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吐蕃遣使请和[7],唐、蕃举行鸿胪寺会盟,唐廷答应割让已被吐蕃战领的州郡,以岁输绢帛换取边境和平。至此,河湟流域处于吐蕃统治之下[8]。而此时正是吐蕃赤松德赞(755年-797年)在位期间,佛教开始在吐蕃发展。赤松德赞迎请印度的寂护、莲花生来藏传播佛教,同时也从西域和唐朝迎请汉传佛教禅宗僧人进藏传播佛教。敦煌文献《顿悟大乘正理决》载,贞元年间,吐蕃“于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①(唐)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决》,见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79)《汉藏佛教关系研究》,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华宇出版社,1984年第815页。“摩诃衍(即大乘和尚)是将汉地禅学传入吐蕃的第一位僧人”[9]。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诱、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10]《莲花生传》载,入吐蕃的译经汉僧有“帕桑、玛哈热咱、德哇、玛哈苏扎、哈热纳波、靡诃衍及毕洁赞巴”[11]。有研究表明,顿渐之辩之前到吐蕃的汉僧有34位之多[12],另外在战争中俘获大批汉族僧尼[13]。《旧唐书》载,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夏四月,庚申先陷蕃僧尼将士八百人自吐蕃而还。”[14]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八月“辛巳,没蕃僧惟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自蕃中还”[15]。如此众多的汉僧在吐蕃活动,充分说明汉传佛教在吐蕃的影响。此时吐蕃佛教的发展主要是接受外来佛教的影响,翻译佛经。桑耶寺的建成标志着吐蕃有了自己的佛教系统[16]。经过赤得松赞和赤德祖赞时期的大力发展,佛教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佛教僧人大多忙于参与吐蕃内部的权力斗争,对佛教的发展倾注的力量不多。藏文史籍中对译经和译师的情况有所记载,而对于佛教发展的规模却少有记载。朗达玛灭佛说明佛教最终没能在吐蕃时代发展壮大,向外传播就更不用说了。再者,从今安多藏语较多的保留了古藏语的事实,也可从侧面说明在赤得松赞和赤祖德赞时期进行的针对译经规范化的文字改革尚未影响到安多地区时,吐蕃王朝就崩溃了,吐蕃佛教的影响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在《安多政教史》中说:“圣教在多麦地区的弘传,虽然没有前弘期与后弘期之分,但毫无疑问在前弘期时,许多智者、成就大师、法王和大臣们以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为众生作过弘法传承,这是存在的事实。”[17]据敦煌历史文献记载,吐蕃晚期以及晚唐五代时期确有吐蕃高僧在敦煌地区活动[18],不过在盛行汉传佛教的敦煌地区活动也只能算是汉蕃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作为管理敦煌佛教僧团的僧官[19],在信奉苯教的藏民中影响也不大,在汉传佛教流行的河湟地区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河陇地区佛教界汉地禅宗有很大势力和影响。敦煌所出755年以后的禅宗经典和语录,证明禅宗在天宝朝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授。这些经典大约有二十部左右。”[20]
吐蕃佛教对河湟流域产生影响是在朗达玛灭佛措施以后,吐蕃僧人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部分僧人不得不远遁他乡,寻找生存的空间,河湟地区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吐蕃禅僧[21]藏·饶赛、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僧[22]。藏文史籍倾向于说许多僧人流离到多麦、多康地区继续传播吐蕃佛教,然而,根据拉钦贡巴饶赛(公元831-915年)①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年代和拉钦贡巴饶赛生卒年历来有两种看法:918年,831-915年;978年,892-975年。两种看法都存在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历史上藏传佛教史家为了佛教法统的连续和记年不清而造成的结果。842年朗达玛灭佛和1042年“上路律传”已基本达成共识。如果按918年,831-915年之说,拉钦贡巴饶赛随藏、约、玛出家、学法就没有疑问,问题之一是按云丹生于842年,云丹六世孙也应生于942年前后,鲁梅等随拉钦贡巴饶赛出家以及鲁梅等受到云丹六世孙支持或接待的时间就产生了矛盾;问题之二是918年到1042年之间有124年的时间,过了124年“上路律传”才开始,说明了“下路律传”在卫藏地区传播的艰难,影响之有限。佛教史家记载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佛法与前弘期的连续。如果按978年,892-975年之说,拉钦贡巴饶赛于906年受戒,三僧已经将近百岁,可能性不大。因此,合理的解释是拉钦贡巴饶赛生卒年是831-915年,鲁梅等人是“从喇钦贡巴绕色的亲传弟子巴贡·意希雍仲的弟子仲·意希坚赞受戒出家”,(东噶·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7-28页。)受到云丹六世孙支持或接待,后弘期于978年开始。如此之说,978至1042年之间也有64年的时间,也说明“下路律传”在卫藏地区传播的缓慢和前弘期吐蕃佛教在吐蕃社会影响之一般。(在今化隆)受比丘戒时(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无法凑足五名授戒师,而不得不邀请两名汉僧的事实[23],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朗达玛灭佛以后,出逃到多麦、多康地区的吐蕃僧人数量是极少的,至少是具有授戒和传教资格的高僧数量是有限的;另外,吐蕃佛教也没有在河湟流域造就具有授戒和传教资格的高僧;再者,拉钦贡巴饶赛应是河湟地区皈依佛教第一人,这是因为三僧在河湟地区数年,似乎没有遇见信佛的吐蕃人,直到拉钦贡巴饶赛皈依佛教。同时也说明了吐蕃移民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已经开始接受佛教了,而在此之前信奉苯教的吐蕃移民尚未接受佛教。《西藏通史》说,藏·饶赛、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僧“经过多麦南部的毕日地区盐湖抵达了玛龙多吉札丹顶西寺。当地人看见着僧衣的僧人时感到惊诧,都说未遭到恶王惩治的僧人出现于此,因而惊惶地逃到附近森林中。”拉钦贡巴饶赛受戒以后,继续外出学法,从事宗教活动。因听说卫藏地区发生灾荒,其进藏学法也就无法成行,自然所学佛法应是跟随受禅宗影响的僧人学法居多的可能性较大。即使是跟随藏族僧人学法[24],其所学佛法的地域也应是深受禅宗影响的。拉钦贡巴饶赛54岁(一说49岁[25])返回丹底寺,“到了丹底寺后发现这里有许多自称为顿悟的瑜伽人,这些人不做善事,专行相悖于佛教之恶行,为了阻止邪见,修建了众多的庙宇和佛塔”[26]。从拉钦贡巴饶赛受戒学法的过程看,在有深厚汉传佛教基础的河湟地区,吐蕃佛教对河湟流域的影响是以掺杂大量汉传佛教禅宗的影响为主,况且“吐蕃佛教伊始就与汉地佛教紧密相关”[27]。“公元940年(应为880年),公巴饶萨四十九岁时返回故里,定居丹笛,广建神殿佛塔,传教弘法,先后收巴贡·益希雍仲、仲·益希坚参、粗·喜饶却等著名弟子十余人。”[28]“喇钦的6名高足弟子之一的巴贡意希雍仲给仲意希坚赞授戒。仲意希坚赞给卫藏十人授戒。”[29]
鲁梅等人是于公元978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从喇钦贡巴绕色的亲传弟子巴贡·意希雍仲的弟子仲·意希坚赞受戒出家”[30],“据说受戒时,仍有汉僧作尊证师。”[31]史籍记载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吐蕃潘罗支和唃厮啰政权时,吐蕃移民的后代已较广泛的接受了佛教。从河湟地区佛教发展的过程看,吐蕃移民的后代所接受的佛教以汉传佛教为主,只是在修炼佛法的过程中加入了他们自己的修炼方法。在今青海省平安县城湟水对岸有白马寺(古称玛藏岩寺)以及今化隆县境内的丹斗寺(亦称丹底寺)的洞窟中都有壁画的残存,据研究认为都具有宋代的风格[32],根据著者的文意来看,此处宋代的风格应是指藏传佛教的风格,也就是说这些壁画制作于唃厮啰政权时期。虽然此时藏传佛教正在形成中,且远未开始传播到河湟地区,但是由藏族僧人所画的具有早期藏式风格的壁画是应该存在的。
二、宋代河湟流域汉传佛教的传播
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的影响,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民众基础,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重建显庆寺碑记》载,“自佛之来西域也,河湟实为首被教化之地。”[33]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隋朝两代皇帝对佛教的传播也是极力弘扬。汤用彤先生认为,隋代佛教史上有两件大事,“一关中兴佛法,一舍利塔之建立。”[34]《法苑珠林》载,“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35]隋朝两代皇帝修建了数千座寺庙,如果说在河湟地区的西平郡、枹罕郡、金城郡、浇河郡、临洮郡以及河源郡等都没有修建一座寺庙似乎是不可能的。史料阙如,无法佐证。炳灵寺石窟第8窟隋代佛像雕塑及供养人壁画可以作为隋代河湟地区佛教发展的证据。今西宁北山寺石窟内中窟内的壁画佛像画具有隋代的风格[36]。
虽然唐代的基本国策是崇奉道教,但唐代却是我国“佛教盛世”时期。河湟地区的佛教发展也从未停止,唐代前期河湟地区的寺庙见于史籍记载的有5座,其中兰州1座、河州3座、廓州1座,唐后期河州有1座寺庙[37],这里没算上兰州的炳灵寺,清代兰州的嘉福寺也是建于唐代[38]。根据史籍所载唐代寺院的数量来看,史籍缺载的河湟地区较小规模的寺院当然还有不少。“喇勤之前,整个安多地区,没有完整的寺院组织”[39]的说法看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今西宁北山寺石窟的两尊露天金刚像具有唐代风格,东窟内的佛像画具有唐和五代的风格[40]。炳灵寺石窟众多的唐代雕塑和壁画像也是河湟地区佛教繁盛的证明[41]。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下令各州(包括长安和洛阳两京)建大云寺一座。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第1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0页。(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690年)》,第14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9页。其中很多寺院可能是由原来的寺院改名而来的[42]。河湟地区的鄯州、廓州、河州、兰州应当都建有大云寺。大云寺的寺名后来有所改变,唐中宗时将大云寺改名为中兴寺[43],后又于公元707年改为龙兴寺[44],唐玄宗时大云寺又改名为开元寺,不过一些地方大云寺依然存在[45],今甘肃成县(唐陇右道成州同谷县)仍有大云寺便是一例[46]。唐玄宗还是密教的第一位支持者,善无畏、金刚智、一行、不空等密宗大师的活动都得到他的支持[47]。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曾请不空住河西武威(唐凉州)开元寺传播佛法[48],并为“士庶数千人”做了密教的灌顶仪式[49]。当时哥舒翰领兵防范吐蕃,河湟地区的守军也归其统帅,因此佛教在河湟的军士及庶民中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哥舒翰奉命率军回师保卫长安,河湟之地空虚,吐蕃势力乘虚而入,占领河湟,并且迁移部分吐蕃部落移居河湟地区。吐蕃移民的到来,也带来了苯教。如前所述,河湟地区的民族融合处在“汉化”、“吐蕃化”的民族化过程中。河湟地区的汉族依然存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佛教依然是河湟居民的主要信仰,并且也对吐蕃移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吐蕃时期青海地区已有较好的佛教信仰基础”[50]应是指汉传佛教的信仰基础,而非吐蕃佛教的影响。“河陇地区佛教界,汉地禅宗有很大势力和影响。敦煌所出755年以后的禅宗经典和语录,证明禅宗在天宝朝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授。这些经典大约有二十部左右。”[51]史籍记载,唐后期河州仍有1座寺庙[52]便是最好的说明,兰州炳灵寺的存在更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宗喀东部的汉族佛寺仍旧存在。”[53]《安多政教史》根据传说认为赤祖德赞(赤热巴巾)曾经率军到过廓州(今贵德),并建了一座装有其头发的佛塔[54]。赤祖德赞是否到过今青海贵德尚难定论,但当时那里建有佛塔是可能的[55]。今天贵德藏式佛塔“乜纳塔”的建造时间尚无确定,因此,当时的佛塔完全有可能是汉传佛塔,元明以后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盛行之后才建造藏式佛塔“乜纳塔”的可能性最大。拉钦贡巴饶赛(831年-915年)受戒时(846年)无法凑足五名授戒师,而不得不邀请两名汉僧的事实[56],说明了当时还有不少具有授戒资格的僧人在河湟地区传播汉传佛教,同时也说明了吐蕃移民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已经开始接受佛教了。对于这两位汉僧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他们来自今化隆县(唐时属鄯州,吐蕃时期属鄯州节度衙)东之堤巴静修院[57];一种认为来自今西宁附近[58];一种认为来自兰州[59]。虽然观点不一,但应该都不是空穴来风,西宁、兰州有寺院自不待言,当时的东之堤巴静修院也应是事实,说明了今化隆县区域内在唐以及唐后期一直有汉僧在活动的历史事实。当鲁梅(又译卢梅)等十人于公元978年到丹底寺(又译为丹斗寺)学习佛法时,“据说受戒时,仍有汉僧作尊证师。”[60]这时已是宋朝初期。史籍记载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吐蕃潘罗支和唃厮啰政权时,吐蕃移民已较广泛的接受了佛教。
汉藏史籍对于宋代汉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状况缺乏记载,《青唐录》和《岷州广仁禅院碑》所载的只是河湟地区民众中信仰佛教的状况。现代研究表明,这里的人民还是以汉族为主。史籍也有汉僧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记载,藏文史籍所载拉钦贡巴饶赛受戒时邀请两名汉僧的事实说明了汉传佛教继续存在。北宋占领河湟以后,“智缘与海渊都利用其僧侣的特殊身份,沟通了甘肃地区汉蕃人民的感情,增进了汉蕃人民的来往,密切了双方关系,而且也使汉僧的宗教权威最大限度得到了当地蕃部尊崇。”[61]即使是吐蕃化的那部分汉人中,对佛教信仰传统的坚持也是有惯性的,再加上藏族(唃厮啰)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又无佛教内部的斗争,只有在传教过程中语言的区别和显密的区分,汉传佛教在河湟流域的继续传播就没有障碍了。
三、宋代河湟流域藏族中佛教的传播
《青唐录》记载了唃厮啰政权青唐城的寺院建筑情况,“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河,水西平远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冈垣,屋至千余楹,为大象,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三十级以护之。阿里骨敛氏作是像,民始离。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触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半,维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号主之宫室亦土覆之。”[62]宋《岷州广仁禅院碑》载,“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之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鴃舌之不可辩,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间,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日坐禅,是其心岂无情粹识理者,但世莫知之耳。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非中土之教为之开示提防而导其本心,则其精诚直质且不知自有也。”[63]从这两则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唃厮啰政权时期佛教在河湟流域藏族中信仰的程度。
宋代河湟流域藏族中传播的佛教始于何时,藏文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关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年代,蒲文成先生在《关于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分歧》[64]一文中,针对藏文史籍所记载的史料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年代应为978年。也就是说,除多麦、多康、阿里以外的藏区,即西藏中心地区的佛教再次传播从此开始。那么,河湟流域用藏语传播的佛教始于何时?见于藏文史籍的记载也就是从拉钦贡巴饶赛开始,即拉钦收徒之年开始,当然,在此之前也应有到河湟流域用藏语在藏族中传播佛教的藏族僧人的可能,在敦煌被汉族人称为“吴和尚”的藏族译师管·法成可以作为旁证。不过,从拉钦贡巴饶赛是苯教徒一事说明了吐蕃佛教影响的微弱。就河湟流域来说,一方面原有的佛教是汉传佛教,另一方面是吐蕃占领期间带来了苯教。拉钦贡巴饶赛的出身就是苯教家庭[65],说明了吐蕃向河湟流域迁移部落的同时,苯教也随之而来。而“吐谷浑人有原始的巫术,后期也信奉佛教。”[66]拉钦贡巴饶赛生活在佛教盛行的地区,自然对佛教早有了解。
河湟流域的藏族是在唐朝中期以后迁移到河湟地区的藏族同当地的汉、吐谷浑、羌等民族逐渐融合形成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哥舒翰调离青海。吐蕃以助平国难为名,乘虚先占西平,再占廓州,然后进入陕甘地区,河西、陇右全被占领,从此河湟地区脱离中原王朝的管辖,由吐蕃控制。762年又通过会盟的方式迫使唐廷答应割让已占领的州郡,至吐蕃分裂,河湟流域一直在吐蕃王朝的管理之下。
吐蕃控制河湟流域以后,逐步将一些藏族部落迁移到河湟地区,同时迫使河湟本地的吐谷浑、羌、汉等民族人民变为奴隶,实行强制同化政策。但是,“河、陇其他地区的汉人,也没有全部沦为吐蕃的奴隶。”[67]至宋代唃厮啰政权时期,河湟流域已经是藏族部落占据多数。由于河湟地区佛教盛行,河湟流域信奉苯教的藏族人民自然要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不过,佛教在河湟藏族中传播却始于拉钦贡巴饶赛,之后唃厮啰政权时期佛教更加盛行。
宋代河湟流域的藏族民众信仰的佛教是否应该属于藏传佛教,祝启源先生在其著作《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中也没有给予明确的定性。蒲文成先生说:“唃厮啰政权时期藏传佛教的派属问题,因限于资料,向来缺乏深入研究,至今尚无定论。”[68]根据《新编佛教辞典》和《佛教文化辞典》[69]对藏传佛教和藏语系佛教的解释,唃厮啰政权时期的佛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定义的内容。但从其传播时间和藏传佛教教派产生的时间上来说,河湟流域的佛教在藏族中传播从拉钦贡巴饶赛开始,在时间上早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各教派的产生,因此,就无法归入藏传佛教教派之内。“当时唃厮啰时期的佛教虽尚未正式形成藏传佛教的教派,佛教徒偏重于念经、坐禅、辩经等宗教活动,戒律较松弛放纵,严格的教规尚未完善,但从藏传佛教发展的整体历史看,属于所谓‘旧派’的宁玛派,并因所处地域毗连内地,受汉地禅宗的影响较深。”[70]如果将其归入宁玛派的发展行列,又与宁玛派的传承在史籍中找不到渊源。但是,宋代河湟流域藏族民众中传播的佛教是用藏语在传播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可将其归入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
河湟流域的藏族政权灭亡之后,北宋控制了河湟流域。“熙河地区,吐蕃部族众多,由于蕃俗佞佛,因此宋朝以佛事怀柔羁縻笼络,借助宗教这一精神武器征服笃信佛教的吐蕃部族。”[71]宋朝就是借助佛教、广建佛寺、重用僧侣来对河湟流域的藏族进行统治的。同时汉僧也在这一地区不断活动,“智缘与海渊都利用其僧侣的特殊身份,沟通了甘肃地区汉蕃人民的感情,增进了汉蕃人民的来往,密切了双方关系,而且也使汉僧的宗教权威最大限度得到了当地蕃部的尊崇。”[72]
1127年宋室南迁,西夏、金分治河湟流域。金统治者所统治的河湟地区,由于北宋的影响,佛教也在继续发展,并且金朝在对佛教的管理上基本沿袭了唐、宋的僧官体制。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至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县西南)天宁寺雕刻汉文大藏经,即后世所谓的《赵城藏》(也称《金版大藏经》)。在金统治河湟区域内的藏、汉民众中佛教也在继续传播。
西夏的统治者对佛教也是极为推崇。史载仁孝(1124年-1193年)在其60大寿的1184年大作佛事活动,广印佛经彩画。这次印经、施经的活动在乾祐二十年(1189年)印施的汉文发愿文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有详细记录。法会上有宗律、净戒、大乘玄密三位国师和禅法师等重要僧人参加,诵读藏文(西番)、西夏文(番)、汉文佛经,还散施西夏文、汉文佛经共达20万卷[73]。三位国师的族别,史金波先生在《西夏佛教史》中说可能是藏族僧人。陈庆英先生考证了大乘玄密帝师的出身,认为他可能是西夏藏族,也可能是党项人[74],曾到印度学习佛法12年,并且还认为大乘玄密帝师是米拉日巴的再传弟子,也曾在萨迦派的祖师萨钦贡噶宁波(1092年-1158年)前学习过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和萨迦派的教法就是在仁孝时期进入西夏王国的。藏文文献《贤者喜宴》对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进入西夏也有记载。王尧先生考证了西夏黑水桥碑立于1176年,碑刻藏文“文字已经规范,绝少不合正字法的书例”[75],也说明了后弘期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影响。不过藏传佛教噶举派和萨迦派传入西夏是在西夏后期,距西夏灭亡只40余年,河湟流域又远离西夏的佛教中心,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西夏佛教是否能对河湟流域产生影响史籍缺载,也只能说可能产生了影响。
藏传佛教宁玛派在康区开始传播是由噶丹巴·得协(1122年-1192年)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建成的噶陀寺开始的,该寺地址在今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的河坡乡境内。噶丹巴·得协是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17岁入藏学习宁玛派教法和《幻网经》等法类[76],不过是否影响了河湟流域史籍没有记载。
根据蒲文成先生的研究,藏传佛教开始在河湟流域传播已经是宋末元初,最早是学经于萨迦派的西纳格西。阿底峡开创的噶当派传入河湟流域是在元代,始自宗喀巴的上师顿珠仁钦(1309年-1385年),他于1349年在今化隆县查甫乡修建了夏琼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杰(1240年-1383年)应元顺帝召请,1359年路经青海,在祁家川的夏宗静房曾为宗喀巴授近事戒,并一度在今佑宁寺一带居住活动。见于文献记载,河湟流域颇有影响的早期噶举派寺院是位于今乐都县曲坛乡,由三罗喇嘛(?-1414年,法名桑杰扎西)于1392年修建的瞿县寺[77]。
处于“汉藏黄金桥”紧要位置的河湟流域是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发源地之一。研究藏学的学者们一般笼统的将宋代河湟流域佛教归为藏传佛教。针对宋代河湟流域佛教的归属问题,由于史料的限制,一直以来缺乏深入研究。蒲文成先生无奈的将唃厮啰时期的佛教归入藏传佛教“旧派”宁玛派,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从河湟流域佛教产生的时间看早于宁玛派,从其传承来说又与宁玛派毫无瓜葛。笔者通过对宋代唃厮啰政权时期及北宋、西夏和金时期佛教在河湟流域传播的时间、范围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宋代河湟流域的佛教发展有两种不同的方式,首先是汉传佛教继续传播,而另一传播方式是在藏族中用藏语传播的深受汉传佛教禅宗影响但不同于藏传佛教的佛教,即历史上的藏语系佛教。河湟流域在藏族中传播的佛教融入藏传佛教序列自元代开始,特别是明末清初时期,随着藏传佛教教派在河湟流域的传播,河湟流域藏族中传播的藏语系佛教也就逐渐融入藏传佛教体系了。
[1][22]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M].吴均 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2][4][12]索南才让.唐代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5).
[3][9][11][16][20][27][51]黄颢.唐代汉藏文化交流[A].藏学研究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198,201,200,199,200,198,200.
[5]张虽旺,王启龙.从赤德松赞时期的石刻碑铭看佛苯并存状况[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5).
[6]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26-32.
[7][宋]肃宗本纪[A].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6)[C].北京:中华书局,1975.165.
[8]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32.
[10]苏晋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Z].萧鍊子 校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212.
[13]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30-31.
[14][15][后晋]德宗上[A].刘昫.旧唐书(卷12第2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5.332,422.
[17][54]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M].吴均 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22,22.
[18][英]F·W·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M].刘忠,杨铭 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9]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J].中国藏学,2005,(2).
[21]蒲文成.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J].青海社会科学,2000,(6).
[23][24][26][56][65]恰白·次旦平措.西藏通史——松石宝串[J].陈庆英译.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248,23,248,248,248.
[25][50][55][58][68][70]蒲文成.青海佛教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26,26,26,26,36,37.
[28][64]蒲文成.关于西藏佛教前后弘期历史年代分歧[J].西藏研究,1982,(3).
[29][30]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M].陈庆英 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27-28,27-28.
[31][32][53][57][60]吴均.论拉勤贡巴饶赛[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1).
[33][清]寺院[A].龚景瀚.循化厅志(卷6)[C].李本源篡修.台湾: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143.
[3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3.
[35][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100)[M].周叔迦苏晋仁 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2894.
[36][40]赵生琛,谢端琚.青海古代文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158,158.
[37][52]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89,89.
[38]四部丛刊续编史部.嘉庆重修一统志(第十六册卷252·兰州府)[Z].北京:中华书局,1986.
[39]吴均.论拉勤贡巴饶赛[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1).
[4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42][44][45][47][49][美]斯坦利·威斯坦因.唐代佛教[M].张煜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7,50,57,57,59.
[43][宋]唐纪二十四·中宗景龙元年(707年)(第14册)[A].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8)[C].[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6610.
[46]管卫中.大云寺与武则天[J].档案,2013,(3).
[48][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目录部》卷2157)·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5)[Z].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881.
[59]吴均.吴均藏学文集(上)[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87.
[61][71][72]刘光华,齐建丽.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144,143,144.
[62]孙菊园.青唐录辑稿[J].西藏研究,1982,(2).
[63]汤开建.宋《岷州广仁禅院碑》浅探[J].西藏研究,1987,(1).
[66]周伟洲.吐谷浑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29.
[67]杨铭.试论吐蕃统治下汉人的地位[J].民族研究,1988,(4).
[69]陈兵.新编佛教辞典[Z].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2-7.
[73]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41.
[74]陈庆英.西夏大乘玄密帝的生平[J].西藏大学学报,2000,(3).
[75]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2).
[76]蒲文成.元代的藏传佛教宁玛派[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77]蒲文成.藏传佛教诸派在青海的早期传播及其改宗[J].西藏研究,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