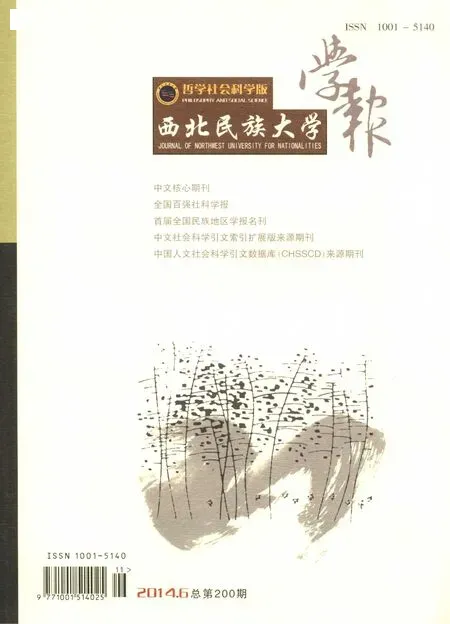浅析《后汉纪·孝殇皇帝纪》西域史料价值
颜世明,高 健
(1.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新疆大学 图书馆,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东汉兴元元年(105年)和帝病逝,刘隆以百天幼童即位,在位八个月即病亡,庙号孝殇皇帝。殇帝享国日浅且尚未亲政,加之东汉史料皆以范晔(398年—445年)《后汉书》为尊,以致袁宏(328年—376年)为之所撰本纪一直受后人冷落。惟周天游从辑佚学角度,指出《后汉纪·孝殇皇帝纪》(以下简称《殇帝纪》,其引文均析自《后汉纪》张烈中华书局点校本[1],文后直接注明页码)以“本传曰”形式保留《东观汉记·西域传》一则佚文[2],杨共乐指明其中囊含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路线[3]。按袁宏《后汉纪》较范晔《后汉书》成书时间至少要早50年,故袁纪之中保存诸多东汉时期原始资料,如《殇帝纪》誊录“班勇所记”大秦国传文,即为厘清《后汉书·大秦传》史料来源提供线索,同时又可补苴《后汉书》西域史料之不足,现掇拾举出以就教大方。
一、《后汉书·大秦传》史料来源
《大秦传》为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的一篇传记,主要讲述大秦国地理位置、政治制度、风俗物产,是研究东汉与罗马帝国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后世《晋书·大秦传》《魏书·大秦传》《北史·大秦传》《新唐书·拂菻传》均以《后汉书·大秦传》为蓝本增改而来,其史料来源共计三说。
(1)沈约“删众家说”。在范晔《后汉书》成书之前,即有数种东汉史书并行于世,如《隋书·经籍志》著录东汉刘珍(?—126年)《东观汉记》,三国时期谢承(182年—254年)《后汉书》、薛莹(?—283年)《后汉记》,两晋时期华峤(?—293年)《后汉书》、司马彪(?—306年)《续汉书》、谢沈(292年—344年)《后汉书》、张莹(生卒年不详)《后汉南记》、袁山松(?—401年)《后汉书》、袁宏《后汉纪》[4]。梁朝沈约(441年—513年)《宋书》略载范晔《后汉书》成书经过:“(范晔)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5]据此而推范书是以东汉史书为基础删改而成,并未利用档案文书之类原始资料。沈约与范晔生活时代相近,南朝之时众家东汉史书尚存于世,且今将范书全文与《东观汉记》辑本进行比对,范晔照搬其文之处比比皆是,故沈约“删众家说”理应可信。
(2)范晔“转袭‘班勇所记’说”。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序言之中,确切言明西域诸国传记史料来自“班勇所记”。
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6]
班勇(?—127年)乃东汉名臣班超(32年—102年)少子,青年时生活在西域,并于安帝末、顺帝初出任西域长史,范晔《西域传》篇尾又评价“班勇所记”天竺国传文优点与缺陷:
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7]。
天竺国传记亦为《后汉书·西域传》中一篇,范晔评析内容与天竺国传文完全相符,其中隐含文意即出自班勇之手。然范晔《西域传》记事时间下限并非止于班勇生活时代(127年),如顺帝阳嘉元年(132年)敦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王击于阗,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于阗王攻破拘弥国,故范晔所言《西域传》全文皆转自“班勇所记”难令人信服,只可将范语理解为西域诸国历史地理及“异于班固”的风土、民俗为“班勇所记”,并不包括东汉王朝与西域诸国战和关系之类叙事。
(3)余太山、林英“删减鱼豢《魏略·西戎传》说”。鱼豢《魏略·西戎传》成书于魏末晋初,其中载有大秦国传文,与范晔大秦国传文行文相似且较之内容更为丰赡,余、林二人以鱼豢《魏略》成书时间在范书之前,藉此判定范晔《大秦传》系删减鱼豢之文而成[8-9]。《后汉书·大秦传》史料来源三说中,沈约“删众家说”已为古今治史者所证实,是说并无异议。范晔“转袭‘班勇所记’说”语出撰者自言,余太山、林英“删减鱼豢《魏略·西戎传》说”言之有据,范晔之古说与余、林之今说相互抵触,故厘清范晔《大秦传》史料来源的关键在于古说与今说的取舍,取舍之后尚需糅合沈约“删众家说”。《殇帝纪》亦详载大秦国传文,传文内容与范晔《大秦传》全文基本相同,少数文句为范书所不载,现将袁宏《大秦传》与范书相异之文节录如下,袁文有、范文缺的文句以[]标识。
和帝永元中,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临大海而还,[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而班勇亦见记其事,或与前史异,然近以审矣]。
大秦国一名黎轩,在海西。汉使皆自乌弋还,莫能通条支者。[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人谓英曰:“海广大,[水咸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风,时三月而渡;如风迟,则三岁。故入海者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具问其土风俗]。
大秦地方数千里,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种植树蚕桑。[国王]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軿白盖小车,出入击鼓,有旌旗幡帜。起宫室,以水精为柱及余食器。王所治城周环百余里,王有五宫,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宫听事,止宿;明旦复至一宫;五日一遍而复还。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民欲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会乃议事。王无常人,国中有灾异,风雨不时节,辄放去之,而更求贤人以为王,受放者终无怨。
[其长老或传言]:“其国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相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惊,而有猛虎、师子遮食行者,不有百余人,赍兵器,辄害之,不得过。”又言:“旁国渡海飞桥数百里。”所出奇异玉石诸物,多谲怪不经,故不述云,[西南极矣。山离还,自条支东北通乌弋山离,可百余日行]。
《殇帝纪》大秦国传文当为甘英出使大秦闻见录,以甘英询问、安息(即帕提亚波斯王朝)长老答复形式叙述大秦国历史地理概况,范晔则将《殇帝纪》中心人物甘英、安息长老略去,体裁由以叙述为主的记叙文转变为以描述为主的说明文。相比而言,《殇帝纪》大秦国史料更具有原始性,从中可窥探大秦国史料来源,即甘英抵达安息、欲使大秦受阻后,“具问其土(即大秦)风俗”,安息长老一一予以答复,后“甘英临大海而还(西域都护府驻地它乾城),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以禀复西域都护班超。“(甘英)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班勇亦见记其事”,此“事”当既包括甘英出使大秦之事,又当包含甘英所讲“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其理由有二:其一,《殇帝纪》、范晔《西域传》之中安息、大秦两国(以上二国均居葱岭之西)传文基本相同,按范晔之言安息、大秦国传文乃“班勇所记”;其二,范晔《西域传》载录西域诸国地域范围横跨葱岭之东西,西域诸国又“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殇帝纪》葱岭西“诸国”之事撰者当为班勇。由上可推范晔《西域传》“班勇所记”与《殇帝纪》“班勇记其事”内容或相同,甘英所述“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中大秦国部分,最终班勇将之载录史册,范晔省去其繁杂过程。
袁宏《后汉纪》序言之中,将编修《后汉纪》所依据史料简要说明: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掇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
袁宏《后汉纪》史料来源于九种文献:荀悦《汉纪》、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汉山阳公记》(汉山阳公即汉献帝刘协)、《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诸郡耆旧先贤传。作为《后汉纪》其中一篇,《殇帝纪》亦当据上述九种文献而撰。前揭《殇帝纪》又收录班勇所载大秦国传文,以此递推大秦国史料当存在“班勇所记”之中,而“班勇所记”全文或收存在上述九种文献之中某文献之内。综观《殇帝纪》之中“班勇记其事”及范晔《西域传》“班勇所记”,内容均涉及西域诸国交通、历史地理、风土民俗情况,其体例、内容类同班固《汉书·西域传》及后世正史《西域传》,故可揣度收录“班勇所记”某种文献,处理史料方式应如同范晔《西域传》:传文中西域诸国历史地理概况为“班勇所记”,而传记名称则冠以《西域传》之名,即判别某种文献是否收录“班勇所记”标准为是否专为西域立传,而袁宏所据九种文献之中,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四种纪传体史书之中或立西域传。
周天游将传世文献中所见九种《后汉书》传目及佚文裒辑而出(即《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张璠《后汉纪》、无名氏《后汉书》),九种《后汉书》之中惟有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曾专为西域立传[10-11],二书皆有可能收录班勇记文。无论由司马彪(?—306年)、袁宏(328年—376年)、袁山松(?—401年)生活时代,抑或袁宏自言所据9种文献,可知袁宏并未利用袁山松《后汉书》西域史料,而是采用司马彪西域史料可能性较大。故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可作如此推测:“班勇所记”全文收录在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之中。
再者,周天游辑录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有11佚文,其中关于大秦国佚文6条,6条佚文之中惟有2条佚文与范晔《大秦传》、《殇帝纪》不合: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甘菟”,范晔《大秦传》、《殇帝纪》均作“甘英”;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大秦国名犂鞮鞬”,范晔《大秦传》作“犂鞬”,《殇帝纪》作“黎轩”。可认为书籍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字、衍字,《殇帝纪》“黎轩”不妨视作沿袭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黎轩”称谓。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另外5条佚文中,“天竺国出珠玑”范书、袁纪均未涉及,“宁弥国王本名拘弥”范书、袁纪之中并未撰写宁弥国传记,故亦未曾言及,若将此理解成范、袁将之删去不录也可讲通。
魏末晋初鱼豢撰著《魏略·西戎传》(今已佚失不存),刘宋时期裴松之(372年—451年)斠注《三国志·魏志》将其部分内容纳入注文,鱼豢《西戎传》中大秦国传文较范晔《大秦传》、袁宏《大秦传》内容更为繁富,行文与范、袁二文相似,如:
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但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12]。
由前引《殇帝纪》节文,知本段传文乃安息长老告知甘英的大秦国概况,当出自“班勇所记”,鱼、袁、范三书大秦国类似传文尚有多处。故可揣测鱼豢《西戎传》首次全袭“班勇所记”,司马彪复将“班勇记其事”迻录《续汉书·西域传》,范晔《大秦传》则以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之中大秦传文为基础删改而成,并未亲观“班勇所记”,真正利用“班勇所记”这种原始史料乃鱼豢与司马彪。范晔大秦国史料来源可谓繁杂,可列图示以述其本末:

图1 范晔《后汉收·大秦传》史料源流示意图
故《后汉书·大秦传》史料来源三说中,沈约“删众家说”理应可信,范晔“转袭‘班勇所记’说”省略史料来源繁杂过程,亦是有案可稽,余、林“删减鱼豢《魏略·西戎传》说”值得商榷。同时安帝永宁元年(120年)日南国献大秦幻人[13],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朝贡[14],东汉王朝与大秦国正面接触必然会加深对大秦国认知,亦可视作范晔《大秦传》史料来源渠道之一。
二、《殇帝纪》独特的西域史料价值
东汉时期的西域史料集中分布在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之中,《东观汉记·西域》、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袁山松《后汉书·西域传》辑本亦见零散记载。按范书是以众家《后汉书》删减而成,其中或有删改不当之处,而上言三种辑本共收录14条西域佚文,史料稀缺难以弥补范晔《西域传》罅漏。《殇帝纪》细述西域诸国交通及鄯善、天竺、安息、大秦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状况,其西域史料较范书更具原始性,故既可诠解范书语焉不详之处,复可补苴范书西域史料之不足,现以其中四条西域史料为例简析之。
第一条,“鄯善国治欢泥城,去洛阳七千一百里。”《东观汉记》、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辑本及范晔《西域传》均不载本条,班固《汉书》曰:“鄯善国,王治扜泥城,去长安六千一百里。”[15]《魏书》云:“鄯善国,都扜泥城,古楼兰国也。”[16]按“扜”在上古音中为平声鱼部影纽,拟音[ǐwa],“欢”在上古音中为平声元部晓纽,拟音[xuan][17]。鱼部与元部可相通转,影母与晓母同属喉音,二字读音相若,或均源自佉卢文Khuhani之转译。
《后汉书·西域传》西域诸国与洛阳之间道里,多以长安、洛阳相距一千里为基数,复与《汉书·西域传》中诸国距长安道里相加而得,如《后汉书·西域传》东且弥国距洛阳九千二百五十里,即《汉书·西域传》东且弥国与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与长安、洛阳一千里叠加而来[18]。据此而推《殇帝纪》鄯善王都距洛阳七千一百里,即《汉书·西域传》鄯善王治距长安六千一百里与长安、洛阳一千里累加而出,通过“扜”与“欢”上古音转译、鄯善国都与长安、洛阳道里,可知东汉直至北魏鄯善国都均在扜(欢)泥城。
第二条,“本传曰:西域国俗造浮图,本佛道,故大国之众内数万,小国数千,而终不相兼并。及内属之后,汉之奸猾与无行好利者守其中,至东京时,作谋兹生,转相吞灭,习俗不可不慎,所以动之哉。”袁宏《后汉纪》中“本志称”、“本志曰”、“本志以为”之类文句十四条,“本传曰”一条。袁氏所录东汉史书中,惟有《东观汉记》之中“志书”、“列传”才可配称“本志”、“本传”[19]。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西域》仅从《艺文类聚》中辑录一则佚文:“(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献条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瓮。”[20]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亦载类似文句:“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21]按永元为东汉和帝年号,《艺文类聚》及刘知几《史通》、《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蔡邕别传》、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东观汉记》诸列传均未言及《西域传》[22-23],故可将本则佚文纳入《东观汉记校注·和帝纪》之中,吴树平将之归入《东观汉记校注·西域》证据略显不足。《殇帝纪》收录上言《东观汉记》“本传曰”文句,既可补录《东观汉记校注·西域》佚文,又可佐证《东观汉记》确曾为西域立传。
第三条,“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山离还。”本段文句是为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后汉书》亦有载及:“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24]结合袁、范二书之载,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可进一步补正为:悬度—乌戈山离—条支—安息。
《后汉书·西域传》另载类似路线:“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25]按班勇终生未曾踏足葱岭之西,而《后汉书》葱岭之西行程路线又是“班勇所记云”,故“班勇所记”葱岭之西路线或转自它处。《殇帝纪》又言“(甘英)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而班勇亦见记其事”,既然甘英讲述葱岭西“诸国”的地形与风俗,可能兼及出使葱岭之西“诸国”的交通路线,而补正之后甘英西使大秦路线与《后汉书》路线如此相合,故可推知上引《后汉书》葱岭之西路线乃甘英出使大秦完整路线。
《后汉书》之中皮山即今新疆皮山县附近,乌秅国即今克什米尔洪扎河流域罕萨(Hunza)[26],悬度即《汉书》之中“县度”,均系布鲁沙斯基语Sinda之汉译[27],今克什米尔西北部达丽尔(Darel)与吉尔吉特(Gigit)之间印度河上游河谷地带[28],罽宾国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Islamabad)之西的塔克西拉(Taxila)、白沙瓦(Peshawar)地区[29],乌戈山离国即今以塞斯坦(Seitan)与坎大哈(Kandahar)为中心的阿富汗南部地区[30],条支即今西亚幼发拉底河畔卡尔提阿(Chaldaea)[31],安息即今伊朗高原。甘英大致由皮山西南行,沿叶尔羌河、塔什库尔干河至喀喇昆仑山,翻越明铁盖达坂或红其拉甫达坂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溯洪扎河而下至印度河流域伊斯兰堡临近,复沿阿富汗境内喀布尔河、洛拉河、赫尔曼德河南下至阿富汗南部,穿越伊朗境内萨尔哈德高原,经克尔曼(Kerman)、法尔斯(Fars)、胡齐斯坦(Khuzestan)进入两河流域,后按照原路线返回。
第四条,“(甘英)临大海,欲渡,人谓英曰:‘海广大,水咸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风,时三月而渡;如风迟,则三岁,故入海者皆赍三岁粮。’‘”范晔《西域传》所载与之文字略有不同:“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32]袁纪之中迟风需“三岁”抵大秦,范书作“二岁”,二书均言需储备三年航海物质。《晋书·大秦传》又载:“邻国使到者(即大秦国),辄廪以金钱。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33]故当以袁宏所讲,迟风三年至大秦,需储备三年航海物质为是。
罗马帝国前身罗马共和国(前509年—前27年),曾设元老院决议国家大事,废黜、流放过“王”,与袁、范大秦国传文中国置三十六相议事制度、灾年放黜大秦王制度大体相符(见前引《殇帝纪》大秦传文)。大秦王受理民间诉讼的司法制度,在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并未有类似制度与之相合,诸多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东汉人想象中的大秦国司法制度。前揭大秦国史料乃甘英采获而得,并非时人理想化制度,以吾愚见,或是插述希腊城邦中的雅典制度。
其一,甘英抵至安息西界,临海(即波斯湾)欲渡,安息船人向甘英讲述海中存在令航海者思慕之物,应即古希腊史诗《荷马史诗·奥德赛》之中人面鸟身海妖塞壬(Siren)[34]。历史上希腊与波斯、罗马与波斯之间兵革不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尊崇希腊文化,东征之际将其流播至两河流域,可见或通过战争、民间贸易诸方式,在波斯传播希腊历史与神话知识(《荷马史诗》兼具历史与文学价值,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希腊史的唯一文字史料)。由此而推,安息船人可能同时接受除《荷马史诗》之外的其他古希腊历史知识;
其二,大秦王受理民间诉讼的司法制度,与希腊古风时代(前8世纪—前6世纪)雅典城邦司法制度相近:公元前6世纪中叶,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又译作珀西斯特剌图斯)以武力攫取雅典政权,建立僭主政治(即独裁统治),颁布有利于农民的法令,其中一项即在农村设立巡回法庭,便于农民就地诉讼。
他(即珀西斯特剌图斯)又设立地方法庭,并且常常亲自下乡巡视,调查争执,解决纠纷,以免人们进城,荒废农事。据说,一个于墨图斯人的事——他所耕的田后来称为“免税田”——正是发生在珀西斯特剌图斯某次巡行的时候。[35]
大秦国民间诉讼制度与庇西特拉图巡视法庭都是采取“王”外出巡行,裁决民事纠纷的形式,《殇帝纪》大秦国传文将其巡视过程理想化、简单化,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
综上所举,《殇帝纪》采用直录方式处理东汉史料,保存许多未经删改原始资料,其西域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厘清范晔《大秦传》史料繁杂来源,安息长老将大秦历史地理、民情风俗口述于甘英,甘英返归后将闻知大秦状况禀复西域都护班超,班勇将之载录己书,司马彪收“班勇记其事”入《续汉书·西域传》中,范晔则在司马彪《大秦传》基础上删改,形成今之《后汉书·大秦传》;其二,“本传曰”文句,可佐证《东观汉记》确曾为西域立传;其三,载录甘英出使大秦部分路线,为进一步考证甘英西使大秦完整线路提供重要依据。
[1]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孝殇皇帝纪(卷十五)[Z].北京:中华书局,2002.300-302.
[2]周天游.读〈后汉纪〉札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2):31.
[3]杨共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新探[N].光明日报.2000-10-13.
[4]魏征.隋书·经籍志二(卷三十三)[Z].北京:中华书局,1973.954.
[5]沈约.宋书·范晔传(卷六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1974.1820.
[6][7][14][21][24][25][32]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Z].北京:中华书局,1973.2913,2932,2920,2918,2918-2931,2917-2918,2918.
[8]余太山.〈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J].西域研究,1996,(3):47-51.
[9]林英.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J].古代文明,2009,(4):62.
[10]司马彪.续汉书·西域传(卷五)[A].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05-506.
[11]袁山松.后汉书·西域传(卷四)[A].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84.
[12]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三〇)[Z].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64.861.
[13]范晔.后汉书·西南夷传卷(八十六)[Z].北京:中华书局,1973.2851.
[15]班固.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Z].北京:中华书局,1964.3875.
[16]魏收.魏书·西域传(卷一〇二)[Z].北京:中华书局,1974.2261.
[17]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7,345.
[18]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里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07.
[19]董文武.袁宏〈后汉纪〉的史学价值[J].中州学刊,2001,(3):155.
[20][23]刘珍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西域[Z].北京:中华书局,2011.893,935-938.
[22]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鸟部下·雀(卷九十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95.
[26]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35.
[27]陆水林.新疆经喀喇昆仑山口至列城道初探[J].中国藏学,2011,(1):129.
[28]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汉书·西域传上〉要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00.
[29]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罽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17.
[30]孙毓棠.安息与乌戈山离——读〈汉书·西域传〉札记之一[J].文史,1978,(第5 辑),7-21.
[31]夏德.大秦国全录[M].朱杰勤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8-21.
[33]房玄龄.晋书·西戎传(卷九十七)[Z].北京:中华书局,1974.2544-2545.
[34]张绪山.〈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一段希腊神话[N].光明日报,2006-3-21.
[3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