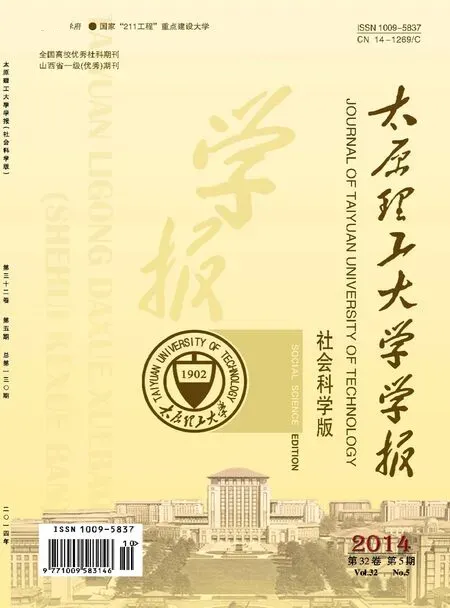平等权的修辞功能研究
戴津伟
(浙江农林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临安 311300)
一、导言
时至今日,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各国宪法普遍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人们都认可平等能提升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和积极性,不平等的对待不会催生幸福,而只会蔓生出偏见和气愤。不管是法学家、伦理学家,还是世界各国的立法都高度关注平等权。然而,平等的含义何在,到底怎样才构成平等却众说纷纭。
当今各国都普遍认可男女平等,通过立法明文规定男性和女性在接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同工同酬。然而,与此同时各国立法一般都规定女性享有产假,高劳动强度的工种不招收女性,我们同样不认为这构成了对女性的不平等。事实上,上述的两种平等并不是一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种平等是不计较男女性别差异,主张无差别对待的形式平等;第二种平等是基于男女的性别差异,出于照顾女性考虑,以形式上的不平等实现实质的平等。现实生活也会出现不同层面的平等观相互抵触的现象,不管我国的法律就退休年龄如何改革,但都会保留女性的退休年龄低于男性的规定,从立法层面看,出于女性身体衰退较早,体力较弱,比男性更早退休具有合理性,但有的女性却认为其身体条件完全足以支撑和男性同等年龄退休,也有男性认为让男性比女性更迟退休,承担更长时间的工作重任,对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已经构成了一种不平等。
可以说“平等权”长着普罗透斯的脸,在不同的情形下变幻出各种面目。不难发现“平等权”具有很强的修辞功能,同样都是采取“平等权”这一表述,所表述的内涵及相应的利益区分标准却大不相同,但都以“同等对待”的名义赋予利益分配以正当性。本文将从“平等权”的含义着手,探讨平等权的多层次含义,结合实例,考察这一术语在多种语境下的修辞功能,并深入阐释其正当性;以此为基础,对当前的各类歧视现象针对性地提出相关解决对策。
二、平等并非绝对相同,而是同等情形同等对待
何谓平等?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探讨过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德沃金等都对这个问题阐释过自己的见解。亚里士多德将平等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尽管平等的含义极为丰富,对其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人们基本能达成共识,即平等并不是指绝对相同,而是相同情形同等对待,不同的情形区别对待。“平等即是相同与不同的应予以有差异的且符合其本质的对待与处理,但并未说明什么是平等或不平等,以及如何地相同或不同地对待处理。”[1]由此出发,相同的主体受到不同对待是一种不平等,不同的主体受到相同对待,同样可能是一种不平等。换言之,同等对待不一定意味着平等,不同等对待也不见得一定是不平等。当然,这里的相同指的是在某个参照标准上的相同,而并非毫无差异。
可见,区别对待并不必然构成歧视。“平等原则禁止对于本质相同之事件,在不具实质理由之下任意地不平等处理,以及禁止对于本质不相同之事件,任意地做相同处理。”[2]如果某种分类及相应的区别对待具有正当理由,能证成其合理性,我们就不会把这种差别对待视为歧视。《现代汉语词典》把歧视解释为“不平等地看待”,《美国传统词典》对歧视的解释是“差别待遇,歧视不考虑个人的优点,而以等级或种类为依据加以区别,表现出偏爱或偏见”。
“平等权就是平等的要求,平等暗含‘比较的意向’,在没有参照对象的情况下,平等不具实质意义。因此,平等作为权利的内容具有依附性,不像生存权、环境权等权利,这些权利的内容本身是独立的。”[3]从这个角度看,平等权本身只是衡量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同等对待的准则,至于权利的内容还得参照具体情形来确定,比如人格的平等尊重,男女平等就业,等等。正是由于平等权的内容依附于相应的具体情形,因此,什么情况属于同等情形,应予平等对待;什么情况又属于不同情形,应予区别对待,这都得依赖具体情形来确定,“平等”的判断也就经常成为个案的衡量问题。
歧视意指没有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如要证明某种情形构成歧视,我们就得论证这种区分缺乏正当性基础,或者目的不正当,或者作为实现目的之手段不合理。“分类必须建立在一种明白区分的基础上,这种区分把组成一个群体的人和事物与那些处于群体之外的人和事物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与想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是合理的。”[4]例如公务员招录时拒绝招收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会认为构成了对这一人群的歧视,因为是否携带乙肝病毒与工作能力并无必然关系。如果某酒店在招聘厨师时明确表示不招收乙肝病毒携带者,我们通常不会持有异议,因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从事餐饮工作的确很可能对前来就餐者的健康带来威胁。
2000年,一家深圳企业发布的招工广告就声称“不招四川籍工人”,有四川籍律师以“地域歧视”为由愤而起诉。据媒体报道,这家企业之所以发布该广告,是因为企业中四川女工人数太多,相互之间说四川话,导致管理阶层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希望通过非四川籍工人的进入,进而形成一个说普通话的工作氛围。这种情形能否构成不招四川籍工人的正当理由呢?不可否认,四川籍工人过多,彼此之间都说四川方言,不方便管理,但这种情形并非只有通过限招四川籍工人才能解决,其实还有其他解决方法,比如强制推行普通话,把其列入工作纪律就是可行的措施。既然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其他替代途径,限招四川籍工人就显得缺乏必要性,从而有失正当。
三、任何平等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平等
人们对平等的追求经历过从适用法律平等向立法平等转变的过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依据法律进行的平等保护。“法律面前的平等意味着平等地服从普通法而不管它的内容如何;意味着它基本上是涉及法律适用、执行和法律运作中的程序性概念;意味着法律面前国家和个人应当平等。”[5]这样的平等是在法律制定之后的执法、司法、守法层面,不计较法律的具体内容,此种平等属于形式平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了这种平等的弊端,如果法律规定本身就不平等,而不平等的法律却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非但不能促进平等,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不平等。于是,各国逐渐关注立法上的平等,强调制定法律时对公民予以平等保护,没有正当基础不得做出区别对待。“‘类似情况类似对待’,并且只有在出现客观上能被证明正当的情况下方能做出差异性规定。就国家机关的职责来说,如果有可供做出评价的标准,那些承担解释、适用和执行法律的机构就不能做出专断任意的区分。它们必须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6]不可否认,立法平等更加注重实质,能从源头上提供合理的区分标准,这较之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然而,什么情形构成区别对待的正当事由?这明显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的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比如男女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有色儿童可以与白人儿童在同一学校上学,这在现在没有疑义,但就在几十年前,这仍是争议重大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立法上的平等标准始终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过去被认为正当的区分标准现在很可能被认为极不合理,现在法律中的区别对待也可能在几十年后被淘汰。我们没法保证当前的平等保护条款肯定就是合理的,加之立法的成本高昂,我们所要做的并非动则拿立法不平等说事,要求修改某些不平等条款,而是如何尽可能利用好当前的平等权条款。
“平等权”作为专业的法律术语,以“平等”和“无差别”的名义,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同等对待”上,事实上,任何同等对待都以对其他群体的区分对待为前提,只是在“平等”的修辞作用下,人们不大会深究作为“同等对待”的划分标准是否正当,相应的利益区分是否合理,从而顺利地实现了对社会公众的说服,为社会资源有限情况下的区分对待提供了正当说辞。
四、平等权不排除特殊照顾
平等意味着同等情形同等对待,但随着人们对平等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种形式平等观不断受到挑战,社会公众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同等对待,也提出了基于差异的特殊对待,对弱者予以特殊照顾,以形式上的不平等实现实质结果的平等。“平等作为应予接受的因素,强调的不是导致差异的原因,而是其所造成的结果,即差异所导致的差异。”[7]这样的平等观就要求考察不同群体的特性差异,有意识地通过制度来“补短”,尽可能地缩小因先天条件差异造成的结果差异。
与平等的分类相对应,歧视可分为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直接歧视是指不考虑合理依据,按照主体的不同条件,直接给予差别性待遇,比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由于直接歧视显而易见,因而又叫显在歧视。间接歧视表面上对所有主体采取统一的标准,但是这样的标准实质上对某些弱势主体提出过高要求,构成了变相歧视。间接歧视又被称为隐蔽性歧视,比如招工时对男女采用同样的身高和体力标准。现在越来越多的歧视都属于间接歧视,表面上一视同仁,但实质上明显对某些弱势群体不利。为了照顾这些相对弱势的群体,很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了对其特殊关照,比如高强度工种不得招收女工等,这种“特殊照顾”在国际上被称为纠正歧视行动。“纠正歧视行动在本质上是把因依某种根据而存在但却处于不利境地的个人或团体作为受益对象,予以特别的关怀而给予法律、政策或措施上的优待。”[8]
很多国家法律都先从正面规定平等保护原则,然后有意识地跟进纠正歧视行动条款作为必要补充。比如《加拿大人权宪章》第15条第1款规定: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和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并且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和平等的法律权益,不受歧视,特别是不受基于种族、民族出身或者种族出身、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者身心缺陷的歧视。紧接着,第二款就是关于纠正歧视行动的条款:第1款的规定并不排斥旨在改善处境不利的个人或团体,包括基于种族、民族出身或者种族出身、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者身心缺陷的根据而处境不利的个人或者团体的条件而规定的法律、规划或者活动。在平等的大前提下,给予了弱势群体适当的照顾。
五、特殊照顾也可能引发反向歧视
纠正歧视行动,给予特殊群体特别的照顾,也必须有适当的度,否则,一旦超过合理的限度,纠正歧视行动反而会构成对未受到照顾群体的反向歧视。“合理差别除了需要合理的依据之外,还必须限定于合理的程度之内。一般来说,没有合理依据的差别即属于不合理的差别,而超过合理程度的‘合理差别’,亦可能构成平等权的原则所不能容许的不平等形态。”[9]过犹不及,过度的特殊照顾同样构成不平等。
例如,基于照顾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立场,西藏和青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低很多,在西藏,450分就已经达到了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而在山东等基础教育发达的省份,这样的成绩可能刚到专科线。这种区别对待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考虑到西藏、青海等省份基础教育薄弱,很多少数民族考生的第一语言并非汉语,必须先辛苦学习汉语,再参加以汉语命题的高考,的确对他们构成很大的挑战,在高考录取时对他们予以政策倾斜,给予特殊照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当这样的特殊照顾幅度很大时,如北京市的同一所重点大学,在浙江省的录取提档线是620分,而在青海则只510分,分数悬殊竟然能达到上百分,这已经不简单是对落后地区的照顾问题,而构成了对基础教育发达省份考生的“反向歧视”。同样的分数,浙江的考生只能进专科院校,而青海的考生却进了重点大学,享受到的高等教育资源有天壤之别,无疑也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就业甚至一生。特殊照顾,本身是通过对弱者的优待来实现结果上的实质平等,但这样的特殊照顾也必须在坚持平等原则的基础下,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否则容易以“适当照顾”的名义,打着“实质平等”的修辞旗号,对其他主体造成了实质伤害。
事实上,反向歧视也可能以尊重或者回馈的名义出现,例如移动话费优惠活动,但只针对教师或者公务员等特定群体,商场推出打折活动,也只有之前消费超过一定额度的顾客才能享有。这样的优惠看似对特定群体的“厚待”,但仔细琢磨,为何就他们享有此等待遇,商家往往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从而在不自觉间对其他群体构成了变相歧视。
六、结语
“平等权”作为核心的法律言辞一直在诉说着同等对待的要求,但与此同时也以“平等”名义掩饰了同等对待的正当标准。从诉诸法院的“乙肝歧视案”和“基因歧视案”来看,录用单位都将责任推向了承担体检的医院,而并没有说明做出“歧视”的合法标准,消除这类显性歧视需要诉诸法律的明文规定,如果有区别,必须将区别对待局限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范围之内;面对过度的特殊照顾等隐形歧视,则需要行为主体解释其正当理由,以免以“照顾”或尊重为名,变相地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2.
[2] 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243.
[3] 徐显明.人权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221.
[4] 梁琼芳,段鸿斌.歧视抑或瑕疵—中国首例地域歧视案的行政法分析[J].理论月刊,2008(07):110.
[5] Black’s.Law Dictionary:Seventh Edition[D].West Group,1999:557.
[6] Jurgen Schwarze.European Administrative Law[M].London:Sweet and Maxwell,1992:547.
[7] [英]丹尼斯·劳埃德.法理学[M].许章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64.
[8] 张明锋.加拿大纠正歧视行动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2006(07):103.
[9] 周 伟.论立法上的平等[J].江西社会科学,2004(0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