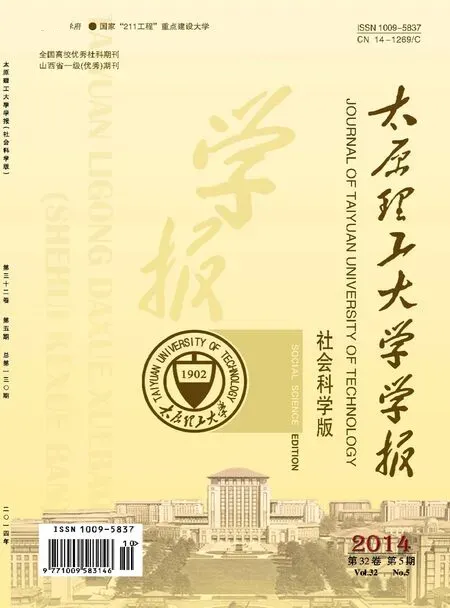中西方英雄主义价值观比较研究
——以孙悟空与哈利波特为例
苏晓萍,杨 洁
(太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杨 洁(1971-),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西文化对比,二语习得。
一、引言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可见,英雄是指才能出众和勇武过人的人,他们大都有远大抱负,不畏艰险,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和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表现出了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行为和气概。而英雄主义正是集结了这些英雄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的总称,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英雄事件和英雄人物来体现的。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都不乏可以堪称楷模的英雄人物:从岳飞、文天祥到克伦威尔、丘吉尔;从关羽、郭靖到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这些显见的英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隐性的英雄主义价值观。本文拟通过对中西方两部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孙悟空和哈利波特进行对比分析,分别从出生背景、成长阶段和英雄结局三个方面来探讨中西方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差异,以期对当今全球化下的文化共融起到桥梁式作用。
二、中西方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差异分析
(一)出生背景的差异
中国文化中的英雄形象塑造遵循“神本主义”的原则,往往具有“高”“大”“全”的特征,更像是神而非人。即使是历史长河中的真实英雄,在文学作品中也会加以神化,具有了超凡脱俗的神威天性,他们的出生自然也异于常人。孙悟空是天产石猴,生于花果山水帘洞。花果山本就是一座仙山,是“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孕育而生”的结果[1]。而山上有一仙石,也是“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1]。这有灵异之功的仙石“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1]。石猴一出世,便是“眼运金光,射冲斗府”[1]。由此看来,孙悟空既无人间父母,也无猴界爹娘,乃是天地精华、阴阳交合而成,世间独此唯一的灵物。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则更为弘扬“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社会及文学作品中的杰出人物出身大都平凡而艰辛:奥巴马出身于草根混血家庭;灰姑娘从小受到继母的虐待;简爱是一个孤女,在孤儿院长大,受到地狱般的烤炙。J.K.罗琳在《哈利·玻特》系列作品中塑造了一个看似虚幻的魔法世界,但除了人力不可及的魔法之外,这里宣扬的人文善恶,竟与现实世界是相通的。哈利波特的父母虽是优秀的魔法师,但他自小父母双亡,寄居在姨母家中,常常受到姨父、姨母和表哥的欺辱。他在这栋房子里是没有生存迹象的,住在黑黑的柜子里,房间里有很多蜘蛛。而他的外形也无任何奇特之处,长着“一张瘦瘦的疙瘩脸”,有“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带着“用许多透明胶带黏在一起的圆框眼镜”,而且看似“比同龄人都要瘦小”[2]。这样的形象实在与普通的邻家男孩没有区别,看不出有任何成为英雄的可能性。
(二)成长阶段的差异
与灵异的出生背景类似,中国文化对英雄的发展过程描述也强调“精英”特点,鲜有提及其弱小的初始阶段。他们一出场,就显现出与众不同、能力非凡的“救世主”特征,如诸葛亮一现世就是隆中对;岳飞一出场就是枪挑小梁王。虽说《西游记》中有述孙悟空得育明师,修成大道,但更为强调的是降龙伏虎强销死籍,一根如意金箍棒,横扫天上地下,高傲刚强,生平从不服人。他在跟随唐僧西天取经之前,是一个“个性鲜活”的原始英雄,入龙宫抢了如意金箍棒,下地狱强行更改了生死簿,七十二变更使其显得能力非凡,偷蟠桃大闹天宫,自封为“齐天大圣”,大败十万天兵。这样的“精英”形象使大多数常人可望而不可即。
西方文化对英雄的点滴成长过程则往往有着着力的刻画。许多年轻人更喜欢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一般孩子的特点[3]。比如他也有困惑、迷茫、软弱的时候,也有翘课、抄作业、上课打盹的时候,也有和老师、同学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有自己最好的朋友、最贴心的知己。英雄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酸甜苦辣的生活中不断历练而成的。当哈利波特在厄里斯镜中如愿看到父母,沉浸在梦幻世界中的时候,邓布利多点醒他:“人不能活在梦里,不要因梦想而忘记生活”[2]。当哈利波特对自己与伏地魔的诸多相似之处感到困惑,以及对自己与密室的诸多联系感到不解的时候,邓布利多再次开导他:“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人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2]。当摄魂怪的力量无处不在的时候,当哈利波特对摄魂怪的反应无比强烈的时候,邓布利多和卢平告诉他:“我们还是可以找点乐子,虽然是在这么黑暗的时期,只要点燃灯,光明就会再现”;“你最恐惧的其实就是恐惧本身,只要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一切都会迎刃而解”[2]。当哈利波特因为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和关爱而感到孤寂自卑的时候,小天狼星劝慰他:“你要记住,所有真心爱我们的人都会在我们的身边,他们永远会陪伴着你,在你心中”[2]。就这样,在长者的关心爱护中,在朋友的支持帮助中,在学校的读书学习中,在面临困难挑战的不断进取中,哈利波特从原先毫无个性特征的懦弱邻家小男孩逐渐成长为承担了战胜邪恶使命的个性鲜明的少年英雄。
(三)英雄结局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道德观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是以“君君臣臣”的等级礼制为社会行为典范的,是讲究忠恕之道的[4]。因此,中国文学中个体对理想的追求,往往呈现出一个圆转的趋向,即从反制约开始,最终皈依到大统之中。《水浒》英雄们从“逼上梁山”到接受朝廷“招安”;贾宝玉痛恶科举仕途而终究金榜题名;阿Q逃出未庄,又借“革命”之势“衣锦还乡”;大哥觉新,始终逃不出“家”的藩篱[5]。孙悟空虽说起初也是狂放不羁,大闹天宫,但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最终摆脱不了“紧箍咒”的束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在“真假美猴王”的战斗中,战胜了内心最后一点“自我”的黑暗面,最终皈依佛门,取得真经,返回东土,得名“斗战胜佛”。最后修成正果的孙悟空,已全然没有了当年大闹天宫的原始野性,已经完全变成了顺服儒家仁义礼制的正面英雄,自然也无需“紧箍咒”对他进行管教约束了。
西方传统文学中的英雄大多是以死亡或流放为结局的,具有强烈的悲剧情怀。俄国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如果没有这个牺牲或死亡,他就不成其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为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力量,实现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5]夜莺以自身的死亡为代价来诠释真爱;哈姆雷特以死亡来唤醒世人心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俄狄浦斯的流放成为杀父娶母宿命论的终结。但是在《哈利波特》中,罗琳一改西方传统的英雄悲剧结局,展示了现代社会中对英雄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一个小人物,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忽然一个特定的情境,一种特有的挑战,唤起了小人物心中的英雄潜质,他们迎接挑战,展示了果敢无畏的英雄气质。哈利波特初到魔法学校,是一个不显眼的小巫师,过着和其他同学一样的生活,但突然间,伏地魔出现了,他必须承担起斗士的职责,去担负自己无法逃避的责任,成长为英雄。小说结尾也采取了更为真实的写法:世界归于平静,英雄的光环散尽,他又回归了“麻瓜”世界,留下的只有灯光、炉火、晚饭、妻子和儿女。小说尾句则更显深意:19年来哈利波特的伤疤再也没有疼过,一切都好。哈利波特的伤疤本是伏地魔留下的印迹,哈利波特本是伏地魔的一个魂器,也象征着他内心本来邪恶自私的一面,在与伏地魔的较量中,也是自身正义与邪恶两面的较量中,正义的能量逐渐强大,战胜了邪恶,伏地魔死了,自身邪恶的印迹消除了,完成了英雄的成长过程。在英雄的使命完成之后,最终再次回到普通人的世界中,正是小说更贴近真实的亮点。
三、结语
《西游记》与《哈利波特》是东西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魔幻神话作品。孙悟空与哈利波特这两个不同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英雄文化价值观。在中国“神本主义”的文化影响下,英雄往往是一种道德才能的楷模,具有神的特征,从出生就异于常人,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不思凡尘,最终要回归儒家正统的思想。在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影响下,英雄来自于草根平民,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常人的矛盾冲突,也有困惑;当挑战来临时,英雄的意识被唤醒,最终又回归到常人中去。总之,不同民族的英雄价值观都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们的理想和愿望,了解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全球文化共融的当今世界,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2] 罗 琳 J K.哈利波特[M].苏 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李 霞.英语畅谈中国文化50主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4] 夏志华.浅析中西方神话中道德观差异以及对英语教学的启示[J].文教资料,2006(01):106-107.
[5]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