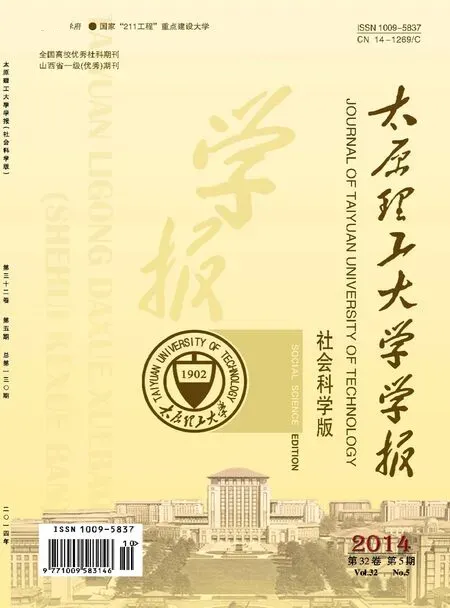宋代隐逸词生命意识探微
李术文
(1.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2.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宋代是一个生命意识高扬的朝代,文人士大夫在生命本体的跋涉与探求中,经历着诸多考验,面对生命的种种无奈,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求。一方面他们在时代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重新整合,在宣泄情绪的同时寻求精神的超脱;另一方面,通过诗意的地理空间来构筑自我的心理空间,在山水园林中寄托生命的忧思。因此两宋文人,无论穷困显达,大都追求一种闲适典雅的生活方式,并以超逸出尘的隐逸情怀和淡泊虚静的审美心态去消解生命的困顿,最终涵养出宋代隐逸词所具有的独特生命意识:自由之心、闲适之情、空灵之境。
(一)自由之心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自我生命意识就被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所制约,由此导致个体精神的长期压抑。文学艺术恰恰能充分抒发个体情感意志,让人性的光芒散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因此,当人们内在的生命愁绪无法在纯思辨的空间自由显露时,常常会选择文学或艺术作为精神的寄托,以此来消解生命困顿所带来的种种烦忧。具体到宋词,尤其是隐逸词,正是宋人自由意识的突出体现,客观上也折射出古代文人意图超越自然生存,追求身心自由的终极人生目标。
两宋词人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往往身不由己。特别是围绕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产生的新旧党争,几乎贯穿整个北宋,流弊之害,罄竹难书。“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景祐诸公则开之也。”[1]仕途风云的险恶激发了宋人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畏祸及身的心理也让大批士子萌生了出世的念头,对自由意识的强烈追求,成为他们最强烈的愿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隐逸词的创作逐渐开始兴盛。如经历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苏舜钦,在变法失败遭遇变故之后,都写下了表达归隐的词作。“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桃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范仲淹《定风波》)。暮春时节,百花争艳,词人暂时忘却官场的纷扰,赏花寻芳,恍入桃花源,在自然美景中呼吸自由的气息。范仲淹从小胸怀大志,欲行变法以图强,然而此时却自称“聊逸豫”,无奈之情溢于言表,足见变法失败对其影响之深。苏舜钦因变法受牵连被除名,寓居吴中,虽常与高僧雅士唱和,随意自适,但内心的愤懑难以消解,“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水调歌头》),于是通过诗意的地理空间来寻求审美的愉悦、精神的自由,借以冲淡仕途困顿所带来的心灵缺失。“潇洒太湖岸,淡伫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瀰间”(《水调歌头》)。欧阳修谪居颍州期间,更是创作了10首《采桑子》,抒写远离宦海之后的自由逍遥之情。
北宋党争除了历时长、范围广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兴治文字狱,这种情况导致文人创作“淡化了参与意识,从而又促使了议论时政的创作倾向向摅写自我生命律动的转化”[2]。党争的反复不定与文字禁锢,给文人士大夫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屡遭贬谪流离,他们饱受了来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煎熬,面对生命的种种无奈,他们将关注的视角由社会转向自我,由外在的事功转向内在的生命思考。可以说,对诗文创作的畏惧心理,对人格自由的无限追求,间接催生了隐逸词的繁盛。如王安石现存词29首,绝大部分为罢官隐居时所作,其中与隐逸相关的词占33.3%.苏轼也在贬谪期间创作了大量的隐逸词,表达了对仕隐的迷茫与困惑,对自由的追求与渴望。如其名作《行香子》写道:“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此词为熙宁六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过七里滩所作。仕途蹭蹬的苏轼泛舟于此感慨遂生。七里滩是东汉著名隐士严光隐居之地,清溪明月,鱼影飞鸿,美景如画。尽管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归隐,但却以归隐作为自己寻求心灵安顿的途径。据木斋先生统计,在苏轼现存362首词作中,有68首共77次使用了“归”字,其中与归隐相关的有66处,约占全部词作的20%,这还不包括其他如“逝”、“隐”、“还”等咏叹归去主题的词[3]。
苏轼之后,逐渐形成一种通过寻求逍遥自在的山林之趣来坚守自我人格独立,进而消解个体生存的困扰的时代风气,从“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苏轼《行香子·述怀》)的希冀归隐,到“一亩清阴,半天潇洒松窗午”(毛滂《烛影摇红·松窗午睡》)的亦官亦隐,再到“回头谢、冶叶倡条,便入渔钓乐”(周邦彦《一寸金》)的彻底归隐,隐居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逃避,而是文人的一种现世情怀,一种精神追求,是文人自我人格独立意识的确立过程。“人生需要追求,也需要一种修养,一种精神上的修养,一种化释种种烦恼的心理调解,使自己摆脱‘物’的奴役和缠绕,处于一种自醒、自明的精神状态,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4]正是基于这种精神追求,才激发了词人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从而使得隐逸词创作有了更为丰富深广的内涵。
(二)闲适之情
纵观整个北宋词坛,文人士大夫几乎都困囿于党争贬谪之中,徘徊于得失进退之间,他们借诗词超脱或者是安慰缥渺的心灵“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胜别解”(苏轼《与子由弟》),或者是抒发虚幻的梦里心曲“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秦观《好事近·梦中作》)。南渡之后,无论是词的主体情感世界还是客体空间场景,与北宋时期相比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与时代风云接轨,与社会生活相连,与民族心律同步。但是,南渡词人在寻求精神避难与心灵超越的过程中,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动荡不安的时代,忧患丛生的民族,沦落覆亡的故土,苦闷压抑的心灵等等。面对这苦痛的现实人生,他们必须找到化解苦痛的方式。而此时,他们的出路已大不如前:“物我本虚幻,世事若俳谐。功名富贵,当得须是个般才”(李纲《水调歌头·似之申伯叔阳皆作再次前韵》),外在的功业已在战火硝烟中化为灰烬,他们能够选择的唯一出路,便是回归自然,寄情山水:“幸有山林云水,造物端如有意,分付与吾侪。寄语旧猿鹤,不用苦相猜”(李纲《水调歌头》)。词人远离宦海,身处山林云水间,获得了精神的彻底解脱。因此,南渡之后无论是隐逸词人朱敦儒、向子諲、周紫芝,还是爱国志士辛弃疾、陆游、张孝祥,抑或是贬谪重臣李纲、赵鼎等人,在他们的隐逸词创作中,随处可见“罗绮丛中无此会,只疑身在烟霞外”(李弥逊《蝶恋花·游南山过陈公立后亭作》)的闲适之情,此时的流连,已不再是梦里的心曲,缥渺的幻影,而是付诸行动的超然。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词人就是朱敦儒。
南渡之前的朱敦儒,颇有麋鹿之性,过着狂放不羁、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首著名的《鹧鸪天》将其清狂生活和孤傲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靖康之变惊碎了他的梅花梦,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反思“梦云惊,陇水散,两漂流。如今憔悴,天涯何处可消忧”(《水调歌头·淮阴作》)。社会的苦难,现实的残酷和生命的艰辛一步步削弱了朱敦儒狂放不羁的个性,他开始远离世俗,遁迹山林,“寻汗漫,听潺湲,澹然心寄云水间”(朱敦儒《鹧鸪天》),词人的审美注意力也从关注自然的瞬间变化和局部景观转为对大自然的整体观照[5],由此创作了大量表现隐逸情趣咏叹闲适生活的词篇,如“清平世,闲人自在,乘兴访溪山”(《满庭芳》),“年年闲梦垂垂了,且喜松风吹不倒”(《西湖曲》),“怎似我、心闲便清凉,无南北”(《满江红》),“身退心闲,剩向人间活几年”(《减字木兰花》),“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临江仙》)等等,这些作品约占其词集《樵歌》总数的60%,他也因此在词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被视为苏、辛之间的一座桥梁(汪莘《方壶诗余自序》)。
梁漱溟先生曾将隐逸文化的特点概括为:“生活上是亲近和喜爱大自然;经济上是淡泊自甘,不理财利;政治上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6]可见隐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对现实生存状态的超越和升华,对于宋人来讲,他们所追求的超逸隐世情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居深山老林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以客观环境为依托,借回归自然以慰藉心灵,因此,他们笔下的世界蕴藏着无尽的山水情韵,“掩柴门啸傲烟霞,隐隐村峦,山上仙家,楼外白云,窗前翠竹,井底朱砂。五亩宅,无人种瓜。一村庵,有客分茶”(张可久《折桂令·村庵即事》)。
即便是词人辛弃疾、张元幹等英雄豪杰,在整顿乾坤、横扫狂虏的梦想被现实无情击碎后,也将心理能量宣泄到文学创作上,将注意力转移到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上。这一点,在张元幹词中表露无遗,“浮家泛宅忘昏晓,醉眼冷看城市闹。烟波老,谁能惹得闲烦恼”(《渔家傲·题玄真子图》)。词人寄身山林,既远离世俗喧闹,又享受闲适之乐。因此,在山水林泉的感召下,南渡词人开始依山傍水营造别墅,渐成一时风尚。如叶梦得退隐湖州卞山之后,修筑石林别墅,闻名于世,“哪知一丘一壑,何处不堪藏。须信超然物外,容易扁舟相踵,分占水云乡。雅志真无负,来日故应长”(《水调歌头·休官咏怀》)。朱敦儒隐居嘉禾,筑岩壑别墅,“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感皇恩》)等等。显然,观赏山水,放情丘壑,已经由消解苦闷、慰藉心灵衍化为一种淡泊的人生态度,一种超脱现实的理想方式,更是一种超越心灵的自我满足:“洗尽凡心,相忘尘世,梦想都销歇。胸中云海,浩然犹侵明月”(朱敦儒《念奴娇》)。隐逸词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其深厚的情感内涵和情感力量,在这些匠心独运的吟咏里,洋溢着对自然和生命的欣喜与热爱,洋溢着浓烈而蓬勃的生命意识。
(三)空灵之境
宋代隐逸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其核心在于审美主体勃发的情绪状态和心理体验,而自由之心与闲适之情正是隐逸词生命意识的感发力量和抒情内结构,即所谓词心。但是,作为抒情美学的发端,它必须与外在之境相融合才能达到抒情的极致——词境之美。正如王国维所言“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人间词话》),因此“每一首词必有意境才有生命”[7]。就宋代隐逸词而言,词境的营造,既是审美主体的抒情外结构,更是体现隐逸词生命意识的又一重要层面。可以说,隐逸词的审美特性主要集中地体现为淡泊空灵的意境之美。如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
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遭谗罢官,离开广西途经湖南,创作了这首“飘飘有凌云之气”(王闿运《湘绮楼评词》)的千古名作。时近中秋,月明之夜,词人泛舟湖上,此时月光皎洁,湖水明莹,词人仿佛置身于一片澄明世界之中,物镜与心境悠然交会,“妙处难与君说”。月夜泛舟的高清雅趣,神与物游的澄明境界,深邃勃发的生命意识,在情景交融中给人以美的感受和启迪。
1.意象选择。作为对清静无为、闲适自在生活的诗意写照,隐逸词构成意象的客体多是色彩淡雅的物象:深山茂林、幽石小径,江湖飞瀑、溪水流云,梅兰竹菊、鸥鹭孤鸿等等,这些具有标志民族文化心理的独特意象,容易造成视觉上的淡雅古朴,嗅觉上的沁人心脾,以及听觉上的雅静清幽之感,既展示了自然的清静澄明,也昭示出宋人的思想心态和审美情趣。如苏庠的《诉衷情》:
“倦投林樾当诛茅。鸿雁响寒郊。溪上晚来杨柳,月露洗烟梢。
霜后诸、水分漕。尚平桥。客床归梦,何必江南,门接云涛。”
倦客鸿雁,月华云涛,轻霜寒露,溪水小桥,这一系列清真幽远的意象群,渲染出一幅明净如水的隐居图,也传达出词人对这种高洁生活的眷恋和沉醉。徐增在《而庵诗话》中说:“无事在身,并无事在心,水边林下,悠然忘我。诗从此境中流出,哪得不佳?”经历时代风云仕途蹭蹬的词人们置身安宁静谧的自然山水中,举目所见的是钟灵毓秀的物象景观,与他们淡泊安适的襟怀相遇合,“故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鲁迅《摩罗诗力说》),自然风物遂与词人襟怀相互融合,使隐逸词呈现出澄明清空的艺术风韵。
2.绘画笔法。词境的创造,也离不开词人对其他艺术手法的融会贯通,其中对绘画手法的借鉴尤为特别。词和画作为客观世界的审美反映,在立意传神的本质上是相同的,李泽厚先生就认为山水画与宋词基本属于同一个艺术品类,“中唐以后最为成功的艺术部门和艺术品是山水画、爱情诗、宋词和宋瓷”[8]。特别是宋代以来,中国绘画流派纷呈,手法多样,逐渐将山水景物作为抒发主观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的手段,强调画家要有“林泉之心”,这些都对宋词的创作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我们在隐逸词吟啸林泉的作品中,经常可以觅到文人山水画的境界,以及词人对绘画技法的借鉴与生新,如工笔勾勒,线条白描,调色点染,写意传神等等。试看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蛮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全词举重若轻,用极其简练的笔法将村居生活一一白描:低矮的茅屋,碧绿的草地,潺湲的溪水,淡淡几笔就将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而出;恩爱的老夫妻,喝酒闲聊彼此媚好,幸福的一家人,神态各异其乐融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意境跃然纸上。
再如吕本中的《满江红》,写菊只“疏篱下,丛丛菊”,写竹则“虚檐外,萧萧竹”,寥寥数语,笔墨极其简省,而菊之意竹之神尽收眼底,所使用的手法正是绘画技法中的写意传神法。
由此可见,隐逸词冰清玉洁、澄静空灵的风格,正是由于词人“喜取清丽之景写淡泊之意,他们都喜欢冰清玉洁、澄澈晶莹、空明萧瑟之美,而写意用笔之轻灵流转,飘然而来,倏忽而逝如野云孤飞风行水上”[9]。除此之外,隐逸词淡泊空灵的意境之美,还有赖于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如对诗歌比兴手法的继承与发扬,对历史典故的摄取与提炼等等,隐逸词人将自我人生的体验诉诸文学艺术,通过艺术手段加以创造,才使得宋代隐逸词呈现出风姿卓越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宋代隐逸词真切地表现了两宋文人关于生命本体的各种体验与感悟,折射出他们面对仕隐进退的矛盾心理,对于人生家国的忧患意识,以及保持人格独立的处世方式,并形成了淡泊空灵的美学风格,其独特的生命意识,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夫子.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86.
[2]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54.
[3] 木 斋.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绪[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224.
[4] 许建平.山情逸魂[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41.
[5] 王兆鹏.南渡词人群体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12.
[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7] 张 伟.浅议词的艺术特质的表现[J].沈阳大学学报,2002(3):46-47.
[8] 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9] 张惠民.宋代词学审美理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