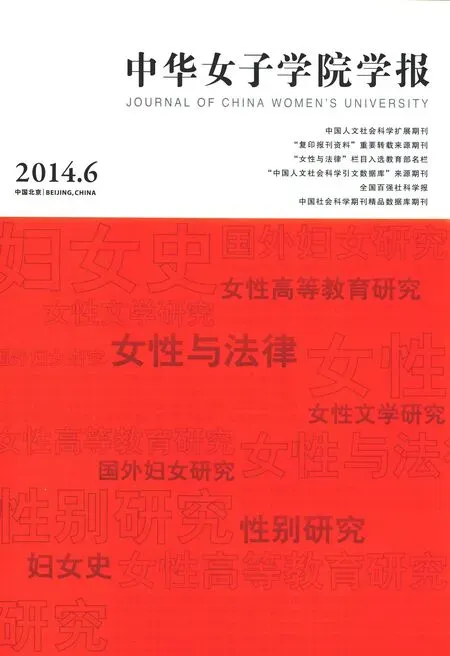从黑人女性文学中母亲身份的变迁看黑人家庭伦理的嬗变
修树新
从黑人女性文学中母亲身份的变迁看黑人家庭伦理的嬗变
修树新
由于黑人女性独特的生存经历,黑人母亲身份具有不同于白人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中的母性身份的内涵。从“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的黑人女性创作中可以看出:在家庭伦理方面,黑人家庭大多呈现出“女人当家长”的一致性。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妮·莫里森、特里·麦克米兰和泰雅里·琼斯的作品再现了黑人家庭历经的百年沧桑,揭示了黑人母亲身份从保存、文化传递到养育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蕴含了家庭伦理的变迁:精神意义上的女家长正逐渐替代传统的物质意义上的女家长。
女性家长;母亲身份;家庭伦理;变迁
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黑人文学一直是由男性作家主导。黑人女性作家真正引起美国文坛的重视并被世界文坛所认识始于70年代之后,在中国评论界得到足够的回应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被伯纳德·贝尔称为“非洲裔美国黑人文化的再生”的“哈莱姆文艺复兴”造就了三位杰出的黑人女作家:杰西·雷德蒙·福赛特(Jessie Redmon Fauset)、内拉·拉森(Nella Larsen)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她们的贡献为黑人女性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异军突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赫斯顿的代表作《她们眼望上苍》是黑人文学中第一部充分展示黑人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在黑人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品以詹妮·克劳福德的三次婚姻为线索,探索了黑人妇女的心理发展轨迹。赫斯顿让一位黑人妇女而不是男人独领风骚,使被遮蔽的女性的自信与自强重新成为社会的关注点。托妮·莫里森塑造的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秀拉标志着黑人女性形象的一个质的飞跃。她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充分把握自我、张扬自我的主体。她凌驾于男人之上,她不再受任何传统、习俗的约束。莫里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老一代和年青一代两类。前者以《最蓝的眼睛》中的波莉、《秀拉》中的夏娃、《所罗门之歌》中的派拉特、《宠儿》中的萨格斯和塞斯等为代表,后者以佩科拉、秀拉、哈格尔和丹芙等为代表。莫里森的文学创作把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带到了巅峰。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坦言:“我重新阅读莫里森的作品是因为不管其社会目的是什么,她的想象都超越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神学争辩学而重新进入一种由具有真正审美尊严的幻想和罗曼司所占据的文学空间。”[1]2
在20世纪90年代登上文坛的美国黑人女作家中,特里·麦克米兰(Terry McMillan)以高产、畅销而尤为突出。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妈妈》(Mama)开始,她接连创作了《等待梦醒时分》(Waiting to Exhale)、《斯黛拉如何恢复最佳状态》(How Stella Got Her Groove Back)、《力不从心》(A Day Late and a Dollar Short)、《一切的中断》(The Interruption of Everything)、《渴望幸福》(Getting to Happy)、《真心相对》(Disappearing Acts)、《谁问过你》(Who Asked You?)等一系列作品。在《妈妈》中,麦克米兰并没有把作品的重心放在揭露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上,而是着力刻画了一位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独立抚养五个子女且从未放弃对自己情感生活追求的黑人母亲米尔德里德,展现了其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和优秀品质。
泰雅里·琼斯(Tayari Jones)发表处女作《离开亚特兰大》(Leaving Atlanta)时,新千年已经开始了。该书于2003年获得“赫斯顿—赖特遗产奖”处女作奖。该奖项是首个由全美黑人作家协会授予黑人作家的全国性文学奖项。2006年,她获得了“丽莲·史密斯奖”;2008年,她斩获“全美艺术家科林斯奖”;2011年,她又荣获了“雷德克里夫学院奖学金”。从琼斯的创作中,我们看见黑人女性文学的一个转向:即关注黑人少女的成长。2011年出版的《银麻雀》(Silver Sparrow)细腻地描绘了因父亲重婚而出生的黑人少女达娜对完整父爱和健全家庭的渴望。
纵观赫斯顿以来的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会发现虽历经时代的变迁,但黑人家庭在家庭伦理方面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女性当家长。母亲身份、母女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本文以赫斯顿、莫里森、麦克米兰和琼斯的创作为研究内容,分析黑人母亲身份内涵的历时演变并透视黑人家庭伦理的嬗变。
一、保存
用通俗的汉语表述这个含义的话,“保存”就是“养活”——提供生活资料,使孩子得以存活。对于“保存”,评论家奥莱利使用的词汇是Preservation,“对于大多数黑人母亲,特别是贫困母亲来说,作为母亲就是要保证孩子的存活,因此保障食物、住所,努力去建造保持安全、合理的环境就成了黑人母性的价值意义所在。”[2]32
《她们眼望上苍》里的詹妮·克劳福德是由曾经当过奴隶的外祖母南妮抚养大。南妮曾多次受到白人奴隶主的侵犯和凌辱,长着“灰色眼睛、黄色头发”的女儿丽菲就是其受辱后生下的。因为担心女儿遭受女主人的迫害,在生下女儿不久,并被皮鞭毒打之后,她挺着血淋淋的后背、带着女儿辗转逃到了她认为“阳光洒满街道两侧”的西佛罗里达。善良的女主人帮助她把丽菲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南妮也期待能把女儿培养成教师。可是,丽菲却遭到了和母亲同样的厄运——在年仅17岁时就遭到学校老师强奸并生下詹妮。丽菲生下孩子后一度沉溺于酒精的麻痹中,之后便不知去向。詹妮对父母没有任何记忆,是由南妮一手带大的。南妮充当了母亲的角色,也就是帕特里夏·希尔·科林斯所言的“他者母亲”(Othermother)。赫斯顿并没有详细描述南妮如何含辛茹苦把詹妮抚养大,小说开篇却细致地描写了南妮如何处心积虑为詹妮安排婚嫁之事。南妮给詹妮安排的丈夫洛根·基利克斯是个已近中年、相貌丑陋、不解风情的男人,但是他拥有60亩地和一栋房子。南妮希望在她弥留之际看到的就是詹妮的生活有所保障。当新婚不久的詹妮并没有体会到南妮所说的婚后爱情而找到她哭诉时,南妮厉声说道:“你在一个大忙的日子跑回来,竟说傻话。你有个一辈子可以依靠的支柱,人们见到你时都要摘了帽子,管你叫基利克斯太太,你却来烦我。”[3]22“……在大路旁买了一栋房子,60亩地……慈悲的主啊!这是我们所有黑女人梦想得到的保护。这叫爱情。”[3]22从南妮的言辞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她对母亲职责的理解:在她看来,母亲的职责就是要让孩子吃饱、穿暖,而精神方面的需求相比之下毫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洛根·基利克斯就是南妮在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世时找到的代替自己履行“保存”职责的替身。
二、文化传承
在莫里森看来,黑人文化传统是黑人力量和智慧的源泉,莫里森小说中的许多黑人女性还承担着传承黑人文化传统的角色。在《所罗门之歌》中,她凸现了妇女在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奶娃的姑姑派拉特生下来就没有“肚脐眼”的事实可以看成是生活在美国的非裔后代与非洲母文化断裂的象征,而派拉特随身携带父亲“头盖骨”的习惯和她那令人震撼的歌声便是其传承与保护黑人文化的努力。
派拉特12岁时,父亲为了捍卫自己的土地被白人枪杀。为了保存自己对名字及其与父母的记忆,她托人把母亲的一件遗物打制成一个小盒子,从《圣经》上撕下印有自己名字的一页并把名字放入小盒。在流浪的生涯中,她一直把小盒子作为耳饰挂在左耳垂上。她还把父亲的遗骨装在口袋里,随身携带。正是这个口袋被“奶娃”误认为是装着50磅黄金的宝藏,处心积虑地想把它偷走。在非洲文化中,祖先崇拜的基本内涵是灵魂崇拜。“用确切的话来说,早期非洲人的宗教,就是崇拜祖先。非洲人相信,他们祖先的神灵对他们的一生有无限的威力。”[4]27-28
派拉特另一独特之处便是她的歌声。“派拉特一天唱到晚”,《所罗门之歌》中有多处对派拉特歌声的描绘。在小说开篇当保险公司代理人史密斯准备飞行时,在楼下的大街上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装束”的派拉特以浑厚有力的低音唱道:“欧,售糖的人飞走了/售糖人走啦/售糖人掠过天空/售糖人回家喽……”[5]10派拉特第二次唱起这首歌谣是在12岁的奶娃不顾父亲的禁令来到姑姑派拉特家时,奶娃亲耳聆听了派拉特和女儿丽巴一边干活一边哼唱:“欧,售糖人不要把我丢在这里/棉花球会憋死我/欧,售糖人不要把我丢在这里/白人东家的胳膊会箍死我……”到和声部分时,丽巴的女儿哈格尔也会跟着唱起来:“售糖的人飞走了/售糖人走啦/售糖人掠过天空/售糖人回家喽……”[5]60-61
美国黑人文学最初是靠口头形式传播并保留下来的。黑人民族音乐对黑人文学有着很大影响。詹姆斯·鲍德温曾经写道:“只有在音乐中,美国黑人才能够讲述自己的故事。”布鲁斯歌曲的结构和伤感的情调常被移植到黑人的文学作品中,来表达人物悲愤忧伤的感情。派拉特所吟唱的“所罗门之歌”记载着奶娃曾祖父的历史。奶娃本是为了寻找派拉特所藏金子而开始的弗吉尼亚乡村的寻宝之旅,却在孩子们传唱的“所罗门之歌”中变成了寻根之旅。奶娃的身心也在寻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达到了精神上的成熟。这一切结果的发生都以派拉特的引领为前提和铺垫。
《最蓝的眼睛》里克劳迪娅的妈妈麦克迪亚太太的歌声也让克劳迪娅觉得生活多了一道色彩,没有歌声的星期六“就会像沉重的煤筐”压在她的心头。
如果母亲心情好,情况不那么糟,她会唱歌,唱些诉说艰难岁月的歌,唱些年轻人相爱又离别的歌。她的嗓音是那么甜美,她的目光是那么醉人,我发现我非常渴望那些艰难岁月,渴望能生长在那“身无分文”的年代里。我渴望经历我的“心上人”离我远去激荡人心的时刻。我“不愿看见太阳渐渐落下……”因为我知道“我的心上人已经离去”。我母亲多彩的嗓音给悲痛带来了色彩,将歌词里的痛苦抹去,使我相信悲痛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悲痛也是甜蜜的。[6]16
“身无分文”的“艰难岁月”就是祖辈历史的隐喻。历史中虽然包含着无数悲哀和痛苦,可是母亲的歌声让克劳迪娅对之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迷恋和渴望。歌声记载了黑人的历史与文化,也向后人传承着其中的精髓。
三、养育
“养育”既包含提供生活所需,使生存和成长成为可能的“养活”含义,又含有“教育”之义。两个方面同等重要。
《妈妈》中的米尔德里德的形象继承了赫斯顿和莫里森对黑人母亲身份的诠释。同夏娃等母亲一样,她为孩子的生存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米尔德里德17岁就生下了大女儿弗里达,在二十几岁时,就成了五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克鲁克无所事事,在外面公然和情妇同居。只要她和男人多说上几句话,或者某个男人多看她几眼,克鲁克就会对她拳脚相向。米尔德里德视她的孩子们为生命的全部意义。为了养活孩子,她做过雇工,当过工人,做过“老人之家”的护工,开过家庭餐馆和舞厅,甚至出卖肉体和伪造签名骗取社会保险,但是她从来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叫屈。只要不向别人要求施舍,她认为一生都“跪着”给白人擦洗地板也没什么大不了。她把自己当成孩子们永远的需要,“一想到孩子们会长大成人,她就像感受到电流经过身体一样受到震动。”当女儿们一个个都有了情感归宿时,她又把精力集中在照顾外孙子们上。
米尔德里德对教育的重视赋予了黑人母亲身份以新的内涵。她经常根据自己和普通黑人的生活经验把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灌输给孩子们。她注重教育,认为孩子们首要的目标是进大学读书,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不介意去讨、去借,或者去偷,你们每一个都要上大学。我是当真的。你们几个都有能力,我一定让你们充分发挥出来。”[7]27在她的教育下,弗里达进入斯坦福大学,安吉尔进入加州大学,多尔也上了大学。
她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并告诫她们物质上的成功并不是唯一的目标。一次,她带弗里达去白人雇主希尔斯家。小女孩被宽敞的房间、华丽的装饰所折服并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赚大钱买一个比希尔斯家还要大、还要好的房子时,米尔德里德语重心长地告诫弗里达:“孩子,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宽敞豪华的房子并不是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正直、体面、一个好丈夫、一群健康的孩子、内心的平静,这些东西应该是你努力从生活中得到的。别的东西都会各就各位,生活总是这样的,你听清了吗?”[7]27
在孩子们的婚恋方面,她尊重她们的选择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女儿们:爱是男女双方稳定交往和走向婚姻的基础。当卜特思决定在中学毕业后就结婚时,她同意了;当安吉尔领回白种男友并因此引发了其他孩子的不满,特别是儿子马尼的强烈反对时,她断然说道:“别说废话。我不想听。他是个好人,非常爱安吉尔。我不管他是不是白人,只要他能让我女儿快乐。”[7]206
尽管米尔德里德在教育子女方面相比老一辈黑人女性形象付出了很多,但是让她对子女表达一些温情或“过多的爱”还是比较困难。在一个圣诞节前夕,她经历失业后再度就业拿到了第一份工资时,面临着的是无数需要购置的生活必需品,还有需要偿付的一堆账单,而最令她难以处理的是孩子们列出的心仪已久的圣诞礼物。她微薄的工资无法让她满足所有孩子的愿望,出于无奈,她让弗里达再等一等,理由是“你是个大孩子了”。当弗里达眼里饱含着泪水点头允诺时,“米尔德里德的内心在示意她把大女儿拥抱在怀里。可是她不能。她的心似乎被一层塑料薄膜包裹住了,使她不能按本能冲动做事。她从不对孩子们表达过多的爱,因为这令她感到脆弱。”[7]37再如,当弗里达离开密执安州的家,远赴加州去读大学时,米尔德里德心中万分不舍,像是面对着和孩子的永别似的。她神情恍惚,“如果问她名字,她都可能说不上来。她知道的唯一的事就是她的大孩子走了。”[7]115以后的几周时间里,她都无法适应,甚至把其他几个女孩叫成“弗里达”。即便是对孩子怀有这么深的爱,当弗里达和她吻别时,她却别过脸,弗里达只亲到了她的脸颊,她的一声“再见”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银麻雀》以同父异母的两个女孩的视角讲述了不一样的母女情。一个男人在亚特兰大的同一小镇拥有两个家:两个妻子和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对另一个了如指掌,而另一个对对方浑然不知。年轻时,戈温相貌出众,在商店工作的她在为给妻子买礼物的詹姆斯包装礼品时为其吸引而坠入爱河。戈温怀孕后被詹姆斯带到阿拉巴马州并注册结婚。生下女儿达娜后,戈温母女每周末和詹姆斯小聚。被父亲称为“秘密”的达娜对同父异母的姐姐乔丽斯充满好奇并主动接近她,成为对方珍爱的朋友。对乔丽斯家舒适的物质生活了解得越多,达娜心中的不满就越强烈,随之而来的则是青春期异乎寻常的叛逆。为了向父亲挑衅,她坚持在午夜时分穿着裸露地去和男孩子约会。她也经常以“詹姆斯”代替“爸爸”的称呼。一天,达娜和乔丽斯约会偶遇父亲和叔叔。为了不让自己身份暴露,达娜把自己反锁在狭小的浴室里差点窒息。戈温获悉之后,手里拿着注册证书来到乔丽斯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了詹姆斯重婚的事实。真相的曝光也结束了达娜和父亲将近17年的周末相聚。篇尾,达娜成了未婚母亲,她也是孩子父亲唯一的爱人。她发誓要成为尊重母女关系的母亲。
虽然琼斯在小说中也描绘了戈温如何努力工作来抚养达娜,包括她已近中年还去接受专门的培训而成为护士,但是作者更着力展现的是作为母亲的戈温如何关注达娜的成长,并在达娜遇到困惑和问题时,及时地给予引导、关爱和扶持,减少了特殊的家庭给孩子造成的影响。相比《母亲》中的米尔德里德,戈温和达娜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在达娜的心目中,戈温就是个“超级英雄”。戈温一贯把孩子视为朋友一样相处,并与之坦诚相待,塑造她坦率、诚实的品质。她常常对达娜说:“我告诉你一切,你也告诉我一切。这是我俩成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们之间必须保持交流。”[8]13
戈温时时关注达娜情绪的变化,注重和孩子的沟通,及时消除孩子心理上的阴影。她总是能巧妙地把自己和达娜被詹姆斯隐瞒的不幸变成她们的优势,让达娜对现状感到满足。一次,5岁的达娜在幼儿园里画了一幅题为《我的家庭》的画。在里面她画上了父亲詹姆斯、自己和母亲还有乔丽斯和母亲拉维恩,并坦诚地跟老师解释说:“这是我的家。我爸爸有两个妻子和两个女儿。”[8]6詹姆斯知道后非常气恼,严肃地告诉达娜不能告诉老师爸爸有另一个妻子的事实,甚至不能对老师说父亲的名字。当达娜天真地问道:“你的另一个妻子和女儿是个秘密吗?”[8]9父亲丝毫没有顾忌小女儿的感受,直言道:“不。你弄错了。达娜,你才是那个秘密。”[8]9面对达娜“我是个秘密吗”的质疑,戈温把达娜搂在怀里,果断地说道:“不。别人只是不知道你。那个小女孩甚至不知道她有个姐姐。你知道一切。”[8]15达娜马上转忧为喜,她虽小却知道“上帝洞察一切”。她和妈妈岂不是和上帝一样无所不知了吗?
正是戈温对达娜在精神上的引导、扶持,才使达娜在一个缺少正常父爱的家庭中得以健康成长,成为一名像戈温一样的母亲。母亲的怀抱对于达娜来讲是温暖的港湾、疗伤的绿洲,母亲拥抱她时散落在她脑后的长长的头发像一幅“神奇的窗帘”。这显然是一个象征——象征保护她的屏障。正因为戈温母爱的滋养,达娜才能够自然地去拥抱自己的女儿弗洛拉,发誓绝不做“绝望的母亲”,并永远尊重母女关系。
四、结语
安德瑞·奥赖利(Andrea O’Reilly)在论述黑人母亲身份时曾写道:“黑人母亲身份的中心是在实践和思想上如何保存、保护,或更通常意义上讲,赋予孩子们以抵制伺机伤害他们的种族主义并完整地使他们进入成年的能力。”[2]4从奥赖利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黑人母亲身份的内涵是关乎后代如何在种族主义社会中健康成长并抵御不利侵害的大事,因此它就具备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也很大程度上说明在赫斯顿、莫里森、麦克米兰和琼斯等作家的作品中,母亲身份、母女关系一直是不变的主题。
[1]Bloom,Harold.Toni Morrison[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0.
[2]O’Reilly,Andrea.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A Politics and the Heart[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
[3]Hurston,Zora Neale.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Z].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1990.
[4](美)约翰·霍普·弗兰克林.美国黑人史[Z].张冰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美)托妮·莫瑞森.所罗门之歌[Z].胡允桓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美)托妮·莫瑞森.最蓝的眼睛[Z].陈苏东,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7]McMillan,Terry.Mama[Z].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87.
[8]Jones,Tayari.Silver Sparrow[Z].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2011.
责任编辑:杨春
Perceiving the Change in Black Family Ethic from the Evolutionary Connotations of Black Motherhood
XIU Shuxin
Because of the unique living experiences,black motherhood has special connotation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hite middle-class nuclear family.Studying the Afro-American women’s literary works pu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Harlem Renaissance to the end of 20th century,we can see the black families generally display amazing consistency in the aspect of family ethic:“having women as the head of the family”.The works of Zora Neale Hurston, Toni Morrison,Terry McMillan and Tayari Jones show the 100 years of vicissitudes of the black families and the evolutionary connotations of black motherhood.The change from“preservation”,“cultural bearing”to“nurturance”also implies the change in family ethic:“female family head”in material sense has changed to that in spiritual sense.
female family head;motherhood;family ethic;changes
10.13277/j.cnki.jcwu.2014.06.010
2014-10-10
I106.4
A
1007-3698(2014)06-0076-05
修树新,女,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及女性文学。13002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宗教视域下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政治书写”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52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