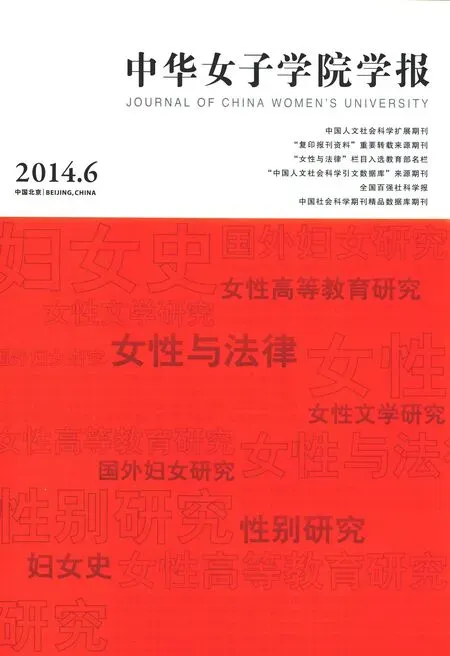西方妇女产褥期状态与护理经验研究
李洁 徐菁媛
西方妇女产褥期状态与护理经验研究
李洁 徐菁媛
相当数量的西方妇女会在产后遭遇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重度疲劳和性生活问题,但缺少相应的专业咨询和帮助。产后抑郁症困扰着部分女性,个体感受、情感支持和社会文化等因素都会影响产妇的情绪,父亲角色和家庭关系也会在产后发生重要变化。朋辈支持、产前咨询和产后机构干预对提高女性的分娩体验和产褥期恢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产褥期健康;家庭关系;产后护理;产后机构干预
产褥期(Puerperium),是从分娩结束至产妇身体恢复到孕前状态的时间段,通常在六周左右,这段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作“坐月子”。①“坐月子”历史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的《礼记·内则》一书中,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时称之为“月内”,是产后必须举办的仪式性行为。长久以来,“坐月子”都被视为东亚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对之加以研究,似乎西方女性在产后并不需要额外的照料和护理。事实上,产褥期是东西方女性共同经历的重要生命时刻,它同样深刻影响着西方女性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关系。在时代剧烈变迁的大背景下,中国妇女的“坐月子”模式也正在经历着从扩展家庭到核心家庭、从单系继承到双系继承、从私人领域到公共卫生领域的变迁。在计划生育政策、市场化冲击和个体主义思潮的多重影响下,中国妇女的产褥期照料模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冲击。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方社会中女性产褥期身心健康、家庭关系和相关护理经验的研究综述,探讨其有益的理论和实践,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下的产褥期文化和实践。
一、西方妇女产褥期的身体与心理状况
在身体方面,相关研究普遍证实:西方女性在产后存在普遍的身体疼痛、重度疲劳及其他身体功能症状。欧切特(Otchet)研究表明:产褥期女性的功能性普遍低于正常女性,具体表现在身体疼痛、社会功能和生命活力三个方面。其中,身体疼痛是指身体的严重疼痛或不适,以至于影响了正常活动;社会功能是指与他人社会交往的质量和数量;生命活力是指精力旺盛水平和疲劳感。此类功能性限制均源自身体问题。[1]汤普森、罗伯特、柯里和埃尔伍德(Thompson,Roberts,Currie& Ellwood)对澳大利亚1295位产后3至10个月的女性就产后健康问题的广泛性和持续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产后8周超过一半(60%)的女性出现重度疲劳,一半左右(53%)的女性出现腰痛,37%报告有肠道问题,30%出现睡眠不足等症状,此外还有部分女性出现痔疮(30%)、会阴疼痛(22%)、持续出血(20%)、失禁(19%)等其他泌尿问题。初产妇(Primiparas)比多产妇(Multiparas)更容易出现会阴疼痛和性生活问题。剖宫产比顺产更容易出现重度疲劳、睡眠不足和肠道问题。[2]类似的,席特(Schytt)等在2005年的研究中指出,瑞士女性产后4到8周,接近三分之二的女性报告有感觉疲惫的问题,超过三分之一的剖宫产女性出现或多或少的术后疼痛,28%到29%的女性出现颈部/肩部疼痛、性生活等问题。[3]
尽管超过一半以上的女性在产后初期受到各种身体不适的影响,但是研究发现大部分女性不愿意向专业医师咨询产后疾病。布朗和拉姆利(Brown&Lumley)的研究指出,造成这种局面有以下几点原因:部分女性认为产后疾病是伴随分娩自然发生的,专业医师对此也无能为力;或是羞于向医生咨询妇科疾病。[4]这一点在梅森、格伦和沃尔顿(Mason,Glenn&Walton)针对女性孕期/产后失禁就医情况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大部分女性对此选择沉默,不就医、不咨询,但是有超过一半的研究对象希望孕期获得专业人员对于该病症的提醒。[5]这方面的研究提醒相关医疗工作者与社区工作者应当在产前培训和产后初期护理阶段,主动告知初产妇在产后可能会遭遇的身体变化与问题,并在产后护理手册中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策略手段,以缓解产妇的身体不适与心理压力。
在情绪方面,女性在向母亲角色的过渡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躁、愁苦等情绪症状。[6]417-419伊曼纽尔(Emmanuel)指出,母体窘迫不单单是一种病症,更可以准确地表述为特指生育期间出现不同程度的与悲伤、哭泣、焦躁和失落相关的症状。[7]保尔森、道贝尔和雷夫曼(Paulson,Dauber&Leiferman)的研究发现:产后抑郁的症状取决于母体孕期与生产期间的主体感受,分为轻度抑郁和重度抑郁。轻度抑郁表现为短而频繁的焦虑、抑郁,并无严重的精神疾病症状;而重度抑郁则表现为严重的焦躁和沮丧,或是出现自杀倾向的产后精神病。[8]诺布尔(Noble)表示该病症伴随着不易察觉的焦虑症状,往往潜在危害着母婴关系,导致母亲认知错位,影响其育儿方式,引发儿童社交和身体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而影响家庭关系。产后抑郁症与产褥期精神病有本质区别,后者是与分娩相关的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它是一种分娩短期内突发性的病症,严重影响产妇本身和胎儿的生命安全。[9]史道奇(Stocky)建议专业人员监护在家待产女性,从而有效控制此类疾病的发生。[10]
导致产妇产后抑郁症的原因是多样的,利思沃伦、麦卡锡和科克伦(Leathy-Warren,McCarthy and Corcoran)的研究特别提醒人们关注社会支持的重要性。这几位研究者指出:产妇的焦虑主要来源于产后的角色变化,她们需要学习新的角色,建立崭新的关系(母子关系),原有的社会关系也要进行重组和调整。因而,产妇的产后适应不只包括其自身的身心状况调整,还包括整个家庭和社会机构对她们施与的社会支持。研究者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对512名初产妇在产后的功能性社会支持和结构性社会支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功能性社会支持(Functional Social Support)中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和评价性支持(Appraisal Support)的缺乏对于产后抑郁的影响最突出,甚至要高于信息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和工具支持(Instrumental Surpport)的重要性。情感支持和评价性支持不足会导致产后抑郁的风险比常人高6到7倍。[11]这一点特别提醒我们要重视来自产妇的重要亲友(包括丈夫和家人)给予其理解和鼓励的重要性。对初产妇的支持并不只是来自于信息经验的提供和物资、人手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对其正在经历的人生变化的理解和同感(Sympothy),以及对她们初为人母的鼓励和肯定。研究同时发现,6周到12周的产妇中,产后抑郁率由13.2%下降到9.8%,说明产后早期抑郁症状更加多发,之后产妇抑郁症状的逐步减少说明产妇本身的自愈能力开始发挥效用。[11]
二、西方产褥期家庭关系研究
产妇的产后照料和恢复不仅关乎产妇本身的身心健康和初生婴儿的照料,而且对丈夫的角色适应乃至整个家庭关系的重新确立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产后丈夫的角色方面,朗沃思(Longworth)等研究发现: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与知觉控制(Perceived Control),丈夫在孩子降生后很难给自己的角色定位。[12]斯蒂恩(Steen)指出,父亲在产科护理服务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既不是病人,也不是访客,情感上和身体上的未归属感让父亲感到遭受排斥和惧怕。只有在父亲们融入到怀孕、分娩与产后照料的过程中才能成功实现角色转换。[13]麦卡文(McVeigh)等对165位昆士兰父亲在妻子产后6周的功能性支持调查中表明:在婴儿照护、私人与社交活动领域中,丈夫的功能性支持最低。[14]赛沃和厄兹坎(Sevil&Ozkan)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具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感、更多地参与社区社交活动与照料儿童活动,并有较高程度的工作相关活动(Occupational Activities)。拥有高学历妻子的丈夫在家庭责任、私人护理和工作相关活动方面也具有较高的均值。[15]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则较少意识到妻子在生育过程中自身的家庭责任和活动参与水平,在产后初期对妻子和孩子的照料程度也相对较低,这既不利于父亲角色的确立,也不利于妻子的产后恢复和适应。
古德曼(Goodman)等研究者对男性产后抑郁现象的研究表明:父亲的产后抑郁和母亲的产后抑郁有着直接相关的密切联系,在其研究的文献中,妻子患产后抑郁时,有24%—50%的丈夫同时患有产后抑郁。他认为,这一发现对家庭健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16]古德曼(Goodman)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表明:母亲的产后抑郁倾向不仅会影响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互动关系,还会继而影响父亲与婴儿之间的关系。[17]可见,产妇的情绪状况不仅关乎其自身的身心健康,还会影响母婴互动关系,继而影响到丈夫的心理状况,以及父亲和孩子的互动模式,甚至最终影响整个家庭互动模式的巩固和稳定。
亚洲产后文化与西方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参与主体的不同,女性家庭成员(通常是婆婆)而非丈夫,是产后护理的主要参与者。这一点就导致亚洲的产后护理并不仅仅关乎核心家庭的稳定和健康,还牵涉到姻亲和扩展家庭等更为复杂的关系。此前医学研究领域指出产后抑郁症在中国很少见,但李等(Lee D.,Yip A.,Chiu H.,Leung T.,Chung T)在对中国产后女性的精神病学研究中发现:产后3个月的中国女性中有13.5%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抑郁症状。[18]卡里宁和亚瑟(Klainin&Arthur)的研究表明:亚洲产后文化包含(针对产妇设定的)特定的活动和饮食,来自母亲、婆婆和其他女性家庭成员会在生活和情感上对产妇进行一系列传统行为的指导。然而,产妇并不是主动选择了这些仪式性活动,而往往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人际冲突而遵从了照料者(如婆婆)的意见;一些传统的产后习俗过于强调严格的行为规范,也容易产生压力、紧张和挫折感;其他一些外部因素(如男孩偏好)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因而,尽管这一系列文化习俗旨在给产妇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但时至今日,也成为家庭人际冲突和情感危机的主要原因。研究进一步指出,包括日本、越南、马来西亚、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在内的产后习俗对于产妇并没有起到安抚心灵的作用。[19]西方研究者对亚洲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也提醒中国研究者需要从更大的家庭视角出发,关注产妇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在社会文化、家庭结构和价值观念快速变迁的当下,更要注意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的协调与融合。
三、西方妇女围产期的相关护理经验
在对产褥期妇女身心健康和家庭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护理体系,根据产前、产中和产后等不同时期对妇女个体及其家庭进行积极的介入和干预,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护理模式和经验。
在产前阶段,专业介入的对象不仅包括临产期的妇女,同时也包括其丈夫和家人。在对产前培训的父母进行心理干预的研究中,马泰(Matthey)等发现心理干预有效地降低了初产妇患产后抑郁症的可能性,并指出干预中的有效因素与丈夫对产妇产后初期经历的认知有关。[20]萨洛宁、乌曼和卡诺曼(Salonen,Oommen&Kaunonen)的研究指出:初产妇和多产妇对于来自护理专家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From Nursing Professionals,简称SSNP)在看法上没有明显差异,但父亲参与产后护理婴儿的天数与来自护理专家的社会支持则明显相关。[21]可见,将男性纳入产前介入对象,将有效提升妇婴的照料水平和身心健康状况。
西方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生产过程中的社会隔绝(Isolation)是引发围产期精神疾病的重要因素。执业医生应该重视认可与开发朋辈支持以预防围产期精神疾病,确保重视并鼓励发展适当的社交网络。[22]拉金、贝格利和德韦恩(Larkin,Begley&Devane)就爱尔兰产妇分娩的经历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进行了质性研究,研究发现大部分女性在分娩过程中感到焦虑和孤立。[23]丹尼斯(Dennis)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朋辈支持在预防产后抑郁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该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分配控制组(常规照料)和实验组(常规照料和朋辈以电话聊天形式),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母亲认为朋辈支持对于预防产后抑郁具有积极作用。[24]随后,丹尼斯和布朗(Dennis&Brown)的研究表明:产后抑郁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预防和治疗,包括朋辈支持、同伴支持、非指导性咨询、精神保健、护士家访和综合模式干预等形式。[25]通过怀孕、生产和产后建立起连续性的关系模式是构成西方产妇积极生育体验的重要因素。[26]
在产后护理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机构干预模式。豪沃思、斯温和特里哈恩(Howarth,Swain&Treharne)指出:产后护理专家的私人化、照料式合作关系是新西兰母亲拥有高质量生育体验的基础。[27]韦格斯(Wiegers)对荷兰产后照料模式(Dutch Model)进行了介绍:一位产科护理助理在产妇产后7至8天中每天至少有3小时到产妇家中向其提供产后专业护理。其中主要任务是监测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向新爸爸妈妈提供指导,观察并帮助他们熟悉新家庭的日常生活,赋予新爸爸妈妈养育新生儿的自信心。[28]芬威克(Fenwick)等研究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希望得到辅助性的产后接触(Postpartum Contact),部分女性还需要额外的跟踪辅助性与针对性帮助。[29]那些在生产过程中经受严重创伤(包括身体与心理层面)的女性特别需要助产士的咨询和支持,产伤咨询干预模式就是为此类女性提供的特殊护理方式。该干预模式与创伤理论一致,注重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强调助产士的角色能为遭受分娩痛楚的女性提供咨询支持。这种服务反映了女性与助产士建立治疗联系的需求,通过助产士将产妇的分娩经历与情感有效化。通过培育社会支持和强化积极应对的策略,探索重拾信心、降低焦虑的方法,以重建创伤产妇的心理平衡。[30]
可见,通过在产前和分娩早期进行多样化的专业护理支持,并积极动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情感介入,确保了西方发达国家妇女的产后恢复和新家庭关系的巩固、确立。
四、经验与启示
通过梳理上述西方文献,我们发现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产褥期妇女都有相当成熟和配套的照料护理模式。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文化与现实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善我国产褥期妇女的照料实践。
首先,倡导医院在围产期间建立专门的知识渗透环节,宣传产妇身心健康与家庭和谐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注重对新生儿父亲的培训和观念引导。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性别观念的影响,对男性的观念引导显得格外重要。新生婴儿和产妇的护理应当由传统上以婆婆、妈妈参与为主的女性领域,逐步走向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新家庭模式。父亲的参与不仅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夫妻良好互动关系的建立,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代际关系间的家庭冲突和矛盾。
其次,医院和社区机构应当为新生儿家庭建立同辈联系,并提供支持平台。中国传统的产后照料模式,往往是有经验的纵向传承。但是已有研究指出,这种自上而下的习俗传递往往给新生儿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和约束,成为产妇精神焦虑和家庭矛盾的来源。因而,医院和社区机构应当更加积极地发挥自身的平台和纽带作用,鼓励新生儿父母参加社区公共活动,建立同辈群体之间的陪伴交流和非指导性信息咨询的关系。在新生儿父母的社区活动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架构体系。通过增强同辈群体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能够避免单纯来自专业人士和长辈的精神压力,释放新生儿父母的心理负担,缓解其社交紧张状况,促使其更好更快地适应角色要求和转变。
第三,在产后社区医院回访环节过程中重视对产妇精神健康和家庭关系的评估。传统的回访环节只重视对产妇和婴儿健康状况的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产后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多发,以及由此导致的其他家庭矛盾的可能。除了喂养和康复建议之外,社区医生应当对产妇给予更多的情感支持和评价性支持,鼓励新生儿父母投身到婴儿照料和新家庭关系的建设之中。对社区医院评估出现问题的家庭应当及时展开社会工作介入。通过以整个家庭为对象,在家庭互动场景中调适成员之间的关系,解决家庭矛盾,构建和谐家庭。对于出现严重心理偏差的个体与家庭,展开更加积极的跟踪辅助与咨询指导。
此外,还要特别增强对生产女婴的农村家庭、生产高危婴儿和不健康婴儿家庭的教育宣讲和身心监护。通过对产后照料模式的重新整合与提升,更好地促进妇女身心健康与家庭和谐。
[1]Otchet,F.,Carey,M.&Adam,L..Gener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 Status in Pregnancy and the Puerperium:What is Normal?[J].Psychological Symptom Status,1999,(94).
[2]Thompson,J.,Roberts,C.,Currie,M.&Ellwood,D..Prevalence and Persistence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Childbirth:Associations with Parity and Method of Birth[J].BIRYH,2002,(29).
[3]Schytt,E.Lindmark,G.&Waldenstrom U..Physical Symptoms after Childbirth: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s with Self-rated Health[J].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2005,(112).
[4]Brown,S.,&Lumley,L..Physical Health Problems after Childbirth and Maternal Depression at Six to Seven Months Postpartum [J].British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2000,(107).
[5]Mason,L.,Glenn,S.,Walton,I.&Hughes,C..Stress Incontinence during Pregnancy and Following Childbirth[J].Midwifery, 2001,(17).
[6]Meleis,A..Theoretical Nursing:Development and Progress[M].Philadelphia:Lippincott-Raven,2007.
[7]Emmanuel,E..Maternal Role Development: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Distress Following Childbirth[D].School of Nursing and Midwifery,Griffith University,Brisbane,2005.
[8]Paulson,J.,Dauber,S.&Leiferman,A..Individual and Combined Effect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Mothers and Fathers on Preventing Behavior[J].Pediatrics,2006,(118).
[9]Noble,R.E..Depression in Women[J].Metabolism,2005,(5).
[10]Stocky,A..Acute Psychiatric Disturbance in Pregnancy and the Puerperium[J].Bailliere’s Clinical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2000,(14).
[11]Leathy-Warren,P.,McCarthy,G.&Corcoran,P.Postnatal Depression in First-time Mothers:Prevalence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Social Support at 6 and 12 Weeks Postpartum[J].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2011,(25).
[12]Longworth,H.&Kingdon,C..Fathers in the Birth Room:What are They Expecting and Experiencing?A Phenomenological Study[J].Midwifery,2011,(27).
[13]Steen,M.,Downe,S.,Bamford,N.&Edozien,L.Not-patient and Not-visitor:A Metasynthesis Fathers’Encounters with Pregnancy,Birth and Maternity Care[J].Midwifery,2012,(28).
[14]McVeigh,C.,St Jogn,W.&Cameron,C..Fathers’Functional Status Six Weeks Following the Birth of A Baby:A Queensland Study[J].Australian Midwifery Journal,2005,(1).
[15]Sevil,U.&Ozkan,S..Fathers’Functional Status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Early Postnatal Period[J].Midwifery,2009,(25).
[16]Goodman,Janice H..P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Its Relationship to M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and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Health[J].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2004,(45).
[17]Goodman,Janice H..Influences of M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on Fathers and on Father Infant Interaction[J].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2008,(29).
[18]Lee,D.,Yip,A.,Chiu,H.,Leung,T.&Chung,T..A Psychiatric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Postpartum Chinese Women[J].Am J Psychiat,2001,(158).
[19]Klainin,P.&Arthur,D..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Asian Cultures:A Literature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2009,(46).
[20]Matthey,S.,Kavanagh,D.,Howie,P.,Barnett,B.&Charles,M..Prevention of Postnatal Distress or Depression:An Evaluation of An Intervention at Preparation for Parenthood Classes[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04,(79).
[21]Salonen,A.,Oommen H.&Kaunonen,M..Primiparous and Multiparous Mothers’Perceptions of Social Support from Nursing Professionals in Postnatal Wards[J].Midwifery,2014,(30).
[22]Jones,C.Jomeen,&J.Hayter,M..The Impact of Peer Support in the Context of Perinatal Mental Illness:A Meta-ethnography [J].Midwifery,2014,(30).
[23]Larkin,P.,Begley,C.&Devane,D..Not Enough People to Look after You’:An Exploration of Women’s Experiences of Child-birth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J].Midwifery,2012,(28).
[24]Dennis,C..Postpartum Depression Peer Support:Maternal Perceptions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2010,(47).
[25]Dennis,C.&Brown,S..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Perinatal Depression[J].Best Practice&Research Clinical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2014,(28).
[26]Dahlberg,U.&Aune,I..The Women’s Birth Experience th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Continuity of Care[J]. Midwifery,2013,(29).
[27]Howarth,A.Swain,N.,&Treharne,G..First-time Mothers’Perspectives on Relationships with and Between Midwives and Doctors:Insights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 of Giving Birth in New Zealand[J].Midwifery,2012,(28).
[28]Wiegers.T..Adjusting to Motherhood Maternity Care Assistance during the Prostpartum Period:How to Help New Mothers Cope [J].Journal of Neonatal Nursing,2006,(12).
[29]Fenwick,J.,Gamble,J.,Creedy,D.,Barclay,L.Buist,A.&Ryding,E..Women’s Perceptions of Emotional Support Following Childbirth: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J].Midwifery,2013,(29).
[30]Gamble,J.&Creedy,D.K..A Counselling Model for Postpartum Women after Distressing Birth Experiences[J].Midwifery,2009, (2).
责任编辑:秦飞
Research on Women’s Puerperal State and Care Experience in Western Countries
LI Jie,XU Jingyua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Western women experience varying degrees of postpartum body aches,severe fatigue and sexual problems.However,there is a lack of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system and assistance. Postpartum depression is another threat to puerperal.Also individual feelings,emotional support and social culture have fairly amount of influence on maternal mood.And great changes among father roles and family relations occur during the period of postpartum.In sum,peer support,prenatal and postnatal consulting agency interventions are crucial to improve women's childbirth and postpartum recovery experienc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family relations;postpartum care;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
10.13277/j.cnki.jcwu.2014.06.012
2014-11-01
C913.68
A
1007-3698(2014)06-0086-06
李洁,女,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发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社会学;100101徐菁媛,女,美国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年和健康社会学。29632
本文系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西方妇女产褥期状态与护理经验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