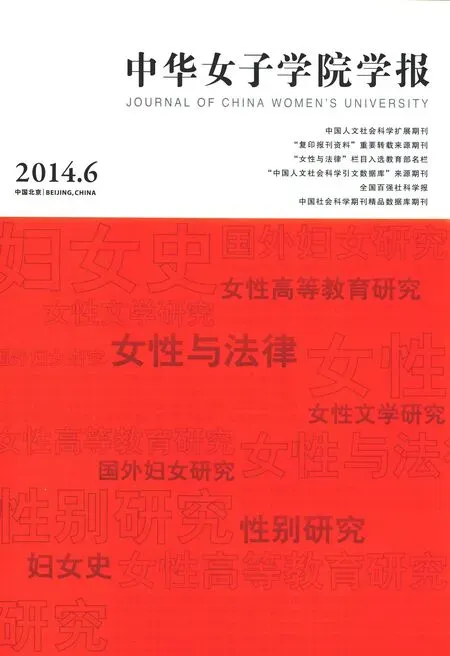有吉佐和子小说《非色》的“他者”形象
寇淑婷
有吉佐和子小说《非色》的“他者”形象
寇淑婷
《非色》是有吉佐和子系列社会问题小说的开篇之作。小说以四位日本“战争新娘”在美国的遭遇为主线,揭露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对人性的残害。“战争新娘”既是性别上的“他者”,又是美国社会的“他者”,同时,在美国社会,黑人又是白人的“他者”。文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就黑人阶层的“他者”处境和“他者”的话语权两方面对《非色》中的“他者”形象做探索性的解读。
有吉佐和子;《非色》;女性主义;他者
一、有吉佐和子与《非色》
有吉佐和子(1931—1984年)是一位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她在文学上的造诣很深,因此被誉为才女。有吉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从1961年开始,她曾先后五次访问中国,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吉的创作视野非常广阔,从初期反映艺人生活的作品《地歌》《木偶净琉璃》《墨》到后来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如《香华》《出云的阿国》《华冈青洲之妻》,从以家庭舞台为主题的《纪之川》《鬼怒川》《祈祷》到以社会问题为背景的《非色》《恍惚的人》《复合污染》,无不堪称经典。因此也为她赢得了“物语能手”、“女子一代记”等多个称号。在众多题材的作品中,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引起了广泛关注,《非色》就是有吉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发表之后,在日本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59年,有吉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以研究种族问题为目的在美国留学了一年时间,《非色》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非色》发表于1963年,是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的典范。[1]这部小说围绕着“种族问题”,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和美国两大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战后萧条的日本,许多妇女迫于生计同美国占领军的下级军士结婚。当这些军士服役期满回国后,日本的“战争新娘”们便随夫远渡重洋来到纽约。然而,等待她们的不是照片中看到的花园洋房式的贵族生活,而是淹没在高楼大厦中的贫民窟的低贱生活。小说描写了同船来到美国的四个“战争新娘”,分别是笑子、竹子、丽子和志满子,她们因为丈夫是黑人、波多黎各籍和意大利籍的美国人而饱受种族歧视,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1931年,有吉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市,然而她的幼年并不是在日本度过的,她很小就随同在银行工作的父亲移居印尼,10岁才回到日本。有吉幼年时代的国外生活以及赴美留学生活,对这部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她能够以一种“异邦人”的眼光,即“他者”的眼光看待问题,分析问题。《非色》这部小说描写的种族问题,是借四位日本“战争新娘”的生活和遭遇表现出来的。“战争新娘”既是性别上的“他者”,又是美国社会的“他者”,同时,对于美国的黑人阶层而言,黑人又是白人的“他者”。本论文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非色》中的“他者”形象做探索性的解读。
二、《非色》中的“他者”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这是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术语。“他者”和“自我”这对截然相反的术语,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强烈表现。一般西方人称自己为主体性的“自我”,而称殖民地的人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他者”。“他者”即是主体的附属品,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表现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毫无疑问,黑人是作为白人的他者而存在的。同时,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被看作是“第二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历史”一部中对女性被确立为“他者”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父权制的社会制度。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边缘地带,处于被压迫地位,没有话语权。
在《非色》这部小说中,笔者认为有两类“他者”存在,第一类是以托姆为代表的美国黑人阶层,他们受到种族歧视,处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剥削压迫。第二类是从日本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以笑子为代表的“战争新娘”,她们既是性别上的“他者”,又是美国社会的“他者”。然而,有吉却赋予了具有双重“他者”身份的“战争新娘”以话语权,借着“战争新娘”的“他者”之口,对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小说中多次提到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由于肤色”,但是,这句话却似乎在提醒读者,正是因为肤色。
1.黑人阶层的“他者”处境
这里所说的黑人阶层的“他者”处境,即指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种族歧视,英文为Racial Discrimination,是指根据种族将人们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并加以区别对待的行为,即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歧视行为。美国的种族歧视表现为,绝大多数黑人因肤色被剥夺了享有与白人同等待遇的权利。种族歧视是对人性的一种蔑视,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非色》这部小说中,有吉在描写黑人的“他者”处境时,没有单刀直入,而是通过主人公笑子等四位日本“战争新娘”在美国的遭遇体现出来的。首先让笑子感到种族差异的是她和托姆的相识、相恋和结婚。因为托姆是个黑人,所以整个恋爱过程都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就连笑子的妹妹都与她划清了界限。毕竟还是爱情战胜了一切,笑子义无反顾地与托姆结了婚,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不久她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她怀孕了,母亲因为担心她会生个黑孩子,所以极力反对。在当时的日本,虽然很多日本女人迫于生计会嫁给占领军的黑人士兵,但是她们不会给黑人生孩子,每当发现怀孕都会把孩子打掉,这已形成了一个习惯。但是笑子还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一次,是母性战胜了一切!当托姆回国后,笑子认为可以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然而她引以为自豪的英语,也因为“有黑人口音”而在面试时遭到了市谷高地的联合国军队第八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拒绝。种族歧视的烙印已深深地烙在了笑子的心上。面对一个完全跟托姆一样的黑人孩子梅丽,笑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受到了嘲讽与轻蔑,梅丽因为肤色跟别的孩子不同,也受到了其他孩子的排挤和欺负。母亲曾经劝笑子把梅丽送到孤儿院,同时跟托姆离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是笑子拒绝了。这个时候,母性又战胜了一切!为了梅丽,笑子选择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到一个梅丽可以自由呼吸和自由创造的地方去。
与笑子同船去美国的还有三个日本女人,分别是丽子、志满子和竹子。笑子和竹子的丈夫都是黑人,竹子的儿子也是黑人的孩子,梅丽很快跟他成为朋友,而丽子和志满子的丈夫都是白人,丽子是个年轻漂亮的日本女人,她的丈夫是波多黎各籍白人男子,英俊潇洒,为了爱情,丽子远渡重洋与丈夫团聚。志满子的丈夫是个意大利籍白人男子。大家都很羡慕丽子找到了门当户对的爱人。四个女人,各自怀揣着梦想来到美国,等待她们的却是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当笑子来到充满豪华气息的国际大都会纽约时,她看到的自己的家却是哈雷姆区一个狭小的半地下室,而且只有一个破沙发和一张床。她无数次地感慨:这当真是美国吗?为了生计,笑子刚到美国,就到内藤餐厅去当服务员,过着艰辛的生活。笑子还受到了同为日本人的井村的骚扰,原因是笑子是黑人的妻子,在他们眼里,黑人的妻子是没有尊严的。在把黑人视为劣等民族的美国,身为黑人妻子的笑子也被有色化,被看成低贱的人,不被人尊重的人。
丽子和志满子的丈夫分别是波多黎各籍和意大利籍的白人,他们虽为白人却也同样受到了歧视。就连身为黑人的梅丽在她的作文《我的家庭》的最后都写道:“我不会同波多黎各人结婚的,因为父亲讨厌他们。”[2]155原来,波多黎各籍的白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竟在黑人之下!
波多黎各在波多黎各语中是“富港”的意思,它是位于大西洋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岛屿国家。该岛屿的面积很小,只有8897平方公里,人口却很多,大约200多万人。波多黎各在1509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又令其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所以,波多黎各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美国为了便于统治,给波多黎各人强行加入“美国公民籍”,于是,大量的波多黎各人便成为名不副实的美国公民。而在真正的美国人眼中,波多黎各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这个事实很出人意料,如果不深入美国社会中,谁会想到白人之间也存在歧视呢!这正如丽子和志满子也不知道这些,她们自以为嫁给了门当户对的波多黎各籍和意大利籍男子一样。
在美国,笑子面对贫困与歧视,没有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了坚强地面对。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黑人的妻子,自己的孩子也是黑人。在笑子的世界里,或许没有人种的区别,她在莱登夫人家里做保姆时,很勇敢地承认了自己是黑人妻子的事实。在她接受莱登夫人的邀请,参加国际性的宴会时,心情无比激动:“明天就不同了。明天我也和夫人一样,作为一名国际人物,同他们平等交谈了。”[2]246笑子当时的内心充满了胆怯,不敢奢望,说明作为黑人妻子的她是多么渴望得到平等的待遇!莱登夫人看出了她的心思,鼓励她说:“笑子,不必犹豫。人人平等,联合国是这方面的典范。”[2]246小说的最后部分,笑子最终选择与黑人站在一起,到黑人的工厂去工作,与黑人同甘共苦。这种选择是心灵深处对黑人的一种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更是向存在严重种族歧视的美国种族制度的一种挑战。笑子以实际行动选择与黑人为伍,实际上是与黑人的平等对话,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女性形象。
1963年11月20日,即《非色》发表的当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除种族歧视。1966年3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禁止种族歧视的存在,将消除种族歧视付诸法律条文之上。1973年11月30日联合国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又再次声明,种族歧视即为犯罪。在小说中,有吉通过四位“战争新娘”的遭遇以及对她们在美国生活的细致描写,揭露了标榜公平、人权的美国社会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以及对人性的摧残,同时也向读者揭示了黑人阶层在美国社会的“他者”处境。
2.“他者”的话语权
关于话语权,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写道: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就是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所以,话语与权力是互为依托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谁掌握了话语权,谁便掌握了一种强大的思想权力。[3]130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性别社会下女性被置于男性的“他者”地位,女性不再是独立意志的主体,而是客体[4],是作为男性的“他者”而存在的,女性要想成为独立的个体,要想成为完整的、具有平等人权的主体,必须要获得话语权。有吉在《非色》故事情节的设计中,无疑是倾向于女性的,也就是说她赋予了女性足够的话语权。小说描写了战败后的日本,笑子为了母亲和妹妹的生计而到占领军的酒馆当服务员,这里没有提到她的父亲,父亲角色的缺失是不言而喻的。小说中所出现的男性,是身为黑人的托姆、波多黎各籍的何塞、犹太人后裔的莱登先生等,这些人虽为占领军却是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代表,他们没有话语权。小说中所能听到的是“战争新娘”的女性的声音,是美国社会“他者”的声音。而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是作为男性的“他者”而存在的,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但在这部小说中,有吉赋予了女性呐喊的“双重奏”,对于小说主题思想的深化更具有表现力。
小说中四位“战争新娘”的遭遇是主线,在这四个人物的塑造上,有吉泼墨最多的是两个人物,即笑子和丽子的形象。两人的性格不同,笑子是个在残酷的生活中不断地接受现实并且顽强地拼搏,最后融入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而丽子则活在自欺欺人的现实世界中,是个虚伪的人,她最终选择了自杀。最初当她们同船来到美国时,笑子因为丈夫是个黑人,不得不在哈莱姆黑人区过着艰辛的生活;而丽子因为丈夫是个白人,她对生活的期待值很高,认为自己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她,波多黎各籍的丈夫即使是个白人,但在美国,地位还不如黑人。丽子没有选择重新回到日本,尽管她在日本的家庭还是富裕的。虚荣心促使她留在了美国,并且用打工挣来的钱购买奢侈品,将照片寄回日本去,炫耀自己幸福、富裕的生活。然而,残酷的现实打碎了她的梦,她怀孕了。在当时的美国,堕胎是犯法的,丽子想把孩子做掉,为此她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但最后还是没能成功。丽子怀孕的事实昭示着她自欺欺人的骗局必将被揭穿,然而她是一个活在梦中的女人,她接受不了家人知道真相的事实,从而选择了自杀。“丽子依靠梦想勉强支撑起来的生活,在妊娠这一事实面前土崩瓦解,女人身体变化强烈地震撼着她的情绪,怎样愚蠢的女人,也会面对现实的。”[2]204丽子的遭遇是可悲可叹的。然而,试想如果丽子能够如其所愿地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白人作为妻子的话,她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究其原因,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断送了丽子的梦想,造成了丽子生活的悲哀。丽子的命运见证了种族歧视对人性的残害,也戳穿了美国社会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谎言。
与丽子的生活态度不同,笑子虽然也挣扎过,她在日本发现自己第二次怀孕时,毅然决然地选择做了人流手术,她不想再有一个黑人孩子降临在人世间。然而,当她到了美国,与托姆共同生活时,却又怀孕了三次,生下了芭芭拉、贝蒂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沙姆,同时,她努力工作,赚钱维持家计和孩子们的开支。笑子的生活态度是积极向上的,虽然作为一个黑人妻子处处遭遇歧视,但她没有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与黑人一起,到黑人的工厂上班,从心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黑人。“我的丈夫是黑人,尤其是我的孩子也是黑人,为什么我没有早点想到这些呢?”[2]259“我已经变质了,就像华盛顿的樱花那样,我是黑人!”[2]260笑子在美国生活的七年时间,深深体会到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其中的辛酸与痛苦自不必说。幸运的是,她最后终于自我觉醒,选择与黑人一起同甘共苦。可以说,笑子自我觉醒的道路也是一条自我解放的道路。
有吉笔下的女性大都是坚强的,正如小说中的笑子,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笑对人生,坚强地活下去。她们是善良的、勇敢的,无形之中向读者传递一股正能量。《非色》中的“叙述话语是女性”[5],有吉赋予女性们足够的话语权,这无疑是对男权话语的一种颠覆,更加突出了小说的女性主题。同时,笑子与丽子命运的鲜明对比,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对人性的残害,很好地展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
三、结束语
《非色》是有吉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的开篇之作,该小说最初刊登在《中央公论》杂志上。1982年秋,《非色》的中文译者李德纯先生在日本会见了有吉。有吉曾为《非色》中译本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没有直接刊登在《非色》的中译本上,但它却道出了作家的创作目的与作品的意义:“读者可能认为,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当时纽约社会的种族问题,而我的意图却是想借美国,来反映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不平等思想。”[6]目前,美国黑人运动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战争新娘几乎全都离婚,她们大部分也已是60岁左右的人了。然而,我认为,只要人们具有的优越感、自卑感在本能上还存在着歧视意识的话,要想彻底解决种族歧视问题是很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小说的主题,“不管再过多少年也不会过时的。”[7]由此可以看出,有吉创作这部小说的真正动机在于消除人类本能具有的优越感、自卑感和歧视意识,主张人类平等。
在小说素材的选择上,有吉没有机械地罗列,而是通过塑造四位“战争新娘”在美国社会的“他者”形象,真实地再现她们的遭遇,这就决定了小说强烈的女性主题,所以,《非色》又是一部女性作品。有吉塑造的人物有血有肉,通过主人公笑子展示了女性的顽强与伟大。对于爱情,她是一位勇于为自己的人生做主的女性;对于孩子,她是一位敢于牺牲的伟大母亲;对于生活,她是一位顽强面对残酷现实的强者。可以说,有吉在这部小说中采用“他者”之“他者”的双层结构,通过“战争新娘”,揭露了日本战败后为了生存来到美国的“他者”形象,再通过她们在美国的遭遇与目睹的现实,揭露了美国社会严重存在的种族歧视。无疑解读这部小说中的“他者”形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与价值,把握有吉佐和子文学的精髓。
[1]李小江.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的典范——《非色》[J].外国文学研究,1988,(2).
[2](日)有吉佐和子.非色[Z].李德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3](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任利伟,梁飞.后殖民语境下《喜福会》中女性话语权的复得[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5]吴菲,任常毅.并非因为肤色——对有吉佐和子的《非色》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8).
[6]李德纯.天涯涕泪一身遥——读有吉佐和子的《非色》[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1).
[7]李德纯.战后日本文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杨春
“the Other”Image in Ariyoshi Sawako’sNot Becauseof Color
KOU Shuting
Not Because of Color is the first of Ariyoshi Sawako’s series of novels on social issues.By following four Japanese wartime brides’suffer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novel reveals the miserable torment brought about by America’s racial discrimination.Those so-called“wartime brides”are not only“the other”by gender,but also“the other”in American society.In this sense,the black people are also“the other”compared with their white counterpart.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black others and their say in the novel.
Ariyoshi Sawako;Not Because of Color;feminist;the other
10.13277/j.cnki.jcwu.2014.06.011
2014-10-22
I106.4
A
1007-3698(2014)06-0081-05
寇淑婷,女,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女性文学。271021
本文系泰山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女性文学视角下的有吉佐和子文学作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T12QW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