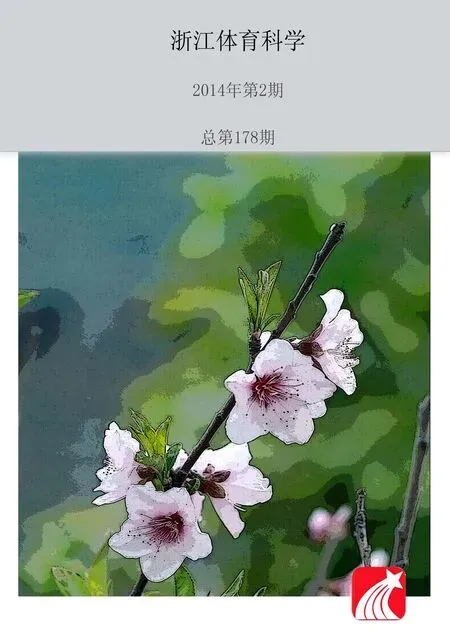竞技运动
——基于身体的返魅
马冠楠
(上海中学 国际部,上海 200231)
人,总被自己所处的时代扣留。现代人正浸溺于一种祛魅的“理智化”生活。当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解密活动无孔不入。“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马克思·韦伯在近一百年前的言语放在今日,更加应验。祛魅后的世界是苍白无力的。在现代技术文明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神灵遭到摧毁,人也因此失去了精神上的依附,普遍徘徊于困惑中。显然,科学与技术远远不是万能的。这也就是为何“康德在科学认知领域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但是在自由意志领域却又引进了上帝。在康德看来科学对于以上帝为标识的信仰,具有无法理解与不可言说之无能性。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道德、信仰问题,如果硬要科学技术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则会陷入谬误[2]。”技术理性是投向客观世界的一种映像式的关照。它遵循的判断法则是人类的主观世界是否精确地统摄了客观世界。显而易见,在充塞技术理性的人类活动中,价值判断付之阙如。这也就是为何无论现代科技何等昌明,也无力解决关涉人类为何存在、如何生存的生存论问题。真理是凌超于现象世界的,而科学技术仅是人类理性对现象世界的直观把握。在现象世界之外,在精神世界与价值世界中,人类倘若仍旧运用科学技术求索真理,那必然是缘木求鱼。在这样的时代困境中,人类需要做出返魅的努力。这种返魅不是谋求技术文明的历史倒退,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期冀重拾道德、信仰、生存价值等人类存在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复归一种崇信迷魅、切近天地神灵的质朴古风。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这场返魅的努力中,竞技运动的价值何在?我们将从竞技运动的神性底蕴与现实发展两个方面对这一疑问进行解答。
1 自然的祛魅:表征与反思
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的存在是先验的。在蒙昧时期,人类对自然怀有一种崇拜、敬畏以及依赖的子民心态与宗教情感。一天的日夜之分、月亮的阴晴圆缺、暴雨前的电闪雷鸣、四季周而复始的更迭、大山的静默无声、江河的奔流不息、万物的繁衍承续……这些自然现象的存在与发生遵从着人类无法解释的规律。彼时,人是附着于自然的。自然如母亲般,为人类的生养提供了食物与居所。同时,自然的伟力也令人惊惧。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走兽草木……万物背后皆有神灵。人类祈求通过祭祀、巫术来得到自然神灵的眷顾与恩惠,通过身心的臣服来获得灾害的免除。图腾崇拜是人类表达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形式。有很多动物(蛇、鹰、豹等)、植物(麦穗、枫叶、桑树等)以及其他自然物(江河湖泊等)被某些部族奉为自己族群的图腾。事实上,不少著名的宗教学者都认为人类最初的宗教崇拜对象是自然物和自然势力。宗教起源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3]。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的巫术与祭祀活动并非仅仅象征着原始人类对自然神(以及其他神秘之物)的顶礼膜拜,同时祈求在臣服的跪拜中达到一种人神的沟通互动。但在十七世纪欧洲兴起启蒙运动之后,世界就踏上了被日渐祛魅的道路。“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4]。”“非神化”也是海德格尔提出的近代五种基本现象之一。理性的高扬与科技的发展使人们不再相信神话与巫术,宗教精神遭到了自然科学的部分阉割;不再相信这世界上存有不可认识的事物,万物都可以被摆放到客体的位置并加以逻辑分析;不再相信生命终极价值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物质受到过度地追捧而成为精神的仲裁。这三点就是自然遭受祛魅的表征,其实也可以说是原因。
当世界祛魅后,理性的不断越界最终导致了理性自身的“二律背反”。它的表现包括:自然沦为盘剥对象、工具理性垄断、人类中心主义泛滥、道德边缘化、宗教精神流离失所等等。马克思·韦伯将世界的祛魅分为两类:自然的祛魅与社会领域的祛魅。其中,自然的祛魅是技术理性发展的直接结果。自然祛魅的过程就是人类对自然神秘性怀有敬畏的心理不断消弭的过程。自然崇拜弱化甚至消失后,人类也因此阻断了自身与自然之物、自然之神的原始联通。尽管现代技术理性的确使人类逐渐摆脱原始蒙昧的羁绊,带来了物质财富喷涌,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与天地的分离,甚至尖锐对立。在讨论科学方法所固有的工具主义特征时,马尔库塞曾引用魏茨泽克的观点。后者认为:“科学通过消除中世纪的神话而起步。但其实它不过是建立了另一种不同的神话而已[5]。”现代科学所创设的“神话”带来的是一种“人神”的湮灭,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神”、“机器神”、“技术神”乃至“金钱神”。这些都可以概括为“物神”。这一由“人神”向“物神”的更易深刻地反映出人类精神的失落与生命价值的贬抑。对祛魅的本质进行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它植根于西方传统的二元论。世界被放到一个对象化的位置,而人类则凌驾于其上。启蒙运动以来,人逐渐成为了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人不再像以前一样隶属于神,世界以人的主体性展开。而人类的主体性高扬起人类中心主义的淫威,所有“非人之物”都成为观察、认识、控制、盘剥的对象。从此,一切神秘无处遁形。事实表明,自然界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而变得彻底透明。恰恰相反,自然界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了,或者说是自我遮蔽了。当没有了原始的“天人互应”,世界也就不再向人类吐露自身的秘密。其实撇开技术理性,通过直觉、冥想、体悟以及感官的直接接触,人类都能够形成对世界的认知。但单向度的工具理性无形中抹杀了人类把握自然界方式的多样性,生存也因此变得单调。面对自然界的祛魅,我们不禁要思考身体的境遇又如何呢?下文将对此展开论述。
2 祛魅世界中的身体图景
一方面,身体同自然界一样,遭受祛魅。人是祛魅的发起者,所以身体在一开始并未成为祛魅的对象。在近代以前,身体是一种神秘的符号。但当祛魅势力不断膨胀,它的对象便从宗教领域、自然领域过渡到人的身体。大卫·勒布雷东以西方解剖学发展为出发点,对身体的祛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基督教统摄时期,人被视作上帝的杰作,任何破坏身体的行为都受到禁忌。因此,外科医生、剃须匠、屠夫以及刽子手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但是随着解剖学在西方的发展(正是身体受到祛魅的过程,笔者注),“身体被置于游离状态,与人分离开来。它作为独立的实体,成为研究的对象[6]。”人开始对身体进行肢解,前无古人地揭示出血管、神经、肌肉、骨骼的各种秘密。随后,受笛卡尔二元论与机械论的影响,身体被贬抑到一种远低于“我思”的境地。在笛卡尔眼中,身体并没有因为是“人的身体”而获得特殊的关注,身体仅仅是“一个由轮子和摆构成的钟表”。身体曾经是“活生生的意义的纽结”,构筑了“一个表达空间”(梅洛·庞蒂语)。但在解剖学技术的解蔽揭秘下,身体之魅不断遭到摧毁。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分析了艺术品是如何在现代技术的影响下进入机械复制的时代,从而失去了自身所独有的“灵韵”。大卫·勒布雷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身体也变得可以替代,现代机械医学的飞速发展使人体构造进入了 “工业复制的时代”。当身体不再是神的创造而成为人的发明,那也就毫无神秘可言。但是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庆幸,那就是解剖学依然无法解释为何身体可以在异常情况下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说明:身体之魅尽管气若游丝,但仍未灭迹消亡。
另一方面,人自身也遭到了物化,身体降格为“身器”。身体在遭到祛魅后沦为资源性实体的过程与自然在遭到祛魅后沦为盘剥对象的过程遵循着同样的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逻辑。世界的祛魅与理性的自负密切相关。马克思·韦伯对理性进行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在西方传统二元论的影响下,理性逐渐自我简化为工具理性。当工具理性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巨大秘藏、为人类社会带来物质福祉的同时,它也异化为一种具有垄断性、霸权性的认识论。在上升为认识论之后,工具理性的作用力就超出了客观的自然世界,拓延至整个世界。在它导向下,不仅一切外物都成为计算与控制的对象,人的身体也同样受到物化,身体成为一种技术资源。海德格尔甚至颇为严肃地预言:总有一天,人类会建立工厂并按照技术的需要来生产男人与女人。考虑到基因技术与克隆技术的突飞猛进,这样的预想似乎不算荒谬。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已经完美地诠释了人的身体如何被物化为机器。祛魅后的身体成为了“新兴学科能够左右、操纵的程序化对象”,它“遭到贬低,也赋予了制造业那分工明确、重复又单调的工作以正当性。身体与机器几乎在制造业中融为一体,不分你我。身体一经与人脱离,便被纳入机器模型的范畴内[6]。”此外,福柯认为,当医生将笛卡尔开创的解剖学发扬光大时,身体还由于成为权力的对象从而遭到规训与惩罚。在与身体有关的惩治仪式中充塞了权力系统的作祟。“边沁关于圆形监狱的规划设计有助于系统地对狱中世界进行管理和监督,从而为学校、工厂和医院建立了一种驯服模式。与此相似,临床医学(Foucault,1973a)和科学意义上精神病疗法(Foucault,1967)的兴起则与医院建筑、囚犯工厂、疯人院的制度演进相对应;在这些机构中,狂野的身体受到种种约束。还可以得到论证的是众多独立学科,比如人口统计学、地理学、道德统计学、社会学的出现表明身体在城市空间中受到更紧迫的神话控制[7]。”由此观之,在受到祛魅之后,身体就如同自然一般,也沦为一种对象性的实体,被迫完成了由“身体”(精神的载体)到“身器”(物质的工具)的衰变。这一衰败仍在继续,要想对抗它,身体必须返魅。
3 竞技体育的返魅价值
3.1 追根溯源——竞技运动的神性底蕴
3.1.1 女祭司的神谕。笔者曾以“现代体育对古老神谕的违拗”为出发点,对《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一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评述[8]。该处提及的“神谕”是指希腊德尔斐神庙中女祭司毕西娅对太阳神阿波罗旨意的传达。阿波罗的预言在希腊人心目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相信在发布神谕这一迷魅仪式中,由于神的授意,女祭司会进入一种迷狂状态,从而可以用模糊的并富有诗性的只言片语向人们传达神的预言。在古希腊,人们对阿波罗怀有深刻的敬畏,所以他们也将女祭司毕西娅口中的神谕奉为圭臬。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迈锡尼文明湮灭了,希腊进入了长达3个世纪的黑暗时代。面对可怕的衰败,伯罗奔尼撒人束手无策,于是国王派代表去德尔斐祈求神谕。太阳神阿波罗只说了一句话,那就是:“你们立即开始体育比赛吧”。之后,伊菲多斯国王还曾亲自前往德尔斐神庙求谕。文献记载,当时女祭司的神谕是:复兴体育比赛,给获胜者颁奖,橄榄枝环,野橄榄树枝编成的环[9]。塞莫斯·古里奥尼斯认为,文明的衰败是因为攻击性的自然本能使人类弃玉帛而动干戈,舍情谊而树敌意。女祭司口中恢复体育运动的神谕藏有巨大的秘密。他从词源学角度出发,指出“KOTOS(希腊语,指内心完全被愤怒占据)”与“KOTINOS(希腊语,音译为‘科蒂诺斯’,指野橄榄枝环)”读音相近,词根相同。野橄榄枝环象征着“人类攻击性本能通过比赛和公平的竞技转化为高尚精神价值的质变过程”,而这一质变过程就是我们的“体育运动[9]”。由此可见,现代竞技运动,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发展与希腊神话、神具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德尔斐神庙的神谕是一个方面,而二者的联系远不止如此: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地与希腊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是同名的;古奥林匹亚体育场的大门开向宙斯神庙;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为重要的宗教仪式就是用公牛向宙斯献祭。这些联系都说明竞技运动并非只是一些肢体动作这么简单。它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神秘,超越逻辑”。当然,这些关于竞技运动的希腊神话在世界遭受祛魅后的现代也许只会被视为无稽之谈,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亟待救赎的张狂与悲哀。
神话是最原始的赋魅方式。希腊的诸多神话将神秘性的外衣披到竞技运动的脊背上。而这种神性的底蕴是竞技运动引领人类踏上返魅之路的根本前提。这里必须说明,我们倡导的返魅并不是要使历史倒退,使人类回归蒙昧状态,而是代表一种精神的复古,对竞技运动原初神性的复归。此外,在古希腊竞技运动中,最受推崇的是运动员纯洁的灵魂与自然的美德。竞技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实现自我、博得荣耀、与神亲近的身体活动。锦标与记录绝不是最主要的现实目的。在古希腊,甚至不存在运动员的成绩记录。考古发现表明,聪明的古希腊人为了努力避免青年人从事有害身心的成绩至上的竞技运动,在每次比赛时都准备不同的铁饼,这样就没人会说自己创造了记录[9]。古希腊人对竞技运动所持有的价值观非常有助于我们对现代盛行不息锦标主义进行深刻反思。作为基于身体的返魅,竞技运动不仅呼唤原初神性底蕴的焕发,而且也有助于重拾竞技运动中故有的朴素道德观念。道德可以被视作是独立于人和自然之外的一种社会现象。如果竞技运动在返魅同时还可以实现对体育道德异化现象的反转,那的确可谓“一石二鸟”。
3.1.2 生殖崇拜与原初竞技。在原始时期,生殖的力量是大自然神秘性的重要来源。生殖与生产一样,是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瓜瓞延绵的根本基础。生殖崇拜也以神话、绘画、雕塑甚至自然山川的形式广泛存在于世界各类宗教之中。例如,关于华夏民族女娲伏羲人首蛇身兄妹交尾的神话、描绘古希腊与罗马生殖之神普里阿帕斯硕大阳具的油画、生殖器盘成眼镜蛇的印度湿婆雕塑以及我国江西龙虎山中的金枪峰和羞女岩等等。本文论及的原始的生殖崇拜与原初竞技的关系主要需要通过裸体审美这一因素进行连接,并且与古希腊文化直接相关。
在古希腊人的文化观念中,神秘的生殖代表着自然无穷的力量。而两性的身体是生殖繁衍的基础,于人于神,皆是如此。所以身体在希腊文化中成为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审美对象,并且它经常以裸体的形式展现自身。同时,生殖的力量与身体的强壮完美是成正比的。在古希腊神话中,波塞冬、宙斯等男性神都是力大健美的,而阿佛洛狄忒维纳斯等女性神都是裸体美丽的。在生殖崇拜观念的影响下,身体的形象得到承认,身体的地位得以提高,并最终造成了身体的赋魅。生殖是基于身体的,是一种力与美的完美结合,这与竞技运动如出一辙。神是神话的主体,人是竞技运动的主体。在古希腊,这两个主体都推崇身体的裸露。从希腊雕塑艺术中,我们也可以窥探由裸体审美透露出的神与竞技运动的密切关系。神、战士以及运动员是希腊雕塑艺术中经常以裸体形式出现的三类身份。《海神波塞冬像》、《战斗的勇士》以及《掷铁饼者》这些雕塑都是以动态的身体姿势呈展出裸体者雄壮有力的形象。李咏吟先生曾指出,在希腊雕塑艺术中,阿波罗神性的诞生于竞技运动是分不开的:“阿波罗神像的诞生于竞技运动分不开……作为一个健美之神,阿波罗神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成了运动和竞技中美的一种象征。正因为如此,希腊雕刻家才能把美的人体和神性的理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0]。”不难发现,神、战士以及运动员这三者具有共同的身体特征:体形匀称舒展,肌肉粗壮有力,面容果敢威严。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运动员与神灵在身体与精神上的相似,古希腊人才会将裸体审美引入运动竞技。众所周知,裸体曾广泛地出现在古希腊的各种活动中,包括祭祀仪式、歌舞表演以及运动竞技。根据德国人利奇德认的说法,公元前720年的第15届古奥运会肇始了古希腊人进行裸体运动竞技的先河。运动员裸体进场、比赛、领奖。在神圣的奥林匹亚,他们受到宙斯的恩典;涂满亮油的胴体在阳光的沐浴下,荣光熠熠;在力量的比拼与速度的竞逐后,他们像神灵一般赢得民众的欢呼与敬畏。就是这样,生殖崇拜经由裸体审美与原初竞技两次过渡,转变为了身体崇拜,而运动员也通过裸体审美实现了自身的赋魅。其实,生殖崇拜不仅使古希腊人追求裸体审美,还使他们热烈地歌颂自由、炽烈的爱情。爱欲促使男女的结合,由此可以复制或者模拟自然界无穷的生殖力量。在雅典奥运会上,所有的冠军都头戴月桂花环。月桂花环的象征意义来自希腊神话中光明之神阿波罗与仙女达芙涅的爱情故事。阿波罗追求达芙涅未果,而后者化作一株月桂树。从此,月桂树就成了阿波罗最爱的树木。他不仅自己头戴月桂花环,并且将此当作勇士的冠冕、诗人和凯旋者荣光的象征。也正是因此,在古奥运会与现代奥运会中月桂花环才成为对冠军的嘉奖。
除裸体审美之外,生殖崇拜与竞技运动还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超越必死的命运。人是向死而在的,但却生来秉持拒斥消亡和衰败的生命意志。这一先验命运带来的生存之痛使人类无时不在探索自我救赎之道。生殖崇拜与竞技运动都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在尼采眼中,人类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生殖力量将重生的可能赋予人类,竞技运动则负载着人类冲破有限性的希望。它们所饱含的超越性生存价值观为人类创设了一种哲学化的存在方式。此点另属他论,此处不做赘述。
3.2 现实发展——竞技运动的类宗教性
3.2.1 宗教式的共同情感。在由祛魅导致的深刻危机中,韦伯认为最为严重的就是世界出现了“诸神之争”。要注意,此神非彼神。此处的“诸神”是指代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信仰这类超验的生存要义。祛魅通过“灭神运动”,使神话(神秘主义的主要载体)在世界中隐遁。韦伯认为,在世界遭到祛魅后,“那些终极的、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1]。”祛魅肇始了一系列决裂现象:人与神的决裂、神话与世界的决裂、个体与群体的决裂、个体与个体的决裂、生存意义与生存的决裂。在个人主义的上升发展中,“人类”这一概念愈加模糊,“我”这一概念挺立出来。其后果就是,人开始在主体性视域内审视除自身之外的一切,并以对象性思维盘算事物的使用价值。显而易见,“人类的个人化历程与大自然的非宗教化并驾齐驱[6]。”我们可以说,人类生存与自然发展的失衡一路伴随着人类物质营造与精神进阶的失衡。在秩序上,祛魅前的世界是更为简单的。人与神的明确划分使个体牢牢地落入人类共同体的怀抱中。人们不仅分享类似的信仰,而且秉持较为整齐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彼时,“我”是安于“我们”之中的。但在世界祛魅后,这一同一性体系便分崩离析了,人们陷入价值体系的纷争中,从对神的共同朝拜转为各自为政的理性算计。随着宗教式的共同情感日渐式微,人类共同体遭到破坏。时空流转,人们似乎已经不再隶属于一个完整的群体,不再酣醉于澎湃激昂的群体激情,不再分享一种朴素的共同情感——人的世界分裂了。
人类社会的和谐与人类族群的和平必须依靠一种宗教式的共同情感进行维系。现代竞技体育在提供集体生活、塑造人类共同体以及培养群体情感方面具有不容质疑的作用。现代竞技运动的高度组织化为体育崇拜构建了坚实的基础。吕大吉先生在论述宗教组织的社会作用时指出:宗教的组织化“把个人性的信仰变成有共同信仰的群体和社会性的组织。由于此,个人性的变动不居的内在信念逐渐固定为共同信奉的制度化的教义信条,分散性的个人崇拜行为逐渐发展为对信仰群体有约束力的信仰体制[3]。”由此可见,宗教组织化对于有利于形成宗教团体,也有利于维系社会群体。同样,现代竞技运动的高度组织化既维系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因为能够培养一种宗教式的共同情感而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竞技运动的规模与影响力已经足以让它与宗教现象相媲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众超过10亿的电视直播事件;2010年NBA全明星赛,108713名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的东西部明星的巅峰对决;有超过1亿的美国电视观众收看了第44届NFL超级碗总决赛……李力研先生在分析体育崇拜现象时十分突出“竞争性”对于体育运动,特别是对于竞技运动的特殊意义。他认为:“体育以其竞争的方式,呼唤着人们投入到这一神圣、崇高、无比壮观的运动中去……体育运动就是人类本能与欲望中有关竞争与征服的宣言书[11]。”我们认为,李力研提出的“他们”是指体育运动竞技的实际参与者,而并没有涵盖竞技运动现象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观众。观众对体育运动的寄托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个人崇拜与共同情感,而这两者又相互交织、唇齿相依。此外,竞技运动的发生伴随着各种仪式。在古希腊,在古奥运会开始前人们都会进行一系列祭祀活动。现代竞技运动同样充满各种仪式活动,例如雅典奥运会女祭司的祷告仪式、每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入场仪式、比赛完结后的颁奖与升旗仪式、球迷的统一着装与加油口号、主队胜利后的相互拥抱,甚至包括球迷的狂欢与骚乱……这些仪式都为竞技运动的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意义的归宿,提供了一种表达共同情感的契机。在直接与间接的竞技运动参与中,人们的身心受到同样的震撼,一种宗教式的共同情感也被培养起来。在现代性祛魅的背景下,竞技运动创设的崇拜语境和群体仪式为宗教意识留藏了一块飞地。我们甚至可以说,竞技运动成为了宗教的一种替代物。
3.2.2 神与神话的重启。笔者曾在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视域内,探讨了竞技运动与诗意的神话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竞技运动是指向一个天地人神四维立体的系统。在本节中,我们将揭示竞技运动员与神、神话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12]。在世界祛魅后,神话的消解也直接导致了神的缺位,人类进入一个“众神无处居住的世界”(海德格尔语)。在诸神逃遁而上帝尚未到来的贫困时代,神与神话的重启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上文我们已经通过裸体审美分析了竞技运动员与神灵的相似之处,并进一步指出竞技运动成为了宗教的一种替代物。对竞技运动员的个人崇拜是现代竞技运动描绘出类宗教图景的必要条件。因为“虚幻的宗教观念要想成为信众共同崇拜的对象,就不能始终局限在主观幻想世界之中,而必须把它表象为信众可以感知和体认的感性物[3]。”所以,在竞技运动创造的宗教氛围中,竞技运动员特别是精英运动员便成为了神灵观念的感性象征。宗教学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人格化”,意指神与人是同形同性的。神虽然具有各种超人间、超自然的属性,但他们依旧具有人形与人性,是一种人的升华。可以说,竞技运动象征着“人”的神格化。人既是有限之物,又是天生的越境者。在生存与毁灭的悖论中,人类必须通过不断逾越自我身体与精神的界限,突破先验有限性的羁绊,迈向永恒的无限。在这一生存的本质要求中,竞技运动就是人类在身体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的同时完成精神进阶的重要形式。人“依其天性生来即近乎神,紧步神之足迹,有达乎神之通路。”竞技运动员是人类的身体贵族,作为饱含生命力的强者,他们以挖掘身体潜能的方式向世界发问。在奔跃腾走中,他们以强健的身体与坚韧的意志编织出凡人的神话。精英运动员可以被视作“人到神的过渡”。在这一问题上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应该将希腊众神视为运动员。因为神性的人格魅力都是建立在“完美”的身体条件上。“追求身体的完美成了通向接近众神的一条客观之路。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胜利可视为神的恩赐,是这种恩赐使胜利者成为了“半神”(也就是说成了“英雄”,其起初的意义就是‘半神’)。[13]”在现代体育舆论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将与神相关的话语引用到对运动员卓越表现的描述中。例如,“神灵附体”、“如有神助”、“超人般的力量”、“上帝之手”等等,而乔丹则被奉为“披着23号球衣的上帝本人”。面对自己的偶像,竞技运动的观众则臣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穿着偶像的球衣,制作表达钟爱之情的横幅,疯狂地呼喊偶像的名字,模仿偶像的动作,听从偶像的号召……一切进行得如同宗教仪式一般。现代竞技运动带来的巨大身心震撼使观众在陶醉于体育崇拜的时候获得一种类宗教的情感。在尼采的艺术生理学中,宗教式的陶醉感是与一种力的丰富相应的。而这种“力的丰富”又是与权力意志、身体强壮以及生殖力量密切相关的。“无论在心理学上还是在生理学上,艺术都被理解为伟大的兴奋剂,都被理解为永远力求生命、力求永恒生命的东西……[14]”体育崇拜是观众对竞技运动的间接参与,它使观众与运动员一样,能够在竞技运动参与中达到兴奋、陶醉的状态。李力研先生认为:“体育崇拜是宗教崇拜的一种否定性的扬弃,是宗教崇拜可贵的颠倒。她把宗教崇拜的对象由天上拉到了地上,并使之剥落掉神秘的外衣。体育崇拜的实质就是宗教崇拜的一种特殊发展[11]”。先生的论点,我们基本认同。但我们认为,现代竞技运动在剥落天神神秘外衣的同时也为运动员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在祛魅时代,竞技运动不仅使运动员成为了神的替代者并塑造出身体神话,也在更加宏观的层次上使人类实现了对自身的赋魅。
4 结 语
世界的祛魅是一个已经发生并仍在进行的现象,而返魅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基于身体的竞技运动具有深厚的神性底蕴。这一秉性将成为它在世界返魅的过程中发挥自身重要作用的先天基础。同时,竞技运动的空前发展使之得以在创造宗教式的共同情感以及重启神与神话两个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主动认识现代竞技运动在世界返魅过程中的功用,是为了增添人类社会的福祉。然而,有些统治阶层却利用现代竞技运动的类宗教性,将它当做社会麻醉剂进行使用。纵览古今,宗教历来被视为一种精神麻醉剂,被当作一种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在这一目的导向下,竞技运动就沦为了社会问题的遮羞布和障眼法,成为一种缓解社会对抗、转移社会矛盾、释放敌意的安全阀,成为了对社会安定和谐的假象进行伪饰的手段。对于竞技运动类宗教性的这种异化情况,我们需要具备清醒的认识并予以抵制。
[1]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9,48.
[2]高兆明.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J].中国哲学史,2003(4):85.
[3]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126-130,294,59.
[4]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39.
[6]大卫·勒布雷东.身体史与现代性[M].王圆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53,86,36.
[7]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388.
[8]马冠楠.一纸煞风景的檄文——评《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J].浙江体育科学,2012,34(1):20-22.
[9]塞莫斯·古里奥尼斯.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沈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9,132,143.
[10]李咏吟.原初智慧形态——希腊神学的两大话语系统及其历史转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17.
[11]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13,2.
[12]马冠楠.竞技运动:人类诗意栖居之道——基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探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2(4):57.
[13]汉斯·乌尔里希·古姆布莱希特.体育之美:为人类的身体喝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4-55.
[14]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