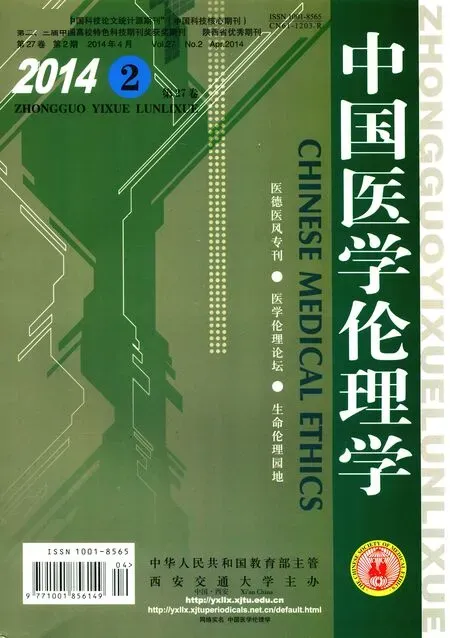“新医改”背景下乡镇卫生院医患信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李亚明,王晓燕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首都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基地,北京 100069,shuxuewang@sina.com)
新医改进程中,乡镇卫生院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工作模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乡镇卫生院的医患信任也表现出新的特征。各种新政策的实施不仅重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的支点,也改变了医患信任建构的模式。探讨医改进程中乡镇卫生院医患信任的发展趋势,将为医疗改革的推进提供借鉴,也为我们理解医患信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维度。本研究基于2013年7~8月在北京市某区3个乡镇的乡镇卫生院进行的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呈现了医疗改革在当下卫生院一级医疗机构的进展,反映了改革进程中基层医疗工作者和农村居民对彼此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切身感受。
1 管理模式的改革提高了卫生院的公信度
观察和访谈结果显示,医疗体制改革消除了某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体制因素。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医务工作者和医疗机构过度追求利益的现象一直是导致医患之间不信任的重要因素。而在医改过程中,“收支两条线”政策的实施使基本医疗服务开始体现出更多的公益性,乡镇卫生院及其医生不再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医务人员开始更多地考虑患者的需要,医疗机构的公信度大大增加,患方对医务人员和卫生院的敌对情绪正逐步减少。
B镇医务科科长于大夫从事医疗卫生工作40多年,经历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和解体,经历了市场化环境下医疗工作的剧变,也经历了当前医改政策的逐步推进,对基层医疗工作的体制沿革和政策变迁有切身感受。他在访谈中讲到,“近年来,收支两条线的实施使基层医务工作者不再需要把挣钱作为最首要的目标。由于新制度的贯彻,病人们开始感到医生不是以追求利益为最终目标,多了一份安全感。另外实行收支两条线以后,院领导也不再需要四处筹钱,转而开始在提高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上下功夫,由此为医生和卫生院赢得了患者更多的信任。目前医院很注重职工的个人发展,鼓励职工参加学历教育,保证职工参加学习的时间。”由此可见,新政策的实施已对卫生院的工作模式和运转状况产生了明显的、重大的影响。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虽然我国大部分医疗机构是公有的,但他们的财政运转还是严重地依赖于营利活动。因此,虽然大多数医疗机构在所有制上是公有,在行为上却是以营利为目的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了让人们能够负担得起医疗保健,政府给基本医疗服务制定了低于成本价的价格。但与此同时,为保证医疗机构不至入不敷出,政府给高新诊断技术制定了高于成本的价格,并允许药品有15%的加价率。这一定价标准造成了不正当的激励机制,医疗服务提供部门90%的经费都不得不从营利活动中谋取,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医生都被转变成了寻求利益的主体。[1]为了寻求最大利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诱导需求的行为,比如开不必要的药,过度医疗,对一些病人提供利润率很高的服务,同时对不能保证治疗费用的危重病人拒绝治疗等,这些行为都损坏了医院和医生的声誉,损害了医疗行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据于大夫介绍,在集体经济刚解体的时候,医疗服务行业走向市场,卫生院医生的工资每月只有30块钱左右,并且政府对卫生院实行差额拨款,所拨工资金额仅相当于医院一半人员的工资总量,另外一半人员的工资,医院就需要自己想办法筹措。如医院增加人员,国家所拨工资也不会增加,多出的费用就需要医院自己解决。这就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就是医生尽量多开药,多做检查。为鼓励盈利,医院实行了科室承包制,诊疗情况与工资挂钩,检查多就挣钱多。因此医院也大量添置检查设备,甚至用贷款的方式购买CT等设备。这种依靠自身经营谋取收入的模式目前在多数城市大医院中依然存在,这也是导致城市医院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医院尽量裁员,医院甚至为了增收节支辞退了护士,因为输液打针这类护士的工作大夫都能做,如果由大夫做,就能省下发给护士的那份工资。
医院进入市场所带来的一个冲击就是破坏了社会结构的平等和稳定,导致了一定的社会不安。不仅卫生院的医务工作者生活没有保障,民众对于基本医疗服务的获取也越发困难。社会经济状况的悬殊再加上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导致一些家庭因病致贫。据估计,每年大约有4%的中国家庭因医疗花费致贫,贫困家庭中有44%的家庭致贫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住院。社会经济的差距和获取卫生服务机会的悬殊也就导致了健康状况的差距,疾病给穷人带来的负担最重,特别是老年人。[2]乡镇卫生院面对的主要是农村地区的患者,医务人员牟利行为同患者无力负担医疗之间的矛盾就更显尖锐。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患者大多假设医生不会从患者的利益出发制定治疗方案和提供治疗建议,患者会对医生持怀疑态度并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选择性地接受医生的建议,甚至在很多时候,农村患者会选择拒绝治疗或根本不去医院就医。卫生院患者人数也大大减少。
医疗制度在设计上将满足医疗服务方自身的经济偿付能力或将提高运行效力的需求放在了增进患者健康利益之前,违反了有利的原则;同时有限的医疗资源分配上的不公,造成一部分患者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健康权利没有得到公正的、合理的、有效的保障,于是这部分群体对医疗行业的失望与不满直接导致了信任的丧失。[3]收支两条线的实施把医生的收益同其治疗活动隔离开来。医生的诊疗工作同其所获得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新体制的贯彻过程中,病人们开始感到盈利不再是医疗机构的最终目标,医生对患者利益的关注正在逐步加强。这些都有利于乡镇卫生院医患信任的重建。
另外,在卫生院进入市场期间,医院领导的最主要任务就是筹集经费,以至于无法顾及医院的其他各项事务。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制后,院领导把原先筹集经费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转移到提高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上。比如目前的B卫生院很注重职工的个人发展,鼓励职工参加学历教育,保证职工参加学习的时间。于大夫认为医学理论进步发展很快,不断更新,需要医生不断学习。目前B镇卫生院评主任医师需要大学本科毕业,院里很多职工都是在职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的。除了医生的道德品行,医生的专业技术水平是医患信任得以建立的最重要基础,医生专业水准的不断提高不仅能增加患者的信任和满意度,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卫生资源的效用。
2 医疗服务方式的转变增加医患亲密程度
收支两条线政策的实施也间接导致了预防保健工作在医院工作中所占比例的增加。目前卫生院的工作和医院不一样,一半的任务都是预防保健。在原先自谋经费的年代,因为预防保健无法为医院盈利,所以受到了忽视。现在因为有国家下发的固定工资,医院防保方面的工作迅速得到加强。当然更有力地推动公共卫生工作的是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政策,该政策的推广促使乡镇卫生院约60%的工作集中在公共卫生方面,超过了基本医疗在其工作量中所占的比例。这部分工作增加了卫生院医务人员同农村患者之间接触的机会,逐步拉近医患之间的关系。大量、系统的公共卫生工作成为建立乡镇卫生院医患信任的新支点。
卫生院医生平均每周下村3次左右做健康宣教并了解村民的身体状况。Q镇卫生院医生同村民建立了一对一的服务。村医办公室里存有“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登记表”,上边记录了每位村民的姓名和电话。凡在表格上有所登记即表明村民与卫生院医务人员签约进行健康管理。管理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健康宣讲,卫生院医生甚至通过发放礼品以及把宣教内容编成快板书的方式吸引更多的村民参加宣教活动,拉近了村民和卫生院医生之间的距离。另一部分是免费检查身体。据附近D村村医回忆,体检原来很少,从2008年、2009年左右才开始常规进行,基本保证一年两次。卫生院医务人员定期到村里来,届时村里进行大喇叭广播,在家里的村民听到广播就聚集到村委会。检查内容包括量血压、心电图,测血糖、血脂等。血液采样当场完成,由卫生院医生带回卫生院进行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通知。医生会建议身体出现问题的村民到区级大医院进行复诊。受访村民认为卫生院的大夫态度都很好,对村民很热情。通过定期查体,很多慢性疾病得到了发现和治疗,从而增加了农村患者对乡镇卫生院医生的信任和依赖感。
有学者用“医患关系的连续性”这一术语指称医患关系维持时间长短、医患见面次数与时间、医患相互熟悉程度。医患交往的持续性被认为是影响医患信任程度的重要因素。医患之间接触时间越长,交往越频繁,就越容易建立互信关系。1999年Dorr等人研究发现,医生与患者保持长期友好的联系更易于让医生相信和同情患者的个人需求,更易于让患者理解医生的难处。[4]在卫生院的公共卫生活动过程中,村民对卫生院医生的行为和道德水准有了直观的了解,卫生院医生对于村民的健康状况和主要需求也获得了全面了解,这种了解是建构深度信任的基础。曾有观点提出,随着人们就医时的自由选择和问诊的随机性不断加大,很多疾病的治疗过程出现间断性,医方与患方的互动多以单次博弈的方式出现,阻碍了彼此之间信任关系的产生。[5]目前乡镇卫生院通过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增加了医患交往持续性,使本来是陌生人的医生和患者逐步建立起熟人关系,医患间亲密程度的增加促进了信任关系的建立。
卫生院医生频繁下乡不仅能够充分了解慢性病患者的身体状况、疾病史和饮食起居,也可以详细的对患者进行指导和教育,建立起朋友关系。比如糖尿病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C镇和B镇卫生院的医生通过对患糖尿病村民的健康管理,与患者深入沟通,发挥不可替代的“降糖守门人”的作用,从而与患者和患者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情感支持为基础建立的医患信任,比以技术信息支持建立的医患信任关系更加牢固,并能形成稳定的、固定的关系。[6]乡镇卫生院有基本固定的患者群体,患者主要是集中在辖区村落的居民,同这些居民间建立亲密的情感联系,将有益于卫生院各项诊疗工作的进行。
3 新政策的落实带来医生沟通上的压力
新医改的各项政策,比如基本药物零差率和“新农合”报销政策等都有助于缓解医患关系压力。但为保障政策的目标得以实现,同时有一系列相关规定用于规范该政策在各级医疗机构的具体操作,这些规定因为给村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方便和不习惯,常常降低患者就医的满意度。同时因为农村地区患者文化水平较低,不了解卫生政策和规定,常常把这种不方便和不习惯归咎于医生和卫生院,从而在现阶段引发了很多患者对卫生院医生的质疑,阻碍了医患信任的建立。在新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只有依靠医生耐心、详细的解说,才能缓解由此引发的医患矛盾。
为保障群众基本用药,减轻医药费用负担,2009年8月,原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作为新医改的重要举措,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工作正式启动。乡镇卫生院实现了基本药物按照进价销售的零差率销售。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全覆盖,大多数省份正在积极推进基层医疗机构的综合改革,通过这项改革,基本药物的销售价格平均下降了25%左右,有益于扭转基层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局面,但医疗机构进药的种类根据医疗机构的级别而有所不同,乡镇卫生院一级的医疗机构有权限进购的药品非常有限,影响了患者就医的满意度。
三级医院可进药品最多,二级医院可以进的药比一级医院多,一级医院可以进的药物品种最为局限。就在这个有限的可进药物名录中,还有很多药无法获得。药物只能从指定的批发机构购进,很多药因批发机构称没有而无法购得。很多受访医生认为批发机构没药的原因是药厂因这些药利润不大所以不生产了。很多这类药物还是很常用、很实惠、很廉价的,比方说破伤风注射液只要1块钱左右,但是这种药有段时间就无法购进,如遇患者需要,只能建议其转到医院去打,给患者增加了麻烦。另外有些患者熟悉的药原来经常用,现在在乡镇卫生院却开不出来了,常常会引发患者的不满和不理解。虽然没有的药物都可以通过其他药物进行替代,但很多患者习惯了使用某一种药,换药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为保证资金的有效、公平地利用,每个乡镇卫生院每年医保资金使用的额度不能超过上一年的120%,如果超出限额,医保资金将难以承受。乡镇卫生院超额3次就会被摘掉医保定点医院的牌子。相应地,所访3个乡镇卫生院为做到这一点,均出台了急性病开药不能超过3天药量,慢性病不能超过2周药量,单次门诊报销金额不超过150元等规定。此后,很多村民感觉到开药变得有点麻烦,想一次多开点药是开不出来的。这样当然可以避免浪费,也能起到保护患者利益的作用。但有很多村民误认为这是医生为了让患者多挂几次号想出的方法,由此产生矛盾。
由此,这些本来意在维护患者利益的制度和规定,成为了在实践中消解医患信任的因素。在政策不断成熟、成形的过程中,政策与实践会经历一个磨合时期,而这个磨合过程所产生的医患关系上的压力只能由医生悉心解说来化解。医患沟通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通过沟通使患者认识到医生所采取的每项措施都是从患者的切身利益出发,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7]特别是在农村,人们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较低,自我保护意识又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沟通能力将对维护医患信任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提出医生的沟通能力与方式将直接影响患者对医生的情感信任。[8]在新医改推进的过程中,加强乡镇卫生院医患沟通环节,通过医生的解释让更多患者了解政策的目标和意义,能够维护患者对医生和乡镇卫生院的信心,由此保证新一轮改革发挥出更大效力。
[1] Winnie YIP,William HSIAO.China's health care reform:A tentative assessment[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613 -619.
[2] Xuanchuan Zhang,Li- Wu Chen,Keith Mueller,et al.Trac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are reform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in a district of Beijing[J].Health Policy ,2011,(100):181-188.
[3] 杨阳.不同医疗体制下医患信任关系之比较:中国与新西兰[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6):34 -36.
[4] Susan Dorr Goold,Mack Lipkin.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challenges, opportunities,and strategies[J].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1999,14(s1):s26-s33.
[5] 高文侠.从“拒签手术”看我国医患信任危机及其消解机制[D].济南:山东大学,2009.
[6] Oliver Ommen,Christian Janssen,Edmund Neugebauer,et al.Trust,social support and patient type-Associations between patients perceived trust,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and patients preferences in regard to paternalism,clarif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severely injured patients[J].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2008,(73):196-204.
[7] 王琦.加强医患沟通缓解医患关系[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4,20(6):361 -362.
[8] 韩晓杰.我国城镇居民对民营医疗机构信任的前因变量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