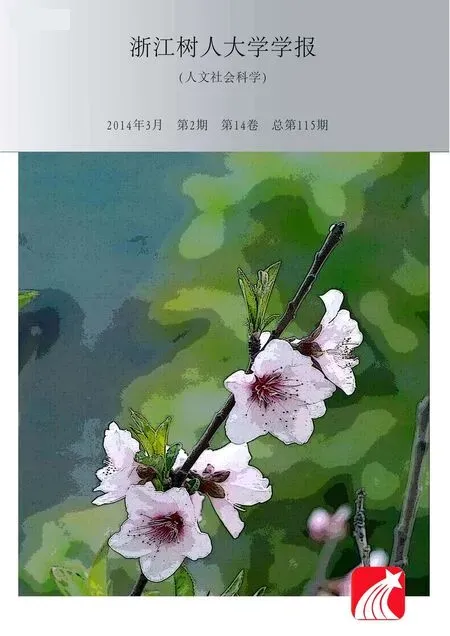论专利先用权的法益内涵及其影响
饶先成
(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专利制度作为西方文明的一大制度创新,曾被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样形容:“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①杨利华:《专利激励论的理性思考》,《知识产权》2009年第1期,第55-60页。专利制度的魅力在于其设置的激励机制,能为发明人提供一定的利益驱使,使更多的知识产品被生产出来,进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技术公开换取垄断保护。然而,专利权并非没有任何限制,我国《专利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了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几种情形,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12 -28,http://www.gov.cn/flfg/2008-12/28/content_1189755.htm。我国大部分学者也将在先使用和权利用尽、临时过境、合理使用等行为一起作为对专利权的限制。在先使用不仅体现了对专利权的限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在先发明人的创造成果,符合专利法的立法目的。专利先用权多用于专利诉讼的抗辩,以免除赔偿责任,并能在“原有范围”进行后续制造或使用。在英文中,先用权被表述为“prior user rights”,与汉语“先用权”一样,均有“权利”之意。然而,我国《专利法》并无先用权的表述。笔者查看了日本和德国专利法的英文版。日本在先使用人可以获得普通实施权,即“non-exclusive license”,而非先用权;德国规定在先使用人有权在德国境内自己实施发明创造,即“be entitled to use the invention”,不过这里的有权是否为先用权尚待考证。再看英美法系中的美国专利法,它将在先发明视为一种侵权抗辩。可见,专利先用权只是一个学理上的称谓,由于受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学界一直用专利先用权来分析在先使用,在学界对其定性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却一直使用着“先用权”的概念。目前,各国司法实务乃至学术界对在先使用已较为熟悉,我国每年也出现了大量在先使用抗辩的专利侵权诉讼。虽然理论界已经对先用权的性质作了分析,但学者们仍在探讨和追求先用权内涵的合理界定。
一、对专利先用权内涵的不同认识
目前,在专利先用权涵义的认识上,大致上有“独立权利说”“抗辩权说”和“在先使用行为说”三种主要观点。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是因为主张这几种观点者从片面角度来看待专利先用权。以下笔者分析这三种观点所存的缺陷。
(一)独立权利说
将先用权的性质定义为独立权利,即先用权不依附于专利权而存在,是一种主流认识。如程永顺在《中国专利诉讼》一书中这样定义先用权,“先用权,是指某项发明创造在申请人提出专利申请以前,任何人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做好制造、使用该相同产品或者相同方法的必要准备,在该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以后,享有先用权的人仍有继续在原有的范围内制造或者使用该发明创造的权利。”①程永顺:《中国专利诉讼》,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该学说认为,先用权作为权利,具有相对独立性,没有专利权的存在,它依然可以存在。②赵栋:《专利先用权中若干基本法律问题初探》,《科技与法律》2011年第3期,第92-96页。然而,该学说存在的缺陷使其自相矛盾。
首先,先用权虽然源于在先使用人的先行行为,法律也将在先使用作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之一,但是不视为侵权与权利的表述相去甚远。言下之意,在先使用本来是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只是在法律上作了特殊规定而已。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先用权人在专利申请日后将其已经实施或做好实施必要准备的技术或设计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被诉侵权人主张该实施行为属于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实施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技术或设计与原有企业一并转让或者承继的除外。”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02-17,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305372。主张独立权利说观点的人士援引该条,认为既然先用权可随企业一并转让或承继,更说明先用权为独立权利。④潘伟生:《专利先用权制度研究》,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14页。而笔者认为,企业之间的转让、合并和继受是企业间正常的商事行为,“随企业一并转让或承继”恰恰说明了其非独立性,就此认定先用权可转让实乃与《解释》的目的格格不入。先用权一旦转让就意味着原有企业的消亡,实际上是否定了先用权的可转让性。《解释》中的“转让或承继”可用民法的基本原理予以解释,由于企业整体发生转让或承继,继受该企业的主体自然就享有原企业的权利,承担原企业的义务。当然,这里的权利义务需作广义的理解。
我国学者援引德国学者梅克尔的“法力说”,认为权利的本质为法律上之力,所谓“法律上之力”系由法律所赋予的一种力量,凭借此种力量,可以支配标的物,也可以对抗他人。⑤韦晓云:《专利侵权中先用权抗辩问题研究》,《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2期,第35-39页。该学说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将其用来论证先用权的权利性质有欠妥当。“法律上之力”是权利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权利当然地享有法律上之力,而享有法律上之力的利益并不都是权利。
(二)抗辩权说
持抗辩权说的学者认为,“先用权是相对于专利权而言的,是对专利权的一种抗辩权,并且是依赖于专利权存在而存在的一种很不完整的无形财产权。”⑥冯晓青:《试析“先用权”及其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的适用》,《发明与创新》1997年第6期,第29页。在《中国专利法详解》一书中,尹新天也赞成抗辩权观点,认为我国《专利法》规定在先使用行为的目的在于豁免先用者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责任。⑦尹新天:《中国专利法详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805页。抗辩权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先用权在诉讼中的作用,也为进一步分析先用权的性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即先用权的诸多缺陷致其无法成为独立的权利。
抗辩权是妨碍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对抗权。民法中的抗辩权是一种实体权利,在诉讼中行使抗辩权即构成了对请求权的抗辩,而对于请求权的抗辩并不当然构成抗辩权,因此无论专利先用权的性质如何,均不影响其作为专利权的一种抗辩。以我国《民法》中的先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为例,在这些抗辩权中,产生抗辩权的原因无一例外的是由于请求权人未履行或实质履行一定的义务。而专利先用权实际上是基于在先使用的行为所产生的一种权益,专利先用权的成立与否与请求权人是否履行相关义务并无直接关联。
然而,仅从先用权的功用断言先用权为抗辩权,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境地。由于抗辩权说认为先用权随专利权的存在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专利权和在先使用共同作为抗辩权的产生原因。该观点明显地混淆了抗辩权的对象与先用权的产生原因,先用权源于在先使用人在申请日前的使用,合法的在先使用行为是先用权的正当性基础。当在先使用人遭受专利权人侵权之诉时,则在先使用人可以其因在先使用而取得的权益来对抗专利权人。很明显,在先使用与合理使用、权利用尽等一样,都可以作为对专利权的抗辩,而并非抗辩权,其性质与诸如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认为先用权为抗辩权的认识是难以成立的。
(三)在先使用行为说
在先使用行为是一个瞬间动作,是后续法律效果的原因行为。与抗辩权说相同的是,赞成行为说的学者也认同在先使用有抗辩效果。如谭筱清认为,在先使用本身不是一种单独存在的权利,而是一种对抗专利权的先使用行为。①谭筱清:《从本案看在先使用与公知技术抗辩的运用》,《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2年7月28日。因此,从本质上讲,在先使用行为说与抗辩权说并无二异,不同的是,在先使用行为说更倾向于将在先使用认定为一种原因行为。若将在先使用仅视为一种行为,必定会带来常理难以解释的现象。在先使用行为发生在申请日之前,可以认为是申请日之前的某个时间段或时刻,然而,在先使用使在先使用人能在后续继续制造、使用专利产品或方法,此时发生在申请日之后的行为是连续的,但无法将其认定为在先使用行为,而是在先使用所引起的法律后果。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在先使用行为说将原因行为与法律后果混淆,将在先使用的原因行为混淆为对在先使用的定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先使用行为说又与抗辩权说、独立权利说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用行为说来对在先使用定性极不可取。故笔者认为,应当在其他学说中寻找出路,或构建一种更为合理的先用权内涵。
二、对专利先用权内涵的新认识
通过以上专利先用权性质的分析,可以对专利先用权的内涵进行新的定位,并从中构建更合理的专利先用权内涵。笔者将专利先用权定性为一种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自然需要先辨析法益与权利的概念。
(一)法益与权利的区别
法益概念源起于德国,随即因其产生的法益侵害说被引入刑法领域,同时法益也为其他法律部门的学者所关注。有学者这样界定权利与法益的关系:“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为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其他法益。”②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笔者认为以上分类略显粗浅,重形式而轻实质,势必会在法益和权利之间造成一定的模糊地带。以专利先用权为例,并不因为学者长期称“在先使用”为专利先用权,就当然地认定其为独立的权利,且学术界对于专利先用权性质的争论并未停止。此外,权利的称谓与历史成因有关。学者在引进专利先用权概念时并没有对其进行严密的论证,待学术界之后对其性质进行论证时,该称谓已成为学术界对“专利先用权”的习惯称谓了。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再次从实证的角度来探究专利先用权的内涵。法益本身首先是利益,利益先于法益,但利益并不当然就是法益。当不同主体的利益相互冲突,法律必须在平衡两种利益中作出选择,确定受保护的法益以及法益的救济机制。权利是类型化的,与之相比,法益更多的是一种罗列,权利由法益产生,但并非所有的法益都能上升为权利。③孙山:《寻找被遗忘的法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59-69页。也就是说,法益是私权产生的母体,许多的利益在尚未达到权利地位之前都是以法益的形式存在的。④李岩:《民事法益与权利、利益的转化关系》,《社科纵横》2008年第3期,第73-75页。
权利和法益都有一定的排他性,一般来说,权利的排他性要强于法益,这是由法益的非独立性所决定的。虽然权利和法益都无法脱离主体而存在,但法益的非独立性更多体现在依附于特定的主体,这就决定了法益无法在不同主体间进行交易。而除了依附于人身的权利无法转让外,大部分权利能够在不同主体间转让。因此,权利的实现可通过主体自身使用,亦可进行权利本身的转让,而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的实现则需依赖于法益主体自身的利用。⑤孙山:《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合理使用的性质界定及立法建议》,《知识产权》2010年第3期,第63-69页。
(二)专利先用权:一种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
专利先用权在采用先申请制的国家被看做是对先申请制度的一个有力补充,消除了先申请制存在的部分弊端。甚至在一贯采用先发明制的美国,也有关于专利先用权的规定,以克服非真正先发明人获得专利权而导致的利益失衡。1999年美国《发明人保护法案》规定了“第一发明人抗辩”规则,即所谓的先用权原则。根据美国《专利法》第273条,某些情况下在先发明人虽然丧失了获得专利权的机会,但是可以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实施该项专利技术,而不视为侵犯专利权。①董琤、李敬东、王韦玮:《美国专利法改革最新动向》,《中国知识产权报》2011年8月31日,第7版。由于在先使用人往往是该专利技术的最先发明人,因而专利先用权意在保护在先发明人对于该技术的智力贡献而产生的法益。可见,专利先用权制度对于整个专利保护体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对于在先使用行为的保护方式以及专利先用权对专利权的限制程度,尚待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证。当权利与法益存在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利益诉求时,势必会产生冲突。在先使用情况下,法益与权利的冲突直接表现为专利先用权与专利权的冲突。
知识产权完全由法律所创设,因而遵守一定的法定主义。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是指知识产权的种类、权利以及诸如获得权利的要件及保护期限等关键内容必须由法律统一确定,任何人不得在法律外创设知识产权。②郑胜利:《论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中国发展》2006年第3期,第49-54页。纵观知识产权法中的各项知识产权,均是法律赋予权利人对某一知识的特许用益权,③张勤:《论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知识产权》2012年第1期,第3-17页。由法律所创设的权利人对某一知识的特许用益权势必亦为知识产权。专利先用权和专利权均为源于知识产品创造而获得的利益,但专利先用权无法享有对在先使用技术的特许用益权,故专利先用权不具有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不可否认,专利先用权仍不失为一种凝结于知识产品之上的利益。
若没有人就某一技术申请并获得专利权的法律事实的存在,专利先用权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在先使用人和其他社会公众都能使用该特定技术。由此可见,无专利权则无对应的专利先用权,这并不意味着专利先用权依附于专利权而存在,因为专利权的产生不是专利先用权的原因行为。故对于专利先用权人的保护并非设权保护,而是基于其对知识创造的贡献而由法律赋予其一定的法益,只有当他人获得了某一技术的垄断专利权时,才有对先用权人保护的必要。称专利先用权为一种法益,那么它是不是一种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呢?笔者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对于知识产权领域,专利权保护属于设权模式的保护,因而源于法律的规定。设权模式因为成文法的局限性,必然需要法律为保护权利之外的利益提供适当的救济手段,而这些需要保护的利益可以被视为法益。④谭华霖:《知识产品法益保护模式探讨——兼论法益与权利之冲突》,《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7期,第109-115页。专利先用权源于在先使用人对知识产品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它与专利权乃至其他知识产权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专利先用权的保护期为与之对应专利权的有效期。法律对专利先用权取得和行使都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这是法律基于专利权人、在先使用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知识产品法益同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往往是新的权利诞生的重要途径,⑥谭华霖:《知识产品法益保护模式探讨——兼论法益与权利之冲突》,《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7期,第109-115页。一旦专利权人与在先使用人的利益出现长期失衡后,法律则会对此作出回应,以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此时,专利先用权则很可能作为一种新的权利而诞生,并对其作一定的限制,如规定先用权人不允许进行许可、设置短于专利权的保护期限等。
由以上分析可知,专利先用权乃是一种未上升为权利的知识产品法益。
三、对专利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基于上述对专利先用权法益内涵的认识,对专利法律理论和实践均具有影响,故笔者就理论和实践层面作举例说明。
(一)知识产品利益的保护模式
有学者将知识产品利益的保护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设权模式,另一种是竞争法模式。⑤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设权模式主要是包含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单行法律法规之中;竞争法模式主要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不过以上两种模式难以涵盖知识产品保护的所有模式,“专利先用权”就是游离于这两种模式之外的法益保护模式。该模式与设权模式的区别由权利与法益的区别所决定,自不赘述。法益保护模式与竞争法模式的不同在于其保护目的的差异,竞争法模式意在通过保护知识产品利益来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当然,法益模式与竞争法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以说法益模式包含了竞争法模式,但在设权模式和竞争法模式保护之外,还存在未被包含的知识产品利益,这些知识产品利益为法益模式所调整。
由此可见,法益保护的相关规范虽早已存于立法之中,但未作为知识产品利益的主要保护模式而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本文虽然仅对专利先用权的法益内涵作了一些思考,但折射出关于知识产品利益保护模式的质疑。
(二)专利权与专利先用权之间的利益平衡
专利先用权是对专利权的一种限制,二者之间有着知识产权领域普遍存在的利益平衡。所谓的利益平衡则是指专利权人与在先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配与专利申请制度、专利权人和在先使用人对知识产品的贡献有关。而认识专利先用权的法益内涵,是把握专利权与专利先用权利益平衡的前提和关键。
专利先用权并非完全依附于对应的专利权,而是有其独立的法益。该法益是基于先用权人对知识产品的贡献,正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地创立了微积分,并创立了有名的“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因此,专利先用权人对于知识的创造有其独立的贡献。将专利先用权看做专利权的附庸,难免会磨灭先用权人对知识产品的独立贡献,进而容易忽略或弱化对专利先用权人的保护,导致利益失衡。
专利先用权之所以被认为依附于专利权,是因为专利先用权只有在专利权人提起诉讼时才得以体现,但即便专利权人不提起诉讼,在先使用依然是客观存在的法益。该法益能够对抗不特定对象,只有当专利权人获得了专利权后,这个对象才被特定化。因此,专利先用权在对抗专利权人的属性上为积极法益,而在对抗公众的属性上为消极法益。利益平衡只是在专利权和专利先用权之间划了一条相对清晰的界线而已。这条界线在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反馈下,将得到进一步的微调。
(三)专利先用权作为专利产品的合法来源
我国《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12-28,http://www.gov.cn/flfg/2008-12/28/content_1189755.htm。这一条是关于作为未经许可的第三人提供合法来源而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然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承担责任,该第三人的行为仍然属于侵权行为,仍需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②吕娜:《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合法来源抗辩——以专利侵权诉讼为例》,《人民司法》2007年第19期,第88页。笔者认为,专利产品倘若由专利先用权人所制造,则第三人不构成侵犯专利权,也不用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因为专利先用权人的制造行为属于合法行为,第三人对合法制造的专利产品进行销售不必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专利先用权并不只与在先使用人的利益相关,还涉及公共利益。专利先用权的法益内涵是以上结论的法理依据,若专利先用权仅为抗辩权,则显然不能作为第三人不构成侵权的依据。
一般而言,专利先用权的内涵并不影响专利侵权纠纷的实务处理,对实务影响不大的问题往往会被学术界所忽视。不过专利先用权在各国专利法中都还存在疑义,因而专利先用权的属性决定了其走向。在承认专利先用权是一种法益的前提下,那么基于这一法益而为的合法行为不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这或许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可以重新审视专利法中的一些问题。如,作为对专利先用权的“原有范围”是指专利申请日之前的原有范围,还是专利公开之后的原有范围?因为在专利公开之前,在先使用人并不知道存在这样的专利申请,那么是否应该给予在先使用人在专利公开之前扩大生产的权利呢?这些均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
——以实体法与程序法为透析视角
——兼评专利法第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