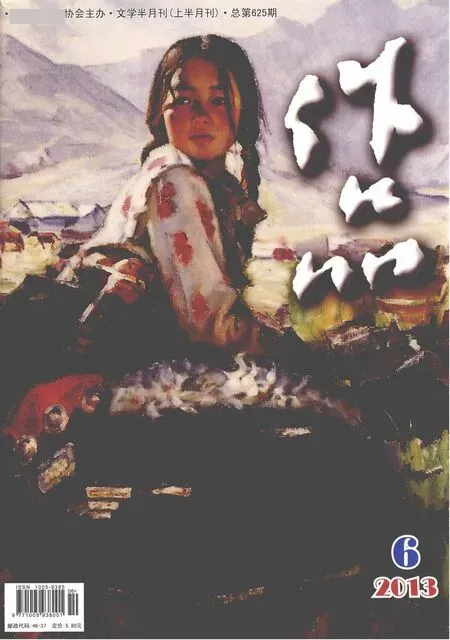七脚蜘蛛
1
水塔那时候可以说是无所事事,至少在我看来他一个月就忙一次,通常是在二十几号的样子——我估计那时他正好要交房租吧。总之,他老是在那几天到阅览室来,把他的电瓶车停在门口,磕嗤磕嗤走进来。“我来了。”他的声音本来就大,在安静的阅览室里,更是洪亮。看书的,看报的,都举起头来看他。他竟然也没不好意思,继续大声说话。我把食指放在嘴上,示意他安静点,这里可不是废品站,这里是阅览室,看书的地方,不是捡垃圾的地方。有时我真的烦透他了,水塔,就他,没别人。我本性格很好,那些看报的老人一个问题问我一百遍,我都得微笑作答。
“丢。”他朝我翻了一下白眼,走到一边,把一个月积下来的上百斤报纸扛上了肩。那些报纸我还得帮他整理好,捆好。他是这样说的:“我可没兴趣伺候它们。”不过,报纸能卖个好价钱,大多时候他只是嘴上说说,心里巴不得一个月能给他两百斤报纸。他说:“你们真是浪费钱哦,看看,好多报纸根本就没人看,还没打开过,人家一送过来就被你丢一边了。”我说:“关我屁事,爱看不看,我还懒得往上摆呢。”事实上,一天几十份报纸,我真是懒得弄,虽然一天的工作也就是这么点事。其实长时间观察下来,我发现这个社区的年轻人一般是不看书的,也不看报,中年人呢?偶尔也会进来走走,问看书是不是免费的,当我说一切都是免费时,他们转身又走了。进阅览室的,不是小孩,就是老人,小孩看童话、漫画,郑渊洁的,几米的;老人看报纸,基本也就固定那一两份,《参考消息》、《人民日报》——一个人从看童话、漫画到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期间得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水塔说的没错,好多报纸只是摆设。但我觉得他得了便宜还卖乖。
水塔从没给过我钱,他等于每个月从我这里白拿了一百来块。照水塔的话说,我这小资产阶级,没必要跟底层人民争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倒也没那意思,毕竟上面也不过问。再说,水塔时不时会请我出去喝几口酒,有时遇到没烟了,他给自己买的同时,也会隔着桌子扔给我一包。那会儿,我感觉水塔挺哥们。
2
我和水塔是在电子厂认识的,那时他是拉长,我是物料员。有一次,水塔问我想不想发财,我愣怔了一会,发财,谁不想啊?当然想啦。水塔说他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废品站老板,我们联手把厂里的锡条偷出去,能卖个好价钱。我本是老实人,可也糊里糊涂的,听了水塔的话,半夜三更,瞒过保安,偷出了十几斤锡条。结果钱是卖了一点,可我们也从电子厂滚了出来,老板扬言要找警察抓我们,我怕,水塔说别怕,他没证据;老板还说要找外面的小混混揍我们一顿,我也怕,水塔说,别怕,我认识小混混的头。水塔果真带着我去见了几个黄毛刺青的老大,喝酒抽烟,豪言壮语,花了不少钱,可后来也没人来揍我们,我感觉钱花冤枉了,水塔骂了我一顿,“你就这缺点,才没长进,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知道吗?”刀不刀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没多久我们就没钱吃饭了。那些老大也奇迹般地消失了。我和水塔只好各奔东西,打工搵食,期间有联系,知道水塔在从事废品收购工作,刚开始是帮人拣货,苯是苯,氯是氯,铜是铜,铝是铝……后租了房子自己干,开回收站。而我,也是踩了狗屎运,由于喜欢写点酸溜溜的文章,几年后,竟然被安排到图书馆工作,后分配到社区管理阅览室。同样是拿死工资,可比在工厂时牢固多了。
是我联系水塔来我们阅览室拉报纸的。我说,你尽管来拉吧,这里我说了算。水塔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估计是在表示景仰。心想几年不见,我竟然当上可以说了算的领导了。谁知,水塔费了半天的劲找到我们社区,见我一百平方的阅览室其实就相当于一处养老院,说成幼儿园也行,他突然哑然失笑。不过,他倒是挺感动的,不是报纸的问题,自然也不是钱的问题,是我还能想起他的问题。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报纸的问题,还是钱的问题。我说每个月下来一百斤报纸没问题,能卖一百来块吧。水塔摆摆手,“行外,真是行外,你这一百斤,到了废品站,往他的称上一放,就是五六十,你不知道,我混了多年,这一行再清楚不过,吃人不眨眼。说白了,要不是哥弟,我真懒得来你这里拉这点货。”他抬头看了一眼墙上“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标语,“我没跟你说过吧,我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一天十几万进出。”我信以为真,我知道做生意的都大起大落,看他骑来的是一辆破旧的深威牌电瓶车,我猜想,他正处于“大落”阶段吧。
那天水塔还给了我一张名牌,上面印的名目是“三友再生能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你有名片吗?”我说我没有。我突然自卑起来。水塔明显有些失望。但我们彼此都存有对方的号码,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交换名片的必要。
3
那些日子,无论白天夜里——其实挺扯淡的,夜里的社区连个下楼的人都找不见——我都闲得没事做。那真是天底下最清闲的工作了。我整天看书,几乎都把整个阅览室的书看完了,就连养生秘方和十月怀胎的都不放过。水塔第一次发短信问我“什么是七脚蜘蛛?”时,我刚好就在翻阅《中国爬行动物图鉴》,兴趣盎然地研读响尾蛇发出的声音是否带有音乐的节奏,也就是说,响尾蛇能否成为未来乐队里的一样乐器——真是蛋痛的想象。我接着翻遍整本书,也没寻到七脚蜘蛛的资料,蜘蛛倒是不少,多为八脚,不见有七脚的。我回道:“没有七脚蜘蛛,就像没有三条腿的人一样。”
不过,水塔信誓旦旦,说他真的在租房里看到一只七脚蜘蛛。他躺在床上,观察了半天,终于决定给我发个短信询问,他以为我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懂得多的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可我的回答让他感觉气愤。看样子是我对现实熟视无睹,并企图掩盖抹杀。“你们读书人就这样,明明就是这样,非要说成那样,我都看见了,就在我家墙壁上,你看,它还在爬呢,就七只脚,没错,七只,一只不少一只不多,我都数了上百遍了,不信,你可以过来看下,看现实是怎么撕烂你的谎言的……”他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好像那只蜘蛛就是他的女人,他的女人突然多出了一条腿,吓得他半夜睡不着,胡思乱想了。
我才没空理他呢。我承认,这时候,我是很烦他的,没错,就他,水塔,没有别人了。
事情还没完。第二天,水塔跑阅览室来找我,那天并不是一个月的二十几号,也就是说,他不是来拉报纸的,而是专程来找我的。找我也没别的事,还是说那七脚蜘蛛。他说他昨晚失眠了,躺在床上,好不容易眯了一会,竟感觉有一个庞然大物压住了他,让他喘不过气,又叫不出声音。他说他是清醒的,可就是动不了,仿佛整个身体都不属于自己了。他能清楚地听到屋外宝源路上来往轰鸣的泥头车,也能听到耳边盈盈作响的蚊子的声音,可他就是听不到自己喊出来的声音——他确定自己喊了,真的喊了。他隐约还能感觉到压在他身上的庞然大物有好多手脚,因此,压住他的四只手脚就显得绰绰有余……
我笑了起来……那时候笑,确实有点不厚道。
我说:“是不是七只脚啊?”
他说:“我也这么怀疑。”
后来一段时间,水塔不怎么敢回家睡觉,但他的房子得租下去,得堆放他那些回收回来的塑料、铜铁、纸皮等。我去过他的房子一次,在麻布村,一座旧楼,有个单独的院子,那样的楼房深圳真的难找了。水塔不知从哪弄来一个艺术化杉木招牌,横在院子门口,上面写着:三友再生能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我想,如果不仔细看,人家会以为这是一处艺术品店或者隐藏偏僻的个性酒吧呢。水塔说租金不贵,房东和他是老乡,暂时还没钱起高楼,一处旧房有人守着也是好事。我看屋里屋外都堆满了废品,那么乱,那么脏,别说是七脚蜘蛛,养出个响尾蛇或者小恐龙,也是没问题的。
水塔便总是找借口,在我那过夜,平时海量的他,那段时间一杯就醉,胡言乱语,然后赖在我那里不走。我的女朋友有时会从南山过来看我,晚上自然免不了做爱。我说,水塔啊,今晚我可要干活了。水塔说:“明白,你把阅览室的钥匙给我,我去那里睡。”我吓一跳,但也没办法,看他那么厚颜无耻的样子。我说,你得保证明天一大早就得走,免得被社区的人看见了去上面投诉我,说我用阅览室收留流浪汉。
水塔说:“等我在深圳买了房子,我请你和弟妇住大厅,海阔天空地干!”
不得不说,水塔的志愿很宏伟,我辈想都不敢想。如今在深圳的人,要是有买房的理想的,那就跟读小学那会说要当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一样远大悲壮。
4
“想不想买房?在深圳。”水塔低着声,问我。
他难得头一回能在阅览室里小声说话。
“我正在谈一笔大生意,我跟你说过,别看我们整天和破破烂烂打交道,如果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妈的,那年把我害惨了,光铜就亏了我十几万。不说这些,我的意思是,我们这行其实也是赚大钱的,前几年,算是暴利行业。现在机会来了,一笔大买卖,做了保证赚钱,我资金不够,你要能帮点,我给你算股份,赚了,本钱还你,再分红,怎么样?当然,你手头得有多余的钱,靠它吃饭的可不行……”
我才不会再上他的当,就像以前在电子厂我听从了他的主意,结果就搞砸了。再说,我的女朋友肯定也不同意,她是个小气的客家女人,我把阅览室的报纸让水塔免费拉走这事,她就骂过我好几次,说我傻,被朋友利用,一个月一百块钱都够她买玉兰油和护舒宝了。这我还没跟她结婚呢,我难以想象跟她结婚后的日子。当然,我想不了那么长,过一天是一天,我可没水塔那样励志。
水塔却不依不饶了。他的耐心和韧性在说服我这件事情上表现得那真是可歌可泣。他几乎隔一天就来阅览室一次,他不去我的住所,应该是怕遇到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不会给他好脸色,尤其是知道他是来“要钱”的。我的女朋友会在一旁面无表情地说:“人生有三大悲剧,一是出生贫寒,二是交友不慎,三是娶错老婆。”她的意思是我前两个悲剧都遭遇了,唯独第三个没有——她自认是个好女人,是贤内助。水塔则不这么认为——甚至在水塔看来,我的所有“悲剧”,都源于认识了她。事实上,除了水塔,我真的没有什么朋友了,我的圈子越来越窄,有时我感觉深圳也就一个社区那么大,我的目光连社区里最低矮的楼房都越不过去。
或许水塔说的没错,“不能再这样了,谁都不敢保证明天会不会死去,是不是?车祸——”他看着阅览室门口的电瓶车,“这家伙,每天不知有多少被泥头车卷到轮子底下,血肉模糊,脑浆就像豆腐浆,在柏油路上晒成了豆腐干……”
“你是不是又被七脚蜘蛛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笑着问。
“不瞒你说,已经好几回了,每次我都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没有谁能帮我一下,我只能靠自己,慢慢挣扎过来。我再也不住那样的鬼地方了,我再也不过这样的鬼生活了……他妈的,深圳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楼,就真的没有我的份,还有你,我觉得你也应该振作一下,你看看你工作的这个鬼地方,半死不活的,每天守着这些狗屎一样的书,满嘴口臭的老人,还有连拉屎拉尿都不能自理的孩子,有意思吧你——”
没意思。真没意思。
水塔说的一点都没错。
5
为了让我放心,水塔给我打了欠条。我说水塔,我可是把全部家当都押你身上了,我连女朋友都没敢告诉。水塔拍着我的肩膀笑:“女人嘛,你只要能给她更多的钱,她比什么都高兴。”之后几个月,水塔来拉报纸的时候,会跟我说说生意的进展情况,算是对我这个股东的负责。他越来越消瘦。他说他经常失眠。“尽早搬个地方,可能就好了。”水塔说。我知道水塔之所以迟迟不搬,全因为那儿的房租便宜,独门独院的,太适合做废品生意了。
“那只七脚蜘蛛。它白天躲起来,一到晚上就出现在墙壁上。我寻思着是不是应该把它打死。”水塔说。
“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医生,你越来越瘦了。”
“你还不相信?”
“有时我也会觉得闷,快死的样子,在大街上走着,都那样。”
“老实说,我现在其实挺享受那个过程的,仿佛在和死神搏斗,在最后一口气将断未断的时候,我赢了,厄哦,我大喘一口气,从没感觉生活那般美好,起死回生一样。”
“所以你没舍得把它打死。”
“我怕它一死,我就醒不过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水塔,大概四五个月吧。打电话,不是无法接通就是关机。我也懒得理,他大概是生意忙起来了。听他说过,废品生意和电子厂一样,也有淡季旺季的。将近过年,正好是旺季。期间我查阅了不少资料,也未能找到七脚蜘蛛的存在。倒是有些传说,在粤东一带,说七脚蜘蛛是“七脚拐鬼”,它实际上不是蜘蛛,是一种魔力,谁要是在夜里遇到它,谁就得经受那种魔力的考验,也就是在死的边缘挣扎——妈呀,竟然跟水塔说的一模一样,我真想把我的发现告诉水塔。
而这时我却遇到了麻烦事。我把女朋友的肚子搞大了,我记得每次都是戴了套做事的,没想到还会出差错。我从未想过结婚的事,更别说当爸爸了。我怕得要死,甚至都不敢再靠近女朋友,尤其是她微微隆起的肚子。太可怕了。“你要当爸爸了。”她笑着说,跟电视剧里的女人一样煽情。可我一点都不配合,我竟然哭了,求她把孩子打掉,我真的不想当爸爸。说实在话,我无法想象我竟然要过上为另一个生命负责的生活。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世界经典插图选登里科·托玛索在1937年为《星期六晚邮报》创作的黑白插图。
她不同意,她也跟着我哭。她要和我结婚,然后把孩子生下来。
我说:“就三分钟,无痛人流。”
她给了我一巴掌。
我想征求水塔的意见,却联系不上他,后来我想,水塔肯定是反对的,他连我和她交往都反对,更何况结婚生子。我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商量这样的事情。
过年我带着女朋友回了一趟老家。我不想的,是没办法。对我所犯下的错误,开始要偿还了。我在家里闷闷不乐。我女朋友却像个主人那样在我家上下窜动,看样子就像是我随着她回家的一样。她大概已经把怀孕的事告诉了我母亲,母亲乐得啊,不顾满口的蛀牙,哈哈大笑。母亲那几天恨不得把院子里能走动的东西都杀了给我女朋友吃,补身体,生个大胖小子。她堂堂正正地做上了我母亲的儿媳妇,我却一点准备都没有。
“什么时候结婚?”她问我母亲,好像跟她结婚的不是我。
“过了年就结吧。”我母亲说。
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可养不了那么多人。
“怎么说,不都说是政府的人了?”母亲问。
“听是好听,也就那么点工资,要不是我,鬼才干呢?”
“你养不了,家里来养,你不想要孩子,我们还想要孙子呢。”母亲这么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实际上,我是一点钱都没有。可我不能说,否则她们会问我钱去哪了,我总不能说借给水塔做生意了。
不怕人笑话,我真希望那个肚子逐渐大起来的女人能摔一跤,走着走着,就那样摔了,那该多好。一了百了。
6
她辞去了天虹首层化妆品推销员的工作,大摇大摆地搬进了我的住所。可怜我的住所不过二十平方,住一个人的时候还觉得有点空,又住进了一个人转身都会背擦背了。没办法,一个女孩怀着身孕死心塌地要跟着我,我还能做什么——按照书里写的,此时此刻,我应该感动得泪流满面。
她早早算好了预产期,做好一切准备,衣物、毛巾、奶嘴奶瓶,甚至是童床童车,买了一大堆回家,把住所弄得像水塔的废品站一样乱。我想我得找水塔把钱要回来,要不然吃饭都成问题了。
水塔的手机还是没打通,我只好去麻布村找他。他的大门锁上了,我趴在门上从缝里看见他的电瓶车,多时未用,已经长锈。水塔会去哪呢?看来他没忙生意上的事,院子里一点废品积货都没有。我找来房东一问,才知道水塔已经离开深圳几个月了。但水塔特意交代,房子继续租,租金继续交,他会回来的。
谁也不知道水塔在搞什么鬼。
十万块钱,对于任何一个在深圳站稳了脚跟的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对于我,那可是一大笔钱,而且这笔钱的存在,也证明着我的存在,是我多年来在深圳打工的证据,我的工作证证明不了,居住证证明不了,租房合同也证明不了,惟有那笔不大不小的钱,它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我在深圳过着。
怎么办?但其实也没什么办法。
住所的阳台刚好能看见深夜灯火通明的西乡街,那些高大的木棉树一到冬天就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像是抻直的枯瘦的肢体;还有凤凰木,凤凰木的叶子似乎比较坚强,它的花开得那么红那么艳,似乎完全与城市无关,自顾自地长着开着。
我习惯在睡不着的时候看恐怖电影。好莱坞关于蜘蛛的电影不少,他们把蜘蛛塑造成危险残忍的动物,因为腿脚众多,它们拥有让人震慑的威仪感。
当然,我的失眠,或许跟宝安大道抢修地铁的噪音有关。
7
终于有了水塔的消息。他说去了一趟云南,回来了,在广州,刚把深圳的号码换上,第一个就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以为我把你的钱拐走了?”他问。
两天后,水塔回深圳,请我喝酒。他看起来又黑又瘦。
去云南干什么?
做生意。
想不到水塔的废品生意还能做到美丽的云南去。
水塔没有具体说什么。但他的回答让我感觉踏实,一是我觉得我的十万块飞不了了;二是感觉水塔挺有能耐的,至少比我要强得多。那晚我看水塔都觉得亲切,像是失散多时的亲人,突然见上了面,就差没抱头痛哭了。
我跟他讲粤东地区那个关于七脚蜘蛛的传说,似乎真有其事。他无所谓的样子。他说他离开深圳几个月,在异地他乡,夜里睡觉还是会感觉窒息。他说看来真不是那只蜘蛛的问题,传说自然也是瞎说。他说他怀疑自己的身体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可他又不敢上医院检查,他害怕,就像有一个病魔隐藏在他的身体,随时等着与他摊牌。他不想让病魔得逞,邪笑着露出它那狰狞的表情。凭什么,一件东西可以操控另一件东西。他说他这三十多年活得挺窝囊的,不会因为这点挫折而妥协……
那晚说了很多,也喝了很多。我不知道水塔在云南经历了什么,还有他是不是真去做生意,甚至他有没有去过云南。这些,都是值得疑问的。
他支持我结婚,并答应先把十万本钱还给我。这让我感觉十分意外。期间我的手机响了多次,我知道是女朋友在催我回家。我没接,甚至没拿出手机来看。水塔叫我回去,我没听他的,继续喝。我把手机关了。那晚究竟喝到几点,我们都忘了,只记得后来我们相互搀扶着,打了的士,回到了麻布村。
我们都在院子里吐了。说实在话,院子本来就臭,那些堆积多日的纸皮和塑胶发出一种难以辨别的臭味。混合上我们吐出的秽物,就更臭了。水塔那个窄窄的木板车根本不够两个人睡。水塔便让我睡床,他自己坐在破沙发上,他说他也不一定睡得着。我隐约听见他在看电视,一个有名的相亲节目。没多久,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我浑身无力,像是被人抽取了全身的力气,动不了,发不出声。外界的声音离我越来越遥远——我明明知道水塔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看电视,可我就是无法让他知道我的困境。我就快要死了,或者说一个身体,就横跨在鬼门关的中间,只要对方稍稍一用力,我就烟消云散,只在门口遗落一只皮鞋,或者在沙土上落下几划挣扎的痕迹;但如果我这边再多点意志,似乎也可以与之抗衡的。我在这里找到了希望,一下子,整个事情便显得悲壮起来,仿佛一个人的垂死挣扎,背景音乐应该是紧张而浑厚的交响。啊,我终于明白水塔说过的那种感觉,类似于起死回生,更准确一点,我会认为是茅塞顿开,厄哦,当氧气通过咽喉一下子进入了我的肺部,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赢了。
我没把这个短暂却也漫长的斗争告诉水塔,我下了床和他一起看电视,节目里因为一个女孩嗲声嗲气的样子,我们哈哈大笑。
那只七脚蜘蛛出现在了电视上方的墙壁上。是我先发现的,我说:“嘿,你看,是这只蜘蛛吧,我数数看,是不是七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嘿,还真是七只脚。”
水塔说:“几个月不见了,它好像也瘦了一些。”
我说:“我还真不信了,真是七脚?”
我凑前去观察那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蜘蛛。我发现它的七只脚,三只在左,四只在右,不对称。问题就在这里。而且它爬行的样子一点都不稳重,它失去了平衡。我恍然大悟,摇着水塔的肩膀说:“我知道了,我说呢,它是掉了一只脚。弄到最后,原来它只是一只身体残缺的蜘蛛……”
8
水塔又失踪了几个月,连我的喜酒也没来喝。他往我卡里打款,还我十万块,可我收到的却是二十万。我问他,他说是分红,或者是他给我的结婚礼金。“行啦,就这么说,我得把号码换了,我现在西藏,忙得很。”我感觉水塔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奔跑,像只瘦弱的马。
我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了,她有时会把我拉到身边,强迫我把耳朵贴在她的肚皮上,听里面的动静。我想这应该是每个准父亲应该做的,可我真的不想,我对她肚子里面的生命充满恐惧。该死的,我还越来越觉得妻子的肚子,和水塔屋里那只七脚蜘蛛,简直像极了。
我已经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了,好多事情让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面对。我期盼水塔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我们哥弟俩,这下可发了,可以找个有阳光的日子,去第五大道看房子啦。”
我期待着这一天,并感觉这天迟早会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水塔做什么生意,看样子肯定不是废品生意。或者,他有没有在做生意,都是个疑问。他有点神出鬼没,让人捉摸不透。
一个月后,果真出事了。警察找到阅览室,要我配合调查一个人。我问谁,他们说:“水塔。”警察先是问我和他认识不?我点头。什么关系?我说先是同事,后是朋友。你知道他现在在哪?我摇头,我真不知道。你得说实话,他现在是通缉犯,你隐瞒的话,就是包庇。我哪敢?我吓出一身冷汗。我是老实人。我问:“他干嘛啦?”没人具体回答我,他们只是在走的时候,说水塔联合黑社会组织,参与某地的冰毒生产,为毒枭们提供了含有麻黄素的感冒药,并从中赚取暴利。
我才知道,水塔所谓的生意,竟是如此地铤而走险。
没多久,水塔落网了。但经检查,水塔已经是肺癌晚期患者,医生说这跟他长期和废品打交道有关系。水塔躺在医院里,已经骨瘦如柴,我经常去看他。最后一回是在中秋前夕,我带了月饼,还有刚满月的女儿。问妻子去不去,妻子说:“就是为了那十万块,也要去看一下的。”正如水塔所说,这个女人认钱不认人。
“不怕你笑话,”水塔最后对我说,“那只缺条腿的蜘蛛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一睡下,我就害怕再也醒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