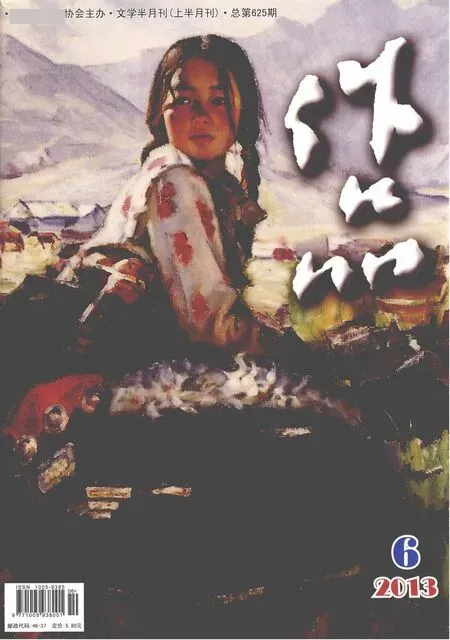新锐的多重面孔

2011年,广东作协主办的《作品》杂志下半月刊开设了“新活力”栏目,以每期一半左右的篇幅,先后推出了彤子、陈崇正、王威廉、李德南、卓奇文、王哲珠、叶清河、于馨宇这八位广东青年作家的作品专辑。随后又相应地开设了“岭南批评”栏目,邀请知名批评家对这些作者的作品进行解读。这种重视培养新人的举措,引起了《南方日报》等媒体的关注;“新活力”栏目中刊登的不少作品,也先后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2011中国中篇小说年选》等选刊、选本收录。有的作者,更籍着这一机缘,顺利地推出了个人的长篇小说。这种相对集中的出场方式,对这些作者的创作起到了激励与推动的作用。
也许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最近《作品》杂志又打算推出“广东本土新锐小说家、诗人专号”。较之“新活力”栏目,这次的专号,既有彤子、陈崇正、王哲珠三位作者再次入选,也有不少新的面孔。通过本期的作品,我们也多少可以看到他们在写作上的同一与差异。
一、写实的本土叙事
这些青年作家中,彤子、陈崇正、王哲珠等,都注重开掘自身的本土经验,有志于赓续岭南文学的书写传统,挖掘岭南文化的底蕴。他们的写作,分别涉及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等岭南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写法上又有所不同。正的这些作品,还带有鲜明的“80后”特色。琼瑶小说热、计划生育、大学生就业难……这些和“80后”这一代人有关的文学现象或社会现象,都是他在创作中所念兹在兹的。《春风斩》篇幅不长,只有两万字左右,却同样涉及“80后”所经历过的诸多公共事件,叙事密度大,叙事手法也非常多样。傻正、孙保尔、向娟娟三人的“伟大的友谊”,是整篇小说的主线。此外小说还穿插了几条不同的副线。小说主要从“傻正”的视角展开叙事,他与孙保尔、向娟娟自小就是朋友。向娟娟一度对“我”(傻正)有好感,后来与孙保尔来往,遭到孙保尔家里反对后,又一度回到“我”的身边。“我”与孙保尔、向娟娟既有很多的共同记忆,又与他们分别有些寻常或不寻常的经历。这里面的线索,互相缠绕,但说到底,都是对友情、爱情的回忆与诉说。
在叙述的中途,《春风斩》也一度将叙述重心移至向娟娟和她的家人身上。计划生育,可看作是理解这一家庭的核心事件。向娟娟的父亲向四叔以杀猪为生,这一人物形象,多少让人想起周星驰《国产零零七》中那位“风度翩翩的猪肉佬”。“每天早晨他起床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撒尿,而是用玻璃杯倒满一杯白酒,随手在橱柜里抓两颗橄榄,坐到门口的树桩上半眯着眼睛喝起来……他仰起头也不说话,就算是打过招呼。”对于这样的细节,看过周星驰电影的,或许都会觉得似曾相识,忍俊不禁。有意思的是,向四叔身上,又多少融入了一些武侠的因素。“半头猪,一百来斤,他一拎前后两条猪肘子,就能稳稳当当将之扔到板台上,跟扔一个皮球似的。哐当,猪肉在板台上晃动了一下。然后向四叔开始在手摇水泵边磨刀,霍霍,霍霍。”“向某人今天把话撂在这里,一边是刀,一边是钱,你们自个选,屋瓦你们想捅也尽管捅,人是不会给你带走,向某人杀猪无数,也不怕杀几个人。”向四叔拎猪的动作,还有一番自我表白,都颇具侠气。可是接下来,便出现了向四叔因计划生育被抓去结扎的场景。通过结扎这一情节,有些英雄气息的向四叔,又回到了常人的层面上。这正是典型的后现代技法。
在《春风斩》的第六到八节,叙述的重心再次回到了我、孙保尔、向娟娟身上。这里面,既有对“伟大的友谊”这一青春主题的再度叙述,又引入了一新的公共事件:S A R S。在这里,陈崇正所关心的并非是S A R S发生的前因后果,而更多是以S A R S作为背景,讲述孙保尔误信传言,倒卖陈醋与板蓝根的荒唐经历。在小说的第九、十节,小说又写到S A R S所带来的恐慌,也涉及最近几年大家所关心的医患关系等话题。就这样,一九八零年代以来的诸多公共事件,被整合在了一部中篇小说里。
陈崇正曾在微博上透露,写《春风斩》的动因,是为了“纪念”十年前的S A R S事件,可实际创作出来的作品,已非原来的设想所能涵盖。在小说中的具体行文中,《春风斩》还不断地提及老狼的校园民谣、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张国荣去世等“80后”的集体记忆。从文本中所涉及的诸多公共事件和细部的修辞来看,《春风斩》俨然成了是陈崇正从“80后”的视角出发、为“80后”而作的、“怀旧”的文本。这种面向时代主要问题而写作的努力是值得期许的,然而,电影对白体的游戏式对话,还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的游击战术,过多地考虑读者趣味的写法,也削弱了小说的深度。当然,从后现代的立场来说,反讽和游戏本身就是写作的终点和目的,深度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乌有之物。
三、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纠葛
陈再见的《七脚蜘蛛》和王哲珠的《医道》,放在一起进行对读,恰好能看到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之间的微妙纠葛。
多年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指出,从基层上,中国是乡土性的。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土中国在走向没落,城市中国则开始引人注目。很多原本生活在乡土上的人们,纷纷开始入城,陈再见便是其中一员。他来自广东陆丰,到深圳后有过打工经历,后来得益于深圳较好的文化政策,借助专职写作的形式亦能相对自如地生活。最近,他又开始在某社区图书馆工作。与这种生活经历对应,他近年所写的不少作品,也以打工题材居多。《七脚蜘蛛》中的“我”,就有不少作者本人经验的痕迹。
《七脚蜘蛛》的“我”与水塔,都来自粤东,曾一起到深圳的电子厂打工。水塔一度成为拉长,“我”则是物料员。水塔做人比“我”要活络,有时候甚至会为了钱而不惜偷窃。他们和别的过来人一样,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买房买车,扎下根来,成为深圳这一新兴城市的一员。而对于庞大的打工族来说,这就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借用小说里“我”的看法,“那就跟读小学那会说要当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一样远大悲壮。”当诸多的困难甚至是困境在眼前展开时,的确有不少人,会像“我”一样,选择过半逃避、半妥协的生活,或者是和水塔一样,耗尽心思,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两条路,都不乏典型。
《七脚蜘蛛》并没有写到乡土生活,也没有写到“我”与水塔对乡土的态度。可是很显然,他们并不想回到乡土世界里,继续以往的生活。哪怕在城市里过着一种流离的生活,似乎也比回去要强。乡土的记忆又总有其坚韧的一面。比如小说里的七脚蜘蛛,既真实地存在于水塔那堆满废品的出租屋里,又与他们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在粤东是否真有七脚蜘蛛是“七脚拐鬼”这么一说,但这种特殊的经验与记忆,确实成了小说里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我”,不再像更早的离乡入城者那样,在城与乡之间有那么多的心理纠葛,但依然是社会变迁途中的中间物,必得承担社会历史所给予他们的命运。也因着七脚蜘蛛这一意象,他们的命运便具有了隐喻般的力量——住不下来、又不能离去的城市,对他们来说,也正是一只七脚蜘蛛。它有属于自身的魔力,“谁要是在夜里遇到它,谁就得经受那种魔力的考验,也就是在死的边缘挣扎。”
与陈再见相比,王哲珠的写作,更多是扎根乡土,尽管她也有《那世那人》这样注重语言实践、诗意空灵的作品。我之所以认为她的《医道》可以和《七脚蜘蛛》进行对读,首先与小说里的陈当这个人物有关。他的人生,与《七脚蜘蛛》里的“我”与水塔不尽相同,但都有乡土和城市生活的经历,三者同属一个形象序列。不同于“我”与水塔那种决绝地离开乡土的人生态度,陈当对乡土世界有自己的眷恋和情怀。他本有机会留在城市,能比《七脚蜘蛛》里的“我”与水塔要更容易地在城市里扎根,却选择了留在寨里。这是另一种的人生选择,也是承担命运的又一种形式。
小说里的圆木这个人物形象也值得注意。《医道》的语言是柔软的,和圆木的心灵对应。《医道》也没有多少曲折的情节,不过是写圆木因为思念自己的父母,跟医生说自己病了,希望能通过医生的努力,让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能回来和自己过生日。最终,陈当也答应了小男孩的要求,宁愿承担来自圆木父母方面的苛责,替圆木实现这再平常不过的愿望。王哲珠将小说取名为《医道》,显然是有自己的深意——提醒大家多关注“道”,顺应生命和心灵的需要,不要为“术”所束缚,为外界的喧嚣所干扰。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温和的提问: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到底什么最重要?在巨大的城乡变动面前,我们是选择过一种功利的、物质化的人生,还是更重视情感,继续守护土地的本根?
四、新锐的想象与内心生活
吴纯、张其鑫和静颜都是非常年轻的作者,也都有非常好的写作机缘。生于1987年的吴纯,去年凭短篇小说《驯虎》获得台湾的联合文学奖,以文坛黑马的形式进入我们的视野。如今,我们通常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新锐”之为“新锐”:一、年纪较轻便开始受到文坛关注,并能逐渐发出自己声音;二、写作中具有鲜明的探索精神,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文学范式或提供新型的美学经验。吴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兼具这两种特点。不管是她所关注的问题,还是她的表述方式,都与前人有明显的不同,具有鲜明的异质性。
不同于陈崇正、陈再见、王哲珠这些出生较早的“80后”对社会现实经验的关注,《驯虎》和《猎鹿》并无清晰的时代感,而更多是朝向个体的内心,向内挖掘。《猎鹿》带有些许童话的色调,有两个故事单元。第一单元,主要是讲“我曾有过一段多灾多难的牙齿成长史”,讲述“我”如何排斥吃肉,还有周围的人对肉类的耽溺。作为个体的“我”,最终也被家人所教化,“终于融入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各种唧唧咕咕的吃肉聚会中谈论说笑。”第二单元,则借助写实和幻想等手段,讲一头熊如何猎杀鹿,熊最后也被人类所猎杀。小说也附带地提到某一个食客猎杀17头鹿的疯狂。这两个故事单元,在小说里被吴纯用吃肉这一行为和其他的细节很好地缝接起来。所有的这些似乎只是作者一次无关紧要的臆想,无关宏旨。但作者的笔墨还是隐约地指向了文明与野蛮这个人类的基本生活命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过烹饪等手段,还有诸如“印有粉色兔子的餐具和花朵图案的切肉器”等器物,让食肉行为变得文明起来。可事实上,在这文明的底部,依然是野蛮的猎杀。人之杀鹿和其他动物,与熊猎杀鹿一样残忍。在“吃”这一层面上,人并没有摆脱动物性,而是和动物处在同一个序列。人在生物链上,其实也是猎食者,是暴力的施予者。
在写作的过程中,吴纯有意把上述主题打碎。遣词造句时,她又特意选择了一种生物学和医学式的语言。比如“我们从幼年开始就接受了吃肉类食物的训练,母亲教我们如何用侧边的牙齿使力,如何让上下颚配合无间,利用牙齿凹槽的力量把肉自然碎开。”“花色的脂肪皮肉之后,脉搏和血管被胡乱扒开。猎物剧烈悲惨地渗着血水颤抖,它撕纸条一样拉开右肱骨,再若有所思地扔掉,最后不小心把整个头颅拧了下来。它抱着一颗鹿头,鼓着嘴坐在草地上,像个不知所措的懵懂孩童。”这种处理方式,和小说的主题是暗合的——这些表述,既适合人,也适合其他动物。它也起到了一种陌生化的美学效果。
在吴纯的写作中,想象占了很大的比例。就此而言,张其鑫的小说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我曾如此孤独》,和陈崇正的小说也有些相似之处:语言都带有黑色幽默的成分,但张其鑫小说中的抒情气息比陈崇正的要重一些。小说虽命名为《我曾如此孤独》,叙述重心却不在“我”身上,更多是借助“我”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家庭内部的种种不堪或不幸:祖父是强盗,父亲因为毒品而坐牢,母亲与人偷情,祖母有毒害祖父的嫌疑,哥哥夏答杀害前恋人的父亲胡屠夫,夏答又死于车祸……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造成“我”之孤独的原因。最后,“我”选择了出家。这一连串的意外,暴露了小说的编造痕迹,也削弱了小说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对张其鑫来说,稍微注意一下写实的手法,多融入一些现实生活的经验,也许会有更大的提升。
和《我曾如此孤独》相比,静颜的《小日子》在写法上要平实得多。它并没有多么复杂的情节,而是写一个家庭内部不无琐碎的生活,写家人的喜怒哀乐。再有就是年轻人开始逐渐长大,告别童话般的单纯和理想,开始努力理解生活庸常的一面。无须讳言的是,小说里所透露出来的对生活的理解,都是清浅的。当然,对于一个才二十岁的年轻作家来说,要理解人生种种的复杂、幽微,还为时过早。
五、诗歌写作的两种面向
本期刊发的两位诗人的诗作,在风格上差异极大,几乎是对立的两极,也代表着当下诗歌写作中两个不同的路向。
这次入选的不少作者,多是依靠直觉、才情和经验来写作,唐不遇则更强调知识、教养对写作的意义。他既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也有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草木三章》、《隐士三章》、《杜甫三章》、《自传三章》等诗作,更多是尝试对中国古典意象与古典题材进行现代转化。这种现代,是立足于自身的文学传统而生成的。这既包括把很多古典的意象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新旧的交错和融合。再有就是立足于当下的生活,重新理解古典文化、古典文学的人物及其精神。例如《杜甫三章》,文末标明是为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而作。既然是纪念,是一种历史性的回望,就难免会把当下的视角也带到诗歌里——这便是伽达默尔所说的阐释学境遇。“这一夜,你睡得一点也不安稳,/像是睡在穷人的坟地。/在黑暗中呼吸的不是你的肺,/而是生存漏风的肚脐。”“你的鞋子比道路更懂得/这个国家为何诞生又抛弃你,/此刻它们在床脚下醒着:/卑微和苦难,哪个更像鞋里的沙子?”“骨头,只是大地的一处闲笔。”诸如此类的诗句,都写得内敛,有力,唤起我们的现实感受。借助这些杜甫、李贺这些历史人物,唐不遇介入现实的情怀与意图,亦在在可见。
《天堂三章》、《脸谱三章》、《幻象三章》,还有《彗星三章》中的《兰波》则偏于现代,承接的主要是西方诗歌的脉络。尤其是“在那三年里,你像一根火柴/刮擦着巴黎咖啡色的磷。/火焰照亮天堂和地狱,/灰烬洒进面包和酒。//这就是你独特的炼金术/在胃酸过多的梦里,洗涤着/疯狂的食物,沾满颜料的词语……/那一个个声音的气泡。”这样的小节,不管是意象还是句式,还有内在的精神,都更符合西方诗歌的传统。
两个不同的诗歌传统,在唐不遇的写作中,有时候也会合二为一。例如《自传三章》中的《潭经》这一首:“背对着瀑布,坐在岩石上,/水流从脊背冲刷而下,/骨头想哇哇大哭,/深绿的潭水/紧紧收缩着。//在别的女人的子宫里/我再也没有听见/儿时第一声哭泣的回声。/我成熟的肉体,/睡觉时依然蜷着。//在另一块岩石上/一条蛇,犹如瑜伽大师。/当它直起身子,潭水一阵猛烈阵痛,一尾红色的鱼跃出水面。”
“背对着瀑布,坐在岩石上”、“潭经”、“深绿的潭水”、“一尾红色的鱼跃出水面”这样的字眼和诗句,在中国古典诗中较为常见;其他的意象和诗句则是“西化”的,现代的。然而,它们被用在同一首诗里却不显得分裂或冲突。也正因为有学养作为根基,唐不遇的诗,往往透露出一种在“80后”里并不多见的成熟、节制与从容,在技艺和经验、艺术与政治、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知性、语言与存在等方面均能保持平衡。
与唐不遇的这种沉着、庄重相比,乌鸟鸟所写的,多是“撒旦的诗篇”,充满了亵渎的激情和快感。他有意借助“狂想”来穿透生活,挖掘诗歌的可能性。他的诗一如他的名字,奇异,滑稽,生猛,凌厉。这次发表的系列组诗,主要是借用一种“负面的想象力”来完成的。姜涛曾提到一个观点:“在一般的文学经验中,存在着基本的价值等级,比如崇高/邪恶、优雅/粗鄙,光明/黑暗,天空/大地等一系列的‘二元模式’。在经典的文学想象中,这些价值等级是稳定的,比如北岛的诗歌想象就依据这一等级产生,或者说完全是‘正面的’。而海子虽然在观念上是‘反现代’的,但在感受上,却发展了波德莱尔以来现代文学关于‘黑暗’、‘恶’的关注,并形成了他想象力的核心……”他把这命名为“‘负面’的想象力”,这正是乌鸟鸟的“狂想体”的重要特点——它们也处处充满黑暗的、恶的事物。
《那些年我们常常在夜晚压倒青草一片狂想》这一首,主要写少年身体觉醒时的苦闷和叛逆,还有来自教育体制方面的压抑。这可以说是一个早已陈旧不堪的主题,乌鸟鸟却借着这种“负面的想象力”创造出诸多奇特的关联与意象,刷新我们的经验:“卷曲的人毛”与“羞耻的苔藓”,“义务教育的围墙顶部尖尖的玻璃碎片”与“龇咧的鳄鱼之嘴”,“青春的操场”与“宽阔的温床”,“少女”与“怀孕的花朵”……这是一种极其放肆、大胆的“青春写作”。

注释:
①“本土”并非是一个只有单一内涵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和参照系中,常常被赋予不同的涵义。例如在后殖民理论进入我们的批评视野后,“本土”也被用来指称和西方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中国经验”。“广东本土新锐作家、诗人专号”中的“本土”,则主要是对写作者出身地的限定,即他们来自广东各个地级市,都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这里所使用的本土经验、本土叙事等概念中的“本土”,则更多是在岭南文化、岭南文学的层面上使用。
②姜涛:《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